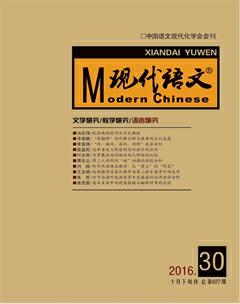從蘇軾《次荊公韻四絕·其二》析其詩歌創作
○吳莉莉
?
從蘇軾《次荊公韻四絕·其二》析其詩歌創作
○吳莉莉
摘 要:蘇軾的《次荊公韻四絕》是既有重要文獻價值,又有文學價值的一組詩,其中第二首詩歌,不僅反映出宋代當時濃厚的理性精神、蘇軾對客觀世界的深刻思考;也反映出宋代詩壇用工深刻的習慣,以及蘇軾在詩歌創新上的努力;且從這首詩中,亦可以窺見蘇軾受莊禪影響而形成的委順自適的心境,對其詩歌有著重要影響。
關鍵詞:蘇軾 理性 以文為詩 委順自適
蘇軾和王安石這兩位著名的文學家,二人在文學上惺惺相惜,在政治上卻頗有嫌隙,二人的關系一直被后世學者關注,而蘇軾的《次韻荊公四絕》一直被認為是蘇軾與王安石盡釋前嫌、言歸于好的證明,因而頗受研究者關注。但研究者多是以此詩為媒介,對二人的交往進行發掘,反而對詩歌本體的研究有所不夠。蘇軾的《次荊公韻四絕》除了可作為蘇王二人交往關系的重要參考文獻,其本身亦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尤其是其中第二首,集中了蘇軾詩歌創作的幾個重要特點。
一、月印萬川的理性精神
朱熹有言:“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而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1],“太極只是個理”[2]。朱熹借禪宗之說來闡述“理”,也反映了宋詩人詩歌多理性精神的共性。宋詩人詩中的山川景物并非與詩人情感融為一體的情感符號,而是詩人說理的各種媒介,詩人的最初與最終目的,都是一個“理”字。蘇軾的《次荊公韻四絕·其二》亦體現出深刻的哲理思索,“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詩人寫竹,寫花,寫綠苔,最終目的卻在“造物”上。“細看造物初無物”,詩人面對自然景色,綠苔紅花,未生出類似“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這樣的美妙想象,而是陷入關于“造物”的理性思考。蘇軾有不少詩都言及“造物”,如:“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遍”(《泗州僧伽寺塔》),“生成變壞彈一指,乃知造物初無物”(《次韻吳傳正枯木歌》),“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墨花·并序》)等。“造物”即是“自然”,是蘇軾對天人關系的理性思索。“造物初無物”則體現出蘇軾對道家思想的接受與思考,正如郭象在《南華真經序》中說:“上知造物無物,下知造物之自造也”[3],蘇軾認識到自然是以其所以是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存在著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游》),自然有其自身的規律與存在方式,不需強求人力,體現出唯物主義傾向。蘇軾有不少詩歌是反映出詩人冷靜可觀的理性精神,詩人將自己對客觀世界的理性思考,如他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與“當局者迷,旁觀者親”的觀念契合,而《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下種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則反映出詩人樸素的辯證觀。
蘇軾和其他宋詩人一樣,強調詩歌的理性精神,而這一理念對詩歌創作最直接的影響則是詩歌中的寫景變成言理的媒介,而損害了盛唐詩當中情景渾融的境界,但也正是如蘇軾一般的宋詩人主動求新求變,才使宋詩從晚唐五代的“悲哀為主,風流不歸”的“緣情之溺”中解脫出來,形成自己“深析透辟”“氣骨勁瘦”[4]的風格。
二、用工深刻的才學之詩
嚴滄浪評宋詩:“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5],蘇軾雖非可以強調來歷出處,但在時代大背景影響之下,在創作詩歌之詩不可避免受其影響。如這首《次荊公韻四絕·其二》,“斫竹穿花破綠苔”之句可窺見韓退之“竹洞何年有,公出斫竹開”之句;“小詩端為覓榿栽”則脫胎于杜子美的《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細看造物初無物”則明顯化用了郭象的“上知造物無物”。用字求來歷出處雖然使詩歌沒有盛唐詩“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玲瓏透徹”[6]之美,卻顯出詩人極為深厚的文學積累,使得詩歌所承載的內容與學識大大增加。
蘇軾對于詩歌的用工刻苦還反映在其“以文為詩”的孜孜探求上。趙翼《甌北詩話》稱:“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以文為詩”最早由韓愈倡導,主張詩歌創作中引進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現手法,突破近體詩的種種束縛和羈絆,借用形式較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來進行詩歌寫作創作主張,蘇軾集成了韓愈的這種理念,并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表現出來。正如《次荊公韻四絕·其二》實則是記敘了前兩句描寫了詩人所見的景色,后兩句則直接以議論的方式,表達出詩人的理性思考所得,這種以明白如話的語言揉入詩歌正是“以文為詩”的重要特點。雖然后人對“以文為詩”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軾對詩歌的創新探索之功。
三、委順自適的達觀心境
“追求主題心性的自由,主張自性清凈、隨緣任運的禪宗思想更為深入地滲入到蘇軾的價值體系,并于老莊道家思想渾合交融”[7],因而形成了其委順自適的達觀心境。《次荊公韻四絕·其二》中言“春到江南花自開”,詩人放任自然,而不力強,造物自由其規律,春至江南,繁花自然盛放,無需人力干涉。寫作此詩時,蘇軾剛離開黃州謫所,王安石亦身體多病,不問政事,兩位因新政而結下心結的人,此刻卻都是在政治上頗受打擊,客居異鄉之人。中國文學史上的遷客騷人向來都是帶著滿腹的憤懣的,而蘇軾面對這種情況,卻未生出頹喪之氣,甚至對王安石似有幾分勸解之意,“春到江南花自開”:順其自然,該來的都會來的。這種順應自然,知足自適的達觀心境,是蘇軾詩傳達給人極為可貴的精神滋養。這種心境并不是偶然地在這首《次荊公韻四絕·其二》,而是貫穿著蘇軾的大部分創作中,也是他評判詩人的重要標準。他的《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裊裊風蒲亂,倚倚水荇長。小舟浮綠鴨,大杓瀉鵝黃。得意詩酒杜,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詩人沉醉于自然之中美景之中,享受自然恩賜的愜意時光,而不去執意追尋那種忙碌的人生。另外“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少年游·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更是他委順自適心境的寫照,蘇軾被貶嶺南歸來之后,別人擔心他嶺南的歲月難熬,而他卻坦然自在,無論是海角天涯,窮山惡水,只要內心安寧,即使遠在天涯,心內也和居于家中一樣平和,這種不為外物悲喜而輕易動搖內心,而是順應著變化調整自己,委順而自適的心境,是蘇軾身上極為可貴的閃光點。
而蘇軾推崇陶淵明,很大程度上,亦是推崇其恬然自適的生活態度——“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陶淵明這種自適的心境與真淳的性格與正與蘇軾契合,因而深為蘇軾所推崇,蘇軾甚至創作一百余首“和陶詩”,表達對陶淵明的崇拜:“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和飲酒》),甚至在《和歸去來兮辭》中竟然說自己是陶淵明之后身:“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詩。賦歸來之新引,我其后身蓋無疑。”蘇軾一生仕途坎坷,輾轉飄零,然而其詩并未像多數遷客騷人的詩一般,彌散著濃濃的蕭瑟怨懟之氣,而是充滿曠達疏闊、泰然達觀之感,實在是因詩人深受莊禪之影響,而形成了委順自適的達觀心境。
蘇軾之詩雖相較其“自是一家”之詞略有遜色,但在時代共性引導、詩人努力突破與詩人自我心性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其詩歌在整個宋代詩歌中亦呈現出獨特面目,不僅是研究蘇軾其文學創作,亦是研究宋詩乃至宋文化不可忽略的部分。
注釋:
[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409頁。
[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70頁。
[3]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頁。
[4]繆鉞:《詩詞散論》,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
[5]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頁。
[6]郭紹虞校釋,嚴羽:《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頁。
[7]吳增輝:《蘇軾和陶而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探析》,浙江學刊,2010年,第1期,第124頁。
(吳莉莉 江蘇南通 南通大學文學院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