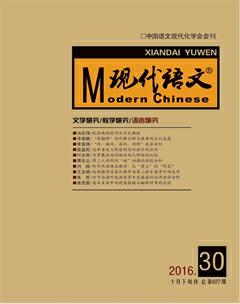中學“記”類古文文體辨析
○李秀梅
?
中學“記”類古文文體辨析
○李秀梅
中學教材中以“記”命篇的古文,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柳宗元的《小石潭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乍看起來似乎都屬于游記一類,實際上是有區別的。在復習課教學時,應對它們作歸類比較,以游記的文體特點為參照,厘清上述幾篇古文的文體特點及區別,使學生對其有清晰的認識。
一、“記”的文體歸屬和游記的特點
“記”是古代常用的文體,《文心雕龍》把它歸為“書記”類,涵蓋范圍非常廣泛,可以記書畫雜物,可以寫臺閣名勝,可以記人事,也可以記山水游賞。選入中學教材的這幾篇,大致歸屬兩類,《岳陽樓記》《醉翁亭記》屬臺閣名勝記,《小石潭記》屬山水游記,《桃花源記》《游褒禪山記》也被歸入山水游記,但又有爭議。
之所以這樣劃分,首先是基于對游記文體特點的厘清。山水游記的文體特點核心有三,其一在題材上是描寫自然山川、風物及觀感,其二“必須是作者親身游歷的記錄”[1](P359),其三有清晰的游蹤,在寫法上重寫實景,移步換景,時間和空間在同步變化。以這些特征去鑒別上述幾篇古文,就易見出不同了,只有《小石潭記》屬于典范的山水游記。《小石潭記》一文,小邱——篁竹——小潭(底、岸、中)——潭西南——坐潭上,游蹤清晰,具體地記錄了一次游賞的歷程。
二、亭臺樓閣記的特點及與游記的不同
亭臺樓閣記,是“古人在修筑亭臺、樓觀,以及觀覽某處名勝古跡時,撰寫敘文,以記敘建造修葺的過程,歷史的沿革,以及作者傷今悼古的感慨等。”[1](P353)《岳陽樓記》一文,首段交代作記的緣由。次段由概括地寫“巴陵勝狀”“岳陽樓之大觀”,轉寫“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三四段承接,一悲一喜,末兩節則直抒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與抱負。全文緊扣“岳陽樓”,敘述、描寫、議論、抒情融為一體。是典型的亭臺樓閣記。
山水游記和亭臺樓閣記的區別在:“臺閣名勝記記事性比較強,而且是刻石的;而一般山水游記則以專心描繪山川自然景物為內容,主要寫旅途的見聞和對大自然風光之美的感受,而且山水游記是不刻石的。”[1](P359)筆者以為,二者的區別還體現在:臺閣名勝記,因為描寫對象是固定的,即空間的固定,在寫景上多從時間角度入手。而《岳陽樓記》《醉翁亭記》從立意看,都是借以抒懷,不是寫某一次游賞的經歷,沒有游玩的“路線圖”,只能描繪同一地點在不同時間的景物變化。《岳陽樓》寫在“朝”“夕”“霪雨霏霏”“春和景明”時登樓的不同觀感;《醉翁亭記》次段概括地寫醉翁亭四周山間景致,從山間“朝暮”寫到“四時”,三四段具體寫一天也從白晝寫到“夕陽在山”(當然,這不能看作某一次具體的游玩,實際是歐陽修日常與民同樂的經驗累積),都是從時間變化入手。
三、游記變體
《游褒禪山記》,從文題看,應屬山水游記;讀其文,由洞口的石碑寫到前洞,再寫到后洞,游蹤清晰,是一次具體的游覽,是一篇游記。但它和《小石潭記》相比,又有不同。這篇“游記”重點不在描寫山洞的“奇偉、瑰怪、非常之觀”,而重在表達在游覽中的思考、感悟、“所得”:人做任何事情,包括治學,都必須有堅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不輕易放棄,盡力盡志,才能達到最高的境界,才能終生無悔。作者還借碑文漫滅,后人訛傳的現象,表達學者應“深思深取”的觀點。從結構布局上看,第一段末兩句“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實是為“余于仆碑”一段議論文字伏根張本;第二段“其下平曠”至“遂與之俱出”,重在敘事而非繪景,“敘游事,筆筆伏后議論”[2](P482),這段簡要的敘事,是為下文的議論服務的,整篇文章實是“借游華山洞,發揮學道。”[2](P483)就全篇看,“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句中“學者”實是全文暗藏的眼目,吳楚材評云“直至此,方點明學者。記意寓體,收拾已盡。”[2](P483)《游褒禪山記》重在表達學者治學之道,在游記的衣缽下加進了議論和說理,是議論文體對游記體的滲透,也是宋代重理趣的表現。總之,《游褒禪山記》是游記中的變體,是別開生面之作。
四、《桃花源記》并非游記
《桃花源記》不可視為游記。褚先生指出“《桃花源記》,內容屬于虛構,是以游記體的形式表達某種社會理想之作,與真正的游記文不是一回事。”[1](P348)而對“社會理想”的內涵,朱光潛以為是不受政府典章制度擾亂的農耕生活,一個淳樸的烏托邦,人生的樂趣也只在“桑麻閑話,樽酒消憂”:
陶淵明的心中有許多理想的境界。他所景仰的“遺烈”固然自成一境,任他“托契孤游”;他所描寫的桃花源尤其是世外樂土……《桃花源記》所寫是一個理想的農業社會,無政府組織,甚至無詩書歷志,……這境界頗類似盧梭所稱羨的“自然狀況”。[3](P324)
梁啟超先生也把《桃花源記》看作小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正是浪漫派小說的鼻祖。里頭說的:‘……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憇。桑竹垂余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這是淵明理想中絕對自由、絕對平等、無政府的互助的社會狀況;最主要的精神是‘超現實’。”[4](P121)
另外,《桃花源記》最早被收入志怪小說集《搜神后記》,是被編者看作小說的。近人周振甫指出《桃花源記》“有具體時期,‘晉太元中’;有具體地點,‘武陵’;有具體人,‘漁人’。有具體經歷,漁人緣溪行,到水源,由小洞到桃花源。有具體境地,有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有‘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人物,‘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有情意,‘設酒殺雞作食’。有對話,‘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有重尋,‘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一切寫得如漁人曾親歷其境。這樣把傳說和理想化為實境,是一種寫法,是文章學中化虛為實的寫作法之一。”[5](P135)周先生把《桃花源記》所具有的小說的鮮明的敘事性特征說得很透徹了。綜合起來,《桃花源記》雖然在體式上具有游記的特征,但又有很多的虛構,是借用游記的外殼讓讀者信以為真罷了,不應歸入游記類,應被視為小說。
五、虛實比較
通常我們把寫眼前景、事、人看做實,把想象、回憶的景、事、人叫虛;把景看作實,把情、理看作虛。從虛實的角度看,《小石潭記》作為山水游記,側重對實境的描寫,虛境(情感)含在對景的描繪中;《桃花源記》在文體上是游記和小說的互相滲透,借游記的外殼,把虛境(社會理想)寫實化;《岳陽樓記》《醉翁亭記》對實境進行縱向(時間向度)的延伸;《游褒禪山記》則由實境(游賞)向虛境(治學的道理)開掘,側重寫虛境。
通過對“記”類古文的歸類比較,可以獲得較清晰的文體意識,有助于閱讀心理的養成和寫作能力的提升。
注釋:
[1]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安平秋點校,[清]吳楚材,吳調侯選注:《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
[3]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4]梁啟超:《作文入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
[5]周振甫:《中國文章學史》,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李秀梅 安徽蒙城 蒙城縣第八中學 23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