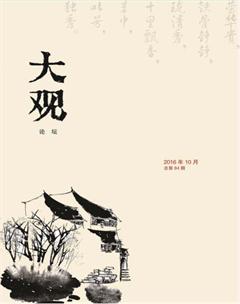畢飛宇小說《玉米》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探究
摘要: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文化負載詞雖能折射出中華民族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化,卻也給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本文以畢飛宇小說《玉米》及其英譯本Three Sisters為研究對象,探討譯者葛浩文林麗君夫婦對小說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所采用的策略和技巧,以期為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實現更好地“文化傳真”提供借鑒。
關鍵詞:《玉米》;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
一、引言
《玉米》是當代作家畢飛宇的代表作之一,獲“魯迅文學獎”,英文版Three Sisters由美國翻譯家葛浩文林麗君夫婦合作完成,獲2010年度“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玉米》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蘇北農村王家莊三姐妹玉米、玉秀和玉秧的不同遭遇和命運,揭示政治和權力對人性的摧殘。小說中出現了大量有關中國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的詞匯及俗語諺語,也就是所說的文化負載詞,這些詞匯給譯者的翻譯也帶來一定困難。本文將具體討論葛浩文夫婦處理《玉米》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和動機。
二、《玉米》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分析
關于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研究,異化和歸化不失為兩種有效的手段。這兩種策略由韋努蒂系統提出,他認為歸化策略在翻譯中消除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而異化策略是在翻譯中凸顯語言和文化的差異,保持原語的異質性(Venuti,2004),這也是他本人所提倡的翻譯策略。
筆者通過對《玉米》漢英文本中文化負載詞的搜集和歸類,發現譯者主要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具體采用了直譯及直譯加解釋的翻譯技巧,盡量忠實于原文,保留原文中的異質性元素。在不影響讀者理解的前提下,譯者采用直譯技巧實現對文化負載詞的異化,如將“帝修反”譯為imperialists,revisionsists and reactionaries,“地主富農”譯為landlords or rich peasants,“工分”譯為work points,“寧做雞頭,不做鳳尾”譯為Better to be the head of a chicken than the tail of a phoenix,“殺雞給猴看”譯為kill a chicken to scare the monkeys,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漢語中的一些諺語表達。
然而,由于大多數西方讀者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生活和語言了解甚少,通過對文化負載詞的直譯而實現的異化往往會給西方讀者造成困惑,譯者就需要根據原文內容在直譯的基礎上適當增加解釋,把原文中的文化負載詞解釋得更清楚或者將文化負載詞的隱含意義明示出來,在保留異質性的同時提高譯本可讀性。例如:
原文:雖說是狐假虎威,好歹總算是出了門了,見了人了。
譯文:Though she was drawing strength from her sisters fierce demeanor--the fox parading along behind the tiger--at least she was out in public.(Howard Goldblatt & Sylvia Lin,2010:99)
原文中的“狐假虎威”是漢語成語,屬于語言文化負載詞,起源于先秦時代寓言故事,字面意思指狐貍假借老虎的威勢嚇唬其它野獸,比喻仰仗或倚仗別人的權勢來欺壓、恐嚇人。這個成語故事的隱含義對于國內讀者來說是不陌生的,然而在翻譯時,若直接譯成“the fox parading along behind the tiger”,西方讀者因為沒有相應的文化背景知識,很容易產生困惑,因此譯者根據原文內容,增加了解釋“drawing strength from her sisters fierce demeanor”,向西方讀者明示該成語的隱含義。由此,既實現了對文化負載詞的異化,同時又兼顧了西方讀者閱讀需求,使西方讀者真正了解改成語的形式和意義,豐富英語表達,實現了“文化傳遞和交流”。
雖然葛浩文夫婦主要采用了異化翻譯策略以保持原文文化負載詞的異質性,但也在部分之處采用了歸化翻譯策略,更好地提高譯文可讀性。如原文中有這樣一句描述,“家里人多,過去每一次吃飯母親都要不停地催促,要不然太拖拉,難收拾,也難免雞飛狗跳”,最后一個小分句出現了成語“雞飛狗跳”,譯者處理為“Squabbles inevitably resulted”,雖略去了成語的字面形式,卻也更好地將這個成語在原文中的意思表達了出來,且更簡潔,與譯文之前的內容銜接得更流暢。
然而葛浩文夫婦中也有誤譯之處,如將原文中的俗語“有棗無棗打一棒罷了”譯為“hitting a date tree just for the sake of making contact with something”,這句俗語意指隨便試試運氣,而譯文卻完全偏離了原文的意思,且讀起來比較生硬,意義表達也不清楚。這還是與葛浩文夫婦的生活環境和漢語水平有關,畢竟葛浩文是美國人,林麗君是臺灣人,二者都不是在中國大陸生活,對漢語中的一些俗語理解不夠透徹也情有可原。總體來說,瑕不掩瑜,葛浩文夫婦對《玉米》中的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還是很適當的。
三、結語
關于《玉米》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葛浩文夫婦主要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盡量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異質性,實現“文化傳真”,也從側面反映了葛浩文重視文化交流的翻譯觀;同時輔以歸化翻譯,提高文本可讀性。此外,關于譯文中的個別誤譯現象,也給中國文學作品英譯實踐帶來一些啟示,一方面可以以英語國家高水平漢學家及翻譯家為主力來譯介中國文學作品,使譯文語言更地道,同時也要挑選國內高水平譯者參與譯本的校對工作,尤其注重校對作品中的文化現象,使得西方讀者了解到正確的、地道的中國文化,更好地實現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Goldblatt,Howard & Sylvia,Lin.Three Sisters[M].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
[2]Venuti,Lau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畢飛宇.玉米[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
[4]柴立珍.葛浩文翻譯觀探析——以《玉米》英譯本為例[J].時代文學,2013(04):164-165.
作者簡介:秦丹丹(1989—),碩士,河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