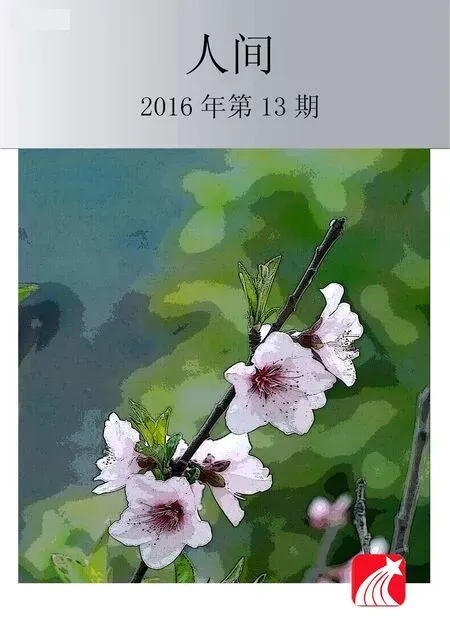扒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
賈蘭蘭(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3)
?
扒竊行為如何適用法律
賈蘭蘭
(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3)
摘要:扒竊是盜竊的一種行為類型,然而對于扒竊卻比一般的盜竊具有更高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刑法修正案(八)》將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并列入罪,明確規定只要實施以上行為即構成盜竊罪。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扒竊的入罪量刑卻存有很多爭議。
關鍵字:扒竊;盜竊;刑法修正案(八);隨身攜帶的財物
近些年來,扒竊犯罪日益猖獗,成為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群眾出行安全的一大公害,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定。為了有力打擊扒竊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將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并列入罪,明確規定只要實施以上行為即構成盜竊罪,而且沒有犯罪數額、次數的要求。然而在實務中對于扒竊的界定、入罪標準以及如何處罰卻爭議不斷。本文將就司法實踐中辦理扒竊案件爭議問題的各種觀點進行淺析。
一、扒竊行為的認定
刑法規定扒竊對象是“隨身攜帶的財物”,但如何理解“隨身攜帶的財物”,是貼身財物還是包括近身財物,最高檢和最高法的理解就不一樣.
最高檢在《檢察日報》上刊登的《解讀“兩高”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指出:“隨身攜帶”應該理解為一種實際的支配或者控制的占有狀態。隨身攜帶的財物包括被害人帶在身上與其有身體接觸的財物,以及雖未依附于身體,但置于被害人身邊,可用身體隨時直接觸摸、檢查的財物。①最高檢認為隨身攜帶是一種包括控制和支配的范圍,并不一定緊貼身體。
而最高法院在《人民司法》中刊登了對《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文指出:我們經研究認為,扒竊行為中“隨身攜帶的財物”,應當限縮解釋為未離身的財物,即被害人的身體與財物有接觸。②原因是:第一,這樣能夠恰當反映扒竊相對于普通盜竊具有更為嚴重的危害性。如果被害人通過身體部位與財物接觸,直接占有和控制著財物,這就意味著行為人通常不可能直接將財物偷走,而必須貼近被害人,采取掏兜、割包等手段偷走衣服或包內的財物。行為人實施這種扒竊行為,具有更大的主觀惡性,也更容易發生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嚴重后果,對這類行為,不論盜竊數額多少都應予以定罪處罰具有合理性;如果財物已經脫離了被害人的直接占有和控制,行為人伺機竊取,相對不容易被人及時發覺,而且引發犯罪分子危害受害人人身安全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對竊取這類財物的,就不宜認定為“扒竊”,而應按普通盜竊處理。第二,符合立法本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一書指出:“扒竊行為往往采取掏兜、割包等手法,嚴重侵犯公民財產和人身安全,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且技術性強,多為屢抓屢放的慣犯,應當予以嚴厲打擊。”第三,符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識。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扒竊”是指“從別人身上偷竊財物”。所以,無論從立法精神還是從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來看,均應當將“扒竊”解釋為盜竊與被害人身體有接觸,能夠為被害人直接占有和控制的財物較為合理、妥當。
二、扒竊行為的入罪標準的把握
張明楷教授指出,扒竊入罪雖然不要求數額較大,但這并不意味著任何財物都是刑法的保護對象。作為扒竊對象的財物,必須具有價值。從實際上看,作為扒竊對象的財物,一般都是具有客觀價值的財物。其次,某些紀念品、身份證、出入境證件、信用卡、存折等,本身不一定具有經濟價值,但對所有人、占有人具有使用價值,社會觀念也認為對這種物品的占有值得刑法保護,因而應當成為扒竊的對象。《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幾種盜竊行為類型已經表明,只要對所有人、占有人具有使用價值,即使其客觀上沒有經濟價值,也可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
《刑法修正案(八)》基于扒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考量,取消了數額和次數的限制,但是由于其仍屬于刑法分則第五章侵犯財產犯罪的范疇,因此有的人認為如果僅僅具有扒竊行為就認定犯罪打擊范圍過寬,也不能認為一切物品都是扒竊的對象。因為刑法雖然規定盜竊罪是為了保護被害人的財產,但是,根據刑法的性質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關系,由于扒竊行為其本身的危害性較大,即便對財產的侵害極為輕微,也有可能對受害者的人身造成很大的危害。不能認為,沒有竊取到有價值的財物,就忽略行為的危害性。
三、扒竊犯罪的既遂、未遂的認定
一種觀點認為,扒竊的成立不應有數額限制,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扒竊行為,就成立盜竊罪。因為行為人已經實施了扒竊行為,這一行為足以充分反映其人身危險性及對法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行為人是否實際取得財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為人實施的扒竊行為本身的人身危險性。
張明揩教授認為扒竊是盜竊罪的一種行為類型,由于盜竊罪屬于侵犯財產罪,所以不能將扒竊視為所謂的行為犯,即不能認為只要是實施了扒竊行為,即使分文未取也成立盜竊既遂。對于扒竊仍應以行為人取得了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物為既遂標準。因此,扒竊但取得的是不值得刑法保護的物品的,只能認定為盜竊未遂。另一方面,對于扒竊未遂的,既不能一概的以犯罪論處,也不能一概的以不犯罪論處,是否以盜竊罪追究刑事責任,就取決于其行為的情節是否嚴重。
參考文獻:
[1]陳國慶、韓耀元、宋丹《解讀“兩高”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2013.6.5
[2]胡云騰(專委)、周加海、周海洋《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4第15期
注解:
①陳國慶、韓耀元、宋丹《解讀“兩高”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司法解釋》2013.6.5
②胡云騰(專委)、周加海、周海洋《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4第15期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5-0077-01
作者簡介:賈蘭蘭(1990.9-),女,山東臨沂人,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2014級法碩(非法學)研究生 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