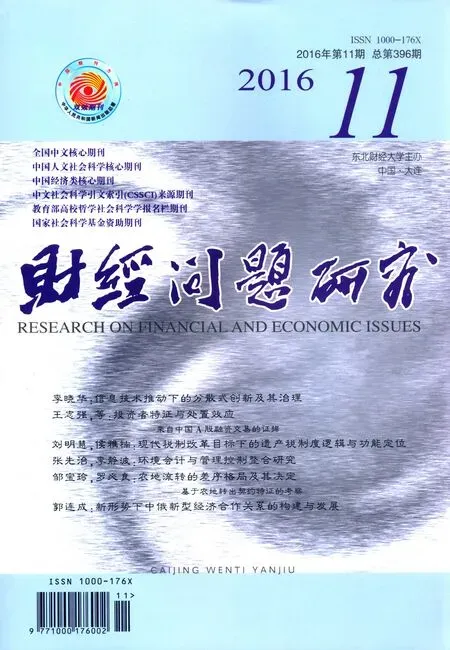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
——基于烏魯木齊的經驗分析
費 清,盧愛珍
(新疆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
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
——基于烏魯木齊的經驗分析
費 清,盧愛珍
(新疆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城鎮化發展的質量直接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本文以1978—2013年烏魯木齊經濟數據為基礎,以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誤差修正模型與因果檢驗分析,發現烏魯木齊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雙向的促進關系;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對城鎮化率有正向作用,但城鎮化對其他兩者的作用不明顯,即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不足。基于此,筆者提出烏魯木齊在實現城鎮化與區域經濟、產業協調發展的過程中,應注重研究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供給側結構改革,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等政策建議。
城鎮化;產業結構;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改革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城鎮化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的資源集聚、消費拉動和空間支撐作用;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鎮化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三是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積累效應與學習效應,及其對城鎮化的帶動效應。
長期以來,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研究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在城鎮化方面,國內外許多學者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大量的研究。Moomaw和Shatter[1]通過實證得出,城鎮化會隨產業結構調整、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上升。Black和Vernon[2]建立了城鄉兩部門增長模型,分析了土地要素、非農部門等資本投入對農業產出的影響。吳福象和劉志彪[3]認為,長三角城市群的推進對當地經濟轉型升級和增長發揮著新引擎作用。程開明[4]研究發現,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正向關系。Brückner[5]研究了以非洲為代表的發展中地區,發現在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對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蘇劍和賀明之[6]通過實證認為,經濟方面的變量決定著潛在的城鎮化水平,而非經濟變量產生的是實際城鎮化率與自然城鎮化率的離差程度。肖國榮[7]研究了經濟增長、城鎮化、產業結構與土地價格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得出產業結構與土地價格是負相關關系,而其他相互關系均為正向關系的結論。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了生產要素投入方向與方式的變化,進而產生集聚效應,推動城鎮化進程。Pandey[8]實證發現,勞動力在各產業中的分布變動會對城鎮化產生明顯的作用。Gilbert和Joseph[9]提出城鎮化率與第二、三產業占比的提高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而與第一產業則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郭克莎[10]提出,城市化進程與產業結構及相應的就業結構之間有較強的聯系,特別是工業化對城鎮化進程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王傳民[11]基于系統動力學的分析,提出縣域產業構成及各產業間關系與縣域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王智勇[12]認為,對西部落后地區而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應注重以工業化為導向、第三產業跟進。柯善咨和趙曜[13]利用結構—規模協同效應回歸擬合法,分析了產業結構和城市規模對我國城市經濟效益的協同影響機制,認為不同規模的城市應采取不同的產業與城鎮化策略。
在我國經濟增長與城鎮化、產業結構的關系方面,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師應來[14]研究了城鎮化與其他經濟變量的關系,發現城鎮化率、人均生產總值和產業結構有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城鎮化水平與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占比之間的相關性不高。韓峰和李玉雙[15]認為,城鎮化進程有助于湖南省產業結構升級。孫曉華和柴玲玲[16]通過實證得出,城鎮化是影響三次產業中勞動力就業占比變化的重要因素,而第三產業就業占比的上升推進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楊志海等[17]針對縣域城鎮化水平與城鄉二元收入格局的關系進行實證,結果表明縣域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對城鄉二元收入結構具有收斂作用。王立新[18]通過實證得出,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是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盧學法和杜傳忠[19]運用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發現短期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而較長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動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呂煒和謝佳慧[20]認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地區在產業結構上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地區的城鎮化存在著差異化的路徑選擇。
在上述的研究中,學者們或側重于研究經濟增長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或側重于分析產業結構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或針對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城鎮化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但多數的研究直接將某省、某大片區(例如西北、華北)、甚至全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往往忽視了樣本區域內部的發展差異,導致相關分析結果的精確性不高,所提出政策建議的針對性不強,缺少對特定城市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城鎮化三者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在總結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利用1978—2013年相關數據,對烏魯木齊的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以期掌握烏魯木齊在上述三個方面的相互作用情況,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也為今后研究特定城市的城鎮化水平、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與計量模型
1.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
本文所采用的協整關系檢驗、ECM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等實證方法都要求數據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所使用的是ADF單位根檢驗,該檢驗是零假設檢驗,即“H0:時間序列yt是非平穩的”。ADF的基本形式如式(1)所示:
(1)
其中,k代表最優滯后階數,該階數對檢驗結果有著重要的統計影響。滯后階數的確定一般使用赤池準則(AIC)和施瓦茨準則(SC),能使兩者的值達到最小的參數k就是最優滯后階數。若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ADF檢驗值大于臨界值則接受原假設,時間序列非平穩;反之,則拒絕原假設,即時間序列平穩。
2.Gr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的目的是為了確認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作用方向。其檢驗思路為,設有兩個變量x和y,若x的變化引起了y的變化,則x變化的發生應早于y的變化。常用的回歸方程為:
(2)
其中,C1代表常數項,r代表因變量滯后期長度,q代表自變量滯后期長度,隨機誤差項ε1t與變量不相關。為了完成對任何自回歸滯后期長度n的Granger因果檢驗,式(2)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F檢驗的零假設為βj=0(j=1,2,…,n),F統計量基于以下公式計算:
(3)
其中,RSSV代表滿足βj≠0(j=1,2,…,n)條件下式(2)的殘差平方和,RSSR代表滿足βj=0(j=1,2,…,n)時式(3)的殘差平方和,T代表樣本容量,q代表變量y的滯后期長度。若F統計值比F-分布標準值大,則y不能接受x的零假設,表明y變化是x變化的原因。若檢驗x對y的因果關系,則將變量y與y的滯后項和x進行回歸。如果上述兩個檢驗均否定原假設,則證明變量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三)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CM)的基本形式為:
(4)

三、經驗檢驗
1.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城鎮人口比率(Ur)代表城鎮化,以第二產業占比(Indu)、第三產業占比(Serv)代表產業結構,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Y)代表經濟增長情況,選擇烏魯木齊1979—2013年相應指標的數據,使用Eviews 7.2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新疆統計年鑒》、新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新疆五十年》等。同時,為了在不影響數據間相互關系的前提下避免多重共線性,本文對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
2.數據平穩性檢驗
為檢驗是否存在時間趨勢,本文將對數化后的各變量序列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原序列對數化后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

表1 平穩性ADF檢驗結果
3.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擴展的Johansen檢驗方法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確定變量間存在的長期線性關系。由表2可知,在零假設情況,5%臨界值水平下,特征根跡統計量與最大特征值檢驗值大于顯著性水平;反之,特征根的跡統計量與最大特征值檢驗值均小于顯著性水平。

表2 Johansen 協整檢驗結果
協整檢驗結果顯示,變量之間存在一組協整關系,基于此,本文建立協整方程如下:
lnY= -2.11+0.83lnIndu+1.17lnServ+0.71lnUr
(-12.44)(2.81)(3.79) (2.21)

(4)
而為了檢驗序列的平穩性,需要對殘差項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殘差平穩證明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協整關系。第二、第三產業結構、城鎮化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彈性系數分別是0.83、1.17和0.71,說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每發生1個單位的變化,第二產業會變化0.83個單位,第三產業會變化1.17個單位,城鎮化率會變化0.71個單位。

表3 協整方程的殘差檢驗
4.誤差修正模型
為了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短期關系,及其長短期自我調節機制的變化情況,本文在協整模型的基礎上加入殘差系數,對變量一階差分后構建ECM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ΔlnYt=0.12+0.91ΔlnYt-1+0.41ΔlnYt-2+0.79ΔlnIndut+0.21ΔlnIndut-1+1.03ΔlnServt+0.39ΔlnServt-1+0.66ΔlnUrt+0.10ΔlnUrt-1-0.39ECMt-1

(5)
5.Granger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只能說明城鎮化、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并不能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及作用方向進行全面分析,需要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確定。確定Granger因果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并進行檢驗,得出如下結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lnY是對數值lnIndu、lnServ、lnUr的Granger原因;lnIndu、lnServ也是lnY的Granger原因;但lnUr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特別地,在考察城鎮化率與產業結構的因果關系時,lnUr不是lnIndu與lnServ的Granger原因;但lnIndu與lnServ均是lnUr的Granger原因。
6.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上述檢驗,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變量一階差分后平穩,且存在著一組協整關系。通過協整方程的構建,可得到變量間長期關系的系數分別為0.83、1.17和0.71,且模型的殘差序列平穩,說明變量間存在長期、較明顯的穩定關系。
第二,誤差修正模型表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化率、第二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之間存在著短期的關系,模型對樣本的擬合程度好。在差分后,滯后兩期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對當期仍存在正向關系,但與滯后一期相比影響衰退。第二產業比重和第三產業比重對當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作用是正向的,當期的作用效果比滯后一期的大。此外,模型中誤差修正系數較小,說明因變量的短期自我修正能力不強,即經濟增長在城鎮化與產業結構的影響下向穩態增長率的收斂速度慢。
第三,Granger因果檢驗反映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但城鎮化率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之間僅存在單向關系,即城鎮化不是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Granger原因,但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是城鎮化的Granger原因。這與傳統經濟理論及類似實證研究結論不同,體現出本文所選樣本城市具有獨特性,其城鎮化的發展對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并沒有有效的推動作用。
第四,從經濟意義通過經驗分析可以看出,烏魯木齊的經濟增長能夠有效推動城鎮化率的提高,但城鎮化率對烏魯木齊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同時,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第三產業占比的提升是城鎮化進程加快的推動力,但其反向關系不明顯。由此可見,烏魯木齊的城鎮化水平雖然較高,但城鎮化對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貢獻程度較低,未能有效地將城鎮化進程中所集聚的資本與人力資源轉化為生產力。此外,在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烏魯木齊第三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大于第二產業。
四、政策建議
第一,促進城鎮化與經濟協調發展。近年來,烏魯木齊的城鎮化率已處于全國前列,為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結合實證分析結果可知,烏魯木齊的經濟發展與城鎮化水平之間出現了不匹配的現象,城鎮化進程并未對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有力的推動作用。當前,烏魯木齊仍在加快推進高鐵、會展、白鳥湖、城北新區、古牧地、城南經貿合作區等新區的建設,面對已經出現的問題,應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結合烏魯木齊實際制定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避免大躍進式的追求數量,避免粗放式發展,減少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實現產城融合。
第二,研究和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在“新常態”背景下,烏魯木齊應結合自身發展實際,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由數量轉向質量,進一步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當前,烏魯木齊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應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推動農業生產現代化,增強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堅持創新驅動,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對烏魯木齊而言,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較高,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強,為此,應抓住“一帶一路”戰略和“五大中心”建設的重大機遇,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大力發展過境運輸,建立國際物流分撥中心。
第三,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近年來,烏魯木齊較好地利用了后發優勢,淘汰落后產能,第三產業對地區經濟的帶動力較強,產業結構升級取得了階段性成就。但隨著城市發展的飽和,與周邊地市的產業相似程度提高,后發優勢的利用空間逐步縮小。為此,烏魯木齊應主動創造自己的先發優勢,培育高端要素、高端產業和高端市場,建設創新高地。充分利用城鎮化帶來的集聚效應,以“一帶一路”戰略為依托,廣泛吸引以技術、品牌和質量為核心的新產品、新產業和新市場,做大做強地方特色,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
第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釋放出“十三五”經濟轉型發展的新信號。面對城鎮化推進中出現的問題,烏魯木齊應針對自身產業結構調整與城鎮化發展中的問題,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和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要著力推動創新并擴大有效供給,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推動新型城鎮化的質量提升,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此,烏魯木齊應結合當前實際,重點培育涉及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健康、養老、保險、文體、法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和教育培訓等領域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并在財稅、金融、價格、社保和土地政策等方面給予政策激勵。
[1] Moomaw, R.L., Shatter, A.M.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Bias Toward Large Cit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6,40 (1).
[2] Black, D., Vernon, H.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3] 吳福象,劉志彪.城市化群落驅動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來自長三角16個城市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08,(11):126-136.
[4] 程開明.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協調度研究[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0,(9):85-91.
[5] Brückner, M. Economic Growth,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2,71(1): 26-36.
[6] 蘇劍,賀明之.對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一個定量解讀[J].經濟學動態,2013,(9):88-94.
[7] 肖國榮.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城鎮化對土地價格影響的實證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4,(10):42-44.
[8] Pandey, S.M.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Urbanization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 of Ind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7, 25(2): 265-278.
[9] Gilbert, A., Joseph, G. Citie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in the Third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16-217.
[10] 郭克莎.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2,(2):44-45.
[11] 王傳民.縣域經濟產業協調發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63-65.
[12] 王智勇.產業結構、交通、民族與縣域經濟發展——以云南省為例[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2,(5):123-131.
[13] 柯善咨,趙曜.產業結構、城市規模與中國城市生產率[J].經濟研究,2014,(4):76-88.
[14] 師應來.影響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因素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6,(10):90-93.
[15] 韓峰,李玉雙.城市化與產業結構優化——基于湖南省的動態計量分析[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0,(4):8-15.
[16] 孫曉華,柴玲玲.產業結構與城市化互動關系的實證檢驗[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22-27.
[17] 楊志海,劉雪芬,王雅鵬.縣域城鎮化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嗎?——基于1523個縣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42-48.
[18] 王立新.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城鎮化——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財經論叢,2014,(4):3-8.
[19] 盧學法,杜傳忠.新常態下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基于省際動態面板數據的廣義矩估計[J].管理現代化,2015,(6):19-21.
[20] 呂煒,謝佳慧.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重新認知與理論思辨[J].財經問題研究,2015,(10):3-10.
(責任編輯:楊全山)
2016-07-1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形勢下新疆承接產業轉移的金融支持研究”(11BJY02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招標課題“區域金融發展促進新疆與中亞貿易投資轉型的實證分析”(050113B02)
費 清(1990-),男,江蘇徐州人,助教,碩士,主要從事貨幣政策與區域金融研究。E-mail:15981776183@163.com
盧愛珍(1965-),女,新疆烏魯木齊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貨幣政策、區域金融和保險等方面研究。
F293.1
A
1000-176X(2016)11-01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