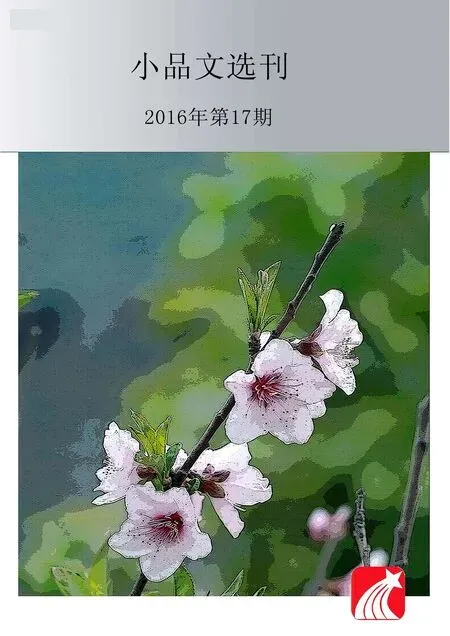《呼蘭河傳》的語言藝術
陳 媛
(山東師范大學 山東 濟南 250000)
《呼蘭河傳》的語言藝術
陳 媛
(山東師范大學 山東 濟南 250000)
《呼蘭河傳》是蕭紅一部重要的長篇作品,通過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東北小城呼蘭的風土人情的描寫,真實生動的再現了呼蘭城民眾貧困、卑瑣的生活狀態和麻木愚昧的精神狀態。而她獨特的敘述語言為作品涂上一層迷人的色彩,本文主要探討《呼蘭河傳》兒童化語言的詩意表達。
兒童視角;詩意語言
《呼蘭河傳》是蕭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蕭紅主要以一種童年視角,用孩童般天真稚氣的語言和發散性的兒童思維自然率真的表現記憶中的畫面,將故鄉小城呈現在讀者眼前。正如矛盾所言,它是一部不像小說的小說,“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1]
1 兒童化語言的詩意表達
蕭紅在用兒童化的語言敘事時,將兒童化語言的美感發揮到極致,使作品呈現出詩的特質,無論是敘事性的描述還是繪景抒情,都蘊著淡淡的情思,作品氛圍隨作者心理情緒變幻又統一在回憶思緒之中,實現兒童化語言的詩意表達。穿插在故事之間的“一種富于靈氣的稚拙式”[2]的語言讓人耳目清新,尤其在描寫景物時散發著一種盎然的激情,甚至忽略了故事本身的平淡無奇。如《呼蘭河傳》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抒情性景色描述:“晚飯一過,火燒云就上來了”,“這地方的火燒云變化極多,一會紅堂堂的了,一會金洞洞的了,一會半紫半黃的,一會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黃梨、紫茄子,這些顏色天空上邊都有。”作者對晚霞的描寫如詩如畫,對天空中出現的各種顏色,形狀的變化,以及黃昏時分人們悠然的心情都表現了出來。
另外,蕭紅在小說中還以詩歌的形式直抒胸臆,在各種文體間穿梭自如并實現恰當表達。當夜深人靜的時候,跳大神的鼓聲響起,作者以詩意的語言抒發情感:
“滿天星光,滿屋月亮,人生何如,為什么如此悲涼。”
“跳到了夜靜時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個個都打得漂亮!”
“若趕上一個陰雨的夜,就特別凄涼,寡婦可以落淚,鰓夫就要起來仿徨。”
在跳大神散場后,鼓聲帶著抹涼意一聲聲敲打在人們的心頭。這里作者對人生孤獨、長夜凄涼的描寫,給人一種充滿惶惶與蒼涼的陰郁之美。從每句的末尾“悲涼”、“漂亮”、“彷徨”可以看出,三句單獨成段列出的個人情感抒發,不僅有詩的意境,連語言、節奏、韻律都詩化了。有時作者有意識的采用詩歌的手法結構組織語言,“回環往復”,如在文章第四章中前四小節的首句依次重復為:“我的家是荒涼的”,“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3]。反復的傾訴加強了情感的分量,營造了一種荒涼的氛圍,使讀者首先被一種情緒感染。因此說《呼蘭河傳》既是小說,又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
2 兒童化語言的實現方式
“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十分潛心于語言。他們深知,除了語言,小說就不存在。”[4]《呼蘭河傳》讀起來更像是一篇回憶性質的抒情散文,蕭紅采用兒童化的語言,細膩的筆觸形成了自己的文字格調,產生了獨特的藝術審美效果。“初讀有些生澀,但因其內在力大,還是很能吸引人的。她有時變化詞的用法,雖顯幼稚,但成功之處也就在天真。”[5]《呼蘭河傳》中兒童化語言的實現也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言語組織方式。比較明顯的有以下幾種,分別加以論述。
2.1 反復。文中有很多兒童化思維下產生的非理性認識,作者故意通過詞語的反復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式自我肯定,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耍賴孩童形象躍然紙上。如“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話,就開一個謊話”、“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這里的反復是一個兒童眼中有擬人情態的黃瓜玉米,并對這些黃瓜玉米可以自己隨意控制的生長堅信不疑,產生一種自然的天真情態。又如第三章中“我”表達對《春曉》這首詩的喜愛之情,“覺得這首詩,實在是好,真好聽,“處處”該多好聽。”通過對“好聽”的反復,強調了感受深刻的部分,同時也表現了一個天真孩童的憨態。
2.2 修辭。文中使用大量修辭格,比喻、擬人、夸張、排比、反問、通感等,通過字、句的精細達到描述的鮮活,“至濃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這是蕭紅使用修辭技巧的勝人之處,日常生活的瑣碎,自然景物的平常,經蕭紅妙筆點染清新俊麗,“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通感如“那粉房里的歌聲,就像一朵紅花開在了墻頭上,越鮮明,就越覺得荒涼”,將粉房里的歌聲比作開在墻頭的紅花,為歌聲涂抹上了悲涼之色,并且具體為越鮮明越感到荒涼。
2.3 方言。蕭紅作品中有許多地方十分靈活的使用方言,表現了一種兒童語言的特色。方言對兒童的影響是深刻的,終身難以忘懷,在作者以孩童眼光敘述故事時,各種鮮活的故鄉方言便涌入心頭。文中方言的使用自然貼切,在不造成閱讀障礙的前提下,擴大了語言表現力。如“小驢一到冬天就住在磨房的屋里,那小驢還是照舊的站在那里,并且還是安安敦敦地和每天一樣地麻搭著眼睛。”,“麻搭”一詞表現小驢無精打采,眼睛似睜非睜的狀態,十分形象。
2.4 錯位。蕭紅語言兒童似的稚拙感還來源于詞句語法的刻意不規范,即言語上的錯位,而這種不規范使文本在脫離典雅端莊的傳統審美規范的同時,產生了一種特異的拙樸與新鮮。如“因為馮歪嘴子隔著爬滿了黃瓜秧的窗子,看不見他走了,就自己獨自說了一大篇話,而后讓他故意得不到反響。”兩位主角在談話時發生的代詞混亂值得注意,“實驗表明,兒童在敘述時對靈活的代詞轉換有一定困難,轉換程度越高,理解程度越低”[6]。句子成分脫漏省略,如“有二伯偷了這澡盆之后,就像他偷那銅酒壺之后的(樣子)一樣。”[7]另外,如“祖母一死,家里繼續著來了許多親威。”,此處的“繼續”為“陸續”更為恰當,屬于純粹的用詞不當。
[1] 茅盾:《〈呼蘭河傳〉序》,見《蕭紅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第10頁
[2] 趙園:《論小說十家》,《論蕭紅小說兼及中國現代小說的散文特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第215頁
[3] 文貴良:《呼蘭河傳》的文學漢語及其意義生成,文藝爭鳴,2007/07
[4] 汪曾棋:《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07 第36頁
[5] 《孫犁選集》(理論集),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04 第330頁
[6] 朱曼殊主編.兒童語言發展研究[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7] 趙家新:《視點回指和言語錯位——呼蘭河傳的話語分析》,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陳媛(1992.11—),女,漢族,山東菏澤,在讀研究生,山東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
1206.6
A
1672-5832(2016)05-006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