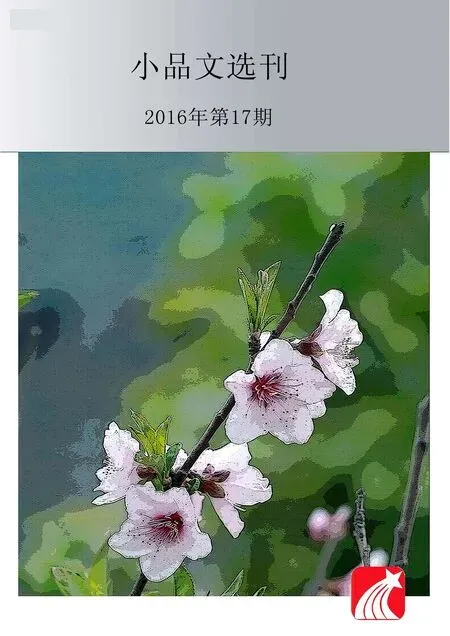大理白族“繞三靈”的旅游化探討
朱 青 張 娟
(云南民族大學藝術(shù)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大理白族“繞三靈”的旅游化探討
朱 青 張 娟
(云南民族大學藝術(shù)學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繞三靈”是大理白族最重要的傳統(tǒng)節(jié)日之一,節(jié)日集中體現(xiàn)了白族多元包容的文化內(nèi)涵,展現(xiàn)了白族長遠悠久的歷史記憶。本文主要以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繞三靈節(jié)日如何在當今社會環(huán)境下更好的存續(xù)下去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旅游化”的口號,即把白族“繞三靈”與旅游化相結(jié)合,以期達到該節(jié)日得以保護和傳承并可獲得一定經(jīng)濟效益的雙贏目的。
白族“繞三靈”;旅游化;保護
白族的“繞三靈”有多種叫法,又稱“繞山林”、“逛山林”等,每年農(nóng)歷二十二至二十五,成千上萬的白族民眾便會自發(fā)的在喜洲附近組織在一起進行本主崇拜儀式,主要的集會地點有:慶洞村的“神都”,河矣城的“仙都”以及馬九邑的本主廟(保安景帝廟)。其中儀式內(nèi)容包括歌、舞、曲,誦經(jīng)等娛神娛人的活動形式。因此,參與人數(shù)之眾多及活動形式之獨特,成為大理白族最為盛大的民間民俗活動,和最具特色的本主崇拜儀式。
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繞三靈”在當今社會也面臨著種種危機,“靜態(tài)”保護與傳承模式慢慢地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狀。因此,為積極尋求白族“繞三靈”的生存模式,將其更好地保護和發(fā)展下去是我們眼下的重中之重。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設(shè)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文化強省”的口號,“繞三靈”作為大理白族的文化標簽,將其旅游化也正是響應了省委省政府的號召。
山東大學王德剛教授在《旅游化生存: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現(xiàn)代生存模式》一文中集中探討了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發(fā)展,并指出非物質(zhì)文化的旅游化生存模式具有兩種形態(tài),一是舞臺化生存——景區(qū)旅游模式;二是生活化生存——社區(qū)旅游模式。舞臺化生存主要是將“繞三靈”進行藝術(shù)加工和深化后呈現(xiàn)在舞臺上,以滿足觀眾游客的審美需求。例如,“繞三靈”活動中的繞三靈調(diào),霸王鞭舞,金錢鼓舞,雙飛燕舞,花柳曲舞以及包括洞經(jīng)會的洞經(jīng)音樂(南詔古樂)等藝術(shù)形式都可作為舞臺化生存進行藝術(shù)化的對象。生活化生存主要是觀眾游客想了解更多有關(guān)白族“繞三靈”的內(nèi)容,以及追求其原真性,便直接到當?shù)厣鐓^(qū)進行感受和體驗,以滿足自身的新奇心理。當然,凡事都具有兩面性,白族“繞三靈”進行旅游化后也不例外。
1 旅游化后的積極與進步意義
將白族“繞三靈”進行旅游化后的積極與進步意義是值得肯定的,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增加當?shù)卣约皡⑴c人群的經(jīng)濟收入,帶動本地區(qū)白族參與的積極性,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繞三靈”能夠得以重構(gòu)與延續(xù),以藝術(shù)化的途徑進行加工后展現(xiàn)出白族新的精神風貌與民族特色,體驗出多元包容的文化內(nèi)涵,也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到白族豐富悠久的繞三靈活動。因此,可以看出“繞三靈”旅游化后的積極與進步意義是可觀的。由此,可以總結(jié)為以下幾點:
第一,前沿意義。白族“繞三靈”進行旅游化必定要與當今社會所處的時代特點相結(jié)合,并很好地把握時代脈搏,了解社會動態(tài),認識發(fā)展規(guī)律后才能尋找出真正適合其存續(xù)和發(fā)展的文化土壤,才能繼續(xù)生根發(fā)芽,這樣也才能體現(xiàn)出其前沿性。
第二,經(jīng)濟意義。旅游會與經(jīng)濟相關(guān)聯(lián),通過對白族“繞三靈”的旅游化過程不僅可以使當?shù)匕鬃迕癖娫黾右欢ǖ慕?jīng)濟收入,也會使當?shù)亟?jīng)濟得到一定的發(fā)展;而且此儀式也得到了保護和傳承。
第三,進步意義。白族“繞三靈”旅游化后會更多的民俗文化和藝術(shù)愛好者對此關(guān)注,影響范圍將會進一步擴大;其次,經(jīng)濟效應也會讓更多的白族青年自覺地參與進來,不至于出現(xiàn)參加“繞三靈”儀式群體的老齡化問題;最后,更會進一步鞏固他們的民族情感,增強他們的民族自豪感,讓他們的緊緊地團結(jié)在一起。
2 旅游化后所帶來的問題
“繞三靈”之所以旅游化是為了避免其在當今社會消失的可能性,以及得到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如果旅游化過度的話,會造成文化意義和內(nèi)涵的變異,反而影響其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由此,在旅游化后難免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
第一,原真性問題。金錢鼓舞、繞三靈調(diào)等“繞三靈”特有的藝術(shù)形式為迎合觀眾的審美需求,會經(jīng)過藝術(shù)的加工和提煉從而進行舞臺化展演,舞臺展演的藝術(shù)形式會被觀眾和文化消費者認為是“超真實”的儀式形態(tài)。由此超真實成了評判真實的標準和原則,真實就受到了超真實的影響和制約,而真實就會慢慢遠去,傳統(tǒng)的白族“繞三靈”也會隨之失去其原真性。
第二,情感歸屬問題。白族人的情感維系始終是對本主的虔誠信仰,經(jīng)旅游化后會導致傳統(tǒng)的白族“繞三靈”變成一種純粹以盈利為目的的活動形式。由此,“繞三靈”儀式也將會從其“神圣性”轉(zhuǎn)變?yōu)椤笆浪仔浴保瑫r間久之便會潛移默化地使白族人的意識思維里面淡化對本主的神圣性信仰,情感歸屬的意識也將會隨之慢慢減弱。
第三,傳統(tǒng)意義喪失問題。傳統(tǒng)的白族“繞三靈”歷史悠久,內(nèi)容豐富,意義深遠,是白族民眾對本主進行崇拜和祭祀的一種莊重儀式,歌、舞、曲等白族“繞三靈”中特有的藝術(shù)形式也主要伴隨著娛神的目的而產(chǎn)生。經(jīng)過旅游化后的“繞三靈”主要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和觀眾的文化藝術(shù)需求,從而將傳統(tǒng)意義的繞三靈活動中特有的藝術(shù)符號進行了現(xiàn)代藝術(shù)理念的裝扮,體現(xiàn)出當今社會所流行的藝術(shù)要素。由此,具有傳統(tǒng)意義的白族“繞三靈”儀式由對本主的崇拜和祭祀轉(zhuǎn)變?yōu)閷οM者與觀眾審美心理的迎合。
3 結(jié)論
作為國家首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白族”繞三靈“對于國家和政府來講,需要制定更多的法律政策來進行保護,使得白族”繞三靈“儀式得以更好地延續(xù);對于整個白族群體來講,要以本民族文化為榮,盡自己的努力去保護和傳承,使其永久地成為本民族的文化符號;對于社會個人來講,都應該積極地去認識和宣傳。然而,無論是國家、本族、還是個人所做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避免“繞三靈”消逝和遠去,能夠使其得以被保護和傳承。通過將其旅游化的方式在當今社會是普遍流行的保護和傳承模式,因為這樣既可以獲得客觀的經(jīng)濟效益,又可以使其得到很好地保護和延續(xù),以此達到雙贏的目的。但又不得不考慮其文化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在旅游化過程中又需要注重其文化特點,把握其文化規(guī)律,盡快地找到適合其生存的文化沃土,更好的適應當今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狀,以此得到永遠保護和傳承。
[1] 張曉萍,李鑫.旅游產(chǎn)業(yè)開發(fā)與旅游化生存——以大理白族繞三靈節(jié)日開發(fā)為例[J].經(jīng)濟問題探索,2009年12期
[2] 王德剛,田蕓.旅游化生存: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現(xiàn)代生存模式[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10年01期
[3] 吳興幟.遺產(chǎn)的抉擇——文化旅游情境中的遺產(chǎn)存續(xù)[M].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2月
朱青(1991.08-),男,河南許昌人,云南民族大學藝術(shù)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藝術(shù)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張娟(1991.04-),女,湖南懷化人,云南民族大學藝術(shù)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少數(shù)民族電影。
K892.2
A
1672-5832(2016)05-01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