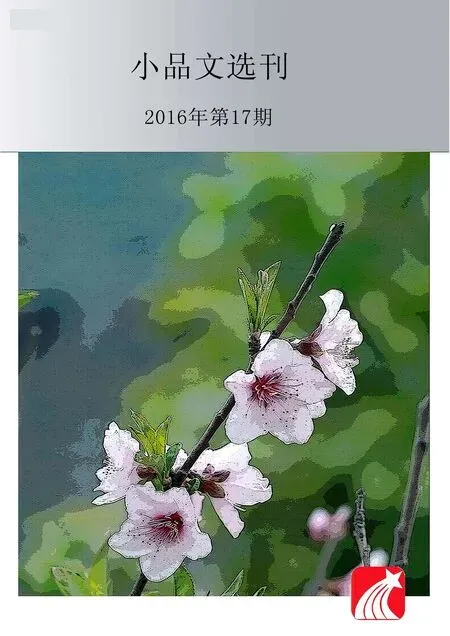農(nóng)民工對(duì)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影響研究文獻(xiàn)綜述
史 璇
(云南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與政法學(xué)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農(nóng)民工對(duì)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影響研究文獻(xiàn)綜述
史 璇
(云南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與政法學(xué)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近年來(lái)農(nóng)民工和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已經(jīng)成為學(xué)術(shù)界的熱點(diǎn),在流動(dòng)背景下,農(nóng)村治理表現(xiàn)出一定的困境。學(xué)術(shù)界在對(duì)這一困境進(jìn)行總結(jié)的基礎(chǔ)上挖掘其中的原因,并提出相關(guān)建議對(duì)策。但是近年來(lái)的研究系形成的理論性成果不足,研究的針對(duì)性不夠,具體路徑探索以及對(duì)流出地治理的研究的成果較少,因此以上幾個(gè)方面的研究還需要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
農(nóng)民工;農(nóng)村治理;綜述
導(dǎo)論
農(nóng)民工問(wèn)題和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問(wèn)題是近年來(lái)農(nóng)村社會(huì)學(xué)界比較關(guān)注的話題。外出務(wù)工農(nóng)民的產(chǎn)生是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礎(chǔ)之上,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特別是90年代以后,農(nóng)民流動(dòng)的浪潮逐漸擴(kuò)大,農(nóng)民工在工具合理性的指導(dǎo)下“離土離鄉(xiāng)”,以獲得更多的經(jīng)濟(jì)收益。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要求處理好政府、社會(huì)組織以及農(nóng)民之間的關(guān)系,同時(shí)在三種主體的聯(lián)合作用下推動(dòng)農(nóng)村社會(huì)保障、農(nóng)村環(huán)境以及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各方面的建設(shè)。農(nóng)民工作為農(nóng)民的重要組成部分,給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帶來(lái)重要的影響。
農(nóng)民工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他在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從宏觀層面上看就是從政治的角度對(duì)農(nóng)村的各種資源進(jìn)行分配應(yīng)用,因此農(nóng)民工在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用政治參與這一維度進(jìn)行表達(dá),農(nóng)民工的政治參與對(duì)農(nóng)村的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早在世紀(jì)初,華中師范大學(xué)徐勇教授就主張把農(nóng)民工納入有序政治參與中來(lái)。[1]他認(rèn)為農(nóng)民工在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意識(shí)以后就會(huì)在在行動(dòng)中表達(dá),一旦沒(méi)有正確有序的路徑,農(nóng)民工就會(huì)選擇沉默,而沉默帶來(lái)的后果如果從隱性變?yōu)轱@性,則會(huì)造成不必要的甚至巨大的社會(huì)損失。改革開(kāi)放以后,村民自治成為農(nóng)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新時(shí)期在村民自治的基礎(chǔ)上,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逐漸出現(xiàn)在學(xué)者的視野中;從微觀上看,不同的農(nóng)村在自治模式的選擇上由于不同的背景選擇的不同。本文將從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現(xiàn)象對(duì)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造成的影響為視角,對(duì)這一研究主題進(jìn)行文獻(xiàn)綜述。從宏觀上把握研究的現(xiàn)狀,從而指導(dǎo)研究的進(jìn)行。
1 農(nóng)民工給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帶來(lái)的影響
農(nóng)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給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帶來(lái)了積極影響,同時(shí)也帶來(lái)了一些問(wèn)題。在利用積極影響進(jìn)行治理的過(guò)程中,也要解決流動(dòng)帶來(lái)的困境,以便形成發(fā)展。
1.1 農(nóng)民工給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帶來(lái)的積極影響
農(nóng)民工帶著對(duì)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追求,流入經(jīng)濟(jì)相對(duì)發(fā)達(dá)的地區(qū),在提供充足勞動(dòng)力,促進(jìn)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同時(shí),自己也獲得了較大的經(jīng)濟(jì)收益,并且擴(kuò)充了視野反過(guò)來(lái)帶動(dòng)流入地的發(fā)展。徐勇指出,農(nóng)民流動(dòng)不僅帶來(lái)了人地矛盾的緩解,而且加速了資本積累,提升了人口素質(zhì),帶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shí)帶動(dòng)了流入農(nóng)村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2]此外袁書(shū)華、賈玉潔、付妍從城市和農(nóng)村兩個(gè)角度論述了新生代農(nóng)民工帶來(lái)的積極意義。對(duì)于城市來(lái)說(shuō),農(nóng)民工壯大并更新了產(chǎn)業(yè)大軍,加快了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同時(shí)促進(jìn)相關(guān)政策的改進(jìn)和支撐城市的運(yùn)行;對(duì)于農(nóng)村來(lái)說(shuō),農(nóng)民流動(dòng)的發(fā)生解決了農(nóng)村剩余勞動(dòng)力問(wèn)題,返鄉(xiāng)農(nóng)民工成為農(nóng)村脫貧致富的主力軍,同時(shí)為農(nóng)村的發(fā)展注入新活力。[3]最后,楊文芬在她的碩士畢業(yè)論文中講到農(nóng)村中人口流動(dòng)帶來(lái)的新氣象除了增加收入,促進(jìn)思想解放外,還能夠帶動(dòng)新型能人的產(chǎn)生,社會(huì)治安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善以及緩和干群關(guān)系的作用。[4]美國(guó)政治學(xué)家亨廷頓認(rèn)為流動(dòng)可以消除社會(huì)頹廢。對(duì)于農(nóng)村村民來(lái)說(shuō),橫向的流動(dòng)增加了獲得經(jīng)濟(jì)利益的機(jī)會(huì),就從某種程度上減輕或者消除了原來(lái)存在于農(nóng)村的尋釁滋事、小偷小摸行為,維護(hù)了農(nóng)村社會(huì)治安的穩(wěn)定。
1.2 農(nóng)民工給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帶來(lái)的消極影響
1.2.1 對(duì)流出地的村治帶來(lái)的困境。
民主選舉是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由村民自己直接選舉或者罷免村委會(huì)干部。它是進(jìn)行村民自治的基礎(chǔ)條件。民主選舉針對(duì)的是全村具有選舉資格的村民,但是農(nóng)民工群體的外流,造成的后果是村民自治無(wú)人治。[5]此外,王水現(xiàn)在他的碩士論文中寫(xiě)道對(duì)于流出地的民主選舉來(lái)說(shuō),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xiàn)為農(nóng)民工的流動(dòng)降低了民主選舉的質(zhì)量,同時(shí)由于選民的流失,候選人的范圍相對(duì)縮小,降低了選舉結(jié)果的質(zhì)量。同時(shí)由于剩余的部分村民多數(shù)是婦女和老人,因此民主決策也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不科學(xué)。[6]
對(duì)于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來(lái)說(shuō),民主管理的目的在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wù),民主監(jiān)督的目的在于村務(wù)公開(kāi),把村干部的評(píng)議權(quán)和知情權(quán)交給村民。但是現(xiàn)階段對(duì)于民主管理來(lái)說(shuō),管理主體的弱化或者喪失以及民主管理的客體更加復(fù)雜。民主監(jiān)督的困境在于監(jiān)督動(dòng)機(jī)的弱化以及降低約束力。[7]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做的不夠會(huì)影響資源和物品的配置效率,影響留守人群的社會(huì)福利,降低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配置效率。[8]
1.2.2 對(duì)流入地的村治帶來(lái)的困境
從民主選舉的角度來(lái)看,對(duì)于流入地來(lái)說(shuō),外來(lái)人員又很難參與到村民自治中來(lái)。鄉(xiāng)村社會(huì)的內(nèi)在束縛和外部排斥,使得具有選民資格的農(nóng)民工參與不到本地的民主選舉。[9]除此之外,從國(guó)家的角度來(lái)講,憲法以及村委會(huì)組織法規(guī)定,農(nóng)民工可以參加戶口所在地的民主選舉,對(duì)于流入地來(lái)說(shuō),農(nóng)民工沒(méi)有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依據(jù)。幾年來(lái)國(guó)家適應(yīng)發(fā)展的需要對(duì)此進(jìn)行了初步調(diào)整,各地區(qū)也在不斷創(chuàng)新農(nóng)民工的政治參與模式。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的政治參與,相關(guān)的研究還是比較多的,對(duì)于流入地來(lái)說(shuō)參與流入地的選舉是農(nóng)民工政治參與的第一步,做好這一步民主決策、管理、監(jiān)督才有了基礎(chǔ)。但是農(nóng)民工參與流入地的民主選舉存在著原始性的障礙性因素:認(rèn)知觀念、利益制約、社會(huì)支持、法理操作以及戶籍等層面。[10]
2 面對(duì)困境的對(duì)策
農(nóng)村的發(fā)展,離不開(kāi)治理的引導(dǎo),面對(duì)農(nóng)民的流動(dòng)產(chǎn)生的困境,不同的學(xué)者深入農(nóng)村實(shí)地調(diào)查,以獲得關(guān)于農(nóng)村治理的第一手資料,并且根據(jù)自己的學(xué)術(shù)積累,經(jīng)驗(yàn)積累,對(duì)存在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據(jù)農(nóng)村的現(xiàn)實(shí),趙樹(shù)凱指出鄉(xiāng)村問(wèn)題的解決遵循兩個(gè)原則:鄉(xiāng)村問(wèn)題內(nèi)部化和鄉(xiāng)村問(wèn)題社會(huì)化。[11]
面對(duì)困境,陸益龍認(rèn)為,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的困境主要是由流動(dòng)者的不確定預(yù)期影響機(jī)制、社會(huì)阻隔機(jī)制和慣性作用機(jī)制等造成的,解決這些問(wèn)題,要著力把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制度轉(zhuǎn)移與農(nóng)村“留住機(jī)制”的建構(gòu)結(jié)合起來(lái)。[12]另外,劉於清和陳朋分別從流出地和流入地為基本角度提出具體建議解決困境。前者針對(duì)流出地的基本狀況,提出四點(diǎn)去解決流動(dòng)背景下新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出路:培養(yǎng)農(nóng)民參與公共事務(wù)的熱情;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shí)現(xiàn)形式;挖掘新農(nóng)村建設(shè)新型管理者;關(guān)注農(nóng)村社區(qū)“留流”人群,彰顯人文關(guān)懷。[13]陳朋則主要從:構(gòu)建協(xié)商溝通機(jī)制;完善社區(qū)治理機(jī)制;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創(chuàng)新選民登記機(jī)制等四個(gè)方面的措施來(lái)解決流動(dòng)中流入地社區(qū)選舉帶來(lái)的困境。
3 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具體路徑
農(nóng)民工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但是農(nóng)村社區(qū)是農(nóng)民工的棲身地。不管是流入地還是流出地,農(nóng)民工作為產(chǎn)業(yè)大軍的主題力量,都在影響著社區(qū),因此社區(qū)治理離不開(kāi)農(nóng)民工的參與。
首先,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需要有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王道勇主張研究農(nóng)民工要強(qiáng)調(diào)農(nóng)民工的主體地位,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以及農(nóng)村社區(qū)的發(fā)展需要在一種“共融性社會(huì)”中展開(kāi),它指的是不同的社會(huì)群體互相溝通,消除歧視,彼此尊重的和諧社會(huì),其目標(biāo)是共融基礎(chǔ)上的共贏共生。[14]其次,參與的主體地位。劉小年從主體的視角出發(fā)來(lái)解決農(nóng)民工的政治參與問(wèn)題,尊重農(nóng)民工的意愿,按照農(nóng)民工社會(huì)分層形成的條件,漸進(jìn)發(fā)展走城鄉(xiāng)統(tǒng)籌的道路。按照農(nóng)民工的意愿有條件的將一部分完全納入城市治理;一部分參與鄉(xiāng)村治理;一部分參與特定內(nèi)容的城市治理;大部分根據(jù)其利益在城鄉(xiāng)程度不等的政治參與。[15]最后,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具體路徑分析。針對(duì)流入地的特殊情況,陳亞輝結(jié)合廣州中山市農(nóng)村的具體經(jīng)驗(yàn)提出了農(nóng)民工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路徑選擇,從利益相關(guān)者的視角出發(fā),考察村特別委員制度。外來(lái)農(nóng)民工作為村特別委員參與村(居)治理的原因在于這一群體與本地村民之間存在利益相關(guān)性,同時(shí)他提出政府、基層黨組織、社區(qū)自治組織以及非傳統(tǒng)治理主體的協(xié)商意愿、信任關(guān)系及制度平臺(tái)構(gòu)建是社區(qū)利益相關(guān)者合作治理的關(guān)鍵。[16]
4 總結(jié)
農(nóng)民工作為重要組成部分,應(yīng)該在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現(xiàn)階段的研究成果雖然比較豐富,但是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的問(wèn)題。
首先,理論成果不足,針對(duì)性不強(qiáng)。現(xiàn)階段對(duì)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研究催生了一定理論成果的誕生,例如以徐勇教授為代表的政治學(xué)理論,以賀雪峰教授為代表的農(nóng)民行動(dòng)單位理論,以及由村民自治到社區(qū)自治理論等等,都為農(nóng)村治理提供了理論支持。這些理論的誕生是研究者深入基層,深入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成果,深刻體現(xiàn)了現(xiàn)階段我國(guó)學(xué)者的人文關(guān)懷精神。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現(xiàn)階段的理論成果并不豐富,不能夠完全反映不同的地區(qū)狀況,因此還需要學(xué)者們孜孜不倦的努力爭(zhēng)取獲得更大的收獲,為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提供理論指導(dǎo)。
其次,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路徑選擇有限。現(xiàn)階段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參與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的研究較多,但是多數(shù)是從流動(dòng)的背景出發(fā),探討流動(dòng)帶給農(nóng)村社會(huì)治理的影響,而對(duì)于農(nóng)民工在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中的作用方式路徑選擇研究較少。學(xué)者們提出的對(duì)策并不能夠給農(nóng)民工或者村莊治理者帶來(lái)具體的、可操作性的具體路徑,因此筆者建議應(yīng)結(jié)合研究成果,實(shí)現(xiàn)參與路徑研究的繁榮。
最后,對(duì)農(nóng)民工與流出地農(nóng)村治理研究的關(guān)注度不夠。現(xiàn)階段學(xué)者關(guān)注流入地農(nóng)村的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常態(tài),對(duì)流入地農(nóng)村治理的關(guān)注度明顯高于流出地。對(duì)文獻(xiàn)資料進(jìn)行了解發(fā)現(xiàn),21世紀(jì)的前十年,相關(guān)的研究還是有一些的,但是最近幾年的研究就相對(duì)較少了。由于村莊呈現(xiàn)松散化狀態(tài),農(nóng)民工在參與流出地農(nóng)村治理中的作用基本上很難發(fā)揮,只能靠返鄉(xiāng)的農(nóng)民工中精英的能力發(fā)揮有限作用。因此村莊內(nèi)農(nóng)民工這個(gè)群體作用的發(fā)揮對(duì)于村治來(lái)說(shuō)意義重大。雖然有學(xué)者提出根據(jù)農(nóng)民工的意愿,一部分農(nóng)民工有條件的參與流出地農(nóng)村治理,并提出作用平臺(tái)建設(shè)。關(guān)于流出地治理的路徑研究基本上沒(méi)有形成系統(tǒng),因此需要將相關(guān)的研究繼續(xù)鋪開(kāi)。相對(duì)于流入地,流出地農(nóng)村普遍較為貧困,因此對(duì)農(nóng)民工在流出地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刻不容緩,關(guān)系到貧困人口的減少和農(nóng)村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
[1] 徐勇 把農(nóng)民工納入有序政治參與中 農(nóng)村工作通訊 2010.2。
[2] 徐勇 徐增陽(yáng) 流動(dòng)中的鄉(xiāng)村治理[M]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2003。
[3] 袁書(shū)華、賈玉潔、付妍 新生代農(nóng)民工問(wèn)題研究[M]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
[4] 楊文芬 農(nóng)村人口流動(dòng)對(duì)鄉(xiāng)村治理的影響研究[D]西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2012.
[5] 李增元 村民自治到社區(qū)自治[M]山東人民出版社 2014。
[6] 王水現(xiàn) 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和出路[D]蘇州大學(xué)碩士論文 2010。
[7] 王水現(xiàn) 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和出路[D]蘇州大學(xué)碩士論文 2010。
[8] 陸益龍 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及其社會(huì)影響[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15.1。
[9] 李增元 集體產(chǎn)權(quán)與封閉鄉(xiāng)村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社會(huì)流動(dòng)背景下的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J]甘肅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14.3。
[10] 陳朋 流動(dòng)中的社區(qū)選舉:現(xiàn)實(shí)困境及釋困機(jī)制[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xué)報(bào) 2012.11。
[11] 趙樹(shù)凱 農(nóng)民的新命[M]商務(wù)印書(shū)館 2012.
[12] 陸益龍 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及其社會(huì)影響[J]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15.1。
[13] 劉於清 社會(huì)流動(dòng)背景下新型農(nóng)村社區(qū)治理困境與出路[J]荊楚學(xué)刊 2014.10.
[14] 王道勇 農(nóng)民工研究范式:主體地位與發(fā)展趨向[J]社會(huì)學(xué)評(píng)論 2014.4.
[15] 劉小年 農(nóng)民工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機(jī)制研究:主體的視角[J]寧夏社會(huì)科學(xué) 2010.3.
[16] 陳亞輝 利益相關(guān)者臺(tái)作:農(nóng)民工參與社區(qū)治理的路徑選擇[J]社會(huì)主義研究 2015.3.
史璇(1989-),男,漢,河南夏邑人,研究生,云南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與政法學(xué)院,研究方向:發(fā)展社會(huì)學(xué)。
f291.1
A
1672-5832(2016)05-015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