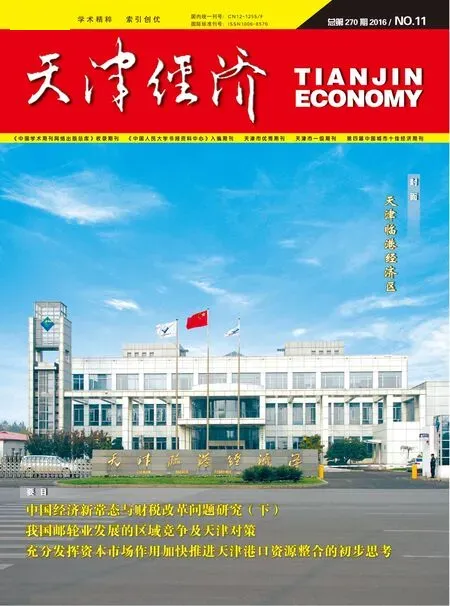中國經濟新常態與財稅改革問題研究(下)
◎文/安體富
中國經濟新常態與財稅改革問題研究(下)
◎文/安體富
2016年6月27日,安體富教授在天津市經濟發展研究院做了題為“中國經濟新常態與財稅改革問題研究”的演講。本文根據安體富教授的講稿整理而得,未經本人審閱。因內容較多,分兩期刊登,本期刊登下半部分。這部分主要研究以下三個問題:加快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深化稅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稅收制度體系。
財稅改革;預算制度;轉移支付
三、深化財稅改革,適應與促進新常態的實現
(一)加快構建現代財政制度
1.建立現代政府預算管理制度,實行“陽光財政”
現代政府預算制度是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礎。預算編制科學完整、預算執行規范有效、預算監督公開透明,三者有機銜接、相互制衡,是現代預算管理制度的核心內容。當前,應重點推進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設。
(1)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預算執行結果有別于預算預期的平衡狀態將成為常態,特別是年度預算赤字可能突破。要進一步嚴格規范超收收入的使用管理,原則上不安排當年支出。年度預算執行超赤字,要建立跨年度彌補機制。若要實現跨年度預算平衡,還應該抓緊研究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增強財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財政可持續性。
(2)實施全面規范的預算公開制度。借鑒國際經驗,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注重頂層設計,明確實施步驟,積極穩妥地推進預算公開。逐步擴大公開范圍,細化公開內容,不斷完善預算公開工作機制,強化對預算公開的監督檢查,逐步實施全面規范的預算公開制度。
2.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1)我國轉移支付制度的
現狀與問題。中央轉移支付規模現狀:2013年中央財政支出69560億元,其中,中央本級支出20703億元,占比29.8%;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48857億元,占比70.2%。出現的問題是:中央本級支出與向地方轉移支付之間的比例為30∶70,比例過于失衡,很不合理,導致了轉移支付成本增加,效率損失過大。
(2)中央轉移支付結構。2013年一般性轉移支付24538.4億元,占比48.9%,大于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占比;稅收返還 5052.8億元,占比10.1%;原體制補助1274.5億元,占比2.5%。出現的問題是:一是稅收返還與原體制補助屬于維護既得利益,不符合公平原則,很不合理;二是專項轉移支付比重過大。
(3)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現狀:2013年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9812.3億元,占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40%,占轉移支付總規模19.6%。出現的問題是: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占轉移支付總規模的比重過低,只有20%,難于發揮彌補地方收支差距和實現均等化的作用。
(4)關于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幾點想法。
第一,調整中央財政支出中,中央本級支出與轉移支出之間的比例關系。可否調整為70∶30,或60∶40。
措施:一是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將義務教育、醫療衛生與社會保障等的相應事權與支出責任上調由中央政府承擔;二是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地方政府支配的財力。
第二,調整中央轉移支付結構。科學界定轉移支付分類中的概念,如:一般性轉移支付、均衡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財力性轉移支付等,其內涵和外延現在定義不清楚。
我國一般性轉移支付數易其名,1995年稱 “過渡期轉移支付”;2002年改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原來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改稱“財力性轉移支付”;2009年改為“均衡性轉移支付”,原來的“財力性轉移支付”改為“一般性轉移支付”;2011年財政部收支科目分類中又改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原來的 “一般性轉移支付”改為“均衡性轉移支付”。
轉移支付按其性質可分為三大類:均衡性轉移支付(公式化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和政策性轉移支付。
均衡性轉移支付,用于彌補地方收支差額,應占到轉移支付總量的70%以上;地方收支差額的90%,應通過上級轉移支付予以彌補。
專項轉移支付,其規模不能過大,項目不能過多。目前一般性轉移支付有22項,除其中的均衡性轉移支付外,其余的21項,就其性質都屬于專項轉移支付,加上現有的專項轉移支付22項,合計共43項。到了下面項目更多,例如,江西省太和縣,2010年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達到129個,名稱五花八門,總額50萬元以下的項目近70個,資金最少的項目只有1000元。
專項轉移支付的范圍:一是中央委托地方的項目;二是重大的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三是外溢性的項目,如禁止開發地區的項目。
應成立專門委員會,討論審查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應進行效益評估。
政策性轉移支付,是指中央采取宏觀調控政策時進行的轉移支付項目,如2009年4萬億元投資項目。政策性轉移支付項目,在政策取消時,這些項目應隨之取消。
現行的稅收返還、原體制補助和結算補助,應予取消。還應建立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3.改革財政支出管理,優
化財政支出結構
(1)清理規范重點支出掛鉤機制。據統計,目前與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的重點支出涉及教育、科技、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社保、計劃生育等七類,2012年僅財政安排的這七類重點支出即占全國財政支出的48%。
支出掛鉤機制,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僵化,肢解了各級政府預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這也是造成專項轉移支付過多、預算管理無法全面公開、資金投入重復低效的重要原因。
(2)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支出有步驟地退出一般生產性競爭領域,轉向公共需要領域,解決其職能的“缺位”、“越位”問題。
財政支出重點應該是支持我國城鎮化的建設以及保證基本公共服務,因此必須加大對城鎮基礎設施、教育、衛生、醫療、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需求的投入,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繼續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扶持力度,實現農民就地就業等社會目標;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稅式支出;適當降低經濟建設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重,減少對國有企業虧損的補貼。
同時,引入PPP模式,卸掉財政資金背負的“重負”,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調動社會資本并發揮各自優勢,解決城鎮化的資金需求。
(3)加強財政支出的績效管理,提高財政支出使用效益。
(4)建立財政風險基金,及時防范和控制財政風險。財政風險基金的來源構成可考慮:一是參照總預備費的提取方法,在財政支出中按一定比例列支;二是上年度尚未運用的總預備費;三是其他來源。該風險基金和財政后備基金可共同構筑起財政安全的保護屏障。
(二)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
1.合理劃分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
一是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關系全國政令統一、維護統一市場、促進區域協調、確保國家各領域安全的重大事務集中到中央,減少委托事務,以加強國家的統一管理,提高全國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二是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將具有地域管理信息優勢但對其他區域影響較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
三是明確區域性公共服務為地方事權。將地域信息性強、外部性弱并主要與當地居民有關的事務放給地方,調動和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更好地滿足區域公共服務的需要,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四是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
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承擔中央事權的支出責任,地方承擔地方事權的支出責任,中央和地方按規定分擔共同事權的支出責任。
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支付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
根據事權和支出責任,在法規明確規定前提下,中央對財力困難的地區進行一般性轉移支付。
省級政府也要相應承擔起均衡區域內財力差距的責任,建立健全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
2.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要根據稅種屬性特點,遵循公平、便利和效率等原則,合理劃分稅種。
將收入周期性波動較大、
具有較強再分配作用、稅基分布不均衡、稅基流動性較大、易轉嫁的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將其余具有明顯受益性、區域性特征、對宏觀經濟運行不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稅種劃為地方稅,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以充分調動兩個積極性。
(三)深化稅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稅收制度體系
1.優化稅制結構,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
第一,當前我國稅制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影響
目前我囯稅制結構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直接稅比重偏低,間接稅比重偏高,我國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例,大體上是 “三七開”,即直接稅占30%,間接稅占70%。
2013年,來自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與車輛購置稅等間接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為64.1%,除此之外還有關稅、城建稅等一些稅種,加總接近七成,而所得稅僅占25.3%。
與國外比較,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均以直接稅為主體。
2012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美國為 82.2∶17.8;日本為81.3∶18.7;法國為69.6∶30.4;英國為 66.7∶33.3;OECD國家平均為 56.8∶44.2(2009年)。
發展中國家則情況有所不同,其中金磚四國中:南非為59.9∶40.1;巴西為51.9∶48.1;俄羅斯為 43.9∶56.1;印度為36∶64。
可以看出,就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直接稅比重明顯偏低,間接稅比重偏高。
第二,稅制結構失衡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良影響
商品稅屬于生產稅包含在價格之中,稅負過重會干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這也是企業感到稅負重的一個重要因素,從而影響企業的盈利水平和居民工資與收入的提高,還會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其處于不利地位。
間接稅對貧富差距會產生逆向調節。這是因為,間接稅最終是由消費者承擔,而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恩格爾系數相差巨大,窮人的恩格爾系數要大大高于富人,從而窮人購買消費品中承擔的稅負與其收入相比,要大大重于富人。這必然會加劇貧富差距。

表7 OECD成員國稅收收入結構變化(%)
在目前我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間接稅比例過高,會鼓勵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追求GDP,而不是提高經濟效益和居民收入,從而不利于經
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間接稅與價格捆綁在一起,會抬高價格水平,容易引起通貨膨脹。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而具有調節職能的直接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目前在稅收收入中占比很低(5.9%),居民財產稅基本處于缺位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這就要求,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部署,通過深化稅收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
如果將社會保障稅加入稅制結構中,目前我國的稅制結構已是雙主體結構,即使如此,仍應提高直接稅比重。
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是可能實現的。《決定》明確提出,這一次深化稅制改革要以“穩定稅負”為前提,在此前提下,主要進行稅制內部結構的優化調整,即在降低間接稅比重的同時,“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這需要通過稅種的合理配置與改革來實現。
2.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即“營改增”
“營改增”,是當前我國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重頭戲”,是減少間接稅比重的最主要舉措。
根據試點行業2013年直接減稅規模(1402億元)測算,估計,若按全行業實行“營改增”計算,大概減稅在5000億元左右。
在“營改增”全面完成之后,按照《決定》的要求,將進一步“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減化稅率”。同時,會伴隨著稅率的相應下調,再考慮到逐步將不動產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減稅規模將達到1萬億元左右。這必然會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負水平。
“營改增”的減稅效應,將為提高直接稅比重,提供巨大空間。
3.消費稅改革
現行消費稅制度存在征收范圍較窄、課稅環節單一且靠前、稅基偏小、稅率結構欠合理等問題,對消費行為調控作用總體偏弱,迫切需要進行改革。
消費稅改革的重點: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適當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將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產品以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等納入征稅范圍;調整征收環節,弱化政府對生產環節稅收的依賴,促進解決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問題,努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調整部分稅目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的調節作用。
4.個人所得稅改革
為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可作以下幾方面改革:
第一,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納模式,可先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和稿酬所得納入綜合課征,以后再逐步擴大,其他所得仍實行分類課征。
第二,合理確定費用扣除標準。目前實行的單一的、“一刀切”的費用扣除標準,不考慮不同納稅人家庭的負擔情況,有違公平,今后應將老人贍養費用、子女撫養費用、無收入配偶費用、殘疾人撫養費用等,逐步納入費用扣除標準之中。
另外,應區別納稅人收入的不同情況,實行有差別的費用扣除標準。例如,當富人的年收入達到一定高的水平時,可以降低或取消扣除費用標準,以發揮其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
第三,加強對個人收入的監控。目前我國個稅收入占比低,主要是對富人收入的真實情況不掌握,據胡潤《財富》雜志在2011年的財富報告中顯示的中國內地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人數及其消費情況,據
此匡算,我國富人的年收入應在10萬億元左右,假定實際稅率按20%計算,可征稅2萬億元,占當年我國全部稅收收入的20%左右。
為解決這一問題,應加快社會信息制度建設,加強對個人收入的監控。借鑒囯際經驗,主要有這樣幾條:
一是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納稅人永久單一稅號,個人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及財產等方面的信息都應歸入其中;
二是大力推行非現金結算,加強現金管理,嚴格控制現金交易;
三是普遍實行聯網制度,建立稅務網絡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企業、商店、工商、房管、證券、海關、公安等網絡的對接。這是最大限度地掌握納稅人信息的關鍵。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個人收入來源不透明的問題。
5.房產稅改革
目前我國的房產稅僅對經營性房產征收,對個人所有非營業用房產免稅,這使得房產稅規模很小,難于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
2012年,房產稅收入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1.4%,占地方稅收總額的2.9%,這與目前我國的巨大房產規模,極不相適應。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從“六五”到2012年,全國房屋竣工面積559億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面積387億平方米,據此,按當年全國平均房價(6000元/平方米),稅率假定為1%,然后,減半征收,則可征房產稅16770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16.7%,占地方稅35.4%;其中,住宅可征房產稅11610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11.5%,占地方稅24.5%。
可見,從長遠看,房產稅具有很大潛力。
房產稅的改革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開征房地產稅,涉及千家萬戶,會直接增加居民、特別是富人的稅收負擔,為減少阻力使改革順利進行,應采取逐步推進的政策。應先立法,后改革。改革的順序,可考慮實行:先城市,后農村;先營業用房地產,后居民住宅;先豪宅,后普通住宅等等。
二是,房地產稅應貫徹公平原則。從理論和國際實踐上說,現代房地產稅是建立在受益稅的理論基礎之上,所以在大多數國家是對房屋普遍開征的稅種。從試點經驗教訓上看,滬渝兩市的房產稅(除了重慶獨棟別墅外)都是對增量房征稅,不但稅收收入規模有限,也弱化了房產稅的其他功能。因此,基于以上理由,未來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應為除了公益性房地產之外的大部分房地產。
三是,在扣除標準的設計方面,應貫徹不增加或少增加普通居民稅收負擔的原則。扣除標準,可實行按住宅套數和人均住房面積兩種辦法,由居民自行選擇。根據目前我國的住房情況,建議對第一套住宅免稅,第二套住宅減稅,對三套以上住宅全額征稅。按人均住房面積作為扣除標準的話,考慮到目前我國人均住房面積為30多平方米的狀況,可選擇人均50平方米的扣除標準(可規定一個20%的上下浮動幅度,由各地區自行選擇),這與按上述住宅套數的扣除標準大體相當。
四是,稅率設計的問題。稅率是影響稅負水平的重要因素。國際房地產稅平均稅率在1%~2%之間,從稅收組織收入和調節貧富差距及住房供求的作用看,我國普通住宅征稅稅率應不高于1%,對別墅、高檔公寓、多套房產和空置房地產可以考慮提高稅率到3%,未來如果對農村房地產征稅應考慮低稅率,如0.5%。
五是,稅收優惠的設計的問題。借鑒國際經驗,可包括以下內容:
政府部門、慈善機構、教育機構等公益性房地產;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如盲人、老人、殘疾人等自住的房地產等,實行直接減免稅。
當房地產稅稅額占收入達到一定比例時,則應予減免稅額,即“斷路器”原理,用來解決房地產稅的稅基 (房價)與稅源(收入)不一致的問題,保護低收入者的正常生活。
對一些特殊人群,實行稅收救助措施。例如,對一些高干和離退休老干部,用現有工薪收入不足以繳納稅款的,可實行延遲繳稅,待病故后,再結合遺產清理,補繳稅款。
六是,建立稅收保全措施的問題。在國外,由于房產位置固定,不易移動,信息透明,加之房產稅的受益原則,因此,通常征稅成本低,不易偷漏稅。在我國,由于社會條件不同,法制不健全,納稅人遵從度較低,房地產稅直接面對千家萬戶,在此情況下,如何完善征管制度,建立稅收保全措施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可以考慮,將房地產稅的繳納,納入社會信用體系,對欠繳和不繳納稅款的納稅人,將其列入不良信用名單,使其在出國、經商、轉移資產、辦證等社會經濟活動中受到一定限制。
6.資源稅改革
(1)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
第一,將再生速度較慢、難度較大的可再生資源納入征稅范圍,包括森林資源、灘涂資源等;第二,將我國較為稀缺且浪費嚴重的可再生資源納入征稅范圍,如水資源;第三,將與生態環境聯系密切,不宜大量開采的資源納入征稅范圍,發揮資源稅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功能,除森林資源外,還包括草原資源、漁業資源等。
(2)完善資源稅的計征方式
繼續完善從量定額與從價定率相結合的計征方式:對于消耗強度過大、需求增長迅速且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資源品實行從價定率計征辦法,除原油、天然氣外,還應包括煤炭、非金屬礦和金屬礦原礦等礦產資源以及森林資源等;對于需求量比較穩定、數量(范圍)便于統計或市場化程度不高的資源產品實行從量定額計征辦法,包括鹽、水資源和草原資源等。
(3)提高資源稅的稅率水平
對于消耗速度過大且稀缺程度較高的資源實行較高的稅率,如某些稀缺的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對于消耗速度不高、儲量較大或鼓勵開發的資源實行低稅率,如鹽、地熱資源等;對于需要保護但與居民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資源可以實行較低的稅率,如居民用水。
(4)清理整合其他收費項目
目前在資源領域存在名目繁多的各類收費和基金項目,加重了企業的負擔,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應該利用資源稅改革的機會,科學地清理整合各類收費和專項基金,切實減輕生產企業負擔,確保收費項目的規范化。
(5)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資源稅調節功能的實現是依靠價格傳導機制產生的,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對資源稅功能的發揮至關重要。因此,應當加快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將由行政干預為主的價格形成機制轉變為市場作用為主、行政干預為輔的價格形成機制,逐步放開政府對價格的管制,發揮市場在資源價格形成中的決定作用,使資源價格充分反映資源的全部價值和供求關系。
責任編輯:孟 力
F812.42
A
1006-1255-(2016)10-0003-07
安體富(1938—),中國人民大學。郵編: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