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革命”對民主化影響
龔 穎 周仁標
(安徽師范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顏色革命”對民主化影響
龔 穎 周仁標
(安徽師范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民主化不等于民主,民主化表示的是一個通向民主的過程,而民主則是一種既成的狀態。關于民主化理論,西方學者有很多論述,主要的就是羅伯特·達爾與塞繆爾·亨廷頓,在此所討論的民主化是由亨廷頓提出并界定的概念。1974年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沒有隨著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于1991年截稿而終止,相反,冷戰結束以來,民主化以“顏色革命”、街頭抗爭和互聯網政治的結合這種新趨勢展開,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處于社會轉型階段展開,給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引人深思。民主化的新趨勢主要以“顏色革命”呈現世人,但也在發展中國家中出現困境,需要加以分析。
“顏色革命”;民主化;社會轉型;街頭抗爭
冷戰結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繼出現“顏色革命”,建立起西方式代議民主政權或為民主及其他議題而抗爭。首先是原蘇聯國家,如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 “郁金香革命”,反對派以選舉做文章,認為選舉存在暗箱操作,發起街頭抗爭,并推翻政府組建新政府;2010年以來,以突尼斯青年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為導火索,引發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3年以亞努科維奇暫停簽署與歐盟聯系國協定,引發的烏克蘭危機;2014年臺灣地區因反服貿引發的“太陽花學運”;2014年因爭取2017年普選引發的香港“占中”運動等。國際社會層出不窮的以“顏色革命”為名的街頭抗爭運動令人眼花繚亂。這不禁讓人遐想,國際社會是否出現了新一輪的民主化浪潮?
民主化不等于民主,民主化表示的是一個通向民主的過程,而民主則是一種既成的狀態。關于民主化理論,西方學者有很多論述,主要的就是羅伯特·達爾與塞繆爾·亨廷頓,本文所討論的民主化是由亨廷頓界定的概念,并且主要談的是民主化過程中的置換。1974年以來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沒有隨著亨廷頓 《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于1991年截稿而終止,相反,冷戰結束以來,民主化以顏色革命、街頭抗爭和互聯網政治的結合這種新趨勢而展開,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處于社會轉型階段展開,給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治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引人深思。本文主要從對民主化與“顏色革命”的界定、民主化進程中的新趨勢、顏色革命的動因分析及其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困境來探討顏色革命對民主化的影響。
1 民主化及“顏色革命”界定
本文之所以使用亨廷頓對民主化的界定,第一個原因在于本文主要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視角來探討民主化問題,而亨廷頓在其巨著《第三波》中分析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是根據發展中國家來界定的。這不同于達爾在《多頭政體:參與和反對》中涉及的第三波民主化問題,達爾主要探討的是代議制民主國家的民主深化問題,是發達國家的民主問題。第二個原因則是與“顏色革命”相聯系,而“顏色革命”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試圖通過發展援助、政治承諾以及慈善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反對派給予扶持、對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者給予支持并鼓動其通過街頭抗爭等方式實現政權的更迭,以圖建立對其有利的政府。他們樂見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顏色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第一,間接干涉以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權;第二,輸出西式民主。
根據統治集團和在野集團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亨廷頓區分了三種不同的轉型進程即變革、置換和移轉。變革主要是執政者自發性的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民主的過程;置換是反對派發動的推翻執政當局或實現政權更迭及政治訴求的民主過程;移轉是政府與反對派聯合采取行動以實現民主的過程。根據亨廷頓對三種轉型進程的區分,結合對“顏色革命”的界定,我認為可以把“顏色革命”歸為民主化進程的置換進程。首先,實施“顏色革命”的主體是反對派;其次反對派的主要目的是實現政權的更迭和政治訴求;第三,反對派政治參與的方式是街頭抗爭。這些特征與亨廷頓所闡釋的第三波民主化具有相似性。
通過對“顏色革命”特征的考察,可以發現步入后冷戰時代的民主化的一些新趨向。
2 民主化進程新趨勢

“顏色革命”盡管在冷戰后期的“和平演變”中有所體現,或者說是“和平演變”的延續,但當前的“顏色革命”參與主體及施行工具與“和平演變”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發達國家試圖發動“顏色革命”的目的是實現政權更迭,這與反對派的目的不謀而合。當前的“顏色革命”更多涉及的是關于選舉的議題,這與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所涉及的推翻威權政體也有著不同,當前的“顏色革命”不僅有推翻威權政體的內涵,在更廣泛意義上是實現政權的的更迭,是對具體政治訴求的表達,是實現權力再分配的體現。“阿拉伯之春”是因為社會不平等引發的對阿拉伯部分國家專制政權和威權政權的沖擊;“太陽花學運”是因為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簽署摻雜“臺獨”勢力的經濟議題和政治博弈的學生運動;“占中”運動反映的是政治參與、“普選”、民主訴求。在“太陽花學運”“占中”事件中體現出的一種新趨向是以學生為主的街頭政治抗爭可能成為今后民主化進程的主要運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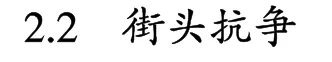
抗爭政治理論指出抗爭政治是由抗爭行為、集體行動與公共政治的交集構成的,是一種間歇性行動,它的發生不具有規律性和連續性。抗爭成為民主化的一種工具,在成功實現民主轉型過程中,有著一定的條件:集體行動;提出全國性和公共性民主訴求;對行動目標的策略性設計;抗議組織的權力集中;和平方式。持續的街頭抗爭是民主化進程中反對派與政府不合作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是“顏色革命”中使用的最廣泛的形式。從“太陽花學運”與“占中”事件中可以反映街頭抗爭的組織性,都是以學生組織為主,如香港“學聯”;他們的行動目標具有針對性,如“太陽花學運”的反服貿,“占中”的“普選”。街頭抗爭是一種間歇性行動,這與其目標、訴求的實現程度呈正相關,反服貿只是告一段落,并沒有顯示它的結束,當臺灣地區當局和“立法院”商討的監督議程達不到反對者訴求時,沒有證據顯示其不會再一次發起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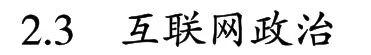
國民教育的提升,國民素質的增強,網民基數的擴大,使互聯網成為一種有效工具,可促發國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途徑。互聯網政治在中國成為一種可能,并且其在一些西方國家已經被使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主化的進程。互聯網政治在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主要就體現在它的政治動員速度、政治抗爭的工具性、政治參與的效率性上。復旦大學劉建軍教授在參加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辦的 “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了 《互聯網政治的中國意義》報告,他認為互聯網政治可以從技術型、治理型和政治層面理解。技術型的互聯網政治主要是將互聯網作為政治的一種技術型工具,如網絡選舉;治理型的互聯網政治是用互聯網來加強公共治理,如電子政務;政治層面是將其作為諸如網絡抗爭等政治動員手段。他認為“顏色革命”是基于網上政治與網下政治的互動。當前的政治抗爭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互聯網的作用,互聯網具有傳染性,即其政治動員、輿論造勢、傳播迅速的作用。在境外,臉書、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體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境內,QQ、微信、微博等通訊工具能夠將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迅速傳播。互聯網在“阿拉伯之春”的作用是促進人們之間的溝通及動員速度,由于2010年12月17日警察沒收了布瓦吉吉的推車,在他向政府申訴被拒后而選擇了自焚,這一自焚照很快遍布在社交媒體上,僅僅一天的時間,突尼斯就完成了社會動員,西迪布吉德市隨即爆發游行示威,引發騷亂,并迅速蔓延至全國。這也促使突尼斯政府的置換及部分阿拉伯國家當局的變革,推進了中東地區的民主化進程。
從以上分析可以初步看出“顏色革命”的主要形式便是街頭抗爭,而互聯網政治為“顏色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平臺。不管是“玫瑰革命”“橙色革命”還是“栗子花革命”等都通過一定的形式或多或少地對民主化的進程有一定影響。
3 “顏色革命”的動因分析

后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中產生了兩個重大變量,一個是9·11以來的反恐戰爭,將人們的視野拉到非傳統威脅上,這促發了中東地區政治格局的轉變及動蕩;另一個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紛紛面臨如何恢復經濟的問題。這使發展中國家不僅要想方設法恢復經濟,同時還面臨嚴峻的國際環境。
但是更為緊迫的是發展中國家自身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在發展中國家內部面臨著各種亟待解決的問題,如貧富差距、就業困難、“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結構失衡、社會撕裂、民族認同、政治腐敗、環境惡化、政治機制不完善等。這些議題都可能成為誘發“顏色革命”的因素。
阿拉伯之春的背景是長期的反恐戰爭引發的社會動蕩、貧窮;經濟危機引發的失業;社會結構的固化、貧富差距的懸殊、社會的不平等。烏克蘭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親西方與親俄方的社會撕裂、國家認同危機以及高官腐敗問題。“太陽花學運”與“占中”事件以學生為主的背后都有著青年學生對就業問題、國家認同問題的影響。
在威權政體或不完善的民主制國家和地區中,政府都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在發展中國家,公民政治參與的訴求是在不斷提高的,而威權政體或不完善的民主制國家和地區則比較缺乏政治參與的渠道,甚至在威權政體中可能存在政府當局為維護政治穩定故意壓制公民的政治參與,這不利于緩解公民的政治訴求。如“阿拉伯之春”中布瓦吉吉以極端的自焚方式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門沒有滿足他拿回推車的訴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功能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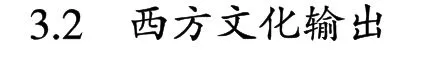
無論是西方政治家、還是西方國家的學者與普通民眾,都存在一種西方文化優越論的偏見,他們總是以西方的價值標準作為標尺來衡量、批判非西方國家,自由、民主、人權都是他們的標尺。亨廷頓、弗朗西斯·福山等“西方文化論”者認為,現代民主是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西方基督教文化是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論內核,而西方民主發展的條件與道路是引導世界民主化進程的唯一標準。亨廷頓認為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尤為不利于民主”,因此他們有義務向非西方國家輸出西方文化,而煽動非西方國家的“顏色革命”成為文化輸出的一項重要途徑。
劉洪潮在“美國的‘民主化’戰略中的街頭政治”一文中列舉了十條民主化輸出戰略:利用親西方的團體和個人打先鋒,為街頭政治營造適宜氛圍;開辦講習班,培養街頭政治的骨干力量;精心挑選代理人;設立指揮部;選好突破口;慷慨解囊,為反對派搞街頭政治提供資金;利用媒體“妖魔化”當權派,為反對派奪權制造“法理”依據;大打“經濟牌”,對當事國選民誘壓兼施;施高壓不準當局動武,為反對派放開手腳奪權保駕護航;帶頭宣布不承認不利于反對派的選舉結果,為反對派翻力挽狂瀾。 “顏色革命”是西方國家文化輸出成果的見證,非政府組織、基金會在“顏色革命”前期的反對派骨干培訓、民主價值培養、街頭抗爭程序和機制的設定上,在“顏色革命”過程中的資金支持和輿論造勢上,在后期的民主機制的構建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依靠美國政府撥款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目的在于在目標國和地區開展民主滲透活動,培育親美勢力,以推動民主的名義插手他國內政。2012年NRD用于烏克蘭的資金為338.1824萬美元;2005—2008年NED向全國國際民主事物學會提供用于支持其在中亞項目的資金為173.3675萬美元,這為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發生的“郁金香革命”作了準備;2007年用于香港的資金為36.9983萬美元。在“占中”事件中,西方報紙和政府(以英美為主)公開指責中國對香港“普選”的回避,據《文匯報》報道,NED及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究院(NDI),自香港回歸以來,就長期在香港活動,如出資、培訓反對派等。烏克蘭危機中,西方國家更是明目張膽的給予親西方者經濟和軍事援助,強化對俄羅斯的制裁。
而西方推行其“民主化”不只是局限于文化維度,在經濟、政治等其他維度上均有行動及價值觀念滲透。西方主流媒體都會在其政體下蒙上一層全民民主的外衣,然而這只是事實上的金錢民主而已,以此進行所謂的“民主滲透”。
4 通過“顏色革命”來實現民主化的困境
亨廷頓認為民主化會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民族和宗教問題,政治領導人作用,外部勢力的新政策,示范效應或滾雪球,民主轉型的時機,新興民主國家所面對情境問題的數量和嚴重性以及民主制度的性質等。這些因素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顏色革命”后會不同程度的有所體現,這也使試圖通過“顏色革命”來實現民主化帶來一些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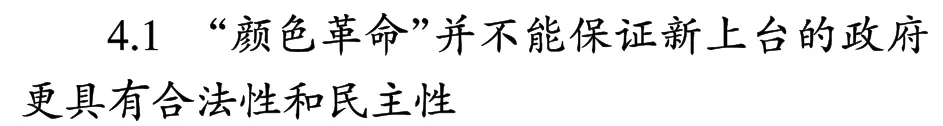
以埃及為例。2011年1月25日,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影響,面對埃及存在的嚴重社會不公、政治腐敗、失業等問題,埃及爆發一系列街頭示威、游行、集會、罷工等抗議活動,要求穆巴拉克政府下臺。2012年通過選舉,代表穆斯林兄弟會的自由與正義黨主席穆罕默德·穆爾西贏得總統大選,成為埃及史上首位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但是穆爾西的上臺并沒有擺脫埃及政治動蕩的局勢,社會治理的失敗、宗教主義抬頭使穆爾西民選政府合法性及民主性遭受質疑,并最終引發2013年軍事政變,穆爾西被趕下臺,現在埃及又重回軍人政府統治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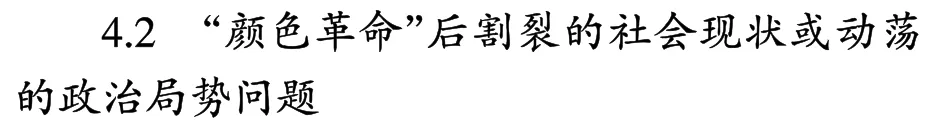
發生“顏色革命”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社會撕裂或政治動蕩問題。埃及既存在世俗派與宗教派的紛爭,也面臨著軍人政府的不確定性問題。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發生“郁金香革命”,但在2010年大選前后再次發生政治騷亂。烏克蘭“橙色革命”反映了親西方與親俄方的撕裂,這種撕裂在2013年進一步擴大,并演變為“烏克蘭危機”,攪動著國際局勢的發展。“顏色革命”后,國家民主化進程不僅沒有實質性進展,反而陷入反對派推翻執政當局又被下野黨派或勢力推翻的怪圈,這是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還是政治衰敗?政權的更替以社會認同的撕裂和政治動蕩為代價,這顯然也給民主化理論帶來解釋的困境。

民主需要一定的限度,民粹不等于民主,互聯網政治一定程度上確實給政治發展帶來了新的選擇工具,也使個人言論自由得到充分體現,但缺乏規則的虛擬的網絡社會也使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甚囂塵上。不負責任的輿論宣傳甚至是謠言以及“人肉搜索”等帶來的不是民主,它使民主化披上了一層陰影,傷害了互聯網政治這一政治參與平臺。違背民意的“占中”事件中泛民在互聯網上對中央政府的歪曲、鼓動持續的失去正當性的街頭政治抗爭到底等民粹性行為使其“爭普選”成為擺設。以理想化的青年學生為代表的學運也使民粹性更加顯現,還未成年的青年學生是否可以領導合法的社會運動,這些讓人產生疑問。
5 總結
“顏色革命”是內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顏色革命”可能成為民主化的催化劑,但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生的帶有“顏色革命”的街頭政治表明其對民主化進程影響的有限性,它也并不必然帶來民主化進程。“顏色革命”帶來的民主化困境表明民主化的路徑選擇應回歸本土化,在不同國家民主發展的序列需要根據具體國家的政治發展的實際來加以區分,從而避免民主化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同時也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
[1]達爾.多頭政體:參與和反對[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8.
[2]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96.
[3]謝岳.社會抗爭與民主轉型: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威權主義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5.
[4]高正波.“阿拉伯之春”與虛擬社交網絡[D].蘭州:蘭州大學,2014:8.
[5]周敏凱,趙盈.轉型民主問題與現代民主形態多種屬性研究——兼析亨廷頓的轉型民主觀[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92-97.
[6]牛新春,房寧,劉洪潮,等.美國的“民主化”戰略值得警惕[J].國外理論動態,2005,(6):1-8.
[7]張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在中亞的活動[J].國際資料信息,2012,(10):21-25.
[8]景躍進.關于民主發展的多元維度與民主化序列問題——民主化理論的中國闡釋之二[J].新視野,2011,(2):31-34.
THE INFLUENCE“COLOR REVOLUTION”ON DEMOCRATIZATION
GONG Ying ZHOU Ren-biao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
Democratization does not mean democracy.Democratization represents a process leading to democracy,but democracy is an existed state.As for democratization theory,many Western scholars have all kinds of discussions.Main scholars include Robert Dahl and Samuel Huntington.Here,democratization w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the concept defined by the Huntington.Since 1974,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didn't end with the deadline of Huntington's Third Wave:the Late 20th Century Wave of Democratization.On the contrary,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democratization in the form of“Color Revolution”,“street protests”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Internet politics expanded,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which brings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That is thought-provoking.The new trend of democratization is mainly presented to the world in the form of"color revolutions".However,there appeared some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refore,we need to analyze them.
Color Revolution;democratization;social transformation;street protests
D55
A
1672-2868(2016)05-0021-05
2016-07-25
龔穎(1993-),女,安徽蕪湖人。安徽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學。
責任編輯:楊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