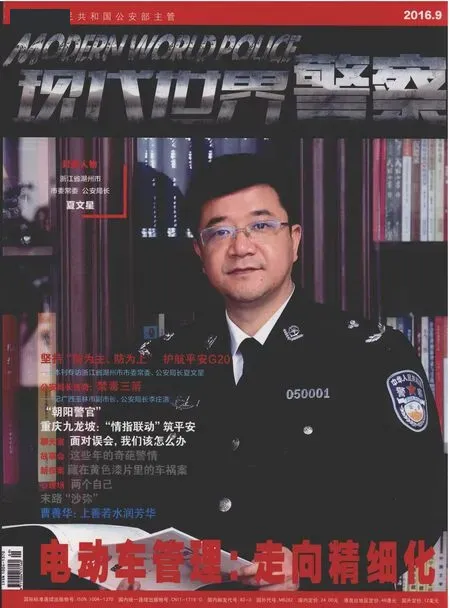制造謀殺犯
文/【美】巴尼·多伊爾 編譯/李一南
制造謀殺犯
文/【美】巴尼·多伊爾 編譯/李一南

1985年,22歲的史蒂文·艾弗瑞因強奸罪成立入獄

史蒂文20多歲的時候曾因入室搶劫、火燒小貓等各種犯罪被逮捕過
2005年的萬圣節前夕,美國威斯康星州發生一起25歲的女攝影記者被殺焚尸案。兩年后,兩名男性以“一級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2015年底,由兩名女導演跟蹤拍攝的十集系列紀錄片《制造謀殺犯》播出。該片圍繞主要案犯的人生軌跡對案情進行了詳細披露,強烈暗示主角無辜,質疑警方辦案程序與搜取證據的合法性。該劇播出兩個月后,引起了全美關注,甚至誘發了多起報復警局的案件。
紀錄片引出的“冤案”
《制造謀殺犯(Making a Murderer)》是美國“網飛(Netflix)”電視臺(系全球十大網絡電視臺中唯一收費的電視臺)在2015年12月18日開始陸續推出的一部系列紀錄片,由勞拉·羅西亞蒂和莫伊拉·迪莫斯兩位女性共同執導,講述了美國威斯康星州馬尼拓沃克縣(以下簡稱“馬縣”)史蒂文·艾弗瑞身上發生的兩起案件。1985年7月的一個早上,當地人潘妮·比恩森正在湖畔慢跑,突然被一個男子拖拽進了樹叢中性侵、毆打,隨后史蒂文·艾弗瑞被指控“性侵”和“謀殺”而入獄。1995年,美國將DNA技術引入司法實踐,并對歷年判決案件所保存的物證進行DNA分析。2003年,分析人員發現,在受害人潘妮的毛發和皮屑中發現了另一名服刑犯的DNA,史蒂文·艾弗瑞被平反昭雪。
2005年,也就是史蒂文·艾弗瑞獲釋兩年后,還在打著巨額司法賠償官司的他又因涉嫌謀殺特蕾莎·哈芭琦(本地攝影記者)而被捕。2007年,他和自己的外甥布倫丹·達西被州法院判決終身監禁。從他第二次涉嫌謀殺被捕的那一年開始,紀錄片攝制組成立,此后從紐約到威州,歷經十年奔波,對這兩起案件進行跟蹤拍攝。為給此片造勢,“網飛”電視臺專門在YouTube和自己的網站上發布了未經剪輯的第一集。
《制造謀殺犯》劇組以精良的制作將殺人焚尸案偵辦過程中的諸多漏洞呈現在觀眾面前,不斷引導觀眾去提問、思考,因此該片播出后迅速躥紅,評論呈現“炸鍋”之勢,各界熱議不斷,各大媒體也因此改變了原來的態度。之前他們完全無視艾弗瑞家人的奔走求助,現在《華盛頓郵報》、NBC電視網及ABC電視網等美國主流媒體都對該案進行了持續跟蹤報道。還有全球最大黑客組織“匿名者”宣布介入,聲稱已找到了“構陷史蒂文的證據”;社交新聞網站Reddit積極響應,在自己網站上登出了案件所有的庭審記錄供討論;全美成功脫罪記錄最好的冤案律師凱瑟琳·澤納已成為史蒂文的新律師……據有關方面統計,截至2016年3月,已有13萬人到白宮官方網站簽名為史蒂文伸冤,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此也進行了回應,稱該案為威州管轄,不屬聯邦法律管轄范疇,赦免權也歸威州州長所有。州長卻明確表態,拒絕行使特赦權。但這些都不影響該劇的聲名鵲起,目前該劇已與HBO電視臺的《厄運當頭(The Jinx)》系列劇齊名,成為揭露美國司法黑暗的著名紀錄片。

史蒂文·艾弗瑞被判決時其母親的表情——她大半輩子都在幫兒子伸冤

辯護律師迪恩

曾與史蒂文·艾弗瑞有“過節”的兩位警員
撲朔迷離的案情
2005年10月,一名陌生男性給雜志社打電話稱有人要賣車。他約了會面時間并特別強調要攝影記者特蕾莎·哈芭琦來拍照,他沒有說明自己是誰,留下的聯系方式是史蒂文·艾弗瑞妹妹的電話。
受害人:特蕾莎·哈芭琦,歿年25歲,當地汽車銷售雜志攝影記者。哈芭琦之前告訴同事們,案發前的10月10日,她曾經見過史蒂文·艾弗瑞一面,也是給車拍廣告。當時史蒂文·艾弗瑞只在身上圍了一條浴巾就出門見她,她表示這人“令她很不舒服”。
主要案犯:史蒂文·艾弗瑞,時年41歲,在家族開設的車輛拆解廠(占地數畝)居住。這次約見是史蒂文·艾弗瑞本人打的電話,留下的聯絡方式則是他妹妹的。
2005年10月31日下午,史蒂文·艾弗瑞兩次給哈芭琦去電詢問她到了沒有,但哈芭琦顯然不知道對方是誰,因為史蒂文·艾弗瑞使用了*67即“隱藏去電號碼(美國)”功能。哈芭琦沒有產生懷疑,她開著自己墨綠色的豐田SUV到了艾弗瑞一家經營的廢舊車輛拆解廠,準備給預售的汽車拍照。當時,史蒂文·艾弗瑞住在一臺拖車上,其他家庭成員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之后,史蒂文·艾弗瑞又給哈芭琦打了第三個電話,并且留言說:“嗨,你說來咋還不來啊?你在哪兒啊?”最后這次他沒有隱藏自己的手機號碼,而這個時候,受害人已經死了。
此后,再沒有人見過特蕾莎·哈芭琦。
特蕾莎·哈芭琦的家人組織了志愿搜救隊進行查找。幾天后,其表姐在艾弗瑞家族的廢舊車輛拆解廠內發現了表妹的車輛,隨即報警。鑒于當時史蒂文·艾弗瑞正和馬縣打著那場白白關了18年冤案的國家賠償官司,威州司法部門指定相鄰的卡柳梅縣(以下簡稱“卡縣”)偵辦此案。
卡縣警方封鎖了史蒂文·艾弗瑞的住處和整個拆解廠。隨著調查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特蕾莎·哈芭琦已經遇害。
夾雜質疑的證據
受害人的車輛在拆解廠被發現后,警方第一次進行了長達八天的勘查,四個月后又進行了第二次徹底勘查。
【骸骨】案發當晚,好幾位證人看到史蒂文·艾弗瑞拖車外的院子里有人點了一把火。警方在這堆灰燼中發現了一些被燒過的和輪胎等粘連在一起的人骨,通過一塊僅存的肌肉纖維和牙齒的DNA,證實骸骨來自特蕾莎。其他的殘骸——明顯也是受害人的骨頭在拆解廠其他兩處垃圾場中被發現。
【車輛】受害人的車輛墨綠色豐田RAV4在拆解廠被發現。有多個證人作證說看到了哈芭琦那臺車。但在看到了哈芭琦的車停在拆解廠后,沒有證人稱看到過哈芭琦本人。哈芭琦的汽車被發現與其他廢棄的汽車停在一起,就在艾弗瑞家族的拆解廠里。
【手機】哈芭琦的手機及其他個人物品在史蒂文·艾弗瑞拖車外一個燒過的油桶里被找到。
【鑰匙】一把屬于哈芭琦的車鑰匙在史蒂文·艾弗瑞的臥室里被找到。這把鑰匙是第七次復勘現場時,被主動參與案偵工作的馬縣警察發現的。紀錄片指出,鑰匙上只有史蒂文的DNA,沒有發現受害人的DNA,這一點讓大量觀眾認為警方存在取證作假的行為。
【血跡】哈芭琦的車中發現多處屬于史蒂文·艾弗瑞的血跡。紀錄片暗示,血液有可能是警察利用職權“導演”的,因為物證室里有一支裝了史蒂文血液的試管破了。
【DNA】在哈芭琦車輛引擎蓋的罩鎖上發現屬于史蒂文·艾弗瑞的汗液DNA。紀錄片未對此進行質疑,似乎也忽略了這一證據。但警方認為這一證據對證明史蒂文謀殺是確鑿無疑而且無法“栽贓”的。

劇集開始時展現的史蒂文·艾弗瑞洗清冤屈的開心畫面

兩位辯護律師每次的辯護都是《制造殺人犯》的精彩之處
【子彈】在史蒂文·艾弗瑞的車庫里發現一個沾有哈芭琦DNA的彈頭殘片。經檢驗,系史蒂文·艾弗瑞拖車內放置的一把.22步槍所擊發。該彈頭是第八次復勘現場時,被主動參與案偵工作的馬縣警察發現的。紀錄片指出,這次復勘距離上一次四個月,在史蒂文的車庫里發現了一個用過的子彈殼和一些沒使用過的彈殼。蹊蹺的是,子彈一直都沒被發現,而馬縣警官出現的第二天子彈就被發現了。而該殘片上沾染了檢驗人員的DNA,證明建材至少是被污染了,且檢驗方還使用了會消耗掉所有樣本的檢驗方法,明顯不妥。這樣的做法不能排除“檢驗人員在將受害人的DNA栽贓到樣本中時,不小心也把自己身上的DNA混入了樣本中”。
【嫌疑人供述】史蒂文·艾弗瑞一直否認自己殺害了哈芭琦,他16歲的外甥布倫丹·達西則承認自己幫助舅舅強奸、殺害哈芭琦并銷毀了尸體。達西有明顯的學習障礙,IQ也低于正常水平,他前后多次修改自己的證詞,一會兒承認自己參與謀殺,一會兒否認。在紀錄片中,達西的部分口供與案件中的證據有多處不吻合之處。如在最初的證詞中,他說自己性侵了那個記者,然后在舅舅的指使下殺死了受害人;又如他在訊問中稱“哈芭琦的喉嚨是在艾弗瑞的床上被割開的”,但警方在偵查工作已明確地予以了否定,因為房間內沒有找到受害人以及達西的DNA。紀錄片根據警方的審訊錄像,質疑有人在操控達西的口供,然后被用來進一步佐證史蒂文謀殺的證據,并且指責達西的公派律師誘導他認罪。
對此案的審訊也是一波三折。在陪審團開始討論時,12人中的七人認為史蒂文是無辜的,三人認為有罪,兩人不確定。在陪審團看了全部證據、經過了漫長的討論后的2007年,陪審團一致最終判定史蒂文·艾弗瑞和達西“有罪”。這一次,威州的“洗冤工程”沒有介入。
此外,還有對現場的不同看法。
【第一現場】既然子彈的彈頭殘片在車庫被發現,此處應為第一現場。受害人在此應該留有大量血跡。但是紀錄片顯示,警方對車庫地板進行了仔細檢查,甚至翹起一部分水泥地板以檢查縫隙,雖然有漂白劑的痕跡,但沒有發現任何血跡或DNA痕跡。檢方對此的解釋是“史蒂文·艾弗瑞用漂白粉進行了徹底的清潔”,然而,正如紀錄片中的專業人士所說的那樣,要對兇殺現場進行徹底的清潔需要相當多的專業知識,對沒有什么文化的史蒂文來說,這是“不太可能做得出來的”。
【第二現場】根據證人陳述和受害人骸骨發現的灰燼,史蒂文·艾弗瑞的院子應該是焚尸現場。紀錄片呈現了法庭質證,辯方律師懷疑警方的取證能力與誠信,因為警方的檢查專家表示“被燒殘骸沒有被搬動后形成的裂痕”,以此證明尸體就是在史蒂文院子里被焚燒的。但律師指出,當時搜集證據的時候“警察直接拿鏟子猛鏟骨頭碎片”居然“沒有產生裂痕”。根據現場勘查,當時焚燒的溫度應該有1500~2000度高溫,而且嫌疑人是冷卻后再去敲擊的,這與現場附近和灰燼中五條輪胎、一個座椅提供的助燃相互印證。
“問題小子”的故事
史蒂文·艾弗瑞,馬縣當地人。他和他的家人經營著一家汽車拆解廠。艾弗瑞家族幾乎沒有接受過什么教育,也不太愿意和縣里的人來往。久而久之,當地人都覺得他們一家古怪、孤僻。20多歲的時候,史蒂文·艾弗瑞曾經入室搶劫、火燒小貓、拿著沒有裝彈的槍和表妹爭執……他因此成了警局的常客,多次被捕,是個“問題小子”。而這些綜合在一起,史蒂文·艾弗瑞就順理成章地被縣里公認為一個高度危險的人物。
《制造謀殺犯》展示了1985年案件偵辦時的一些情節:一是接手案件的警官正好是史蒂文的鄰居,也是史蒂文表妹的好朋友,他很不喜歡史蒂文。二是當受害人潘妮在描述嫌疑人的時候,警官暗示性地說了一句“這描述聽起來像是史蒂文·艾弗瑞嘛”。好了,潘妮在指認時就選定了史蒂文是加害人。但事實上,潘妮描述的嫌疑人的眼睛顏色、身高、體重、發色等都和史蒂文不符,且史蒂文有足夠的不在場證據。但因為受害人指認,史蒂文還是被關了進去。
1985年被控強奸、謀殺的案子讓史蒂文·艾弗瑞在23歲時就被判入獄32年,要不是威州的民間組織“洗冤工程”出面鑒定,他還要無辜地在監獄里再住14年。不但喪失了一個人最美好的青春歲月,也喪失了陪伴五個孩子長大的黃金時光。他把馬縣推上了被告席,要求賠償3600萬美元,而當時的律師曾開玩笑地告誡他:“你要小心哦。”
史蒂文·艾弗瑞是個“耿直人”,他對于在此之前的每一起暴力行為都供認不諱,但是對于性侵潘妮和謀殺女記者的事情他一直否認。從醫學上講,他的智商較低,用美國人的話來說是個“會說話的棒球”。1985年的案子被平反,證明了史蒂文·艾弗瑞的確沒有撒謊,也暴露了馬縣警局當事人對已犯錯誤不糾正、對明顯“可能抓錯人”的情況置之不理的態度,而這些人又參與了第二起涉艾弗瑞的案件偵辦。
那么,第二起案件是否證明了艾弗瑞仍然是無辜的呢?《制造謀殺犯》質疑,如此低智商的人不可能設計出如此狡猾多端的殺人過程。例如,紀錄片稱“只有傻瓜才會在拆解廠留下受害人的車、才會在他的院子里留下燒毀的人體殘骸”。但警方認為,其實史蒂文·艾弗瑞約受害人到汽車拆解廠的行為就證明了他智商不高、設局不“高超”,以至于留下了大量起訴所需的證據。警方認為,只有一個“會說話的棒球”才會在謀殺案現場留下這么多證據,尤其是面對即將到來的謀殺調查而不得不匆匆打掃現場。尸體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燒毀的,一臺撞毀的車不會撞一下就變成灰了,把受害人的車壓扁也不能徹底消除干凈所有證據。
輿情重壓下的警局
作為立案和參與案偵工作的威州馬縣,《制造謀殺者》剛剛播出,就遭到了來自各方的巨大輿論壓力。該縣司法部門對劇組的所作所為表示了極大的失望和憤慨。警方稱:“劇組做了一件傷害威州執法部門的事情,他們應該為此感到羞恥。”馬縣治安官羅伯特·赫爾曼說,該劇是對史蒂文·艾弗瑞作案事實的“謊言”“謠傳”和“曲解”,是將執法部門尤其是馬縣警局釘在恥辱柱上讓公眾鞭撻,讓涉案警官承受威脅和侮辱。警局稱,該劇的播出給馬縣警察局帶來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現在他的工作單位已經在全球臭名遠揚,并且“個別人受到的影響甚于其他人”。

失蹤的特蕾莎·哈芭琦以及與她一起消失的汽車

《制造殺人犯》導演
1980年開始,赫爾曼就在馬縣警局工作,歷任副警長、治安官,他全程經歷了對史蒂文·艾弗瑞和達西的偵辦、起訴與判決全過程,對于2007年法院判決艾弗瑞殺害并焚燒尸體罪名成立一案,他敦促觀眾要從全案角度、立足全部證據視角來審視。因為2005年艾弗瑞因特蕾莎·哈芭琦被謀殺案被逮捕時,正在為第一次冤獄昭雪而在和馬縣打官司。在那次案件中,他被錯誤地當做性侵、謀殺潘妮·比恩森的嫌疑人而蒙受了18年的牢獄之苦,直至DNA鑒定查出真兇,還他以清白。出獄后,他便向縣里索賠3600萬美元的賠償。對全美縮減預算背景下的一個小縣來說,這筆索賠無異于天價。而《制造謀殺者》劇組則暗示,正是這一巨額索賠案成為構陷艾弗瑞殺害哈芭琦的主因。紀錄片播出后,赫爾曼與同事們承受著被公眾指責為構陷艾弗瑞與達西的元兇,騷擾奔著警察局鋪天蓋地而來。“電子郵件和電話接踵而至,指責我們是一個腐敗的機構。”赫爾曼說,“你知道的,說我們爛死在地獄里得了。”
但在認真收看了該系列劇后,他的觀感是,與其說是馬縣警察局陷害艾弗瑞,不如說是劇組陷害了警察局。首先是刻意漏掉一些證據,這樣是為了讓艾弗瑞顯得“罪輕”。特別是案中有一個反轉點,“法庭質證”中治安官舉證——艾弗瑞的汗液DNA,這一證據對當時的12名陪審團成員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是劇集中卻引導觀眾相信DNA證據來自于艾弗瑞的血液——暗示血液可能是由警察栽贓灑到現場的。“DNA并非源自血液,是在受害人特蕾莎·哈芭琦車輛的引擎蓋上被發現提取。而那個DNA與史蒂文·艾弗瑞相符。”赫爾曼辯稱,其他物證,例如鑰匙、子彈等——從那把鑰匙上提取的DNA,每件東西——不是血液證據,一直到從艾弗瑞步槍里擊發的子彈以及子彈上的DNA都與受害人的DNA相符。他們(劇組)的理論站不住腳。劇集會讓觀眾相信,原來是警方與艾弗瑞家族有恩怨啊。赫爾曼補充說,幾天前,有一個人非法侵入了艾弗瑞的家(犯罪現場),猜猜他們(媒體和公眾)怎么說的?他們說,那個人肯定是馬縣的治安官。
STZ 誘導的小鼠糖尿病模型在早期階段會產生氧自由基,如超氧陰離子自由基(? O2-)、過氧化氫(H2O2)、羥自由基(? OH)等會引起小鼠體內促氧化劑和抗氧化劑失衡導致氧化應激,并與 NO 途徑相互作用導致 β 細胞破壞,引起糖代謝紊亂[7]。
接踵而至的恐嚇
在眾多的騷擾和惡毒攻擊后,終于迎來一個付諸實踐的重磅恐嚇。
2016年2月,馬縣治安官辦公室接到一通匿名來電,對方稱“要炸了馬縣的治安官辦公室”。很明顯,這是奔著“為史蒂文爭取正義”而來。而這一切,都源于《制造謀殺者》系列劇的熱播,將馬縣執法部門置于輿論的漩渦中心。這是一個周四,早上6時40分,一名男子匿名給馬縣治安官辦公室打電話,威脅在該辦公室里放置炸彈,并在停車場里放置了“成捆的爆炸物”。

宣布罪名成立時史蒂文·艾弗瑞的表情
這個匿名電話著實把警方嚇得不輕。圍繞馬縣治安官辦公室的搜索一直忙到當天21時,為了確保安全,還同時對法庭進行了安保檢查,結果證明是虛驚一場,沒發現可疑物品。可20分鐘后,第二個“非常類似”的威脅又來了。于是,馬縣警方派出人員接管了治安官辦公室雇員的工作,警方代為行使治安官辦公室的職能,對后者的平民雇員則進行了疏散。在安檢中仍舊沒有發現可疑的活動或物品。馬縣警察局和威州刑事警察局已經組成專案組,對匿名電話的來源與該男子的身份進行查證。
發人深省的問題
2007年,案件事實被呈送給陪審團,檢察官列舉了艾弗瑞有罪的證據。辯方則緊緊抓住矛盾指控警方虛構證據,以此混淆和誤導陪審團,促使陪審團跳開該案,去尋找案件背后的疑問。經過長達兩年的審理,威斯康星州陪審團檢視了全案證據,排除了合理懷疑后認定史蒂文·艾弗瑞有罪。
警方和檢方認為,對一名持理性思維的人,看到史蒂文·艾弗瑞上述犯罪的證據清單后,幾乎不可能還對其犯罪持懷疑態度,受害人是他約出來的,人最后消失在他家,骸骨在他家院里,車在他家拆解廠,車內外有他的DNA,鐵證如山啊!但《制造謀殺者》系列紀錄片的兩位導演卻使用精良的制作手法,進行邏輯嚴密的演繹,并在支撐觀點方面對其中的證據進行了有意識的選擇、對300小時的庭審進行了剪輯,使得一部10小時的紀錄片吸引了公眾的眼球,并引發眾多的“神探”去挖掘案情。
因證據問題推翻起訴,最出名的當屬號稱“世紀審判”的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Simpson)殺妻案。此案審理一波三折,在辛普森用刀殺害前妻及餐館的侍應生郎·高曼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導致有力證據的缺失得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二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從而使該案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疑罪從無案件。從艾弗瑞案中,類似于“辛普森案”的問題可以找到不少,我們可以搜集到一些美國警方因違反辦案程序導致證據方面出現諸多問題的案例。可以說,該案就目前來說明顯無法成為“鐵案”、令人信服。紀錄片一經播出,幾十萬人簽名要求對史蒂文·艾弗瑞給予特赦,警方和檢方飽受詬病也就不足為奇了。
違反“回避”規定是硬傷。作為主辦案件單位的馬縣警察局在偵辦案件中“回避”了,但該局與嫌疑人史蒂文之前案件偵辦有直接關聯的兩名警察沒有回避,導致專案組搜集的證據被質疑。謀殺案發生后,威斯康星州司法部門鑒于主要嫌疑人艾弗瑞與馬縣正在打一場國家賠償的官司,按照司法回避規定,將該案指定鄰縣(卡縣)管轄。但是在案偵工作開始后,馬縣的幾名警察主動提出幫助工作,加入到專案組并幫助專案組在隨后的復勘現場過程中找到了關鍵的物證——死者車鑰匙與一顆沾染受害人DNA的彈頭殘片。更關鍵的是,參加專案的馬縣警察竟然是1985年錯案的兩名直接責任人,他們當時正在因經辦了那起錯案而接受調查。這兩名警察積極參加專案,參與了進屋取證,然后找到了受害人的鑰匙。這一結果固然增加了艾弗瑞謀殺的關鍵證據,但是也正因為他們的“熱心”,導致證據來源被廣泛質疑,輿論甚至認為是警方出于對1985年錯案導致司法賠償和追究責任的恐懼而“自保”,以至于當事警察“導演”了整個起獲物證的過程。
馬縣警察局是有這個認識的——參與偵查會給外界帶來什么樣的感受,然而他們還是參與了。這一行為導致全美國大多數地方都懷疑“證據就是這些參與案偵工作的馬縣警察放置的”,這讓他們百口莫辯。他們沒法預知,這些行為會在今天的媒體時代產生多大影響。尤其是在《制造謀殺者》成功播出后,山寨盜版者又大肆地轉錄傳播,造成的后果就更加可怕。
是的,也正因為好心辦壞事,直接導致馬縣警察局淪為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境地。
史蒂文·艾弗瑞與馬縣和解后得到了40萬美元的賠償,然后聘請了兩名律師迪恩和杰瑞。兩名律師竭盡所能為艾弗瑞做無罪辯護。他們口才一流、親和力頗強,在庭審中表現非常搶眼,受到觀眾的熱捧。艾弗瑞的律師緊緊咬住“鑰匙”證據、血液證據的來源問題,發起了凌厲的辯護攻勢。鑒于這些證據均是在第六次、第七次復勘現場才被發現,且是1995年經辦“艾弗瑞性侵、傷害潘妮案”的主辦警察主動加入專案組后接著發現的,艾弗瑞的兩名律師迪恩和杰瑞就此提出了強烈質疑,暗示這些關鍵證據為馬縣警察栽贓。艾弗瑞的辯護團隊認為,馬縣警察局一直在陷害艾弗瑞,因為艾弗瑞之前的官司有可能追究他們的執法過錯而將他們清除出警隊。這樣的邏輯關系也被兩名女導演所參透。劇組充分利用律師庭上“出彩”這一有利于被告的情節,在紀錄片中濃墨重彩地進行了解說。觀眾觀看后,很多人就認為是警察陷害艾弗瑞,以至于受害人哈芭琦的前男友和其他人開始對艾弗瑞是否為兇手產生了懷疑。相反,一些關鍵證據沒有在庭審中發揮壓倒性的作用,則源于本案檢察官克拉茲表現平平。警方稱:“他在熒屏上一露面,就能把人氣死”,連不少警察都質疑“公訴機關就是這么支持案偵的?”“沒哪個陪審員會享受與克拉茲站在一起”,如此一來,讓公眾心中的天平產生了傾斜。
誠然,馬縣警局面臨著任務重、人手少的窘境,但這是違反刑事執法程序的理由嗎?為了“破案”就可以置法律規定于不顧?不僅如此,該案提取物證和保管證據方面也暴露出個別美國同行幼稚的一面,最終授人以柄,導致警方極其被動。深刻分析該案中存在的程序和取證問題,警示我們要在當前執法困難的形勢下,提高程序意識,堅持規范辦案,才是應有之義。
喧囂尚未散去,影響已經鑄成。正如有網友說,《制造謀殺犯》是一部“值得獲諾獎”的紀錄片,可能不僅會改變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命運,更可能是整個美國司法。一部紀錄片引發如此大的輿論,其實道理很簡單:對于刑事執法,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標榜多么“法治”,每一起案件都必須嚴格按照程序和實體操作。這就是該案給我們的警示。
(注:本文在美國警察巴尼·多伊爾專欄文章、Netflix公司紀錄片《Making a Murderer》及“維基詞典”的“Making a Murderer”詞條翻譯基礎上,借鑒影評作者“噠噠”“Ericye”“小白趙寧”等部分評論觀點編輯而成。在編譯過程中得到成都市溫江區公安分局胡小軍的大力幫助,在此一并致謝——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