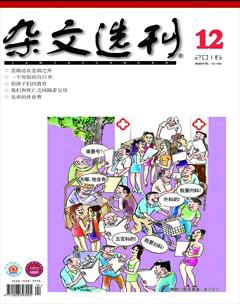托爾斯泰:我不能沉默!
唐寶民
一直以來,托爾斯泰在公眾心目中的定位,就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想起他來,人們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不朽的經典,贊嘆他那輝煌的文學才華;其實,除了文學方面的才華,托爾斯泰還擁有著另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挺身而出的正義感!
1908年5月10日,托爾斯泰從報上獲悉二十個農民因搶劫地主莊園被判絞刑的消息,立即寫文章進行抗議,那二十個農民他一個也不認識,和他沒有任何關系,而且,他的抗議對象,是擁有數十萬軍警憲特的強大的沙皇政權。向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發出抗議,顯然是極其危險的,然而托爾斯泰卻堅定地表示:“我不能沉默!”他在文章中替這二十個農民進行辯護,說他們并沒有犯罪,說他們只是一群“不幸的、被欺騙的人”;相反,他指責整個專制制度才是真正的罪犯!他對政府對民眾進行屠殺的野蠻行徑極為憤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政府的欺騙本質。他當然清楚這篇文章將給自己帶來的巨大危險,但他毫不畏懼:“我寫下這篇東西,我將全力以赴把我寫下的東西在國內外廣泛散布,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結束這些非人的事件,或毀掉我同這些事件的聯系,以便達到或者把我關進監獄,或者最好是像對待那二十個或十二個農民似的,也給我穿上尸衣!”文章見報后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令政府十分尷尬,當局惱羞成怒,逮捕了刊載這篇文章的報紙發行人和一些讀者,但由于托爾斯泰是擁有世界聲譽的文學家,當局不敢對他動手,只能在心中對這個多管閑事的老頭子恨之入骨。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的寫作明顯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早在他寫出《論饑荒》后,沙皇政府就想將他監禁或流放,但因他擁有的巨大聲望而中止。他察覺到了危險的存在,卻并沒有停止批判,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他寫了《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第二年又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他撰文反對日俄戰爭;他同情革命者,在革命失敗后,他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的行為,寫出了《我不能沉默》。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他的創作行為是否伴隨著崇高的責任感,決定了其作品的精神高度和普世價值。藝術家不應該只醉心于自己營造的小天地里,不應該只在象牙塔里自娛自樂,他的創作應該關于道義、良知,應該關于公平、正義,應該以強烈的責任感來關注周圍的世界,對困難群體進行人文關懷,并為他們的不公正發出尖銳的吶喊,晚年的托爾斯泰,面對不公正的社會現實,他沒有把“沉默是金”當成處世的金科玉律,而是發出了銳利的吶喊:我不能沉默!他也因此成為良知和道義的捍衛者,在歷史的星空留下了絢麗的光芒。
【原載2016年11月7日《銀川日報·雜文之聲》】
插圖 /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