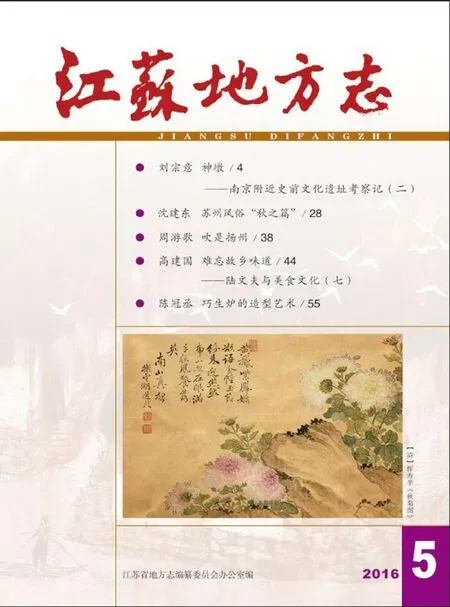歌吹是揚(yáng)州
◎ 周 游
歌吹是揚(yáng)州
◎ 周 游

揚(yáng)州戲曲的淵源,可追溯至兩千年前。揚(yáng)州郊區(qū)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舞女玉佩、百戲彩畫、說唱木俑。特別是兩具雕工精致、神情逼真的說唱俑,形象地表明漢代揚(yáng)州百戲藝人進(jìn)行演唱的生動(dòng)形態(tài)。南朝宋文學(xué)家鮑照在《蕪城賦》中追憶了漢代揚(yáng)州的繁華:“當(dāng)昔全盛之時(shí),車掛轊,人駕肩,廛闬撲地,歌吹沸天。”
琴在樂器中最為古老,廣陵又素有琴名。廣陵琴曲最著名的當(dāng)是《廣陵散》了。據(jù)劉東升《中國(guó)音樂史略》記載,《廣陵散》大約產(chǎn)生于東漢后期。嵇康在魏晉琴壇上赫赫有名。他因拒絕在朝廷做官而得罪了統(tǒng)治者,最終招來殺身之禍。洛陽太學(xué)院的三千太學(xué)生聯(lián)名請(qǐng)求赦免嵇康死罪,但是遭到了司馬昭的拒絕。在刑場(chǎng)上,嵇康索要了一把古琴,安然撫琴,并感慨道:“以前,袁孝尼一直想跟我學(xué)習(xí)《廣陵散》,都被我拒絕了。《廣陵散》要從此成為千古絕響了!”那年,嵇康才四十歲。據(jù)說,《廣陵散》這一曠世名曲,因聶政刺韓相而緣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絕世。
在音樂歌舞方面,隋煬帝楊廣造詣?lì)H高,尤愛燕樂,其醉心于此可謂達(dá)到了狂熱的地步。所謂燕樂,乃游宴時(shí)演唱的比較自由的音樂歌舞,又稱宴樂或俗調(diào)。楊廣在揚(yáng)州盡情享受聲色歌舞時(shí),曾寫下“長(zhǎng)袖清歌樂戲舟”(《江都宮樂歌》)的詩句。虞世南在《奉和幸江都應(yīng)詔詩》中寫道:“虞琴起歌詠,漢筑動(dòng)巴歈。”由此可見,揚(yáng)州在隋代就流行彈虞山琴,擊古漢筑,跳巴渝舞,唱巴渝歌。“后之聆《巴歈》,知變風(fēng)之自焉。”(劉禹錫《竹枝詞序》)
提到唐代揚(yáng)州,首先應(yīng)該想到李頎奉命出使清淮時(shí),在友人餞別宴會(huì)上“請(qǐng)奏鳴琴?gòu)V陵客”(李頎《琴歌》)。據(jù)《云仙雜記》記載,音樂家李龜年到岐王李隆范府上作客,偶聞琴聲,就斷定是揚(yáng)州美女薛滿彈琴。可想而知,薛滿彈奏的琴曲和風(fēng)格具有濃郁的地方風(fēng)味。
與琴相類的,是箏。現(xiàn)在揚(yáng)州古箏業(yè)方興未艾,其實(shí)唐代揚(yáng)州箏藝就已出名,揚(yáng)州美女薛瓊“箏得郝善素遺法,為當(dāng)時(shí)第一手”(《北窗志異》)。開元年間,薛瓊被征選入宮,其母薛媼,“以瓊瓊供奉內(nèi)廷,隨之長(zhǎng)安。”(《情史》)薛瓊曾在宮中為裴玉娥“授其箏法”(《綠窗新話》)。
揚(yáng)州的簫史,始于杜牧《寄揚(yáng)州韓綽判官》一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自從杜牧之后,在揚(yáng)州吹簫或者聽簫,就成了歷代騷客心馳神往的意境。
與簫相類的,是笛。據(jù)唐代李肇《國(guó)史補(bǔ)》記載,李舟生性好事,曾在鄉(xiāng)下發(fā)現(xiàn)一截竹子,堅(jiān)如鐵石,便制成笛子,送給李牟。李牟吹笛,當(dāng)時(shí)號(hào)稱天下第一。他在月夜江上吹奏此笛,其音嘹亮,上徹云表。“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發(fā)調(diào),群動(dòng)皆息。及數(shù)奏,微風(fēng)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怨嘆悲泣之聲。”有次,客人請(qǐng)李牟把笛子給他吹奏,其聲精壯,山河可裂,等吹到高潮時(shí),笛子應(yīng)聲粉碎,客人也不知所之,時(shí)人疑其為蛟龍。
唐代揚(yáng)州又多琵琶高手。徐鉉長(zhǎng)詩《月真歌》寫一位名叫月真的揚(yáng)州美人:“揚(yáng)州勝地多麗人,其間麗者名月真。月真初年十四五,能彈琵琶善歌舞。”月真長(zhǎng)得很美,“風(fēng)前弱柳一枝春,花里嬌鶯百般語”。她彈的曲子大抵是抒寫愛情的,“垂簾偶坐唯月真,調(diào)弄琵琶郎為拍”。
至于揚(yáng)州的歌手就更多了。杜牧《揚(yáng)州》詩云:“誰家唱《水調(diào)》,明月滿揚(yáng)州。”歷史上以唱《水調(diào)》出名的歌手,首推許和子。唐玄宗發(fā)現(xiàn)她音色優(yōu)美,召入后宮,封為才人,當(dāng)晚即行寵幸。不知是因許和子這個(gè)名字太俗,還是希望許和子在演藝上“推陳出新”,唐玄宗在枕席之間賜名“永新”。因?yàn)榘彩分畞y,永新從長(zhǎng)安逃難到揚(yáng)州。據(jù)《樂府雜錄》記載,將軍韋青雅好音樂,因?yàn)闈O陽之亂,“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欄于小河之上,忽聞舟中奏《水調(diào)》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duì)泣久之”。關(guān)于韋青和永新在揚(yáng)州的這一段亂世因緣,后來明代戲曲家汪廷訥曾撰雜劇《廣陵月》,加以鋪演。
唐代貞元年間,揚(yáng)州已有木偶戲。大司徒杜佑鎮(zhèn)揚(yáng)州時(shí),曾對(duì)幕僚劉禹錫說:“余致仕之后,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裥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堂堂大司徒以能看到傀儡表演就很滿足,可見當(dāng)時(shí)的傀儡藝術(shù)已很有欣賞價(jià)值。唐代盛期已有參軍戲。據(jù)唐范攄《云溪友議·艷陽詞》記載:“乃有俳優(yōu)周季南、季崇及妻劉采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云。”淮甸即今揚(yáng)州一帶。詩人王建寫的“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夜看揚(yáng)州市》),杜牧寫的“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yáng)州”(《題揚(yáng)州禪智寺》)等詩句,都分別描述了中、晚唐時(shí)期揚(yáng)州仍是一個(gè)載歌載舞的城市。
五代十國(guó)時(shí)期,揚(yáng)州是吳王楊行密的都城,后來又是南唐的東都,戲曲活動(dòng)沿襲唐代,仍以參軍戲?yàn)槭ⅰA耗┑蹠r(shí),吳王楊隆演和權(quán)臣徐知誥都親自扮演過參軍戲。據(jù)《五代史吳世家》記載:“知誥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
南唐后主李煜的大周后更是一位正史記載的琵琶能手,史載其父周宗是廣陵人。揚(yáng)州五代墓中,曾出土曲頸琵琶,為古代揚(yáng)州琵琶流行史提供了珍貴的實(shí)物。
宋代揚(yáng)州文藝生活仍很活躍。歐陽修在揚(yáng)州當(dāng)過“文章太守”,平山堂后有他著名的“六一堂”,六個(gè)一中就有琴一張,可見宋代的廣陵古琴亦不寂寞。名臣施昌言在真州(今儀征)任江淮發(fā)運(yùn)使時(shí),于城東筑東園,“嘉時(shí)令節(jié),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四方之賓客與往來者共樂于此。”有一次好友范仲淹來訪,他請(qǐng)范仲淹到后堂觀看“慢戲”。范仲淹得知是他的兒子與婢優(yōu)一同演出,似覺有失體統(tǒng),不觀而去。身為北宋重要官員的施昌言,不僅自己喜愛“慢戲”,還要自己的兒子與婢優(yōu)為伍,同臺(tái)演出,而且以此來招待賓朋好友(參見《宋史施昌言傳》)。可想而知,“慢戲”是當(dāng)時(shí)揚(yáng)州頗有名氣的一種戲曲。
元代,北方的雜劇演員紛紛南下。來揚(yáng)州演出的有翠荷秀、賽簾秀夫婦,朱錦秀、天錫秀母女,李芝儀之女童童等一批名擅一時(shí)的演員,被譽(yù)為“雜劇為當(dāng)今獨(dú)步”(夏庭芝《青樓集》)揚(yáng)州美女的珠(朱)簾秀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在揚(yáng)州演出了很長(zhǎng)時(shí)間,演出的劇目很多,能扮演各種男女角色,達(dá)到了“外則曲盡其態(tài),內(nèi)則詳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胡祗遹《朱簾秀詩卷序》)的藝術(shù)佳境。元雜劇著名作家關(guān)漢卿在揚(yáng)州曾與她相會(huì),觀賞了她的演出,在《南呂·一枝花·贈(zèng)珠簾秀》一曲中,盛贊她“出落著神仙”的高超技藝。元雜劇著名作家白樸、馬致遠(yuǎn)、趙天錫、侯正卿、喬吉、秦簡(jiǎn)夫、李直夫等也先后駐足揚(yáng)州,有些劇作家還以與揚(yáng)州有關(guān)的歷史文化名人或揚(yáng)州的社會(huì)生活創(chuàng)作出劇本,如喬吉的《揚(yáng)州夢(mèng)》、秦簡(jiǎn)夫的《東堂老》等。揚(yáng)州本地也涌現(xiàn)出劇作家睢景臣、李唐賓、陸登善、張善嗚、孫子羽等人,創(chuàng)作出《屈原投江》《梧桐葉》《梨花夢(mèng)》《杜秋娘》等10部劇作(參見《江蘇戲曲志·揚(yáng)州卷》)。這一時(shí)期,揚(yáng)州劇壇呈現(xiàn)出繁盛景象。
元末明初,浙江、福建一帶孕育出的南戲在揚(yáng)州已經(jīng)流行,有了演唱南戲余姚腔和海鹽腔的戲班(參見徐渭《南詞敘錄》、顧起元《客座贅語》)。爾后,雜劇逐漸衰微,而南戲日益興盛。進(jìn)入嘉靖、隆慶年間,陸續(xù)出現(xiàn)蓄養(yǎng)優(yōu)伶的家班。民間演劇活動(dòng)也十分活躍,民俗節(jié)日,婚喪喜慶,或宴請(qǐng)賓客,不時(shí)搭臺(tái)演出。揚(yáng)州還建起可供經(jīng)常演出的戲樓、戲臺(tái)。明嘉靖年間昆山腔新聲崛起后,迅速向各方傳播,江淮等地也“競(jìng)效吳腔”。從此,開始了昆劇在揚(yáng)州劇壇獨(dú)占鰲頭長(zhǎng)達(dá)一百多年的局面。
廣陵琴派起始于清代。徐常遇是清初順治時(shí)人,彈琴的風(fēng)格最初近于虞山派,是廣陵派的首創(chuàng)者。廣陵派后來對(duì)于傳統(tǒng)琴曲的加工、發(fā)展很有成就,但是徐常遇在當(dāng)時(shí)對(duì)待傳統(tǒng)琴曲卻非常慎重。他對(duì)“古琴曲傳至今日,大都經(jīng)人刪改”的情況,提出了“古曲設(shè)有不盡善處,可刪不可增”的原則。他認(rèn)為如果“大曲過于冗長(zhǎng)重沓”是允許“大加刪汰而成曲者”。他編有《琴譜指法》,康熙四十一年(1702)初刻于響山堂,以后又重刻于澄鑒堂,經(jīng)他3個(gè)兒子校勘成書,就是現(xiàn)存的《澄鑒堂琴譜》。他的長(zhǎng)子徐祜,字周臣。三子徐祎,字晉臣。他倆人年輕時(shí)曾去北京報(bào)國(guó)寺,“擁弦角藝,四座傾倒”一時(shí)京師盛傳“江南二徐”。康熙皇帝聞其名,召見暢春院。祜、祎對(duì)鼓數(shù)曲。弟兄三人中以徐祎的成就最大,他父親的琴書編輯出版,主要得力于他。李斗亦云:“揚(yáng)州琴學(xué)以徐祥為最。”(《揚(yáng)州畫舫錄》)。廣陵琴派自徐常遇、徐琪以來,“數(shù)百年間,綿延弗替,古樂浸衰之際,吾揚(yáng)琴派獨(dú)能超然長(zhǎng)存,可謂非一時(shí)盛世也”(張子謙語)。的確,廣陵派在其三百年的經(jīng)歷中,雖曾因時(shí)局動(dòng)蕩而時(shí)有起伏,卻能代代相傳、綿延不斷而直至今天,確是中國(guó)琴壇上并不多見的現(xiàn)象。
揚(yáng)州彈詞,亦稱揚(yáng)州弦詞。據(jù)李斗《揚(yáng)州畫舫錄》記載:“王炳文小名天麻子,兼工弦詞。”“人參客王建明瞽后,工弦詞,成名師,顧漢章次之。”當(dāng)時(shí)《玉蜻蜓》為揚(yáng)州弦詞的主要書目,名家有房山年、顧漢章,房山年為“郡中稱絕技……獨(dú)步一時(shí)者”說書名家之一;董偉業(yè)《揚(yáng)州竹枝詞》提到“顧漢章書聽不厭,《玉蜻蜓記》說尼姑”。后來名家還有朱天錫,函璞集英書屋《邗江竹枝詞》稱:“《玉蜻蜓》是朱天錫,‘十嘆’開言有淚痕。堂眷喜聽包節(jié)說,拿喬不肯說‘離魂’。”“十嘆”和“離魂”都是《玉蜻蜓》的關(guān)子書,唱者動(dòng)情,聽者神往。據(jù)焦東生《揚(yáng)州夢(mèng)·夢(mèng)中事》記載,乾隆年間,揚(yáng)州富豪喜彈詞,“延賓聚艷,重彈詞、攤黃家,愛其文也。至婦女消夏,則喜瞽女琵琶唱佳人才子傳奇。”徐珂《清稗類鈔·音樂類》亦載:“揚(yáng)故多說書者,盲婦傖叟,抱五尺檀槽,編輯俚俗語,出入富貴之家。列兒女嫗媼,歡咳嘲侮,常不下數(shù)百人。”至道光、咸豐年間,揚(yáng)州弦詞發(fā)展為二人對(duì)口,唱時(shí)加琵琶伴奏,稱“對(duì)白弦詞”。現(xiàn)代改稱“揚(yáng)州彈詞”。但至今還有一人表演和二人表演兩種形式,前者稱“單檔”,后者稱“雙檔”。
揚(yáng)州評(píng)話亦興起于清初,不久就形成了“書詞到處說《隋唐》,好漢英雄各一方”的繁榮局面,獨(dú)步一時(shí)的書目有《三國(guó)》《水滸》等10部,身懷絕技的著名說書家也有20人之多。到了乾隆年間,有的藝人根據(jù)自己的生活體驗(yàn)加工充實(shí)傳統(tǒng)節(jié)目,有的則創(chuàng)編新書。如屢試不第后成為揚(yáng)州評(píng)話藝人的葉霜林說演《宗留守交印》聲淚俱下,感人至深;浦琳編說《清風(fēng)閘》,塑造了以皮五辣子為代表的一批社會(huì)底層人物形象,影響深廣;藝人鄒必顯獨(dú)創(chuàng)新書《飛跎傳》,諷刺嘲笑統(tǒng)治階級(jí)中的顯赫人物,反映了受壓迫者的心聲,豐富了揚(yáng)州評(píng)話的表現(xiàn)內(nèi)容。上個(gè)世紀(jì)三十年代,上海七家電臺(tái)同播王少堂的《水滸》,與梅蘭芳、胡蝶等明星旗鼓相當(dāng),贏得了“聽?wèi)蛞犆诽m芳,聽書要聽王少堂”的贊譽(yù)。
揚(yáng)州清曲始于元,成于明,盛于清,又稱廣陵清曲、揚(yáng)州小曲、揚(yáng)州小唱等。據(jù)清代胡彥穎《樂府傳聲序》載:“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南曲習(xí)于南耳,故視北曲尤為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后,于南曲可以求之,別為‘清曲’,漸非元人之舊。”清代乾隆年間,李斗在其所著的《揚(yáng)州畫舫錄》一書中,對(duì)當(dāng)時(shí)揚(yáng)州清曲的演出盛況有一段詳細(xì)的記載:“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動(dòng)而歌。有于蘇州虎丘唱是調(diào)者,蘇人奇之,聽者數(shù)百人。”表明當(dāng)時(shí)揚(yáng)州清曲已經(jīng)流傳到很多地方。1956年,張氏彈詞傳人張繼青、張慧依、張慧祥、張麗曾組成“張氏彈詞小組”,編演了《聊齋》中的部分故事。此后,張慧儂、張慧祥分別在江蘇省曲藝團(tuán)、揚(yáng)州市曲藝團(tuán)傳徒授藝,擴(kuò)大了彈詞演員隊(duì)伍,編演了現(xiàn)代題材長(zhǎng)篇《龍馬精神》,中篇《李雙雙》,短篇《焦裕祿》等。
值得一提的是,揚(yáng)州孕育了京劇。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商江春家的“春臺(tái)班”與“三慶班”“四喜班”與“和春班”相繼赴京為乾隆皇帝祝賀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jìn)京促成了“國(guó)粹”京劇的誕生。而這“四大徽班”有的是在揚(yáng)州創(chuàng)辦的,有的是在揚(yáng)州組班進(jìn)京的,有的則是在揚(yáng)州走紅以后進(jìn)京的。因而,“京劇含有大量揚(yáng)州元素。”(翁思再語,參見《文化名人看揚(yáng)州》)
越劇也起源于揚(yáng)州。據(jù)王韜《潭堧雜志》記載,女子劇團(tuán)始于揚(yáng)州,名為髦兒戲。民國(guó)十二年(1923),浙江紹興藝人金云水仿而效之,招收一批年輕貌美的女子,辦起了一個(gè)女子戲班,由此而產(chǎn)生了越劇。
除了京劇、越劇,揚(yáng)州在民國(guó)年間還誕生了別具一格的揚(yáng)劇。不過,那時(shí)揚(yáng)劇還叫“維揚(yáng)戲”,又稱“揚(yáng)州戲”。民國(guó)八年(1919),香火戲藝人崔少華、胡玉海等進(jìn)入上海演出;不久,潘喜云、王秀清、陳宏桃、杭文奎、陳俊玉等也相繼抵滬獻(xiàn)藝,稱“維揚(yáng)大班”,外界稱其為“大開口”。民國(guó)九年(1920),揚(yáng)州花鼓戲部分藝人與鎮(zhèn)江花鼓戲藝人臧雪梅等組成風(fēng)鳴社赴杭州美記公司游藝場(chǎng)演出。此后,揚(yáng)州花鼓戲藝人常組班赴杭州演出。民國(guó)十年(1921),花鼓戲藝人呂正才等人應(yīng)邀組班赴上海“大世界”演出。上海一些演出娛樂場(chǎng)所也相繼邀請(qǐng)揚(yáng)州和鎮(zhèn)江的花鼓戲藝人去演出。揚(yáng)州和鎮(zhèn)江的花鼓戲藝人經(jīng)過磋商,決定將花鼓戲改名為“維揚(yáng)文戲”。外界稱其為“小開口”(參見《江蘇戲曲志·揚(yáng)州卷》)。爾后,“大、小開口”藝人進(jìn)入上海演出日益增多,民國(guó)十五年(1926),上海的維揚(yáng)大班已達(dá)十三副之多。民國(guó)十三年(1924),揚(yáng)州人陳登元在上海創(chuàng)立揚(yáng)州花鼓戲女子科班新新社,為揚(yáng)劇史上第一個(gè)女子科班。以后又培養(yǎng)出金運(yùn)貴、高秀英、潘玉蘭、王秀蘭等優(yōu)秀演員。民國(guó)二十年(1931)秋,“大、小開口”藝人在上海聚寶樓戲館聯(lián)合演出《十美圖》,自此雙方逐漸同臺(tái)演出,掛牌為“維揚(yáng)戲”。維揚(yáng)戲以“小開口”為基礎(chǔ),“大開口”藝人一般都改唱“小開口”,“大開口”戲僅偶爾演一下。“大開口”的“串十字”等常用曲調(diào),則成為維揚(yáng)戲音樂的組成部分。民國(guó)二十五年(1936),成立了“上海市維揚(yáng)戲協(xié)會(huì)”。此時(shí)維揚(yáng)戲班已發(fā)展至三十四副,擁有大小劇目近五百個(gè)。民國(guó)二十六年(1937)五月十三日,以《六十年之內(nèi)南京禁演揚(yáng)州戲》為題報(bào)道南京“禁演揚(yáng)州戲”。揚(yáng)州地方當(dāng)局也曾禁演維揚(yáng)戲。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一部分維揚(yáng)戲藝人曾沿江西逃至漢口,參加“抗日演出第四隊(duì)”,進(jìn)行抗日宣傳演出。與此同時(shí),一大批各具專長(zhǎng)的清曲名家相繼涌現(xiàn)。如工“窄口”的黎子云、王萬青以腔調(diào)柔美、感情深厚著稱于世。陸長(zhǎng)山的“窄口”清亮光脆,曾名噪上海。工“闊口”的鐘培賢嗓音洪亮,韻味濃郁,有“闊口之王”的美譽(yù)。周錫侯唱“闊口”蒼勁雄渾,稱之為“鋼喉”。朱少臣、陳淦卿的“闊口”活潑豪放,又稱“潑口”。其他還有尹老巴子、薩壽安、裴福康、葛錦華、張國(guó)寶、尤慶樂、馬福如等人皆各有所長(zhǎng),享有盛譽(yù)。在操樂器方面也出現(xiàn)了不少杰出人才,如施元銘精通琵琶,被譽(yù)為“琵琶圣手”;朱少臣的撞酒杯,盧國(guó)才的敲瓷盤,皆為一絕。
新中國(guó)建立后,各地的維揚(yáng)戲藝人迅速恢復(fù)演出,揚(yáng)州成立了第一個(gè)維揚(yáng)戲聯(lián)合共和班。1950年1月,由蘇北行政公署決定,維揚(yáng)戲正式定名為“揚(yáng)劇”。從此,這朵扎根于古運(yùn)河畔和長(zhǎng)江邊的藝術(shù)之花,邁入了芳華煥發(fā)的年代。揚(yáng)劇的音樂大量吸取了揚(yáng)州清曲的曲牌和地方的民歌小調(diào),曲調(diào)很豐富,共有一百多種,常用的有《探親》《補(bǔ)缸》《剪剪花》《銀紐絲》《侉侉調(diào)》《老鮮花》《武城調(diào)》《數(shù)板》《串十字》等。很多藝人根據(jù)演出劇情的需要和各自的嗓音條件、唱腔特點(diǎn),從兄弟劇種吸取或自身改進(jìn)、發(fā)展了很多新腔。如《大陸板》《滿江紅》《漢調(diào)》等。又如《梳妝臺(tái)》這一曲調(diào),成為今天揚(yáng)劇舞臺(tái)上最常用也是觀眾最愛聽的曲調(diào)之一。
誠(chéng)然,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隨著歷史的進(jìn)程,所有的戲曲種類都處在成長(zhǎng)、裂變、嫁接、消逝和新生之中,揚(yáng)州戲曲也不例外。揚(yáng)州諸多戲曲進(jìn)入“非遺”名錄,重新震撼了揚(yáng)州市民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