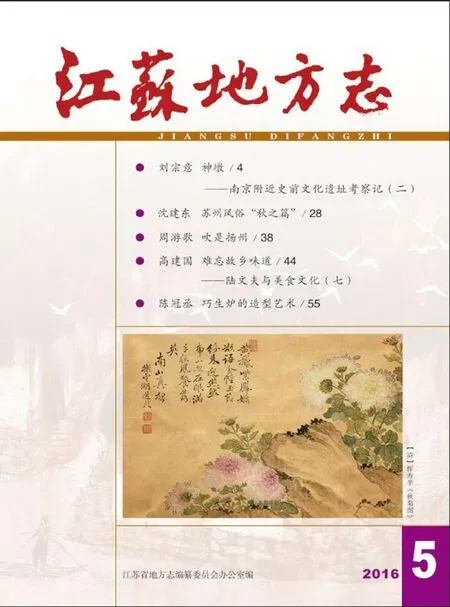只因?qū)@片土地愛得深沉——讀《常熟閑話》
◎ 沈秋農(nóng)
只因?qū)@片土地愛得深沉——讀《常熟閑話》
◎ 沈秋農(nóng)

讀袁文龍先生新著《常熟閑話》(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7),如同少兒時代看“拉洋片”,一詞一景物,一詞一典故,景物多彩而主題鮮明,典故生動又倍感親切。常熟,研究方言者代有傳人。明嘉靖年間,常熟有個叫孫樓的藏書家,將蘇州、常熟的方言字詞搜輯成書,名曰《吳音奇字》,至萬歷崇禎間,同鄉(xiāng)陸鎰對該書作了重編增補,使其益臻完善。民國年間,蘇州圖書館據(jù)鐵琴銅劍樓清鈔本排印,將其編入《吳中文獻小叢書》,一直流傳至今。當代常熟,又有多部方言專著問世,如《吳方言詞典》《吳方言詞考》《常熟方言詞典》《常熟方言詞匯》等,為保存、傳播地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作出貢獻。但這些專著對所輯方言均作條目式介紹,因文字簡潔難于對詞義作深入解讀,而文龍先生的《常熟閑話》與上述各書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對具體詞目的介紹如同說書一樣,抽絲剝繭,娓娓而談,將流傳千年,被一些人認為土得掉渣的常熟方言講析得入情入理,細膩文氣。一壺茶一卷書,窗下細讀,常令人開懷一笑或額手稱奇。何以至此,筆者意為可用有趣有心有情來解釋。
方言是語言的變體,根據(jù)性質(zhì)可分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常熟方言當屬吳地方言。著名語言學家吳宗濟指出:“吳方言的詞匯及語音特色,中古以來就侈讀于士林,散見于傳記。從六朝的子夜吳歌到清末的方言小說,資料之豐富超過任何其他漢語方言。”成書于清嘉慶年間的《何典》就是一部用吳方言寫成的諷刺小說,劉半農(nóng)以為,此書特色“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并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在吳文中,也恰恰是如此。”所謂吳文就是指吳地方言了。有評論說該書所用方言為上海松江一帶,但也有專家認為,該書全文均以常熟方言寫成,并專門做了2000多條注釋,取來一讀,真叫人忍俊不禁,書中無論人物的談吐舉止,還是情景描述都充滿大俗而見諧趣。
趣者,興味也。生趣、興趣、情趣、妙趣,以“趣”組詞者達數(shù)百之多。各地方言不同,上海、蘇州、無錫、常州、江陰、常熟……雖同屬吳地,然方言各有特色,或嗲,或糯,或團,或犟,或硬,或土,細細聽來,趣味無窮。即使在常熟一地,東南西北,就有明顯差別,如辛莊和橫涇、藕渠和老城區(qū)、福山和滸浦……之口音就大相徑庭,可謂十里不同音,對有心研究者來說堪稱興之所至,樂趣盎然。方言源自生活,與社交、勞動、生活密不可分,是思想、情感、民俗、文化的生動反映。據(jù)文龍先生考究,常熟方言與泰伯、仲雍奔吳讓國,輸入中原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經(jīng)過歷史的撫摸與文化的浸潤,常熟方言又有著三千年古文明的沁色。試以“吃”字為例,按字面解釋,自然是為了滿足飲食需要,但在常熟方言中,除了滿足飲食需要外,還有更豐富的意思,如書中所提“吃苦頭、吃牌頭、吃擱頭、吃癟、吃準、吃價、吃著份量……”,這里的“吃”,雖與物質(zhì)需要毫無干系,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是經(jīng)常應用,且感到生動形象而得以廣為流傳。若問何以如此,且聽細細“講章”。講章者就會將個中因由細細說給你聽,顯得理趣交融,言意共生,給人出口成章之良好印象,因此將“說話”說成“講章”則又是常熟方言中的文化特色。因此,方言二字,筆畫雖然簡單,卻是學問無數(shù),自然也就引來有心人為之探趣考究,而文龍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有心人。
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兒的心指的是意識,是精神世界,心欲令其行。在旁人看來,常熟話既無上海方言的嗲,也沒有蘇州方言的糯,顯得很土,但文龍先生卻認為正因為土,而顯得質(zhì)樸、實在、淳厚、本色,大有研究之必要。該書看似“閑話”,卻是對常熟方言研究的“一本正經(jīng)”。作者潛心于對常熟方言的搜集、研究、解讀,在揮筆成文時他并不滿足于對方言中某個詞的意思的基本解釋,而是尋根探源,盡其所知向讀者介紹這個詞的由來、寓意,又舉例說明該詞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如“清官吃麥粥”,文龍先生就給讀者講了這么一個故事:明代永樂年間,常熟進士魚侃先后官拜刑部、工部主事,并一度出任開封知府,雖官居要職,卻清正廉潔。退職歸里,清貧如洗,日常生活只能以麥粥度日。老妻每煮好麥粥常呼:“清官,來吃麥粥吧!”因此,“清官吃麥粥”也就成了常熟百姓贊美清官的口碑詞、口頭語。一句方言,一個故事,一種美德。文龍先生就是這樣一個有心人,將研究方言與研究歷史結(jié)合起來,使讀者理解了方言,也了解了鄉(xiāng)賢,學習了美德。又如“摸著白席角”,則告訴讀者,白席即夏季鋪在床上的草席,摸著白席角,則是指民間喪俗,舊時,人死后,家人會在門板上鋪上白席,陳尸數(shù)日,供人吊唁,入殮前,會剪下一只白席角放到“斷七”時,與其他紙錢物品一起焚化,而作為喪禮結(jié)束之標志。引申到現(xiàn)實生活中,有違法犯罪者直到身陷囹圄才感到后悔,被稱為“摸著白席角”,但已悔之晚矣。兩句方言一正一反,倡導什么,告誡什么,可謂涇渭分明,寓意深刻。為了使讀者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對常熟方言有更全面的了解,作者還就常熟話中的“眾生相”“幽默感”“市井風”作了專題介紹。文龍先生在解讀常熟方言時給人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感覺,解讀、尋源、舉例,集邏輯性、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于一體,開創(chuàng)了傳播解讀常熟方言的新方法、新形式。
情由心生。方言,作為一個地方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維系著數(shù)千年來常熟人的歷史、文化、情感,口口相傳,代代相承,盡管許多人從年輕時外出或接受高等教育,或走南闖北,但一開口仍是滿口鄉(xiāng)音。前國務院顧問、原外貿(mào)部部長、中科院資深院士李強,中學時代就在杭州、上海求學,也曾赴蘇聯(lián)工作多年,又數(shù)十年在北京任職,被京腔京韻所包圍,但他一開口仍是常熟方言,真的是“鄉(xiāng)音未改鬢毛衰”。前年仲夏,筆者一行4人拜訪著名電影導演嚴寄洲,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與嚴老以鄉(xiāng)音交流,一下子拉近距離。臨別時老人一句“再講講常熟話”的鄉(xiāng)音更盈溢出老人對家鄉(xiāng)的深刻思念。文龍先生雖祖籍紹興,但自幼生活在常熟,由此與常熟結(jié)下不解之緣,出于對文化的熱愛,而始終傾心于對常熟歷史文化的研究。又因其常在市電視臺開講常熟掌故,被譽為“常熟老百曉”。常熟人文歷史悠久深厚,尤其生活在當下的高學歷者成千上萬,他們每個人都對家鄉(xiāng)常熟懷有深厚感情,愿意為常熟的美麗繁榮奉獻力量。因此,文龍先生潛心于常熟方言的研究,并非“情結(jié)”二字就能作精度概括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對常熟方言的保護、傳承如此盡力呢?那就是文化自覺與社會擔當。因酷愛于常熟文化,而對其歷史淵源、特色亮點、價值效益、生存狀態(tài)予以格外關注,因其繁榮而欣悅,因其銷蝕而憂慮,因感奮而為之歡呼,因惋惜而傾心呵護,這就是文龍先生的責任擔當。《常熟閑話》的出版體現(xiàn)了文龍先生對生活的熱愛之心,更體現(xiàn)了對常熟文化的厚重深情。行文至此,拙文標題也就躍然流出——“只因?qū)@片土地愛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