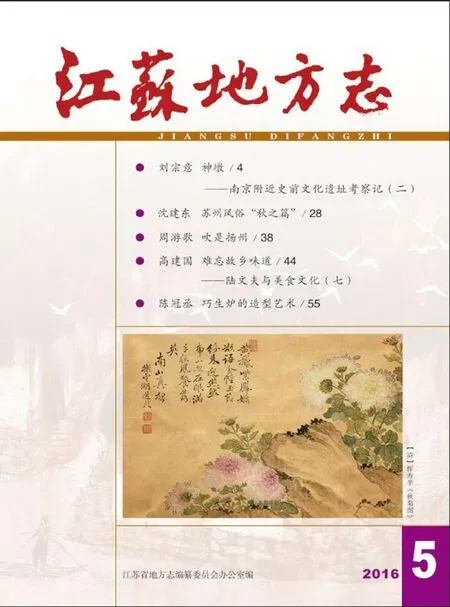1931年7月:洪水襲擊南京城
◎ 經盛鴻
1931年7月:洪水襲擊南京城
◎ 經盛鴻

1931年夏秋間,正是中國危難重重的時期:國內連年內戰,戰禍不斷,民生艱難;日本正虎視眈眈、劍拔弩張,準備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南京的國民政府正處在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中。就在這時,在長江、淮河流域發生了多年未見的嚴重的大水災,造成了極其慘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損失。國都南京也遭受了一場浩劫,空前嚴重的洪災襲擊了南京城及其郊縣廣大地區。
這年入夏以后,當長江上游暴雨成災、滔滔洪水沿江而下威逼南京之時,南京地區則自7月4日到12日,連續九天,大雨滂沱,電閃雷鳴,白晝如晦。在狂風暴雨的沖擊下,南京城內許多房屋倒塌,未倒的房屋也門窗玻璃碎裂,市民驚呼的聲音此起彼伏,在風雨中倍感凄厲。長江中主、客水會合,水位暴漲,南京一帶的長江江面寬達十公里,水面高出兩岸陸地一、二尺,濁浪滔天,聲勢嚇人。南京城東北的玄武湖承受鐘山狂瀉而下的山洪,湖面迅速提高,很快高出城內平地。長江與玄武湖的洪水交匯,一齊灌進市區,南京全城遍地皆水,下關一帶因瀕臨長江,水勢更大。江、湖、河中的魚游上了馬路(參閱《民國日報》1931年7月6日報道;《大公報》1931年7月13日報道等)。
到7月下旬,南京地區大風大雨天氣連續二十余天仍未停止,雨量達618.3毫米,比常年同期平均雨量多出423.9毫米,(《時事月報》第5卷第158頁,1931年9月出版),突破了南京地區在近一百年間雨量最高紀錄。在此期間,先后有六次風暴從南京地區呼嘯席卷而過,風暴次數是前十年間7月颶風過境平均次數的五倍。低氣壓和風暴形成了罕見的低溫天氣,南京地區在7月盛夏期間的平均氣溫只有24.6℃,比常年7月平均氣溫低3℃(《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頁、第136頁)。7月23、24兩日,雨勢特大,暴風雨與洪水交加,沖毀了下關一帶四千多家貧苦市民的棚戶,災民哭喊之聲驚天動地(《民國日報》1931年7月25日報道)。上海《申報》在1931年7月28日報道南京災情說:“(南京城)南北及下關積水,日甚一日。下關方面沖要路面,悉被沖毀,中山碼頭至挹江門一帶,水深過膝。中央黨部(按:今湖南路省軍區所在地)、三牌樓、黃埔路等處竟達胸部。城南秦淮河兩岸,大石壩街、夫子廟等處,水已浸入住屋”。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中一些中央軍政大員在自己的日記中也留下了一些有關此次南京大水災的慘痛記述。如蔣作賓,于7月28日從江西乘船回到南京,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五時抵下關碼頭,街市多沒水中。進城至成賢街附近,則一片汪洋。余之住宅亦進水尺余,因此地多系堰塘,現多填平建筑,修筑馬路亦不修溝道,故水無處消納,亦無處排泄,將來勢必臭污濕氣上蒸,恐不免轉為瘟疫矣”(《蔣作賓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頁)。他不僅記載了當時南京水災的嚴重,而且暴露了當時南京市政建設中的嚴重弊病及其在洪災中的危害。
另一位國民黨元老邵元沖,在7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傍晚驅車到陵園太平門外視察水勢,農田、廬舍損壞甚多,為之惻然。又至玄武門外五洲公園(按:即玄武湖公園),見城外十余丈處堤岸,均為水淹沒,一片汪洋,城內登城垣之石階亦沖毀一段,不能登涉”(《邵元沖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頁)。

《邵元沖日記》書影
南京城內遍地皆水,房倒屋塌。南京城外廣大農村則是一片汪洋,顆粒無收,景象更是凄慘。《新京日報》所刊《南京近郊水災紀實》一文,報道了江寧縣秦淮河兩岸的水災情景:“秦淮河沿岸百數十里,均屬圩田。自7月4日起至12日止(農歷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大雨滂沱……其被災區域,上自江寧縣第七區之謝村,下至長江與南京,長凡百余里,兩岸本有薄堤,此次因連日大雨,山水齊發,河水陡漲三丈余,雖經農民搶救,各圩仍相繼潰決,淹沒田畝達數十萬畝”(轉引自《長江水利史略》,水電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頁)。江寧縣縣長冷某在8月29日“致華洋義賑會快郵代電”中,報告了8月25日該縣沙洲圩、江心洲又先后潰決的慘景,“以此災情慘重,為空前所未有,……遍地哀鳴,驚心慘目”(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31年江蘇大水災檔案資料選輯》,《民國檔案》1991年第4期第28—29頁)。八卦洲災民代表在“致華洋義賑會”的一份呈文中說,該洲“上年曾經被水,今夏七月二十三、四等日復被大水,不特收獲俱無,亦且房屋盡沒。迨八月二十六、七,水復盛漲,儼是陸沉,內洪外潮,雜然交厲,爾時房屋家什牲畜一洗無余,沖入江流者老弱為魚,死亡甚多,凄慘之狀業于中外報端幾經詳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31年江蘇大水災檔案資料選輯》,《民國檔案》1991年第4期第28—29頁)。
在長江以北的江浦、六合兩縣,也遭到了洪水的洗劫。江浦縣“面臨大江,后毗皖境”,在7月一直淫雨不止,到7月23、24兩天,“大雨傾盆,接宵連旦,兼之皖北八百里黃山,蛟洪四溢,直瀉而下,所有圩田埂堤,均被沖潰,即平地村鎮如汶河、東葛、永寧、湯泉等鎮,亦莫不水深數丈,以至津浦路基,被水沖斷十余里,為之停車四、五日。一片汪洋,無分界域,人畜器物,漂沒無遺”(上海《申報》1921年8月28日、1931年8月4日報道)。江浦縣湯泉鎮的基督會致華洋義賑會函中說,該鎮近幾年“兵災迭見,匪禍重逢”,而在1931年7月“大雨連朝,洪水暴漲,街鄉地面俱成澤國,高低圩田一白無際,高埂農家,屋舍沖毀,木料全無,家具完全漂沒。最慘者救命呼聲盈耳,……尸橫于水面者不可屈指矣”(《民國檔案》1991年第4期,第27頁)。六合縣水災也是觸目驚心。該縣自1929年“全境赤地大旱”后,在1931年又“降此八十余年來未見之水災”。六合地理地勢,“西北鄰皖多山,東南濱江,滁河中貫,西去東來,為惟一宣泄水道,容量本隘,又因失修淤墊,忽遇上月(按:指1931年7月)江日起,兼旬以上,晝夜不止,勢如傾盆之大雨,山洪暴注,江潮復漲,以致放濫四溢”,全縣圩田,較低之山田幾乎全部沖毀淹沒,“全災田畝在四十萬畝以上,超過全縣田畝總額之半數”,其余田畝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災害。“登高極目,盡成湖蕩,炊煙斷絕,雞犬無聲”“全縣三十六萬民眾無一能免”,都遭到各種傷害損失。
(《民國檔案》1991年第4期,第27頁。)
1931年的嚴重水災給南京城鄉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苦難。據當時有關部門統計,在這次水災中,僅在南京城區與近鄰,“災戶為10031 家,口數為38787人。災民啼饑號器,備極凄傷。綜計京市田地,多被淹沒,農作物之損失,約及十分之九”(《時事月報》第5卷第158頁,1931年9月出版)。
然而,正當南京與中國廣大地區的災民們家破人亡、啼饑號哭之時,日本軍國主義乘機于1931年9月18日發動沈陽事變,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場更大的災難襲向南京與中國。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民不斷蒙受災難與恥辱的歷史;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英勇奮斗、前赴后繼、與各種自然災害與外敵入侵作斗爭并最終取得勝利、走向民主、繁榮與近代化的歷史。南京地區的近代史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