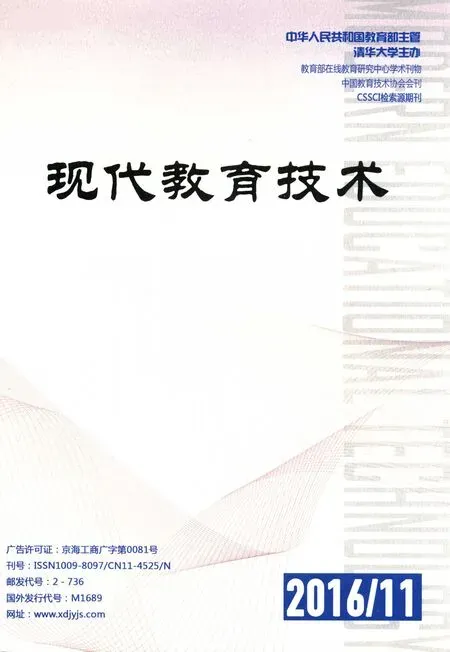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的探究*——以北京化工大學為例
劉小梅
?
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的探究*——以北京化工大學為例
劉小梅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北京100029)
混合式教學(B-learning)是傳統教學(Face-to-face Learning)與網絡化教學(E-learning)優勢互補的一種教學模式。文章介紹了北京化工大學的視聽教學現狀,并基于混合式教學和翻轉課堂理論,設計了“網絡自主學習+翻轉課堂+傳統教學”的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旨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主性與視聽說課的效率。同時,文章對北京化工大學2015級148名非英語專業的本科生進行了為期兩個學期的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的實驗教學,并對教學效果進行了驗證與分析,以期為混合式教學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鑒。
網絡自主學習;翻轉課堂;傳統教學;混合式教學;大學英語
一研究背景
1學校視聽說教學現狀
北京化工大學(下文簡稱學校)于2006年開始實施大學英語視聽說網絡自主學習。自2012年9月起,學校將大學英語課時從256學時減至192學時,每學期的聽力課設為16學時。網絡自主學習成為學生增加語言輸入、彌補視聽說課課時不足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機考(下文簡稱“網考”)成績+網絡自主學習過程分占總評成績的10%。這種學習方式存在缺陷:①學習效果不佳。根據針對2014級146名學生的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可知逾三成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從網上下載答案。②指導不到位。面對機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問題時得不到及時解決。
學校傳統視聽說課使用的教材是《新標準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1][2](下文簡稱《新標準》)。這種教學模式亦存在不足:①難以做到因材施教。根據針對2014級146名、2015級137名學生的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可知逾三成學生在中學沒有上過聽力課。視聽說課的一本教材難以滿足學生不同層次的需求。②口語考試不夠客觀。在實驗室錄音考試中,教師只是根據學生的錄音打分,并未對其口語能力進行反饋;教師與學生進行一對一的口語考試,其評價方式單一,不足以全面挖掘學生的學習潛能。
2 混合式教學和翻轉課堂理論
混合式教學是指網絡線上與線下的混合,通過引進面對面教學來改進E-learning的不足[3]。何克抗[4][5]在我國首次提出混合式教學概念,認為混合式教學把傳統教學方式的優勢和網絡化教學的優勢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教師引導、啟發、監控教學過程的主導作用,又要充分體現學生作為學習過程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張其亮等[6]對混合式教學的理解是:①教學形式上,它是傳統面對面教學與網絡教學的結合;②教學技術上,它基于Web技術,結合視頻、音頻、文本、圖形、動畫等多種多媒體技術;③教學手段上,它是傳統手段與信息技術手段的結合;④教學目標上,它需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地位,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⑤教學評價上,它是過程評價、結果評價等多種評價方式的結合。
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是一種借助現代化信息技術,將傳統學習過程翻轉過來的教學模式。自從Bergmann和Sams采用“翻轉課堂”教學模式以來,該模式在美國已為越來越多的學校所接受。中國教育界也對翻轉課堂教學模式進行了研究及實踐應用,如嚴姣蘭等[7]等嘗試將該模式應用于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
3研究思路
根據上述混合式教學和翻轉課堂理論,本研究將“網絡自主學習”、“翻轉課堂”、“傳統教學”三者結合,設計了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旨在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以提升學生的語言輸入質量;通過在傳統視聽說課中加入“翻轉課堂”模式,以達到因材施教;通過在口語考試中引入互評機制,以挖掘學生的潛能。
二實驗教學的研究設計
1 二語習得理論依據
除了混合式教學與翻轉課堂理論,大學英語視聽說課因其學科特色還需要二語習得理論加以補充——本研究中的小組活動、腳本互改、口試互評等,皆基于二語習得理論而設計。
(1)互動假說(Interaction Hypothesis)
互動假說又稱為“輸入、互動和輸出模型”。2007年,Gass等[8]提出了該假說的整合模式,將二語習得分為四個階段:①被感知的輸入階段。被感知的輸入為下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可能,而學習者獲得被感知的輸入受四個因素的影響,即輸入的頻率、原有的知識、情感因素和注意力;②被理解的輸入階段。學習者經過意義協商,在和本族語者的交流過程中對語言進行調整;在原有知識和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UG)的作用下,被感知的輸入轉變為被理解的輸入。③吸收階段。吸收指的是協調語言輸入和語法知識的一種心理活動。在這個階段,學習者首先對語言知識進行心理加工,輸入的信息與學習者已經內化的原有知識形成對比;然后,學習者對語言知識進行概括,形成記憶鏈——這個過程也是石化現象產生的源頭之一。④整合階段。語言知識被吸收之后,在學習者內部進行整合。整合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新的語言知識發展為學習者的內部語法,一種是新的語言知識被儲存以待進一步加工。
(2)輸出驅動假設(The Output - driven Hypothesis)
2013年,文秋芳[9]提出“輸出驅動假設”,包括:①就教學過程而言,輸出比輸入對外語學習的內驅力更大,輸出驅動不僅可以促進接受性語言知識的運用,而且可以激發學生學習新語言知識的欲望;②就教學目標而言,培養說、寫、譯等表達性語言技能更符合社會的需求。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筆者任教的北京化工大學2015級148名非英語專業普通班(非快班、非慢班)的本科生,分為材料1501-03、高材1507-08、化工1506-07三個班。
3 測量工具
本研究的測量工具包括:①受試者的入學成績;②聽力成績,包括受試者參加《新視野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下文簡稱《新視野》)第一冊[10]、第二冊[11]的網考成績,大學英語C、B級期末考試聽力客觀成績(不包括聽寫);③C、B級口語成績。
三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的構建
根據Tyler[12]提出的課程框架的四要素論(包括目標、內容、內容呈現方式、評估),本研究設計了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其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流程圖
1教學目標
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使其在今后的學習、工作和社會交往中能用英語有效地進行交際,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其綜合文化素養,以適應我國社會和國際交流的需要[13]。
2教學內容
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的核心是“網絡自主學習+翻轉課堂+傳統教學”。就教學內容來說,網絡自主學習使用的是《新視野》,翻轉課堂使用的是自行補充的視頻材料和《新標準》部分內容,傳統教學使用的是《新標準》和六套活頁聽力練習(此練習與四級題型接近)。
3 內容呈現方式
(1)網絡自主學習
網絡自主學習的流程包括兩個部分:①教師方面:發布計劃→跟蹤進度→線上答疑→收集學生自評報告→課內分析問題;②學生方面:制定計劃→按進度學習→填寫自評報告→課內回答問題→網絡機考。教師于每學期伊始發布學習計劃,要求學生一周半完成一課。每冊書共10個單元,學生學完可獲學習過程分5分;未按進度完成或少完成一課,就扣0.5分。教師定期檢查學生的學習進度,觀察其上機時間以判斷是否認真完成學習任務;收集學生的自評報告,觀察其學習動態并線上答疑;對學生存在的共同問題(如語法結構問題)在課上予以講解。學生按進度完成網絡自主學習,填寫自評報告(內容包括聽力能力的自我評估,完成一課所需的時間,每周上機的次數、正確率、存在的問題等)。此外,學生亦可通過短信、微信與教師交流。
(2)翻轉課堂+傳統教學
“翻轉課堂+傳統教學”視聽說課的教學流程如圖2所示。

圖2 “翻轉課堂+傳統教學”視聽說課的教學流程圖
學校學生的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故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應理解并尊重學習群體中學習能力的多樣性,提供如何獲取技能與信息的選擇[14]。為此,“翻轉課堂+傳統教學”課每次增加與話題相關的視頻2~3個,每個長度約5~6分鐘,取自CCTV Dialogue、VOA News、BBC News等。上述補充內容難易程度不等,供受試者自學。此外,教師對《新標準》的使用也進行了適當調整,如讓受試者課前自學該書Inside View部分并組織短劇表演。
根據“互動假說”,語言學習是迫于交際壓力而產生的,互動研究就是要檢驗交際和習得之間的關系并協調這二者之間的注意、意識等認知機制。Gass等的研究結果證實了輸入與互動對語言習得的促進作用——在互動過程中,意義協商尤其是通過協商觸發的本族語者所產生的互動調整能促進語言的習得,因為意義協商能有效地把輸入、學習者的內在能力(尤其是選擇性注意)、輸出這三者聯系起來。
本研究讓受試者通過小組形式交談、討論、評估,每組有6~7名成員。小組互動有助于受試者建立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聯系,形成記憶鏈,并將網絡自主學習、翻轉課堂的輸入變為內化的知識,再以輸出的形式表現出來。下面是具體的實施步驟:
①課前。教師提供補充視頻、設計問題、下達自學任務。補充視頻以Cyber Security Report(選自CCTV, China 24,2016年1月4日)為例,所設計的問題一是:How many pieces of information could have been leaked from websites across China? 問題二是:Who fight against those hackers?這些視頻內容貼近現實,易于引發學生興趣,便于口語練習。具體做法是:讓受試者線上或課下學習補充內容,回答所提出的問題,記錄觀看視頻時所遇到的問題以便課堂討論。
②課堂。教師先用20分鐘與受試者討論視頻中的問題,再用10分鐘提問《新視野》中的相關問題,如:What’s your problem of meeting people?(《新視野》第一冊第三課)How is fashion decided?(《新視野》第二冊第六課)
之后,剩下的60分鐘用于傳統教學活動。其中,《新標準》的Outside View部分重點開拓受試者的視野,以了解西方文化;活頁試題則重點訓練聽力策略,如聽前預測,對所聽信息進行判斷、推理,根據上、下文猜測,根據意群進行理解等——這兩部分內容需課上精聽、精講。最后,教師組織短劇表演或展示受試者的優秀視頻作業。
③課后。教師布置口語作業,如“My University Days”、“An Event in the Spring Festival”。受試者根據話題,撰寫腳本,錄成視頻。在視頻錄制之前,小組成員之間需彼此修改腳本,原因在于“語言輸出活動通過促進學習者的自我意識和有意識的加工從而對二語習得產生促進作用”[15]。之后,教師觀看受試者提交的視頻作業,對其口語表現以錄音形式進行點評(包括糾正發音、語法錯誤等),最后將視頻作業返還受試者。
4 評估
《新視野》網考占總評成績的5%,過程分占5%。口語考試占5%。聽力評估作為期末考試的一部分,占期末考試成績的30%——其中,客觀成績占20%,聽寫占10%。
網考每學期進行1次。試題出自《新視野》,試題長度約40分鐘,滿分為50分。
口語考試采用動態評價方式,主要是評價者的介入與互動。口試以小組形式進行,口試評分標準如表1所示,評分標準提前發給受試者。口試題目涉及課本內容,分為自述和問答兩個部分——發言者在自述部分達到表1的某個級別,就以該分數作為參考;在問答環節,如果發言者沒聽懂問題,回答問題不準確、有語法或詞匯錯誤等,就分別扣0.1分。

表1 口語考試評分標準
注:口語考試評分標準參考了《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16]的標準。
C級口試形式為:被試者首先自述,再由教師提出2~3個問題;其他成員對被試者的口語表現進行評價,然后打分。B級口試形式為:每組成員分為提問者與聽眾;被試者首先自述,再由3~4名成員分別提問,之后教師提問;聽眾為被試者打分。需要指出的是,B、C兩級的口試均進行了全程錄像;由于互評尚處于試驗階段,故只將師評分數計入總評成績。
四實驗教學的數據統計與分析
1 入學分級成績
2015級入學分級試題由北京市統一命題,受試者的成績如表2所示。全年級的入學平均分為52.7分、聽力平均分為12.6分,而受試者的入學平均分為54.2分、聽力平均分為12.7分,由此推出受試者的成績在全年級屬于中等偏上。

表2 入學分級成績(滿分為100分)
2 聽力成績與相關系數
受試者的《新視野》第一冊、第二冊網考成績與期末聽力客觀成績如表3所示。為了檢驗《新視野》的學習效果,本研究將上述成績進行了相關系數分析[17],如表4所示。

表3 《新視野》網考成績(滿分為50分)與期末聽力客觀成績(滿分為20分)

表4 相關系數統計
3 口語考試成績
C級、B級期末口語考試成績如表5所示。

表5 期末口語考試成績(滿分為5分)
4 數據分析
表3數據顯示,受試者聽力的正確率由入學時的63.5%上升至71.1%;表4中網考2與B級的相關系數顯示,網絡自主學習成績與期末聽力客觀成績正相關——這說明大多數人認真自主地學習了《新視野》;特別是材料1501-03班,其入學時的總分與聽力平均分最低,但相關性最強,這說明學習第二語言的動機是學好語言的關鍵因素。表5數據顯示,互評與師評的分數較為接近;在B級口試中,同伴的評價更為審慎,說明同伴互評的方式值得嘗試。表5數據還顯示,受試者的口語能力在提高。
五結論
通過受試者與教師在線上、線下的互動,受試者網絡自主學習的輸入更為有效,以往在網考前集中突擊學習進度的現象幾乎消失。“翻轉課堂+傳統教學”增強了聽力基礎薄弱者的信心,而小組討論、視頻錄制等語言輸出活動激發了受試者新的學習欲望;受試者參與評價可喚起其自我意識,而同伴的評價與反饋有助于受試者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反思與調整,故有利于受試者批判思維能力的培養。研究表明,通過采取新型混合式大學英語視聽說教學模式,受試者的自主學習能力有所增強,其聽、說能力隨之提高。但該模式亦存在不足:①口試的信度——口試的評分標準與打分信度仍需完善;②工作量大——教師1人面對148人,口試時間長,尋找補充材料也需花費很多精力。針對上述不足,本研究擬采取如下措施:①制定更為科學的口試標準,使其操作性更強;同時,從過往的口試錄像中選取樣本,標出水平級別,向學生展示以增加打分的信度。②建立音、視頻資料庫,以選取優質視頻材料。目前,該模式尚處試驗階段,期待該模式的探究能為其他研究者提供借鑒。
[1](英)Greenall S,文秋芳.新標準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第一冊)[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1-127.
[2](英)Greenall S,文秋芳.新標準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第二冊)[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1-126.
[3]田富鵬,焦道利.信息化環境下高校混合教學模式的實踐探索[J].電化教育研究,2005,(4):63-65.
[4]何克抗.從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術理論的新發展(上)[J].電化教育研究,2004,(3):1-6.
[5]何克抗.從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術理論的新發展(下)[J].電化教育研究,2004,(4):22-26.
[6]張其亮,王愛春.基于“翻轉課堂”的新型混合式教學模式研究[J].現代教育技術,2014,(4):27-32.
[7]嚴姣蘭,張巍然,于媛.視聽說課程翻轉課堂校本教學的改革與實踐[J].現代教育技術,2016,(2):94-100.
[8]Gass S M, Mackey A. Input, interaction, and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 Vanpattern B, Williams J.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99-175.
[9]文秋芳.輸出驅動假設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思考與建議[J].外語界,2013,(6):14-22.
[10]鄭樹棠,王大偉.新視野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第一冊)[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1-162.
[11]鄭樹棠,王大偉.新視野大學英語視聽說教程(第二冊)[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1-162.
[12]Tyler R W.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1.
[1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1.
[14]Kinsella K. Understanding and empowering diverse learners in ESL classrooms[A].(英)Reid J M. ESL/EFL英語課堂上的學習風格[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193.
[15]文秋芳.二語習得重點問題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64.
[16]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學習、教學、評估[Z].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60.
[17]韓寶成.外語教學科研中的統計方法[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126-131.
編輯:小米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Blended Visual-aural-oral Teaching Model for College English——Taking Beij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LIU Xiao-mei
Blended learning is a teaching model of the mutual compensation for advantage of both face-to-face learning and E-learning. The paper introduc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dio-visual teaching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designed a new type of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he model was a combination of web-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 face-to-face learning and aimted at improving students’ autonomy in their E-learn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visual-aural-oral course. This model was tested for two terms on the 148 subjects from non-English majors of 2015 grad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his model was verified and analyzed, expect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blended learning.
web-based autonomous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 face-to-face learning; blended learning; college English
G40-057
A
1009—8097(2016)11—0100—07
10.3969/j.issn.1009-8097.2016.11.015
本文為北京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改革項目“大學英語實驗教學體系的構建與應用”(項目編號:2014-ms03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劉小梅,主任,教授,本科,研究方向為第二語言習得、英漢語法對比,郵箱為liuxm10@163.com。
2016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