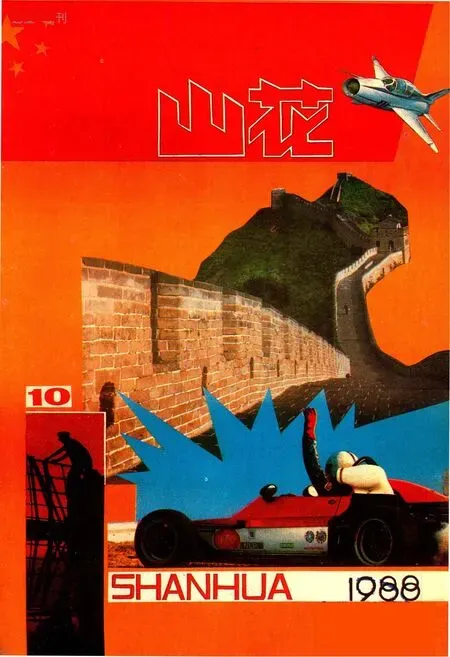串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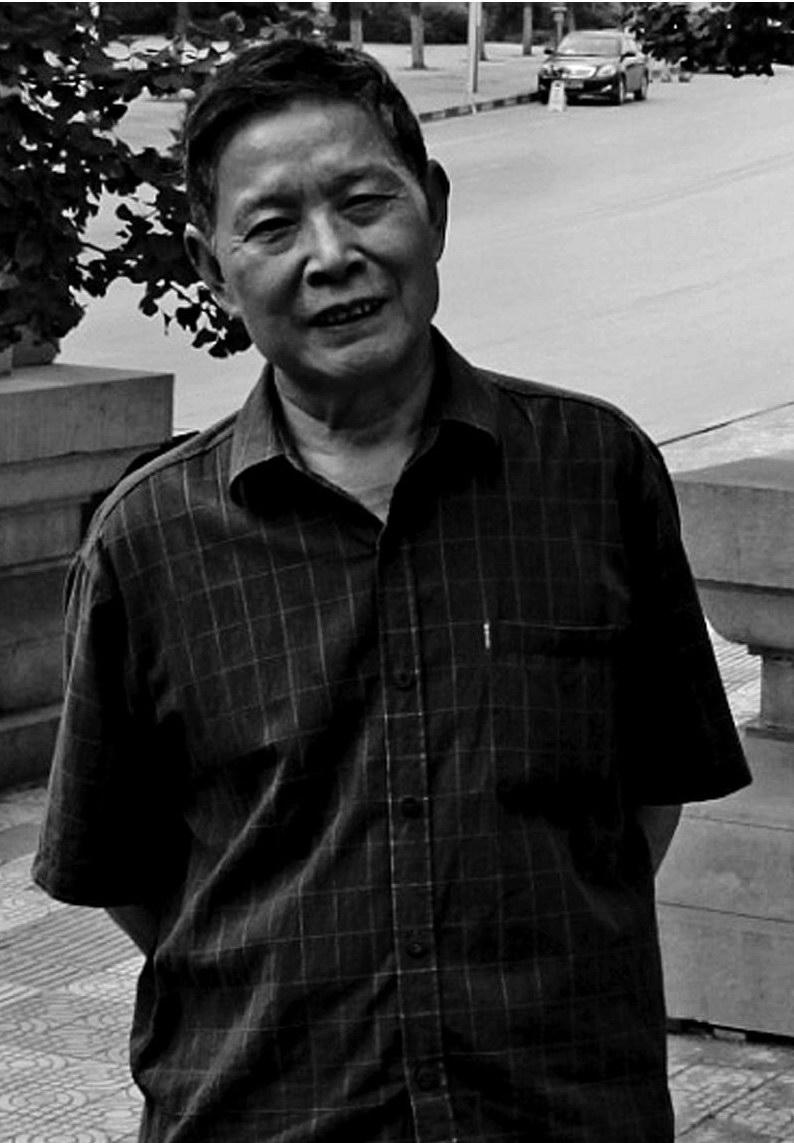
劉隆民,貴陽學院教授,出版美學專著多部,其中《電視美學》被訂為考研必讀專書和部分大學影視類研究生教材。曾出版《一條路上的老貴陽》。
“文革”初期,我和三位同人帶領黔南半農半讀師范學校的14位學生,學習紅軍長征精神,進行步行串聯。我們原準備從遵義經延安走到北京,后因中央下文停止串聯,只走到陜西寧強便停止前進。行期兩個月,行程三千里,留下了一本《“長征”日記》和三本敘述“長征”詳情的家書,共十多萬字。還有十幾張黑白照片,留下了征途中的身影。半個世紀過去了,我把它整理出來,再現那荒誕年代中的這一真實步履及其前因后果,重溫青年時代那遠去的沖動和熱情。值得一說的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聯”,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之前未有過,之后也不會再有。現代人了解這一絕版的歷史現象,可能有一定的認知意義。
“長征”序曲
1965年秋,我從貴陽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分配到黔南工作。到都勻報到后,因“社教”運動需要,暫緩二次分配,先到都勻平浪區參加“四清”。半年后,才把我分到獨山籌洞黔南半農半讀師范學校教書。同我一起分到這所學校的,有貴州大學藝術系的馬克昌、貴陽師范學院體育系的文祖雄等七位同人。還有一位是省外的,即江西共產主義大學的汪壽祥。
籌洞屬于獨山的上司區,離貴州的南大門麻尾只有幾里路。這一帶人煙稀少,滿眼都是荒坡,遙望很像一片有待開墾的處女地,但走近一看,卻植被稀疏,基巖裸露,亂石嶙峋,土層瘠薄,生態環境惡劣。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考察隊曾斷言這是塊“死地”。政府也曾想把這片“死地”利用起來。在這里辦過農場和林場,但都因水土流失嚴重而以失敗告終。“文革”前夕,有關部門又把黔南半農半讀師范學校落址這里。
我們到那里報到時,只有一幢石砌三開間上下兩層的辦公樓,孤零零地立在一個小山包上。不遠的凹地上是一間長方型的食堂,大概有一百多平米。離食堂不遠是一長排石塊砌的小平房,這就是我們的宿舍。我們十幾位老師住在這里,倆人一間。離宿舍不遠有條小溪,我們洗臉、洗腳、洗衣服,都用這一溝溪水。有時上游在洗腳,下游在洗臉,上游在洗褲子,下游在洗白菜。對于這些,最初很不適應,慢慢的才逐步習慣。難耐的是,這里不僅遠離城市,連村寨都看不到。也沒有一個學生,每星期只能見到兩個外人,一是每周來送一次信的郵遞員,二是間或來看田水的老農。學校沒有電話,也未訂報紙,我們同外界的聯系完全隔絕了,只有汪壽祥駕著馬車,偶爾去趟上司、下司或麻尾。為驅散寂寞,排遣無奈,畢業于作曲專業的馬克昌經常拉起二胡,那聲音幽怨而哀婉,如泣如訴。不久,教育部門從上司、基長等地招來了十幾個初中畢業生。這些學生大都來自農村,很本分,因而也未帶來太多的歡笑。
所幸的是,黔桂鐵路從這一帶經過,“籌洞站”就設在離此不遠的地方。從學校到籌洞站,可能不到兩里路。這個小站除了管站的兩個員工外,平時也沒有人。但一有火車停靠,盡管時間很短,也是人聲鼎沸,還有大把大把的傳單,從車上“紅衛兵”手中撒下來,飄得滿地都是。我們幾位老師,算到有車停靠時,便到車站撿傳單。“十六條”“五·一六通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首都破四舊”等,什么都有。正是有了這個車站,我們才了解風起云涌的外面世界。尤其是紅衛兵大串聯和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對我們的沖擊最大。那時的學生,出過遠門的人微乎其微。我到大學畢業,也才去過遵義,省外就想都不敢想。而串聯卻可以免費上北京、到全國,經風雨、見世面,太令人羨慕。遺憾的是,我們當時的身份已不是學生而是教師,沒有資格去享受坐車不要錢的大串聯了。我把這一體會同馬克昌、文祖雄說了,他們都有同感。
大概是十月底,我們在籌洞車站撿到人民日報社論《紅軍不怕遠征難》和“大連海運學院學生徒步走到北京”的傳單。我拿著它,反復地看,似乎發現了什么,手有點兒抖。又過十來天,我們在籌洞撿到一張傳單,說江西省一些中學,學習大連海運學院,由老師領著同學徒步去井崗山串連。我一看,跳了起來,高舉傳單,大聲對馬克昌、文祖雄和汪壽祥說:“我們向大連海運學院學習,向江西紅衛兵學習……步行串連……我們帶著學生去‘長征’……好不好?”他們跑過來,接過傳單一看,先是驚住,不一會兒,幾乎不約而同地也跳了起來:“烏拉!”我們把這一張傳單留下,把其他傳單,一齊撒向天空,撒向那藍天、白云、秋高氣爽的天空。
回到學校,我們幾個就分頭找其他老師和十幾個同學談了上述想法。大家幾乎全部同意,并推舉我和汪壽祥向學校寫申請報告。當天晚上我們就把報告草稿寫好,呈交學校。經過努力,尤其是在全國紅衛兵群起造反的威勢下,學校同意了我們的請求,批推我們從遵義步行到北京的“長征”。
我們的“長征隊”有教師四人,學生14人,共18人。因為汪壽祥學的是政治,大家推舉他當隊長,我管錢糧,馬克昌管聯絡,文祖雄管宣傳。大家分頭進行準備,各司其事。
11月10日。我們在學校召開“長征”前的最后一次會議,決定乘車到遵義,11月21日從遵義起程,經重慶、成都、西安、延安到首都北京。
“‘長征’日記”選述
美國作家彼德·彼阿德說,“日記中的語言根本沒有意義。”的確如此,日記是有什么記什么,基本沒有選擇。我的《“長征”日記》,重復事項就很多,如天氣的陰、晴、雨、雪,沿途的行軍、印傳單、讀毛主席語錄等,天天都有。完全照《“長征”日記》抄錄,似無必要。為此,我將全程分成遵義到重慶、重慶到成都、成都到寧強三段,各段先簡述概況,之后再選述日記中的兩三個特殊片斷,以期在詳略交替中,呈現當年“長征”中的人事景情。我想盡量做到:別人說得多的不說,一筆帶過,如遵義會議紀念館、杜甫草堂等,只選述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即我們“長征隊”的特有事項。同時,我試著用兩支筆述說,一支筆敘述事情的來龍去脈,一支筆記錄隊員們眉毛的顫動、瞬間的笑容。
從遵義到重慶
1966年冬,我們從遵義出征,步行8天,到達重慶。其里程為:遵義30公里一板橋35公里一桐梓35公里一新站80公里一四川趕水20公里一東溪45公里—綦江40公里——一品鎮20公里重慶。
我們“長征隊”18個人,按計劃于1966年11月19日從籌洞乘火車到遵義,依接待站安排,住進遵義賓館。第二天上午,全隊到遵義會議紀念館參觀,并在館前莊嚴宣誓:學習紅軍精神,發揚革命傳統,步行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下午,拜謁紅軍墳。我看見有工人在不遠處施工,便去要了一撮箕和好細沙的水泥漿,刷在“紅軍墳”右側的石壁上,然后在上面刻寫下“走長征路”幾個字。馬克昌當即用120相機,咔嚓一聲拍了下來。這是我們“長征隊”的第一張照片。
11月21日清晨,我們戴著軍帽和袖章,唱著《紅軍不怕遠征難》,高舉“黔南半農半讀師范學校遵義一北京‘長征隊’”紅旗,戴著印有“遵義一北京‘長征隊’”的袖章,背起背包,正式出征了。路上有不少人停下腳步,注目我們的隊伍。一支從成都來的“長征隊”同我們擦肩而過,并相互鼓勵。一路上,文祖雄老師時不時要來個側滾翻,贏來大家的一片贊美之聲。只有一人似乎無動于衷,這人就是高挑秀麗的女生楊文美。遵義郊區的公路,冬天少有人走,空寂清冷。我們“長征隊”的紅旗,像一束游移的火焰,迎風飄動。
婁山關上埋瓷碗作紀念
11月23日清晨,我們來到婁山關腳下。一輛從后面開來的解放牌卡車,在我們的旁邊停下。駕駛員從車窗伸出頭來,說婁山關難爬,叫我們上車,他順路把我們拉上去。我們謝絕了工人師傅的好心,堅決實踐步行的諾言。師傅報以贊美的微笑,開著汽車往前走了。我們沿著彎彎曲曲的公路,轉來轉去到達山頂。這時,天下起了毛毛細雨。透過如簾的雨絲,站在關上回頭往下看,公路就像一條黃龍在雨中盤旋而上,時隱時現。山頂上有塊石碑,上刻“婁山關”三字。碑前放滿了各路紅衛兵們放的袖章、毛主席語錄和像章。不一會兒,天放晴了。馬克昌拿出二胡拉了起來,聲音空曠而嘹亮。我喜歡文史,給大家講了個故事:紅軍當年在這里與王家烈部打了一仗,王部把紅三軍團十二團政委鐘赤兵的腳打斷一只。1954年鐘赤兵任貴州省軍區司令,王家烈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王看到鐘是一條腿,就問鐘何故造成?鐘答道:“敝人的腿嘛,被貴軍在婁山頭借走了,也不知王老先生何時送還?”王家烈聽后,極為慚愧:“罪過罪過!請鐘將軍從重發落”。鐘笑著說:“王老先生,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以后我們還要一同共事,共商治黔大業哩。”真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講完后,突發奇想,為什么不在此留下點東西作個紀念?于是我拿出從家里帶來的瓷碗,用紅油漆在碗面寫上“黔南半農半讀師范‘長征隊’用1966年冬”,然后拿起路邊的廢鐵器刨開泥土,把它深埋在婁山關頂馬路右側。我說幾十年后人們把它挖出來就是文物。馬克昌收起二胡:“能把全隊的名字都寫上更好。”但碗小人多,實在寫不了。離開婁山關時,女學生胡加蕓又把土刨開,將她頭發上的一顆夾針也一道放進去。這是無聲的敘述:“‘長征隊’里有女的。”人們向她投去贊許的目光。
迎難而上,翻七十二拐
12月24日,這是出征的第三天,全隊疲憊不堪。出發前,接待站的同志給我們說:走長路最難的是第三天,還說“沖過第三天,快活似神仙”。此話不假,這一天大家都覺得腳腫腿酸,邁不開步。走在前面舉旗的同學,也把旗桿扛在肩上,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很像電影里的國民黨的潰兵一樣。文祖雄的側滾翻也沒有蹤影了。與我們同向而行來自云南的“長征隊”見狀,也鼓勵我們“堅持沖過第三天”。中午時分,隊伍來到了涼風埡七十二道拐前。這段盤山而上的公路,因180度的回頭彎就超過72個,故名七十二道拐。在抗日戰爭中,它是重慶通往抗戰重鎮貴陽的必經之處,同晴隆二十四道拐一起,為抗戰勝利作出過不朽貢獻。1957年修川黔鐵路時,隧道從七十二道拐山下穿過。我們來到山前,路上的人告訴我們說,可以從隧道穿過,也可以爬七十二道拐,走隧道要少走十多里路。大家商量了一下,都認為雖然很累,但不能在困難面前退縮,還是決定爬七十二道拐。汪壽祥掏出《毛主席語錄》:“大家翻開74頁……”我們一邊讀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一邊沿著不寬的公路,彎來拐去地緩緩移動。走幾步又休息一下,之后再走。大概在第三十幾拐上,我們遇上由內蒙來的長征隊,只有兩個人,背著背包,一人執旗在前,一人緊跟在后。我們不約而同地停下來,互致問候,原來他們大隊人馬都走隧道了,就他們兩人同我們一樣迎難而上。我們同內蒙戰友告別后,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攀登,終于翻過七十二道拐。一只鷹從山那面飛來,從我們頭上掠過。
沖過第三天,確實不覺累了。隊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省界,經綦江、東溪、一品到達山城重慶。
從重慶到成都
在重慶參觀13天后,于12月6日離開重慶,步行1l天到達成都。其里程是:重慶40公里一青木關40公里一慶隆公社30公里一銅梁縣城70公里一潼南縣三匯鎮70公里一安岳毛家公社52公里一樂至回瀾區45公里一樂至紅衛兵中學45公里一簡陽施家壩60公里一簡陽縣城35公里一簡陽三泉35公里一成都。
隊伍住重慶韋家院接待站,對面就是重慶賓館。我們議定,上午集中學習,下午自由參觀。
我們都是第一次到山城重慶,很開眼界。重慶是長江上游的第一大城市,在現代史上輝煌耀眼,一部《紅巖》,更使它閃閃發光。隊友們三五成群,不避寒冷,參觀了紅巖紀念館、曾家巖紀念館、渣滓洞、白公館……
每天上午的學習,都要談一下前一天參觀了些什么,有何體會,然后就各抒己見。長江的滾滾波濤,重慶的“12·4”慘案,什么都講。談得最多的是從哪條路走向西安。老師們主張繞成都走,大部分學生卻希望從重慶直上西安。兩種意見,難以統一。有同學提出我們“長征隊”人多,不如分成兩隊,各走各的。我知道,分隊是假,其實是大多數同學都想坐車串聯,不愿同老師一道步行了。我提議,如果一定要分隊,每隊應有老師。我們把大家帶出來,必須把大家安全地帶回去。想分隊的同學聽了,還是脫離不了老師,終于確定不分隊,繞成都上西安。
有一個從甘肅來的“長征隊”,同我們住在一幢樓。他們有二十來人,年齡相差不大,十七八歲。聯想到我們鬧分隊的事,我問他們是否也有分隊的想法。他們說沒有,但有分岐。隊長主張沿著當年紅軍走的路“長征”,副隊長認為這太機械,我們不可能再去爬雪山、過草地,那不安全。這時走來一位女隊員,她穿軍裝、戴軍帽,胸前戴了五六個大小不同的毛主席像章。她的手在空中一揮,堅定地對我說:“這是兩條路線的斗爭!”看來,每個“長征隊”內部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青木關情思
1966年12月6日,我們離開重慶西行,翻戈羅山,宿青木關。因青木關是陜西、新疆以至蘇聯進入重慶的陸上通道,抗戰時期名噪一時。著名的國立音樂院,就落址這里。我的表姐曾昭萍,在此校少年班聽過課。她后來說,國立音樂院是抗戰后方唯一的音樂院校,為抗日戰爭和中國樂壇作出了巨大貢獻。抗戰勝利后,遷南京,原址改作它用。解放以后以它為基礎,組建了中央音樂學院。有此因緣,一到青木關,我就去尋找它的舊址。我問了幾個人,才知道它離我們駐地不遠。我想約馬克昌同去,但又未找到他,便一個人向舊址走去。為看全貌,我在離它不遠的地方停下來,莊嚴地遙視著這座曾經輝煌的音樂圣殿。遺址在冬日的黃昏中顯得很落寞,只有幾間簡陋的房子在那里靜靜地立著。真想不到《黃河船夫曲》《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都創作于這里,中國第一情歌《康定情歌》也產生于此。我仰視著這曾經輝煌的殿堂,像面對神祗,呼吸都停住了。我好像看到一個龐大的樂隊,在藍天下用圓號、簧管、提琴、低音笛和喇叭,訴說著撼動人類心靈的偉大情感。樂團指揮有時用手勢調動各種樂器,以排山倒海之勢演奏:有時讓合奏的聲音降低,平靜地指揮著小提琴奏出如泣如訴、溫柔優美的旋律;有時吩咐管樂、打擊樂突然加強力量……他揮著手,大汗如雨,激昂有力,指揮棒似乎在吶喊:勇往直前、不屈不撓,努力,努力!向前,向前!……我回到駐地,還沉浸在這種或昂揚、或溫柔的旋律中。
公社老農給“長征隊”排座次
離開重慶的第三天,住慶隆公社。這是個丘陵鎮,有百十來戶人家。當晚,公社為了歡迎我們,同我們進行了聯歡。我們“長征隊”除了大合唱和集體朗誦毛主席的《七律·長征》之外,馬克昌演奏了二胡,文祖雄表演了武術加側滾翻,我也上臺湊合,用貴陽方言朗誦了在“長征”途中寫的一首詩。朗誦完畢,我回到臺下。剛坐下來,側面的一位七十來歲的老人對我說:“你的詩寫得好!”我說:“謝謝夸獎。老人家,您讀過書?”他說:“讀過幾年私塾。”我說:“我也讀過私塾。”這一說,他便陡然同我親熱起來。他說他剛從重慶親戚家回來:“那里到處都是串聯隊,人山人海,哪樣串聯隊都有。”我認真地發問:“串聯隊就是串聯隊,怎么有‘哪樣串聯隊’?”他把長煙桿收起:“有。照我看,串聯隊有三種,第一種是南下串聯隊,兇得很,走到哪里炮轟哪里。他們是甲等串聯隊。好比從前的狀元。”他用科舉考試來相比,我笑了:“第二種呢?”他看著我:“第二種就是你們,步行串聯隊,朝著一個地方,一天只管走路,不造反。你們是乙等串聯隊,好比榜眼。”我很有興趣地問:“誰是探花?”他又抽起煙來:“就是那些成天坐起火車到處串的鬼崽崽們。他們就只曉得玩。”我會心地說:“老人家,您真有研究。”這時,有人宣布聯歡會結束,群眾全都站了起來紛紛散去,老人也走了。晚上,我一直在想,這位小有文化的老農對串聯隊的歸類,還很符合實際。從北京“南下”“西進”“北上”“東征”串聯隊,專門到全國各大中城市煽風點火,如一到貴陽就貼出“六問貴州省委”的大字報。到重慶就貼出“炮轟西南局”檄文。他們大都是大學生,而且了解上層的很多內幕,充滿造反精神。步行串聯的“長征隊”,為到達某一紅色名城或領袖故居,不遠千里,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他們不參與所到之處的斗爭,抱著經風雨、見世面的宗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向前。他們一般來自偏遠縣份,很能吃苦。乘車串聯的紅衛兵,大都是大中城市的中學生,他們沒有任何目的,就是玩。這部分人數量最多。老農按他的標準所排的座次,很有意思。
第二天早上,我把“長征隊”榮獲老農評為串聯“亞軍”的事給隊員們講,大家都笑了。他們好像受到鼓舞,向成都前進的步伐也矯健起來。文祖雄也接連打了幾個側滾翻。
從銅梁到成都,大都是丘陵,但卻有不少精神上的高山。銅梁是國際主義戰士邱少云的家鄉,建有邱少云烈士紀念館。安岳是中國白話詩的開創者之一康白情的故土,他的《和平的春里》,我還能背上幾句。還有簡陽的陳毅,是將軍里的詩人,詩人里的將軍。可惜因忙于趕路,這些地方都沒有好好地看,幾乎一天一個縣,于12月27日到達成都。那一天,大雪紛飛,成都以銀妝素裹的姿容,迎接我們這支來自貴州的“長征隊”。
從成都到寧強
在成都參觀十天后,隊伍于1967年1月11日北上西安,其計程為:成都33公里—廣漢30公里—德陽52公里—綿陽41公里—魏城30公里—梓桐38公里—武連41公里—劍閣71公里—廣元90公里—中子90公里—陜西寧強縣。
我們住成都十四中,地址在成都東面。成都歷史悠久,人杰地靈。我們的駐地離聞名全國的人民廣場很近,住下來后,就迫不及待地去參觀。之后幾天,自由觀覽了城內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文君井、薛濤井等,還專程去了成都附近的寶光寺、大邑地主莊園。
在成都,適逢蓉城“12·31”大游行,看熱鬧的人特多。我沒有去,躲在接待站看母親的來信。母親畢業于貴陽女師,是筑城最后一位私塾先生。我是獨子,無兄弟姊妹,三歲時,父親去世,與母親相依為命。我來“長征”,她很不放心。信中說,她買了一張全國大地圖,每天一起來就在地圖上找我們走到哪里。我也是每三天就寫一封信給她,向她講述我們沿途的情況。同時也接到未婚妻南心的匯款。她還是高三學生,把父母給她的零用錢積起來寄給我,錢雖不多,我很珍惜。在匯款單附言中,她說貴陽大十字的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信中還囑我咐照顧好自己。我也把征途中接待站送的軍帽、紀念章,全都寄給她。遠在征途的我,有她們的切心關懷,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幾天來,成都大雪紛飛,下個不停。接待站人來人往,但大都是全國各地乘車串聯的紅衛兵,“長征隊”很少。一天下午晚餐過后,有一個舉著“鐵姑娘長征隊”的紅旗的隊伍,向接待站走來。她們來自西安,要去遵義。聽說我們要上西安,她們的隊長特別叮囑我們:一定要在封凍前翻過秦嶺,否則就要等到開春。我們謝謝她的關照,并于1967年1月11日匆忙離開成都北上。
金牛道上古跡多
古代川北三條蜀道中,最重要的是金牛道。我們從成都向陜西前進,走的就是這條道。一路上除了廣漢、德陽、綿陽還有點成都平原平坦的景象外,其他的路都在山間穿行,同貴州差不多。沿途雖險要難行,但風光峻麗,分布著眾多的名勝古跡,讓我們享盡眼福。一是三國蜀漢文化。張飛柏、落鳳坡,劍門關,數不勝數。走在這條路上,就像讀一本立體的“三國”。其中的劍門蜀道,峰巒疊嶂,峭壁摩云,雄奇險峻,壯麗多姿,尤其讓我震撼。二是這條路上的盛唐文化十分濃郁。其中的廣元,更令人難忘。這是武則天的家鄉,唐代古跡遍地都是。但因天氣太冷,我忙于找當地接待站給學生解決被子問題。只去了皇澤寺和千佛崖。三是建于秦朝的翠云廊。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下令以咸陽為中心,修筑通達全國的馳道,在道兩旁種上成排的松柏,用以顯示天子的威儀,人們把這些樹稱為”皇柏”。在綿陽、梓潼和劍閣之間三百里的道路兩旁,兩萬多棵古柏,猶如翠云覆蓋著大道,郁郁忽忽,堪與古羅馬大道媲美。遺憾的是,我們都是沿著川陜公路走,同這條古道雖若即若離,但未從中走過。快到劍閣時,離它不到一百米,大家都想過去看看。胡加蕓、楊文美兩個女同學,看見那里盛開的梅花,更為激動。只有馬克昌一人不感興趣,他說:“你們把背包放在這里,我給你們看著,我就不去了。”說完就在地上坐下來拉二胡。在我們的“長征隊”,我同馬克昌被大家調侃為“牛(劉的諧音)饞馬懶”,我喜歡吃,他喜歡坐。這么值得一觀的地方又近在咫尺他都懶得去,真是各有所好。
路遇端著遺像的“長征隊”
1967年1月21日,我們來到四川與陜西的交界處中子鎮。這天的雪下得更大,滿山的北國風光。迎面緩緩走來一個“長征隊”,大約有十來人,身上全是雪。我們相互打招呼,噓寒問暖。當我們擦肩而過時,我突然發現其中一個女隊員端起一張有相框的黑白照。照片上也是個女學生,相框上有一塊青衫,這青衫在飛揚的雪花中特別醒目。我緩步追了上去,想看清楚。她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便傷感地對我說:“我的同學……我們‘長征隊’發起人……出征前夕去世了……我們帶著她完成‘長征’。”說完,她眼里閃過一絲淚光。我舉起右手,向遺像敬了個禮。我問他們從哪里來,她的聲音嗚咽,我聽不清是“山西”還是“陜西”。他們走了,身影逐漸消失。我小跑追上我們的隊伍,汪隊長正在叫大家背誦《毛主席語錄》74頁,我未把此事告訴大家。北風呼嘯,雪更大了。一輛從后面開來的解放牌卡車,在我們的旁邊停下。駕駛員從車窗伸出頭來,說雪太大,叫我們上車,送我們一程。我們謝絕了工人師傅的好心,繼續步行,在雪地上留下了一線深深的腳印。
1967年1月23日,我們第二次越過省界,到達陜西寧強。此縣北依秦嶺,南枕巴山。是大西北進入大西南的黃金通道,素有“三千里漢江第一城”之美譽。這意味著我們已到秦嶺腳下,翻過秦嶺就到了西安,離延安就不遠了。遺憾的是,隊伍到達寧強,只剩下八人了,思想煥散,斗志全無。尤其是離過年的時間只有十幾天了,都想回家過年,歸心似箭。恰逢此時,中央又再次發出停止步行串聯的文件,從西安過來的“長征隊”也說,西安的很多接待站都撤了,不再接待紅衛兵。看來,我們還想再往前走,已不再可能。
我們召開了全隊會議,決定全隊乘車返回貴州,來年春天再說。我們轟轟烈烈的“遵義一北京‘長征隊’”,終于偃旗息鼓,返程回鄉。臨離寧強的那天晚上,漫天鵝毛大雪,地上堆了兩尺厚,路上幾乎沒有人走,只有紅色的大標語,無聲地映著白雪。我在大雪中一人流連在寧強街上,“馳騁”在諸葛亮曾經在此北伐、唐明皇曾越此奔蜀的佳話之中。
“長征”結束后,我們回到學校。那幢石砌的三間兩層辦公樓,依然像一位滄桑的老人,孤零零地立在那地老天荒的曠野上,默默地迎接我們的歸來。
“長征”影事
“長征”結束半年,我調回貴陽,分到二十五中教書。
這時,中央號召“復課鬧革命”,二十五中開始正式招生、上課。那時,上課不多,而且都是講毛主席語錄及其有關文章,用不著備課,只往革命內容上吹。我吹得最多的就是我的“長征”。這同我心中的“電影情結”,有很直接的關系。
我向來喜歡電影藝術。上大學以后,我與同窗、后任“江門日報”主編的司徒明德,苦攻電影理論。那時蘇俄藝術盛行,蘇聯電影便成為了我們崇拜和探討的對象。一場《復活》看完,我們會在校園里討論半夜,而且開口不離“格拉西莫夫”,閉口不離“格布里諾維奇”。寫出一個電影劇本并被采用,是我們的夢想。“長征”雖夭折,但我腦子里總忘不了征途中的人和事,尤其認為步行串聯情節集中,動作性強,外景豐富,很符合電影藝術的傳達要求,并于“文革”中期,開始構思、撰寫反映步行串聯的電影劇本。其情景同我經歷的“長征”差不多,只是人物全是學生,沒有老師。故事梗概是:西南某中學的一隊紅衛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沖破重重阻撓,沿著紅軍走過的路,步行到達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見和鼓勵。情節比較生動,矛盾沖突強烈,人物性格鮮明,很有時代特色。劇本取名《小長征隊》,大約十萬字。
劇本寄給長春電影制片廠,不到一月,就被長影采用,并通知我去長春修改劇本。我途經北京,正遇周總理去世。乘車到長影時,貴陽的蔡葵、李金等在那里改《山寨火種》。同在的還有貴陽市文化局的楊局長、市文化宮的文主任和杜青海。楊、文是領導,杜青海跑堂,動筆改稿的是蔡葵和李金。
我被安排住在日偽時修的“小白樓”改稿。當時正值寒冬,地上的雪有兩三尺深,氣溫零下二十度。屋子里有暖氣并不冷,但一出門就受不了,比我們“長征”時在成都平原遇到的大雪冷多了。著名作詞家喬羽先生住在我對面,他是專程來長影修改歌詞的。我去拜訪他時,他很熱情地給我講寫《我的祖國》時的情景。
廠里安排張希至女士作《小長征隊》的責任編輯,幫助我處理劇本修改中的諸多問題。這是一位很有經驗的編輯,為人善良仁厚。她很贊賞《小長征隊》的選題、結構、人物語言和場景設計,特別指出情節的動作性很強,很適合電影表達。期間,杜青海來找我幾次,要我把《小長征隊》作為市文化局發現和扶持的成果。他到底是代表文化局來做我的工作,還是他自己想插手,不清楚。在貴陽我從未見過杜青海,但聽說過這個人。他來了幾次,看見我不理睬,也未再來。快到過年時,修改工作暫停,我又回到貴陽,準備過完年再去。年后,因病住院開刀,未能按時去長影,只用信與長影聯系,聽取他們的意見,在家修改劇本。劇本修改后,寄到長影。長影領導看了,要我在長征隊中增加一個校長,讓他作為走資派的代表,沿途阻礙小將們“長征”。我回憶了我從小學到大學的校長,哪一位都不會反對學習紅軍傳統,這樣改脫離現實,不可信。我愛人南心說這叫瞎編。由于思想跟不上那個年代的潮流,致使修改進展很小,幾易其稿,都無法達到他們的要求。1976年7月朱德去世,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跨臺,“文革”結束,此劇隨之告終。
從“長征”開始到《小長征隊》落幕,剛好十年,與“文革”同步。其情其景,猶如一個隔世的夢。我的“長征”及其據此寫成的《小長征隊》,雖然沒有造反、奪權、破四舊、批斗走資派,就是學習紅軍精神,但它是發生在那扭曲年代的事,背景荒誕,沒有社會價值。雖然如此,但它畢竟是我青年時代一次難忘的經歷,把它記錄下來,讓今后的人們知道在“文革”荒誕歲月中,曾經有過這樣一段真實的步履,一段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紅衛兵仿“長征”的步履。
后記:“文革”結束,我調貴陽師專。之后,任中文系主任、民進貴州省委副主委、省政協常委。21世紀初,我隨省政協視察獨山。我向當局問起黔南半農半讀師范學校的情況,才知道因那里地質條件不佳,此校未能辦成。現從澳大利亞引進優良草種,以學校原址作基礎,辦起了牧草種籽繁殖場。老師們也早已離開,馬克昌調都勻三中,文祖雄調獨山中學,汪壽祥據說調回了江西。出于懷舊,我還專程去了趟籌洞,一睹當年孕育我們“遵義一北京‘長征隊…的這個荒野中的搖籃。到了那里,放眼望去,原來熟悉的宿舍、食堂都消失了,只余石砌的三間兩層辦公樓,還孤零零地屹立在那小山包上。周圍的大片土地和視野可及之處,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南方草原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