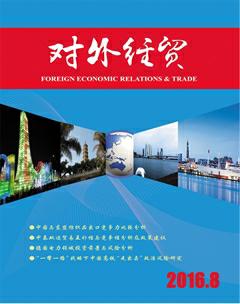我國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效率的區域差異及影響因素研究
汪俠 徐曉紅
摘 要:運用2001—2014年我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面板數據,構建基于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對綠色經濟效率(GEE)進行測算,與不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的傳統經濟效率進行比較分析,考察GEE的地區異質性與演變特征,并進一步運用面板Tobit模型實證分析檢驗GEE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考慮資源環境因素后,長江經濟帶整體GEE較低,存在較大改進空間;三大區域GEE差異巨大,呈現出“下游-中游-上游”梯度分布;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等因素對長江經濟帶及其上、中、下游的GEE均有一定影響,但影響的力度、方向以及顯著性存在差異。
關鍵詞: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效率;SBM模型;面板Tobit回歸
中圖分類號:F2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6)08-0080-04
[作者簡介]汪俠(1989-),男,安徽肥西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經濟、數量經濟;徐曉紅(1965-),女,四川瀘州人,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城市與區域發展。
[基金項目]合肥區域經濟研究院項目“資源環境約束下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及影響因素研究”(項目編號:Y01002276)。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標志著綠色經濟發展被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在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201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正式將長江經濟帶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打造新的經濟支撐帶與增長極。然而,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長江經濟帶資源和生態環境也正面臨嚴重威脅,如何正確處理資源、環境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現環境與綠色經濟共贏已經成為迫切問題。因此,在考慮資源和環境代價的基礎上,構建評價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績效的指標,對于促進經濟轉型、實現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針對經濟效率的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相關文獻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利用傳統DEA方法對經濟效率進行測度,如Hailu & Veeman(2001)將非期望產出變量作為投入變量納入到效率分析的框架之中[1];Scheel(2001)將非期望產出取其倒數變換成期望產出[2];Seiford等(2002)對非期望產出的值乘以-1,然后通過一個恰當的轉換向量使負的非期望產出變成正值[3]。二是對資源、環境因素指標選取的探究,如Hu & Wang(2006)在測算全要素能源效率時僅考慮了能源的投入而沒有考慮環境的影響[4];楊龍和胡曉珍(2010)在計算綠色經濟效率時僅考慮了環境污染而沒有涉及能源投入[5];汪克亮等(2013)、汪鋒和解晉(2015)在考慮環境污染時僅選擇大氣污染物作為其替代變量[6-7]。
本文將從四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拓展:第一,將資源和環境因素同時納入到經濟效率的測算框架中,并將其定義為綠色經濟效率(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簡稱GEE);第二,選取工業“三廢”作為環境污染的代理變量,克服單一污染物指標難以全面反映環境因素對綠色經濟效率影響的不足;第三,構建非徑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來測算綠色經濟效率,解決傳統DEA方法對包含非期望產出的綠色經濟效率測度偏差問題;第四,將長江經濟帶劃分為上游、中游、下游三片區域,利用面板Tobit模型比較分析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因素,據此分析區域綠色經濟發展異質性問題。
二、研究方法
將長江經濟帶每一個省市看作一個生產決策單元(DMU),考察第j0個決策單元DMU
三、綠色經濟效率測算與分析
(一)數據及變量說明
本文研究時間段為2001—2014年,研究對象為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并結合各省市的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將11個省市劃分為上游(四川、貴州、重慶、云南)、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下游(上海、江蘇、浙江)三個區域,以便考察不同區域之間綠色經濟的異質性。實證研究中選取3個投入變量和2個產出變量,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
1投入變量。投入包括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資源投入。勞動投入用當年年末就業人員數與上年年末就業人員數的平均值表示。資本投入用資本存量表示,然而其在統計年鑒中無法直接獲取,可根據Hu 和 Kao(2007)以及Chien 和 Hu(2007)[8-9]提出的永續盤存法計算資本存量:Kt=It+(1-δ)×Kt-1,其中,Kt、Kt-1分別表示第t、t-1年的資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資額,δ表示折舊率,計算中相關變量和參數選取參照單豪杰(2008)的做法[10]。資源投入用能源消費總量折算成標準煤表示。
2產出變量。產出包括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期望產出用200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各省市實際GDP表示。非期望產出選取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衡量,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將工業“三廢”排放量綜合為環境污染指數納入核算框架。
(二)測算結果與分析
運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分別對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2001—2014年綠色經濟效率進行測算。為了與不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的傳統經濟效率進行比較分析,用CCR模型測算不包含資源投入和非期望產出的效率值。
表1結果顯示,在不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時,2001—2014年長江經濟帶的整體經濟效率基本維持在078左右的水平,并且呈現出逐漸上升趨勢。當綜合考慮了資源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時,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經濟效率水平有顯著下降,基本維持在060左右的水平。這一結果說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造成了較大程度的效率損失。可見,不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的經濟效率被高估了,扭曲了對社會福利變化和綠色經濟績效的評價。
從考慮資源和環境因素的綠色經濟效率看,2001年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經濟效率為0577,截至2014年的綠色經濟效率值上升至0689,呈現出穩步上升態勢,表明這一時期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綠色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度逐漸轉好。從11省市的綠色經濟效率水平看,上海的綠色經濟效率長期保持為1,即一直處于最優生產前沿面上,投入和產出規模達到最佳,綠色經濟效率最高,實現環境和綠色經濟雙贏。江蘇和浙江的綠色經濟效率也保持在較高水平,距離最佳前沿面較近,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仍有改進空間。另外,上海、江蘇和浙江三省一直牢牢占據綠色經濟效率前三名的位置,代表著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發展的最優水平,綠色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較為和諧,是被“追趕”的對象。安徽、江西、湖北等8個省市的綠色經濟效率水平都處于較低水平,表明這些地區仍然面臨巨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特征明顯,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產品附加值低,二元經濟特征鮮明,綠色經濟轉型難度較大。
長江經濟帶地域廣闊,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顯著不平衡,上游、中游和下游的資源稟賦、經濟實力、技術條件和對外開放度等差異明顯,導致綠色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只有充分考慮這一差距,才能準確定位不同區域綠色經濟效率損失的真實根源。圖1給出了2001—2014年三大區域綠色經濟效率動態變化趨勢。三大區域綠色經濟效率差異巨大,下游地區最高,其次是中游地區,上游地區最低,呈現出“下游-中游-上游”梯度分布。中上游地區效率值遠低于下游地區和整體平均水平,彰顯了長江經濟帶綠色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現實。
四、綠色經濟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在實證測算我國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GEE的基礎上,以GEE值為因變量,以效率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建立面板Tobit計量經濟模型,考察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1經濟發展水平對長江經濟帶整體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區的GEE有顯著促進作用,這表明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對改善GEE有積極作用,因為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將會吸引較高素質的人才和改進生產技術水平,這些條件為提升長江經濟帶GEE提供了資金、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有力保證。2產業結構對長江經濟帶整體、上游、中游地區的GEE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說明長江上游和中游地區的工業化發展過程是以消耗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然而,產業結構對下游地區的GEE卻有促進效果,這可能與下游地區所具備的優越的生產條件和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有關。3能源結構對長江經濟帶整體及三大地區的GEE影響均顯著為負,意味著煤炭消費比重的提升對于改善GEE是不利的。4外商直接投資對長江經濟帶整體、上游及中游的GEE影響效果為負,說明外資進入抑制了長江上游和中游GEE的提高。即使引進外資有利于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增強自身經濟發展能力,但是引進外資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在這兩大區域是存在的。然而,下游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顯著促進了GEE的提升,這表明下游地區已經不再盲目追求利用外資的數量,轉而更加注重外資的質量。5無論是長江經濟帶整體還是三大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變量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增加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對促進GEE提高會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波特假說”在一定意義上得到了驗證,環境規制會促使企業為降低成本而進行技術創新的同時,也相應減少了工業污染物的排放。
五、政策建議
結合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提出促進長江經濟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綠色經濟效率水平差距的三點政策建議:一是促進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之
間的經濟、技術、產業等方面融合,促進上、中、下游地區產品、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發揮下游地區的核心輻射效應,使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向中上游擴散轉移。二是優化長江經濟帶特別是中上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三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在引進外資時要設置資源環境門檻,不能盲目追求利用外資的數量,而應更加注重外資質量,避免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參考文獻]
[1]Hailu,Atakelty,Terrence S Veeman Nonparametric Productivity Analysi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An Application to the Canadian Pulp and Paper Industr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1,83(3):605-616
[2]Scheel,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Efficiency Valuation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2(2):400-410
[3] Seiford,L M,Zhu J Modeling Undesirable Factors in Efficiency Evalu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2,142(1):16-20
[4]Hu J L,Wang SC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J]Energy Policy,2006(34):3206-3217
[5]楊龍,胡曉珍基于DEA的中國綠色經濟效率地區差異與收斂分析[J]經濟學家,2010(2):46-54
[6]汪克亮,楊力,程云鶴異質性生產技術下中國區域綠色經濟效率研究[J]財經研究,2013,39(4):57-67
[7]汪鋒,解晉中國分省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15(2):53-62
[8]Hu J L,Kao C H Efficiency Energy-saving Targets for APEC Economies[J]Energy Policy,2007(35):373-382
[9]Chien T,Hu J L Renewable Energy and Macroeconomic Efficiency of OECD and Non-OECD Economies[J]Energy Policy,2007(35):3606-3615
[10]單豪杰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10):17-31
(責任編輯:喬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