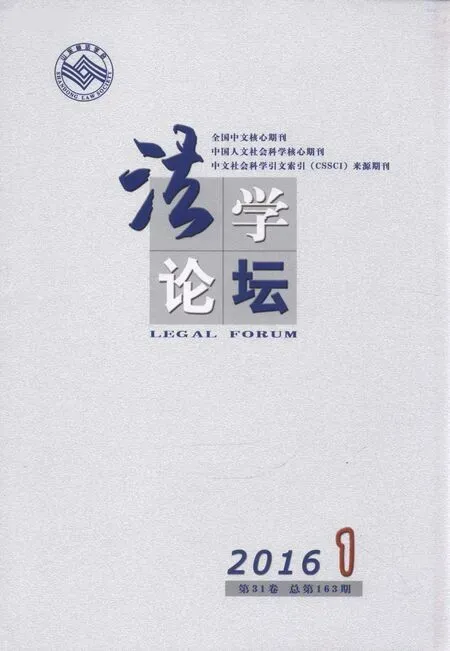晚清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的考察
程夢婧
(重慶大學(xué) 法學(xué)院,重慶 400045)
?
晚清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的考察
程夢婧
(重慶大學(xué) 法學(xué)院,重慶 400045)
摘要:法國1789年《人權(quán)宣言》自晚清傳入中國以來,各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不同的中文譯本。1903年“小顰女士”的譯本,并非如人們通常所認(rèn)為的是《人權(quán)宣言》。但在晚清,有兩個全譯本極為重要,即1907年的“川”本及1908年的林萬里、陳承澤本。通過比較,兩個譯本在序文、名稱及內(nèi)容等方面存在差異。其中,“川”本不乏一些“誤譯”的內(nèi)容。“誤譯”的原因是多樣的,譯者“川”可能受到語言能力、翻譯目的及社會需求的影響。然而,即使“川”本存在“誤譯”,晚清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的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
關(guān)鍵詞:《人權(quán)宣言》;晚清;翻譯;誤譯
西方思想、學(xué)術(shù)與制度、法律在晚清的輸入,是與譯書直接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一個國家、民族,要想了解、學(xué)習(xí)和研討別的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經(jīng)典和法律制度文本,必須借助于翻譯這一極為重要的工具。在晚清中國,面對1840年以來國門洞開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危象與困局,一些敏銳的學(xué)者深刻認(rèn)識到:“當(dāng)今之世,茍非取人之長,何足補我之短。然環(huán)球諸國,文字不同,語言互異,欲利用其長,非廣譯其書不為功。……茍能以新思想新學(xué)術(shù)源源輸入,俾躋吾國于強盛之域。”*周樹奎:《譯書交通公會序》,載張靜廬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57頁。因此,“譯書之宗旨”,就在于“輸入文化挽救衰亡。”他們指出:“兩群相遇,欲互換其智識,則必譯書。……然則今日之支那,其以布帛菽粟視譯書也審矣。”*《論譯書四時期》,載張靜廬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2、60頁。而梁啟超尤其將翻譯西方著作視為救國啟蒙的一大關(guān)鍵。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法國《人權(quán)宣言》(特指1789年《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被逐步譯介到晚清中國,從而讓中國人得以見識《人權(quán)宣言》的真實思想觀念及其制度原則。筆者目前所見,《人權(quán)宣言》在晚清主要有兩個漢譯本:其一,1907年,署名“川”的人將《人權(quán)宣言》譯為《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 “川”不僅對《人權(quán)宣言》逐條進(jìn)行翻譯,而且對其作出了自己的注解。其二,1908年,林萬里和陳承澤將《人權(quán)宣言》譯為《人權(quán)及國民權(quán)宣言》。該譯文系德國耶利內(nèi)克之著作《人權(quán)宣言論──近代憲政史研究析論》第五節(jié)的內(nèi)容。美濃部達(dá)吉先將其從德文譯為日文,后由林萬里及陳承澤轉(zhuǎn)譯為中文。
本文旨在對《人權(quán)宣言》在晚清的兩個漢譯本進(jìn)行比較研究。當(dāng)然,每位譯者對《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及用詞都各不一樣,且各具特色。因此,本文的內(nèi)容并非是對兩個晚清時期的翻譯文本的簡單羅列,而是致力于比較兩個文本之間的差異,體現(xiàn)出兩個文本各自的價值。其中,甚至不乏一些“誤譯”的內(nèi)容。對這些誤譯,本文也加以討論,目的在于將這些誤譯與當(dāng)時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相聯(lián)系,挖掘其背后的更深層次的意義。
在此之前,筆者先進(jìn)行一個糾誤,即人們對1903年上海支那翻譯會社出版“小顰女士”所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的錯誤認(rèn)識。史料證明,該譯本并非1789年法國的《人權(quán)宣言》。
一、“小顰女士”譯本并非法國1789年《人權(quán)宣言》
從目前所知所見的材料來看,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集中出現(xiàn)于20世紀(jì)初的十一年(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間。不論是零散的譯介,還是全本的漢譯,在這十余年中,都有前所未見的突進(jìn)。這當(dāng)然與這個時期發(fā)生的新政、預(yù)備立憲、憲政運動、人權(quán)觀念的發(fā)展以及更大規(guī)模的譯事,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那么,《人權(quán)宣言》的第一個譯本是何時出現(xiàn)的?對這一問題,史學(xué)界有一個普遍的判斷,即從“小顰女士”1903年所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談起,認(rèn)為該譯本就是《人權(quán)宣言》。然而,“小顰女士”譯本是否就是1789年的《人權(quán)宣言》,從而成為了《人權(quán)宣言》的第一個全本漢譯本?對這個問題,不少論著存在誤判。章開沅先生在《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一文中說:張于英所編《辛亥革命書征》中有《譯文四種》(1903年,內(nèi)有《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參見章開沅:《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載劉宗緒主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jì)念論文集》,三聯(lián)書店1990年版,第72頁。這個《譯文四種》,就是“小顰女士”所譯的《政治思想之源》。而熊月之先生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也非常肯定地認(rèn)為,1903年上海支那翻譯會社出版“小顰女士”所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就是法國1789年的《人權(quán)宣言》。該書指出:在《政治思想之源》一書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獨立檄文》和《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該書進(jìn)一步解釋說:“《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通稱《人權(quán)宣言》,全稱《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宣言》,18世紀(jì)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綱領(lǐng)性文件,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通過,1791年《法國憲法》列為序言。”*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9頁。這一判斷并未明確認(rèn)定“小顰女士”的譯本,即為《人權(quán)宣言》在中國的第一個漢譯本,但顯然認(rèn)為它是《人權(quán)宣言》的漢譯本。由此,研究者們在涉及《人權(quán)宣言》在晚清的情況時,無一例外地都從“小顰女士”的譯本談起,如馮江峰說:“1903年支那翻譯會社印行《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這些西方著作和法律文件的翻譯對先進(jìn)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精神上的震撼……。”*馮江峰:《清末民初人權(quán)思想的肇始與嬗變(1840─1912)》,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頁。蘭梁斌在《20世紀(jì)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研究》(西北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3年)中,引用方光華的《戊戌變法與中國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98年第4期,第70頁)一文中的敘述,也說在1902至1903年,《獨立宣言》、《人權(quán)宣言》以及各國歷史書籍,被大量譯成中文(第96頁)。這些論文雖未指明其所說的《人權(quán)宣言》譯本,但可能仍然指的是熊月之著作中提到的小顰女士所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熊著說“小顰女士”所譯即《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馮江峰認(rèn)為其為《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顯然都是將“小顰女士”的譯本視為《人權(quán)宣言》的漢譯本,或者認(rèn)為“小顰女士”所譯即為1789年的那份《人權(quán)宣言》。
然而,據(jù)筆者考察,章開沅先生、熊月之先生以及其他學(xué)者的著述,的確判斷有誤。*筆者在《法國〈人權(quán)宣言〉在晚清》一文(《現(xiàn)代法學(xué)》2013年第5期)中,也按照章開沅、熊月之、馮江峰的說法,認(rèn)為“小顰女士”所譯即1789年《人權(quán)宣言》。筆者的初稿正文中提到:“經(jīng)過多方搜尋,筆者至今未見中譯本《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并注有一個解釋:“檢索顯示,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有《政治思想之源》一書的索引,但卻被告知:或者“無法提供”,或者庫中無此書。經(jīng)請陳剛教授協(xié)助查詢,在所查日本的一些圖書館中,未見該書。此外,西南政法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吳運筑及重慶大學(xué)法學(xué)院博士生任洪濤在中國臺灣交流期間,在一些圖書館查找,亦未見該書。”但這個注解在論文正式發(fā)表時,未予保留。十分幸運的是,其后在圖書館朋友的大力幫助之下,終于在2014年搜集到“小顰女士”的譯本。第一,該譯本收錄在“小顰女士”的翻譯作品《政治思想之源》一書中。該書封面列名《美利堅獨立檄文》(即《獨立宣言》)、《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瑪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以及《噶蘇士戒國人書》四篇。其第二篇的名稱標(biāo)為“《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在其書內(nèi)(第7頁),名稱為“《法蘭西民主國民權(quán)宣告書》”。由此可見,其名稱并非章開沅先生、熊月之先生所說“《法蘭西人權(quán)宣言》”和馮江峰所稱“《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第二,更重要的是,“小顰女士”翻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實際上是1793年法國憲法中的“人權(quán)宣言”部分,由“序言”和35條構(gòu)成。而且,其《政治思想之源》的第7頁,已經(jīng)在“《法蘭西民主國民權(quán)宣告書》”標(biāo)題下,明確標(biāo)明其時間為“1793年”而非1789年。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時期,關(guān)于人權(quán)的宣言書頻繁公布,所以法國被譽為“人權(quán)宣言”的故鄉(xiāng)。在這個時期,“且不計影響較小的人權(quán)文獻(xiàn)(如在人權(quán)宣言制定過程中提出的草案),值得充分重視和研究并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人權(quán)宣言至少有四個,即1789年《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宣言》、1791年《婦女與女公民權(quán)利宣言》、1793年《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宣言》和1795年《人與公民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宣言》。這四個文獻(xiàn)同是法國大革命的產(chǎn)物,并成為大革命人權(quán)思想和原則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馬勝利:《法國大革命中的四個人權(quán)宣言》,載《史學(xué)集刊》1993年第2期。其中,1793年的《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宣言》,是由雅各賓派革命領(lǐng)袖羅伯斯庇爾起草的。*羅伯斯庇爾的著作《革命法制和審判》,收錄了《關(guān)于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除“緒言”外,共有37條(趙涵輿譯,商務(wù)印書館1965年版,第136─140頁)。1793年7月通過的《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宣言》,共35條,比羅伯斯庇爾的草案少兩條,但內(nèi)容并無大的不同。盡管該宣言吸收了1789年《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宣言》的一些內(nèi)容,但兩個宣言顯然各有不同。由此可見,“小顰女士”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或《法蘭西民主國民權(quán)宣告書》譯本,絕非1789年法國《人權(quán)宣言》的譯本,當(dāng)是確定無疑的。
二、晚清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的問世
既然“小顰女士”所譯的《法蘭西人權(quán)宣告書》并非《人權(quán)宣言》的漢譯本,那么,《人權(quán)宣言》全譯本的出現(xiàn),還得繼續(xù)往后追查。僅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這個全譯本在1907年誕生了。這就是《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以下簡稱《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該譯注的作者署名為“川”,譯注全文刊登于1907年2月的《申報》。*《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分三次刊登于光緒33年(1907年)的《申報》,分別為2月17日(西歷3月30日)第9版(譯序及前言、第1至5條)、2月19日(西歷4月1日)第9版(第6至11條)、24日(西歷4月5日)第9版(第12至17條)。下文引用該《譯注》時,不再注明。“川”在譯注之前對翻譯《人權(quán)宣言》作了一個說明:“地球各國之憲法,除英國外,大半取則于法國。而法國憲法之綱領(lǐng),全在人權(quán)十七條。此十七條人權(quán),系于七百八十九年由國會投票決定而宣布者也。故名之曰人權(quán)之宣告。人權(quán)者,猶言人人應(yīng)有之權(quán)利也。此權(quán)利系天賦者也。既為人,既為國民,皆有此權(quán)利。今特釋之如下(原為‘如左’,今改為‘如下’──引者注)。”這一譯文的譯注者“川”,到底是什么人,無法加以查考;譯文是從法語直接翻譯為中文,還是由日文或其它語言轉(zhuǎn)譯,也無從知曉。但是,這一譯注無疑是中國人權(quán)史上極其重要和十分珍貴的史料。
1908年,又出現(xiàn)了另一個《人權(quán)宣言》的全譯本,即《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第一編“人權(quán)宣言論”中所含的《人權(quán)宣言》條款。*全部條文見[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日]美濃部達(dá)士原譯,林萬里、陳承澤重譯,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版。根據(jù)該書日譯者美濃部達(dá)吉博士的“原譯小引”,該書為德國公法學(xué)教授挨里涅克(美濃部達(dá)吉譯為“哀犁難克”,今通譯“耶利內(nèi)克”)的原著。其中,《人權(quán)宣言論》(全名《人權(quán)宣言論──近代憲政史研究析論》)發(fā)表于1895年,盡管只有“五十三頁”,但所論“皆為前人所未發(fā)”。中國福建侯官的林萬里和閩縣的陳承澤,又將美濃部達(dá)吉的日譯本譯為中文,名為《人權(quán)及國民權(quán)宣言》。由此可見,中文本《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所含《人權(quán)宣言》,歷經(jīng)三次轉(zhuǎn)譯:一由耶利內(nèi)克從法文譯為德文,二由日本的美濃部達(dá)吉從德文翻譯成日文,三由林萬里和陳承澤從日文譯為中文。中國吳縣長洲的潘承鍔作為校訂者為中文本撰寫了《〈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序》,序文說:“反諸吾國近政之情狀,信此書重譯之不可少。”這一再三轉(zhuǎn)譯的譯本,也是本文立論的一大史料基礎(chǔ)。
鑒于讀者難以查找兩個譯本以及下文比較的需要,特將兩個譯本全文抄錄如下:
川:《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1907年)
林萬里、陳承澤:《人權(quán)及國民權(quán)宣言》條文(1908年)
宣告之綱:人權(quán)宣告(Dé Claration Tes Aroits de L'homme et Ctoen)國會中之人民之代表,考見國民之涂炭,政界之腐敗,皆由于不知人權(quán),或遺忘人權(quán),或忽視人權(quán)之故。今特將此天然應(yīng)有之人權(quán)、不可賣蔑之人權(quán)、神圣不可侵犯之人權(quán),明白宣布,俾全國社會中人,念茲在茲,雖瞬息之頃,勿忘此相當(dāng)之義務(wù);俾立法行法之人,夢寐之間,均當(dāng)以人權(quán)懸于心目。凡有作為,皆當(dāng)與此目的相符合;俾全國民之一舉一動,時時以維持憲法為責(zé)任,時時謀全國民之利益,而不可一刻偶忘此大義。
職是之故,國會特將此人權(quán)十七條宣誓于吾同人之前,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川)第一條 人之生長與居處,皆有自由平等之權(quán)利。惟因公共利益之故,乃有社會上之區(qū)別。
(林)第一條 人于出生及生存,有自由平等之權(quán)利,舍公共利益外,不得有不平等之處置。
(川)第二條 各種政會之目的,無非保全此天賦之人權(quán),保全此永久不蔑之人權(quán)。此人權(quán)者,何也曰自由也,曰安全也,曰財產(chǎn)之主權(quán)也,曰壓制之抗力也。
(林)第二條 一切政治結(jié)合之目的,在于保持人之天賦不可讓之權(quán)利,如自由,所有權(quán),安全之手段,對于壓制之反抗是也。
(川)第三條 大權(quán)僅在國家,茍其事非由國家之大權(quán)而出,則無論何人,無論何會,均不能行其私權(quán)。
(林)第三條 全主權(quán)之淵源,必存于國民,團(tuán)體及個人所行使之權(quán)利,必為出諸于國民者。
(川)第四條 凡不妨害他人者,人人皆能為之,此即所謂自由也。如天賦之人權(quán),人人皆當(dāng)享有。則此人自行其人權(quán),必以他人之人權(quán)為界限。此界限何由而定,乃以法律定之。
(林)第四條 凡人之行為于不侵害他人范圍內(nèi),得以自由,蓋社會各員之自然權(quán)利當(dāng)同等,非依法律,不得有他限制。
(川)第五條 法律只有一權(quán)。此權(quán)維何,防御有害之事是也。凡非法律所禁者,無論何人,不能阻止之。凡非法律所令其行者,無論何人不能強迫之。
(林)第五條 法律限于對有害社會之行為,有禁止之權(quán)利,法律之所不禁,當(dāng)放任之,法律之所不命,不得加以意外之強制。
(川)第六條 法律者,全國人之志愿與代表也。凡系國民,均當(dāng)爭相協(xié)助,或則直接出其身以任其事,或則舉代表以任其事。所任之事維何,即編制法律是也。法律所當(dāng)保護(hù)全國人共受此保護(hù),法律所當(dāng)責(zé)罰全國人共受此責(zé)罰。凡系國民,皆能居于執(zhí)行法律之任。蓋其位為公位,其務(wù)為公務(wù)也。惟視其人之才德何如耳。才德之外,無他事可區(qū)別其能否勝任。
(林)第六條 法律者總意之發(fā)表也。凡公民有選代表者參與立法之權(quán)利,法律之與以保護(hù)及定其罰則,要當(dāng)均一。法律視公民皆為同等,故公民除按其己之價值及技能外,均得受一切寵號,任公之地位及職務(wù),無所區(qū)別。
(川)第七條 惟為法律所規(guī)定者,始能逮捕,始能拘留。若有人自發(fā)其擅奪之令,目行其擅奪之令,或助人為擅奪之事,或受人指使而為擅奪之事,法律皆當(dāng)罰之。但國民若遇法律上之喚召,若遇法律上之逮捕,亦當(dāng)暫時敬從。若或反抗,是自取戾也。
(林)第七條 非由法定及法定形式,不得提起公訴,及為逮捕與拘留。求發(fā)專恣之命令及發(fā)專恣之命令者,與執(zhí)行者,與命執(zhí)行者,皆罰之。然各公民對于適法之召喚逮捕,為抵抗者罪之。
(川)第八條 法律只值確系萬不得已,顯系萬不得已,乃能行其責(zé)罰。凡輕罪之當(dāng)受責(zé)罰者,必在法律已經(jīng)編定布告之后,且必法律已經(jīng)正當(dāng)施行之后。
(林)第八條 法律非絕對必要者,不得濫定刑罰。無論何人非依犯罪前制定公布及適法之法律,毋得處罰。
(川)第九條 無論何人,當(dāng)罪案未定之先,與無罪之人無異。審判之后,罪案已定,凡嚴(yán)刑之可以刪除者,皆當(dāng)竭力刪除。
(林)第九條 各人未宣告有罪時,皆當(dāng)推測為無罪,雖有時必須逮捕,茍非必要之暴力,而拘束其身體者,法律必嚴(yán)禁之。
(川)第十條 茍不紊法律所定之公共之秩序,則各人意見不當(dāng)妥而不發(fā)。
(林)第十條 凡人之發(fā)表意見,凡在無害于公共秩序之范圍內(nèi),其意見皆無為其妨害者,宗教上之意見亦如之。
(川)第十一條 思想之交換,意見之交換,此為各人最寶貴之權(quán)利。故國民可任意著作,任意印刷,惟有為法律所限制者,不能妄用其自由。
(林)第十一條 思想及意見之自由交換,人之最貴重權(quán)利中之一也。故各公民依其法律之所定,得自由言論、著述及出版,但對于濫用其自由者,負(fù)法律之責(zé)任。
(川) 第十二條 欲保護(hù)人權(quán),不可不有公共之勇力。然則公共之勇力者,為公共之利益而設(shè),非專為私人之利益而設(shè)也。
(林)第十二條 保障人及公民之權(quán)利,要有公之權(quán)力。此權(quán)力者,為公眾利益而設(shè),非為受此權(quán)利之委任者之特別利益而設(shè)也。
(川)第十三條 欲維持公共之勇力,欲維持施行政事之費用,則納稅為萬不能免之事。凡系國民,皆當(dāng)納稅,而又量其力之所能,以為區(qū)別。
(林)第十三條 為維持公之權(quán)力及行政之費用者,不得免公共之課稅,其課稅從各公民之能力平等分配之。
(川)第十四條 凡系國民,皆有決議稅則之權(quán),或躬親其事,或舉代表以任其事,承諾與否,悉出于自由。勻擔(dān)如何,支配如何,征收如何,期限如何,均視應(yīng)用之?dāng)?shù)以為準(zhǔn)。
(林)第十四條 凡公民由自己或其代表者,認(rèn)公之課稅為必要時,得自由同意,有檢其用途與定其性質(zhì)、征收、交納及繼續(xù)期間之權(quán)利。
(川)第十五條 種種社會,均有向官員查賬之權(quán)。
(林)第十五條 社會對其行政之公代理人,有問其責(zé)任之權(quán)利。
(川)第十六條 若無憲法,則權(quán)限不分,而種種社會均無自保其險。
(林)第十六條 不安固社會之權(quán)利保障,且不確定權(quán)力之分立,其社會非為有憲法者。
(川)第十七條 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神圣不可侵犯,惟為公益所必需,則可要索之,但須依公正之條約,而預(yù)給其價。
(林)第十七條 所有權(quán)為神圣不可侵之權(quán)利,故非由法律認(rèn)為公之必要,且與以相當(dāng)之賠償者,不得奪其所有權(quán)。
三、晚清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的比較
晚清對于《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作為晚清憲法史和人權(quán)史的重要事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中國社會政治的變遷,而且會展現(xiàn)出譯者對原文的漢語表達(dá)。因此,有必要深入比較分析其譯本,從而既揭示其文本本身的內(nèi)容,又能透析出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及思想觀念,尤其在幾種不同文本之間做比較性分析,更能展現(xiàn)譯者的不同思想觀念與翻譯技巧。在此,筆者選擇將《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與《人權(quán)及國民權(quán)宣言》兩個譯本進(jìn)行比較。
需要明確的是,因晚清的文字仍偏重于古文,故而筆者的比較與評述,主要是看上述材料對《人權(quán)宣言》所作的“譯”,在涵義、內(nèi)容、精神上是否符合原文。對于字、詞的使用,筆者只會提及對涵義及內(nèi)容有較大影響,以及在選詞上產(chǎn)生較明顯分歧的用詞,不會過多地糾纏一般字詞的使用。
(一)兩個譯本對“序文”的處理
“川”本全文翻譯了《人權(quán)宣言》的“序文”(引言)。但是,林萬里、陳承澤的譯本則未見這一“序文”。據(jù)耶利內(nèi)克的原著,該“序文”被稱之為“特空理的及政治心理之說明”。*參見[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日]美濃部達(dá)吉原譯,林萬里、陳承澤重譯,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版,第4頁。這里所謂“特空理的及政治心理之說明”,李錦輝的今譯本譯為:“一個屬于政治形而上學(xué)純粹理論的教條式聲明”([德]格奧爾格·耶里內(nèi)克:《〈人權(quán)與公民權(quán)利宣言〉──現(xiàn)代憲法史論》,李錦輝譯,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版,第13頁。)這一“聲明”,當(dāng)指《人權(quán)宣言》條文之前的序言。耶利內(nèi)克的著作之所以未錄入這一“序文”,其原因可能是他認(rèn)為,對于其研究而言,只須討論《人權(quán)宣言》的各個條文就夠了,而其“序文”并不重要。他自己就明確指出:“法之《權(quán)利宣言》前文中(即序文),有所謂‘于最高神庇下,斷然承認(rèn)此人類及國民之權(quán)利,且為此宣言’之語,亦與美之合眾國及各州宣言之意義無所異。今略其前文,但對照所列舉之權(quán)利。”*[德]挨里涅克原著:《各國憲法源泉三種合編》,[日]美濃部達(dá)吉原譯,林萬里、陳承澤重譯,中國圖書公司1908年版,第4頁。故此,林、陳的轉(zhuǎn)譯本,獨缺這一“序文”。從這一點來看,林、陳譯本也并非完全的譯本。而“川”顯然沒有耶利內(nèi)克那樣的考慮,所以很自然地保留了“序文”。
(二)兩個譯本的名稱比較
“川”翻譯的《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有一段“譯者序”(見上文)。這一“譯者序”,簡明地表達(dá)了譯注者之所以要譯注《人權(quán)宣言》的基本動機(jī),也闡明了他對人權(quán)的理解,以及關(guān)于人權(quán)與憲法關(guān)系的見解,同時解釋了“人權(quán)十七條”的由來。而譯注者將《人權(quán)宣言》稱之為《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可能是因為該宣言已成為法國1791年憲法的一部分。因此,就兩個譯本的名稱而言,林萬里、陳承澤譯為《人權(quán)及國民權(quán)宣言》更為準(zhǔn)確。
(三)兩個譯本的內(nèi)容比較
從內(nèi)容上看,對兩個譯本進(jìn)行比較,渉及多方面的問題。
其一,兩個譯本中的個別條款之意義有巨大的差別。例如第三條,“川”所譯的意思體現(xiàn)“主權(quán)在國家”,而林萬里、陳承澤則將之譯為“主權(quán)在民”。第十六條,“川”將其譯為“若無憲法,則權(quán)限不分,而種種社會均無自保其險”,這一譯文實際上強調(diào)了憲法的重要性。相較之下,林、陳將其譯為“不安固社會之權(quán)利保障,且不確定權(quán)力之分立,其社會非為有憲法者”,實則強調(diào)了權(quán)利的保障及分權(quán)的重要性。第十七條,林、陳的翻譯為“所有權(quán)為神圣不可侵之權(quán)利”,而“川”譯之為“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王權(quán)”與“所有權(quán)”實為不同的概念。
其二,就條文的語序而言,“川”有時使用“肯定之語序”,而林、陳則有時使用“否定之語序”。這一點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七條及第八條當(dāng)中。對于第七條,“川”的譯文表現(xiàn)了在何種情況下,能夠“逮捕”、“拘留”,而林、陳的譯文,采用了在何種情況下不得“逮捕”、“拘留”。同樣,對第八條,“川”譯為“凡輕罪之當(dāng)受責(zé)罰者,必在法律已經(jīng)編定布告之后,且必法律已經(jīng)正當(dāng)施行之后”。林、陳則譯為“無論何人非依犯罪前制定公布及適法之法律,毋得處罰”。
其三,就條文的用詞而言,“川”在第六、七、十一、十三、十四條中使用“國民”一詞,而林、陳對此有所區(qū)分。其在標(biāo)題及第三條中使用“國民”一詞,此后的第六、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條中,使用“公民”一詞。此外,在第六條中,關(guān)于公職人員的素質(zhì),“川”將其譯為“才德”,而林、陳譯為“價值及技能”。第八條中,林、陳使用“犯罪”一詞,而“川”譯為“輕罪”。第十一條中,“川”將“出版自由”譯為“印刷自由”。第十五條中,林、陳將其譯為“有問其責(zé)任之權(quán)利”,而“川”則譯為“查賬之權(quán)”。
其四,就條文內(nèi)容的完整程度而言,兩個譯本也有所區(qū)別。例如,第七條中,林、陳提及“公訴、逮捕或拘留”,而“川”只翻譯了“逮捕或拘留”,缺少“公訴”的意思。第十條中,林、陳提及“宗教意見”之表達(dá),而“川”并未提及此處。第十一條中,林、陳具體羅列了“自由言論、著述及出版”,而“川”只提及了“任意著作,任意印刷”。
經(jīng)過以上的比較,不難看出,就晚清時期對《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而言,林萬里、陳承澤的譯本是極為準(zhǔn)確、精煉的,屬于上乘之作。林、陳的譯本之所以精準(zhǔn),一個推測性的解釋是,無論是原譯(從法文譯為德文)者耶利內(nèi)克,還是再譯(從德文譯為日文)者美濃部達(dá)吉,是德、日的法政大家。而轉(zhuǎn)譯(從日文譯為中文)者林萬里和陳承澤,也具有良好的法政知識素養(yǎng)。因此,他們對于《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雖然幾經(jīng)轉(zhuǎn)譯,但仍較有可能表達(dá)其原意。
四、“川”本中的“誤譯”
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xiàn)“誤譯”是很常見的現(xiàn)象,甚至是無法避免的現(xiàn)象。毫無疑問,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的翻譯,只能是初步的。而“川”的《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對一些條文的翻譯,不乏精準(zhǔn)之處。但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誤譯的問題。翻譯本是一樁極難的事情,再加上晚清對域外文本的翻譯,不過數(shù)十年歷史,而合格的翻譯人才也不多見,所以晚清的譯書,往往出現(xiàn)不少錯訛。與此同時,因中西語言文字與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巨大差異,容易導(dǎo)致譯者錯誤理解域外的文本所表達(dá)的涵義、觀點與思想。翻譯大家嚴(yán)復(fù)曾經(jīng)指出,譯事有三難,即信、達(dá)、雅。而這信、達(dá)、雅,肯定不是每個譯者都能做到的。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的譯介,也存在著“誤”即不“信”、不“達(dá)”的問題。
(一)“川”本的“誤譯” 之處
在以上晚清中國的兩個《人權(quán)宣言》漢譯本中,林萬里、陳承澤的譯本較為準(zhǔn)確。因此,“誤譯”主要集中于“川”所譯《法國憲法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這一文本。這里所指的“誤譯”大致有如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誤譯”,是指翻譯上的“失誤”,如個別條文的內(nèi)容有所缺失,漏掉了原文中的某一含義,所以翻譯并不完整。例如,第七條中,“川”只翻譯了“逮捕或拘留”,缺少“公訴”的意思。第十條中,“川”并未譯出“宗教意見之自由”的涵義。第十一條中,“川”只提及了“任意著作,任意印刷”,而未譯出“言論自由”。雖然,在“川”的譯本中,“川”對大部分條文作出了自己的注解,注解中有對條文涵義的補充。例如,在第七條的注解中,“川”解釋了“公堂也,民自立而民自入焉,有何不可也”。第十一條的注解中,明確指出“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印刷自由,此三者具而立憲之根基始立”。然而,無論在注解中如何解釋條文的涵義,在條文本身的翻譯中,缺失部分信息,都將被視為對條文翻譯的不精準(zhǔn)。至于為什么會在條文中省去這些內(nèi)容,其原因往往難以考察。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漏譯。
第二種“誤譯”,即翻譯上的“錯誤”,即“錯譯”。通覽《人權(quán)十七條譯注》全文,可以看出,譯者所對條文涵義、內(nèi)容及精神造成誤譯的條款,有第三、十一、十五、十六及十七條。
在第十一條中,“川”將“出版自由”譯為“印刷自由”,并不準(zhǔn)確。印刷與出版并非同一事物。第十五條譯為:“種種社會均有向官員查賬之權(quán)。”但原文為“社會有權(quán)要求其管理部門的一切公務(wù)員報告工作。”“報告工作”與“查賬”,顯然不是一碼事。
第三、十六條涉及一些較為嚴(yán)重的誤譯。第三條譯為:“大權(quán)僅在國家,茍其事非由國家之大權(quán)而出,則無論何人、無論何會,均不能行其私權(quán)。”按《人權(quán)宣言》第三條:“全部主權(quán)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國民之中;任何團(tuán)體或者個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確地來自國民的權(quán)力。”這是對“人民主權(quán)”原則的確認(rèn)。而“川”的譯文,沒有譯出這一原則,反而譯成“大權(quán)僅在國家”。實際上,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第三條的誤譯,顯然不僅僅只有“川”的譯本。就其“誤譯”而言,前引梁啟超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所錄《人權(quán)宣言》第三條的譯文,與原文的差異之大,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原文規(guī)定的是人民主權(quán)原則,說明一國家權(quán)力的來源。而梁啟超所錄則變成了國家主權(quán)問題,指國民全體或一部分不得由外國人管轄或者不可被分割于外國,這不免偏向了民族主義而非人民主權(quán)。而《湖北學(xué)生界》發(fā)表的《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yīng)盡之責(zé)任》一文,也同梁啟超如出一轍。*譯自《支那論叢》并由《湖北學(xué)生界》刊載的《痛黑暗世界》有言:“土地者,國民之所有權(quán)也,東西各國君主,未有敢以國民之土地而擅送友邦者。法蘭西革命之《人權(quán)宣言書》曰:‘國之全體或一部分不可分割于外國。’”這里所謂“《人權(quán)宣言書》曰”,最有可能指的是其第三條的規(guī)定。該文認(rèn)為,這即是民族主義的體現(xiàn)。“自此主義一出,而各國民雖粉骨碎身,不肯奴役于外種人覊軛之下。此十九世紀(jì),所以收民族主義之成功也。”(《痛黑暗世界》,載《湖北學(xué)生界》1903年第4期。)可見這一“誤譯”,在晚清并非個別現(xiàn)象。
“川”的誤譯,尤其體現(xiàn)在第十六條的譯文上。通行的標(biāo)準(zhǔn)譯文是:“任何社會,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權(quán)利獲得保障或者不能確立權(quán)力分立,即無憲法可言。”然而,“川”卻譯為:“若無憲法則權(quán)限不分,而種種社會均無自保其險。”《人權(quán)宣言》原文所揭示的是憲法之所以為憲法所必備的內(nèi)容與精神,即只有“權(quán)利獲得保障”和“確立權(quán)力分立”,才有憲法,否則就沒有什么憲法。該條著力強調(diào)的,是“權(quán)利獲得保障”和“確立權(quán)力分立”對于憲法存在與否的重要性。而“川”的譯文,則是強調(diào)憲法的意義,說沒有憲法就不會有權(quán)限劃分和社會保障。這就顛倒了“權(quán)利獲得保障”、“確立權(quán)力分立”與“憲法”之間的關(guān)系。他還在注解中說:“所謂權(quán)限者,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權(quán)是也,如君權(quán)、民權(quán)之界限是也。”這又在權(quán)力(三權(quán))分立之外,增加了“君權(quán)、民權(quán)”的劃分,也不合原文之意。實際上,“權(quán)限”與“分權(quán)”也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用。
最后,第十七條的譯文,“川”將“財產(chǎn)之所有權(quán)”譯為“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也并不十分準(zhǔn)確。雖然,從“王權(quán)”一詞,可以看出“川”想強調(diào)財產(chǎn)之所有權(quán)的神圣不可侵犯,但“王權(quán)”一詞也并不能直接對譯“神圣的所有權(quán)”這樣一個在法律上較為專業(yè)的詞匯。
(二)“誤譯”的原因
既然出現(xiàn)了“誤譯”,那么“誤譯”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是否也具有一些價值?要對此問題進(jìn)行探析,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誤譯”的存在是否是合理的,亦或是不可避免的?要回答這個問題,則需要追問,完美的翻譯是否是可能的?早在晚清中國,就有一些翻譯家對“好”的翻譯設(shè)立了標(biāo)準(zhǔn),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嚴(yán)復(fù)提出的“信、達(dá)、雅”。嚴(yán)復(fù)曾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對“信、達(dá)、雅”進(jìn)行詳述:“譯事三難:信、達(dá)、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dá),雖譯猶不譯也,則達(dá)尚焉。……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dá)旨,不云筆譯,取便發(fā)揮,實非正法。”*嚴(yán)復(fù)《天演論·譯例言》,載中國翻譯工作者協(xié)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然而,嚴(yán)復(fù)雖明確提出了“信、達(dá)、雅”的標(biāo)準(zhǔn),并對其有著深刻的認(rèn)識,但他的翻譯作品也并非完全達(dá)到“信、達(dá)、雅”之標(biāo)準(zhǔn),且被后人認(rèn)為是“非正法”之作。嚴(yán)復(fù)中期的譯品為“正法”,即本義上的翻譯,道地的翻譯,信、達(dá)、雅三善具備;而初期和末期的譯品多屬于“非正法”翻譯,即變義上的翻譯,是“達(dá)旨”,或“譯述”(即譯中有評、譯中有釋、譯中有寫、譯中有編、譯中有“附益”、譯中有刪削、譯中有案語),甚至采取一種全新的譯法──“引喻有更易”。*參見王秉欽:《20世界中國翻譯思想史》,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3頁。因此,要到達(dá)“信、達(dá)、雅”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是極為困難的。
許多翻譯家或語言學(xué)家同樣認(rèn)為,完美的翻譯是難以實現(xiàn)的。十七世紀(jì)法國最偉大的翻譯家佩羅·德·阿布朗古爾(Perrot d’Ablancourt)的翻譯原則是:“一個翻譯人員能領(lǐng)會詞義就夠了,因為要想把所有的詞都譯出來,那是不可能的。……對于一個作者的著述,從他本人的東西翻譯成我們的東西,只能表達(dá)出原意的大半”*轉(zhuǎn)見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增訂版),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版,第87頁。又如,埃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描述說:“語言學(xué)家早已告訴我們,所有的翻譯都是困難重重的,而完美的翻譯通常是天方夜譚。然而我們也知道,出于實踐的目的,某種差強人意的翻譯總是可能的,不管‘原文’多么佶屈聱牙,畢竟不是絕對不可翻譯的。語言是各不相同的,但還不至于不同到完全無法溝通的地步。”*轉(zhuǎn)見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宋偉杰譯,載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頁。由此可見,語言雖是各不相同的,但仍然具有可溝通交流的空間。所以,即使完美的翻譯難以達(dá)成,但翻譯本身是可能的。
正是由于完美的翻譯難以達(dá)成,才使得翻譯中出現(xiàn)“誤譯”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而造成“誤譯”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如可能是由于語言能力的缺乏,亦或是翻譯技巧的不嫻熟。但是,它還可能受到時代背景、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這可以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翻譯機(jī)構(gòu)或出版社、作者、原作、翻譯的目的、目標(biāo)語讀者的需求和認(rèn)知語境、目標(biāo)語文化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詩學(xué)形態(tài)、譯者等等。*董明:《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頁。這里,筆者將著重從語言及翻譯目的兩方面來分析誤譯的原因。
其一,誤譯可能是由語言本身造成的,包括翻譯者的語言能力、翻譯技巧及其水平的局限。毫無疑問,晚清中國是譯介《人權(quán)宣言》的初始階段,對外文的掌握及翻譯技巧的運用不夠嫻熟,都有可能導(dǎo)致誤譯。此外,譯文是否是由法語直譯而來,亦或是像林萬里、陳承澤一樣經(jīng)過多種語言的轉(zhuǎn)換,由法語到德語到日語,最后譯為中文,也可能造成翻譯的偏差。而“川”之語言能力,譯文是由何種版本譯來,均無法考究,就此難以總結(jié)“川”之誤譯受到語言本身的多大影響。
從“川”本存在的誤譯來看,除去個別條文內(nèi)容上的缺失,還有個別誤譯源自用詞精準(zhǔn)度的缺乏。例如,第十一條中,“川”將“出版自由”譯為“印刷自由”。又如,第十七條的譯文,“川”將“財產(chǎn)之所有權(quán)”譯為“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這都有不確之處。梁啟超曾在《論譯書》中說:“譯書之難讀,莫甚于名號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后又互異,則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載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頁。所謂“名號”,如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等。那么,是否由于“名號不一”,或“非外語不足以表彰新穎之名詞”而導(dǎo)致誤譯呢?實際上,每當(dāng)談及翻譯中用詞的問題,都不得不考慮譯出語與譯入語的對應(yīng)性。換言之,外文中的語詞、概念或涵義是否能用完全與之對應(yīng)的中文予以表達(dá)。通常而言,人們認(rèn)為,如果無法用中文詞語精確地表達(dá)外文的含義,一定是缺乏對等詞。然而,從相反的角度思考,即無法用中文詞語精確地表達(dá)外文的含義,并非一定是缺乏對等詞,而是由于對等詞太多。如果說漢語仍舊是最難翻譯的語言之一,那么可能的情況是,這種難度恰恰在于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假設(shè)的對等詞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而不在于缺少這種對等。*參見劉禾:《跨文化研究的語言問題》,宋偉杰譯,載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頁。這一點,似乎能夠很好地解釋“川”誤譯的原因。
嚴(yán)復(fù)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曾寫道:“蓋翻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dāng)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開。”*嚴(yán)復(fù):《與梁啟超書(三)》,載王栻主編:《嚴(yán)復(fù)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19頁。嚴(yán)復(fù)這一論述的意思是,在中文里仔細(xì)考究,終能找到與西字對應(yīng)之詞。“川”的“誤譯”,即以“印刷自由”代替“出版自由”,以“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代替“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且以“國民”代替“公民”及“人民”,并不在于其創(chuàng)造了與西字不相符合之詞,從而顯示誤譯是由于中文的語詞及概念中缺乏與西字相對應(yīng)之詞。因為無論是“印刷自由”還是“出版自由”,“財產(chǎn)之王權(quán)”還是“財產(chǎn)之所有權(quán)”,“國民”還是“公民”及“人民”,都是已經(jīng)存在的中文詞匯。由此可以認(rèn)為,“川”的誤譯,實際是由于漢語與其他語言間存在大量的對應(yīng)詞,從而使“川”在已存在的與西字相對應(yīng)的語詞中,選擇了并非精確的詞匯。
其二,在以上這些業(yè)已存在的語詞中,“川”選擇了并不完全符合原文意義的詞匯,這當(dāng)然與“川”對文本的理解極為相關(guān),同時也多少受到語言之外的因素的影響,例如時代背景、翻譯的目的及社會需要等等。
如果結(jié)合兩項翻譯理論及晚清的時代背景和格局,似乎就能夠找到一些思考線索。根據(jù)香港中文大學(xué)的王宏志所述,首先,不得不提到倫敦大學(xué)Theo Hermans教授提出的“操控學(xué)派”(Manipulation School)學(xué)說。這一學(xué)說提出,“翻譯是對原文的重寫(a rewriting of the original),且是譯者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對原文進(jìn)行的操控(manipulation)”。換言之,譯者在翻譯時會對原著作出各種各樣的修正、改寫以及整理,從而憑借具有很大“重寫”成分的“譯文”,來達(dá)到他原來所設(shè)定的目標(biāo)。由于譯者和他的譯文所面對的是譯入語文化和譯文讀者,因此,他所設(shè)定的目標(biāo)、他的改寫和操控,都是針對著譯入語來進(jìn)行的。其次,安德魯·利弗威爾指出:“翻譯并不是在真空里進(jìn)行的”(Translation is not done in a vacuum.)。也就是說,無論哪一位譯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語言,面對完全不同的讀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疇下運作,受到各種各樣主觀的或客觀的環(huán)境條件所制約,因而在翻譯時會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不同考慮,根本不可能翻譯出跟原文一模一樣的譯文來。*參見王宏志:《一本〈晚清翻譯史〉的構(gòu)思》,載《中國比較文學(xué)》2001年第2期。這些觀點,對我們解釋“川”的誤譯,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回到晚清的情景中來看,一方面,晚清士人正著力進(jìn)行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各種立憲運動蓬勃開展,人們逐漸認(rèn)識到憲法的重要性。金觀濤、劉青峰的研究表明,“1900年以后,‘憲法’的使用次數(shù)明顯增多,并分別形成了1906、1913年兩個高峰。”*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xiàn)代重要政治術(shù)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頁。1900年,梁啟超談到“憲法”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時說:“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旨也。西語原字為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又說:“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梁啟超:《立憲法議》,載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407頁。而在1906年清政府開始廷籌備立憲之后,“憲法”一詞就更常常出現(xiàn)在不少大臣的奏折之中。這些表明,晚清士人對立憲與憲法,是何等的向往。因此,“川”在翻譯《人權(quán)宣言》第十六條時,可能帶著宣揚憲法的目的,從而在譯文中強調(diào)“憲法”的意義,也就不難讓人理解了。另一方面,晚清中國正經(jīng)受外國列強的入侵和欺壓,處于民族存亡的關(guān)鍵時刻,急需建立現(xiàn)代國家觀念和民族認(rèn)同意識。實際上,在1895至1900年之間,梁啟超曾主張“人民國家”:“使國家成為人民國家,則制造國魂之機(jī)器也。”然而,到了1905年以后,在與革命派的辯論中,梁啟超傾向于“國家主權(quán)說”,并提出了“開明專制論”。*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xiàn)代重要政治術(shù)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頁。由此看來,對《人權(quán)宣言》第三條的翻譯,無論是“川”本所譯“大權(quán)僅在國家”,還是梁啟超所譯“主權(quán)在國”,都反映了晚清士人追求國家強盛與民族獨立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重要翻譯家,把翻譯當(dāng)成改良社會、救亡圖存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翻譯動機(jī)和選材上將社會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因此,清末的翻譯往往重意譯,即注重原作思想、觀念的傳輸,不太在乎原文語言形式上的表達(dá)。從這一角度而言,似乎能夠接受并包容“誤譯”的存在。與此同時,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現(xiàn)有的各種翻譯標(biāo)準(zhǔn)大多過于強調(diào)忠于原文或原文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譯文面貌的其他影響因素,尤其是目標(biāo)文化、翻譯動機(jī)、譯文用途、譯文讀者”。*參見楊平:《翻譯的政治與翻譯觀念的再思考》,載《天津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07年第2期;王克非:《近代翻譯對漢語的影響》,載《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2002年第6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將目標(biāo)文化、翻譯動機(jī)、譯文用途等要素考慮在內(nèi)的對翻譯優(yōu)劣的評價,都必須考慮到法律文本對嚴(yán)謹(jǐn)性的要求。法律文本及其翻譯,尤其是法律條文的翻譯對嚴(yán)謹(jǐn)性的追求,與文學(xué)等翻譯有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在法律文本的翻譯中,任何用詞以及表達(dá)的出入都將改變整個條文的涵義。因此,即使將晚清翻譯法國《人權(quán)宣言》的目的、社會需求考慮在內(nèi),也不能化解翻譯中存在的誤譯所造成的誤解。
除此之外,“川”誤譯的另一個原因,可能還在于,其譯注文本并非法國《人權(quán)宣言》單一完整的譯本,而是將譯文與譯注相結(jié)合的文本。由于這一方式,“川”在心理上覺得,即便在翻譯時使用了并不完全精準(zhǔn)的用詞,但可以用注解的形式來加以補救。
(三)“誤譯”的價值
當(dāng)然,即使是像法國《人權(quán)宣言》這樣的法律文本在晚清的翻譯中存在著“誤譯”,這些“誤譯”也并非一文不值。如果說精準(zhǔn)翻譯原文本來的含義,傳遞原作者本身的思想,是翻譯的基本目的和意義,那么“誤譯”也能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正是由于“川”的誤譯可能包含了歷史大背景及社會需求等各項復(fù)雜因素,這樣的“誤”才更值得深入挖掘,從而更深入了解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的不同解讀。而“川”對于“平等”、“自由”、“國民”、“權(quán)利”等各種名詞的使用,也構(gòu)成了晚清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說,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思想史,就是一張由各種新名詞為網(wǎng)結(jié)編織起來的立體多維的觀念之網(wǎng)。幾乎沒有哪種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詞、新概念作為網(wǎng)結(jié)構(gòu)造而成的。因此,要認(rèn)知各種近代新思想,測量其社會化程度,就不能不從總體上考慮這些新思想所包含的各種重要的新詞匯、新概念的形成、傳播和社會認(rèn)同問題。在這樣的認(rèn)識之下,“川”的誤譯,不可絕對否定。
與此同時,根據(jù)“川”的誤譯,人們似乎能夠提出許多超出翻譯本身的更為深刻的思想性問題。例如,晚清中國如何理解“國民”、“公民”、“人民”這三個名稱的內(nèi)涵?是否缺乏對三者涵義的分辨?以及如何看待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又如,“川”將“任何社會,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權(quán)利獲得保障或者不能確立權(quán)力分立,即無憲法可言”,譯為“若無憲法,則權(quán)限不分,而種種社會均無自保其險。”那么,晚清中國是如何看待憲法與權(quán)利以及分權(quán)的關(guān)系,又是如何看待憲法的地位的?這些都是晚清人權(quán)思想發(fā)展過程中極具價值的問題。
總而言之,在《人權(quán)宣言》的兩個譯本中,“川”的譯本存在一些誤譯和偏差,這當(dāng)然是由于完美的翻譯是難以達(dá)成甚至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川”的翻譯可能受到時代背景、翻譯目的及社會需要等因素的影響。雖然存在一些誤譯與偏差,但也多有精準(zhǔn)之譯,這些都是人們了解和認(rèn)識《人權(quán)宣言》的基礎(chǔ)。不同的譯本,對用詞、語序、句式的選擇,無論精準(zhǔn)或錯誤,都蘊含了晚清士人對《人權(quán)宣言》的獨特理解。毫無疑問,這些翻譯對《人權(quán)宣言》在晚清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責(zé)任編輯:王德福]
收稿日期:2015-10-21
基金項目:本項研究及論文獲得重慶大學(xu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0903005203298)資助。
作者簡介:程夢婧(1987-),女,重慶人,法學(xué)博士,重慶大學(xué)法學(xué)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憲法學(xué)與人權(quán)史。
中圖分類號:D90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9-8003(2016)01-0151-10
Subject:O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uthor & unit:CHENG Mengjing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Since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was brought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ions appear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Ms. Xiaopin’s translation in 1903 is actually not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as people usually thought. Two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important, which is Chuan’s version in 1907 and Lin Wanli and Chen Chengze’s version in 1908. To compare thos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differences are found in their prefaces, titles and contents. Besides, there are some mistranslations in Chuan’s translation. The reasons to mistranslate are various. Chuan might be affected by his language ability,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he social need. Nevertheless, even though some mistranslations are in Chuan’s translation, the values of both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Déclar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ll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mis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