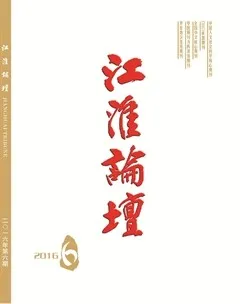析印度尼西亞解釋和運用《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合法性與缺失
李潔宇
摘要:印度尼西亞對《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和運用主要體現(xiàn)在國內(nèi)海域制度和海洋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的立法、海事管理、海域劃界中。印度尼西亞為推動《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了群島國家制度,爭取到了其主張的群島國家的權(quán)利,在海域劃界中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tǒng)一,捍衛(wèi)了對馬六甲海峽的權(quán)利,這些都是行使和履行《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表現(xiàn)。印度尼西亞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立法關(guān)于環(huán)境污染防治懲罰和批準(zhǔn)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等方面的規(guī)定明顯違反《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在群島水域內(nèi)指定海上航道也不符合法定程序,這些都是其解釋和運用《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不合法之處。
關(guān)鍵詞:印度尼西亞;《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群島水域;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馬六甲海峽
中圖分類號:D993.5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6-0131-006
印尼不僅是沿海國家,更具有意義的是,它是群島國家。印尼不遺余力地使第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接受了其提倡的群島國家定義及群島基線方式,這是印尼捍衛(wèi)陸地領(lǐng)土和海洋權(quán)利訴求的起點和支撐。保持群島的完整性和捍衛(wèi)群島國家的權(quán)利是印尼爭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保障。本文將分析印尼對于《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特殊貢獻(xiàn),評價印尼解釋和運用《公約》的得與失,探尋印尼解釋和運用《公約》的特征與可借鑒之處。
一、印尼海域制度和海洋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的立法對《公約》的解釋和運用
印尼對《公約》的出臺作出了積極貢獻(xiàn),它的國內(nèi)立法對《公約》的解釋和運用有值得稱道之處,也有明顯有失偏頗的地方。
(一)國內(nèi)立法中倡議的“群島國家”和“群島基線”被《公約》吸納
《公約》第四章“群島國家”是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長期推動的結(jié)果。至《公約》1982年出臺,印尼關(guān)于“群島國家”的利益訴求已付諸了20多年的努力。
第一次海洋法會議上,印尼傳達(dá)了自己的理念,群島是一個鑲嵌著島嶼的水體,而不是處在水中的島嶼。連接這些島嶼和位于其周圍的水域和島嶼本身共同構(gòu)成群島,群島是單一整體。[1]這一概念沒有被接受。在1960年3—4月的第二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上,印尼反對3海里的領(lǐng)海寬度,堅持主張用直線基線方式確定印尼的群島基線及12海里領(lǐng)海寬度。[2]第三次聯(lián)合國海洋法會議接受了印尼關(guān)于群島是水域和陸地統(tǒng)一體的建議,《公約》第46條款反映了印尼的群島概念,而且兼顧了群島國家的安全關(guān)切及政治利益和其他國家的航行權(quán)利。
(二)環(huán)境立法特點表現(xiàn)為可操作性強(qiáng),責(zé)任界定明確,但對違規(guī)行為的規(guī)定超出了《公約》賦予的權(quán)限
《公約》高度重視保護(hù)和維持海洋環(huán)境,其視為締約國的義務(wù),印尼根據(jù)本國國情,完善環(huán)境立法,使其帶有較強(qiáng)的可操作性,但是,其環(huán)境立法存有僭越《公約》賦予締約國權(quán)限的情況。《公約》只是籠統(tǒng)規(guī)定,締約國應(yīng)制定法律法規(guī)和采取其他措施防治各種渠道的海洋環(huán)境污染。印尼立法指出,在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從事各種類型的行為時,行為體應(yīng)該預(yù)防、控制和對海洋環(huán)境污染進(jìn)行糾偏。
印尼立法指出,在其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蓄意破壞或污染海洋環(huán)境的行為體,應(yīng)根據(jù)其海洋環(huán)境保護(hù)法律法規(guī)被施以威脅。[3]此處未指明具體的威脅所為何意。《公約》第230條規(guī)定,對于外國船只在領(lǐng)海以外所犯違反關(guān)于防治海洋環(huán)境污染的國內(nèi)法律法規(guī)或可適用的國際規(guī)則和標(biāo)準(zhǔn),僅可處以罰款。[4] “領(lǐng)海以外”明顯包括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在內(nèi)。如果威脅對在其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內(nèi)從事這種違規(guī)行為的行為體處以罰款之外的刑罰例如監(jiān)禁或拒絕回應(yīng)相關(guān)船旗國迅速釋放的要求,明顯有悖于《公約》的規(guī)定。
(三)關(guān)于無害通過權(quán)的規(guī)定體現(xiàn)了時代性與兼容性
無害通過是所有國家不管是內(nèi)陸國還是沿海國在某個領(lǐng)海均可享有的權(quán)利,這項權(quán)利在1958、1962和1982年的國際海洋法文件中均得到認(rèn)同。印尼關(guān)于無害通過權(quán)的立法經(jīng)歷了變遷,跟上了國際海洋法的變化,也兼顧了普遍適用的相關(guān)國際法規(guī)則。
1962年印尼通過《外國船舶在印度尼西亞水域內(nèi)無害通過的政府條例》對外國船舶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水域的無害通過進(jìn)行規(guī)范和管理。《條例》規(guī)定,除非事先通知印尼海軍,否則政府船舶和軍艦以及潛水艇在水面上航行將被認(rèn)為是有害的,應(yīng)被立即驅(qū)逐,還對捕魚船和科考船的通過作了規(guī)定。[5]
2002年,印尼通過《外國船舶在印度尼西亞水域行使其無害通過權(quán)時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政府條例》,對《公約》第19條進(jìn)行了補充,將破壞自然資源、水下管道、導(dǎo)航設(shè)施的行為列為有害通過行為,保留了對于捕魚船和科考船的規(guī)定,去除了對軍艦和政府船舶的專門性規(guī)定。
1982年之前國際海洋法文件并沒有特別規(guī)定軍艦的無害通過權(quán)利,所以當(dāng)時各國對這一權(quán)利的行使施加了各種規(guī)范性的規(guī)定。《公約》明確規(guī)定無害通過權(quán)利同樣適用于軍艦、用于非商業(yè)性用途的政府船舶,印尼立法也隨之進(jìn)行了相應(yīng)調(diào)整,并對《公約》嚴(yán)重污染海洋環(huán)境的非無害通過行為進(jìn)行了細(xì)化,同時兼顧了國際船舶避碰規(guī)則。
(四)關(guān)于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管轄權(quán)的立法較為強(qiáng)勢,權(quán)限范圍超出了《公約》規(guī)定的權(quán)力清單
印尼于1983年頒布了由總統(tǒng)簽署的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5號法令,并對其作出公開解釋。該法對《公約》的原則性語言進(jìn)行了細(xì)致化處理,但因較為強(qiáng)勢在某些方面偏離了《公約》的規(guī)定。
印尼立法指出,未經(jīng)印尼共和國政府許可在其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內(nèi)修建或使用任何人工島嶼、設(shè)施和結(jié)構(gòu)的行為均為非法。[3]而《公約》的實際規(guī)定是,締約國在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對于用于勘探、開發(fā)、管理、養(yǎng)護(hù)海床和底土及上覆水域自然資源或用于勘探和開發(fā)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其他經(jīng)濟(jì)活動的設(shè)施和結(jié)構(gòu)具有管轄權(quán)。[6]
印尼政府發(fā)表公告,在其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內(nèi)開展的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應(yīng)有利于增進(jìn)印尼本國的福祉,如果在接到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申請的四個月內(nèi),印尼政府并沒有申明拒絕這個項目,或要求得到關(guān)于項目的其他信息,或申請開展項目的外國人或國際組織關(guān)于之前的項目尚有尚未履行的責(zé)任,則視為6個月后印尼自動批準(zhǔn)這個項目。《公約》則規(guī)定,如果意欲在某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或大陸架開展的某項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有利于增進(jìn)人類的海洋科學(xué)知識或增進(jìn)整個人類的福祉,則沿海國應(yīng)該毫不耽擱地批準(zhǔn)這個項目,并且在國內(nèi)立法程序中為這種批準(zhǔn)提供便利。印尼修改了《公約》毫不猶豫批準(zhǔn)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的規(guī)定,生硬地加上6個月的前置時間條件,更默認(rèn)印尼政府在此期間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拒絕批準(zhǔn)項目,可見其在批準(zhǔn)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海洋科學(xué)研究項目方面強(qiáng)調(diào)主觀利益而忽略了《公約》的硬性規(guī)定,以致偏離了《公約》的正常運行軌道。
二、印尼在海洋劃界談判事務(wù)方面對
《公約》的解釋和運用
印尼和16個國家協(xié)定均采用了談判的方式。另外還有6個尚未完全解決的海域劃界爭端:和馬來西亞未解決關(guān)于安巴拉特海的爭端,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未解決馬六甲海峽的劃界爭端,未批準(zhǔn)和澳大利亞的《珀斯條約》,和東帝汶、帕勞均未展開劃界談判,和菲律賓未解決大陸架劃界爭端。[7]印尼在劃界問題中適用《公約》特色鮮明,具體分析如下。
(一)堅持用談判方式解決劃界問題
《公約》規(guī)定,如果發(fā)生領(lǐng)海重疊爭端,相關(guān)國家應(yīng)該首先用協(xié)定方式解決爭端,若不能達(dá)成協(xié)定,除非出于歷史原因或其他特殊情境,則用中間線方式解決爭端。關(guān)于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和大陸架劃界問題,《公約》未明示任何方式,只是規(guī)定相關(guān)國家用能產(chǎn)生公平結(jié)果的建立在國際法規(guī)則基礎(chǔ)之上的協(xié)定來解決爭端。關(guān)于重疊海域劃界問題,《公約》顯示了極強(qiáng)的結(jié)果導(dǎo)向,談判是通向協(xié)定的具體路徑,締約國之間的重疊海域劃界問題由他們直接通過談判加以解決。談判是利益交換和智慧博弈的結(jié)果,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綜合體現(xiàn)。
印尼堅持用談判方式解決和相關(guān)國家的重疊海域劃界問題。東帝汶獲得獨立后,曾向聯(lián)合國發(fā)表外交照會抗議印尼1996年提交的領(lǐng)海基線聲明,清楚地闡明反對哪一個具體位置的基線及反對原因。印尼和東帝汶存在懸而未決的領(lǐng)土爭端,海域劃界爭端無從解決。印尼曾在利提干和錫鉑丹島的歸屬問題上輸?shù)袅斯偎綶8],較少傾向于訴諸于國際司法程序解決海域劃界爭端,從其實際表現(xiàn)看,印尼更傾向于和東帝汶用談判方式解決劃界爭端。
(二)在談判中堅守國家利益的底線
《公約》談判歷時9年,在無法達(dá)成一致的問題上出臺了見仁見智的條款,即無法適用同一標(biāo)準(zhǔn)的條款,締約國可以對這些條款進(jìn)行不同理解。例如,如前所述,關(guān)于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和大陸架劃界的問題,《公約》沒有給出標(biāo)準(zhǔn)答案,歷史性權(quán)利的介入增加了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和大陸架劃界的難度。群島制度是《公約》新確立的制度,群島國家和其鄰國的利益如何兼容,也是劃界中必然考慮的因素。
群島基線是《公約》規(guī)定的群島國家權(quán)利的起點,其初衷在于維護(hù)群島國家政治上的統(tǒng)一性。1971年和1972年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關(guān)于大陸架劃界談判中,印尼提出了群島基線,以此作為測量大陸架的起點,得到澳大利亞的認(rèn)可,而當(dāng)時距離《公約》頒布還有近10年時間,印尼為堅守國家利益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三)堅持靈活性,分解復(fù)雜問題使其簡單化
根據(jù)《公約》規(guī)定,沿海國領(lǐng)海以外依其陸地領(lǐng)土的自然延伸,直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qū)域的海床及底土構(gòu)成大陸架,如果從領(lǐng)海基線起到大陸邊的外緣不足200海里,則延伸至200海里。
1997年印尼和澳大利亞簽署了一攬子解決劃界問題的《帕斯條約》,規(guī)定了三條劃界線。一條將1971年和1972年的大陸架劃界線延伸至印度洋的公海,即認(rèn)可澳大利亞大陸架延伸至帝汶海槽的主張;一條是在上述海域長達(dá)70公里的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劃界線,和1981年雙方確定的臨時漁業(yè)執(zhí)法線一致;一條是印尼爪哇島和澳大利亞圣誕島之間同步劃分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和大陸架的分界線,因該爭議海域深度不適于油氣開發(fā),澳大利亞于是放棄爪哇海槽是雙方大陸架分界線的立場。[9]
第一條劃界線認(rèn)可了澳大利亞堅持的外大陸架外部邊界主張,使澳大利亞獲得了面積廣袤的外大陸架。第二條邊界線劃分了重疊的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兩條邊界線并不同一。第三條邊界線是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和大陸架的合二為一。可見,印尼在和澳大利亞的談判中發(fā)揮了靈活性,一事一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四)運用相對收益思維,和談判對手達(dá)成雙贏結(jié)果
第四章“群島國家”的條款是群島國家爭取的結(jié)果。印尼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洋法會議上均提出了把群島作為一個單一整體界定群島國家領(lǐng)土的原則及群島基線方式,未得到滿意回應(yīng),第三次海洋法會議終遂其愿。印尼基本沒有簽署《公約》之前關(guān)于海洋問題的國際條約。[10]《公約》第47條規(guī)定,如果群島水域位于群島國家直接毗鄰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則根據(jù)這個國家和群島國家的既存協(xié)定,這個國家傳統(tǒng)上在該群島水域內(nèi)享有的捕魚權(quán)利和其他的合法利益應(yīng)該繼續(xù)維持并得到尊重。印尼和馬來西亞是直接相鄰的國家,他們商定在《公約》頒布之前就群島國家地位問題和歷史性權(quán)利問題達(dá)成協(xié)議。1982年,他們簽署《關(guān)于群島國法律制度和馬來西亞在位于東、西馬來西亞之間的印度尼西亞領(lǐng)海、群島水域以及印度尼西亞領(lǐng)海、群島水域和領(lǐng)土上空的權(quán)利的條約》,馬來西亞承認(rèn)印尼的作為群島國家擁有對其主張的群島水域的主權(quán),印尼則承認(rèn)馬來西亞在其群島水域的捕魚權(quán)利,包括不得暫停的軍事活動在內(nèi)的航行權(quán)利和飛越權(quán)利,維護(hù)和檢修電纜和管道的權(quán)利,實施搜救的合法權(quán)利,以及和印度尼西亞聯(lián)合進(jìn)行海洋科學(xué)研究活動的權(quán)利。[11]
三、印尼在海事方面對《公約》的解釋和運用
印尼是群島國家,也是用于國際航行海峽的沿岸國家,印尼對于群島水域的主權(quán)應(yīng)被置于國際航行海峽制度之下。印尼在解釋和運用《公約》時既有合法捍衛(wèi)海峽沿岸國家主權(quán)和管轄權(quán)的一面,也有超越《公約》賦予權(quán)限的一面。關(guān)于印尼在海事管轄方面對于《公約》的遵守和違反,具體分析如下。
(一)非法懸停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
《公約》第47條規(guī)定,群島國家可連接群島最外緣島嶼或干礁最向外突出的點劃定群島基線,被群島基線封閉起來的水域是群島水域,群島國家對之擁有主權(quán)。第52條規(guī)定,所有國家的船舶在某個群島水域內(nèi)享有無害通過權(quán),群島國家可為保護(hù)國家安全所需要懸停這種權(quán)利,但這種懸停需正式公布后才發(fā)揮效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群島通過權(quán)利,群島水域中的無害通過權(quán)利相當(dāng)于沿海國家領(lǐng)海中的無害通過權(quán)利,可以基于維護(hù)安全的理由被懸停。而如果群島國家行使了劃定群島海道的權(quán)利,則其他國家應(yīng)對群島海道保持適當(dāng)顧及,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回報,群島國家不能懸停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很明顯,這是《公約》在群島國家對群島水域主權(quán)和其他國家航行權(quán)利二者之間作出的平衡。
1988年,印尼封鎖了巽他海峽(sunda)和龍目海峽。[12]這兩個海峽位于印尼的群島水域。當(dāng)時印尼還沒有指定群島海道,其他國家應(yīng)該通過正常用于航行的海上航道行使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公約》規(guī)定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旨在防止群島國家以位于群島水域內(nèi)的國際航行海峽是其領(lǐng)土為由對其進(jìn)行封鎖的可能性。印尼封鎖這兩個海峽等于懸停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明顯違反了《公約》締約國的義務(wù)。
(二)非法懸停用于國際航行海峽內(nèi)的過境通行權(quán)
《公約》規(guī)定了用于國際航行的連接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一部分和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另一部分之間的海峽內(nèi)的過境通行權(quán)。海峽過境通行權(quán)和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是對保持處于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一部分和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另一部分之間的國際航行海峽開放性的雙重保險。《公約》第三部分“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規(guī)定,海峽沿岸國的主權(quán)和管轄權(quán)的行使受本部分和其他國際法規(guī)則的限制。第37條規(guī)定,過境通行權(quán)適用于在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一部分和公海或?qū)俳?jīng)濟(jì)區(qū)另一部分之間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第44條規(guī)定,過境通行權(quán)不應(yīng)予以懸停。[6]
美國海軍對巽他(sunda)海峽的使用日益增多,是美國在菲律賓蘇比克灣的海軍基地和印尼迪戈加西亞軍事和通訊設(shè)備之間的直接通道,也是北太平洋國家通往東非、西非或者繞道好望角到歐洲航線上的航道之一。印尼群島水域內(nèi)的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龍目海峽,翁拜(Ombai)海峽和帝汶(Timor)海峽連接公海的一部分和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的一部分,又是著名國際水道,適用于過境通行權(quán)。印尼在封鎖巽他海峽和龍目海峽之后,借口《公約》尚未生效逃避國際社會的譴責(zé),聲稱這是印尼在行使自己的主權(quán)權(quán)利。
(三)群島海上航道的設(shè)置違反《公約》法定程序
在指定群島海道或指定分道通航制度實施之前,群島國家應(yīng)向?qū)iT國際組織提交建議有待于后者批準(zhǔn),后者只批準(zhǔn)和群島國家議定的航道或通航制度。可見,根據(jù)《公約》規(guī)定,群島國家有權(quán)利選擇指定海上航道或制定通航制度與否,但是如果選擇這樣做,應(yīng)該履行提請國際組織批準(zhǔn)建議的義務(wù)。
國際海事組織規(guī)定,如果批準(zhǔn)了群島國家提交的群島海上航道建議,則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就可在這些航道上行使,否則,在群島國家沒有指定海上航道或指定了部分海上航道的情況下在正常使用的航道行使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
印尼是第一個指定群島海上航道的群島國,但他并沒有遵照法定程序?qū)⒑I虾降澜ㄗh提請國際海事組織批準(zhǔn),是單邊行為。[13]2002年6月,印度尼西亞通過《關(guān)于外國船舶和飛機(jī)行使海道通過權(quán)通過指定群島海道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的政府條例》,以國內(nèi)立法形式指定了3條南北航向的海上航道。海事組織海上安全委員會和船舶路線一般性規(guī)定將印尼的海上航道稱為部分性海上航道,并規(guī)定,在印尼的群島海上航道生效之后,其他國家仍然可以通過用于國際航行或飛越的正常通道行使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5]
國際海事組織正視了印尼群島海上航道的程序缺失,隱晦地承認(rèn)其合法性的不完善。通過非合法程序確立的印尼群島海上航道不能和正常群島海上航道相提并論。對于正常群島海上航道而言,群島國家有權(quán)利要求其他國家在這些海道行使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但印尼卻不能阻止其他國家通過正常航道行使群島海道通過權(quán)。
(四)自覺捍衛(wèi)對于馬六甲海峽的管轄權(quán)
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沿岸國,這兩個海峽完全由三國的領(lǐng)海和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構(gòu)成。《公約》第43條規(guī)定,海峽沿岸國和使用國應(yīng)在建設(shè)導(dǎo)航設(shè)施以及設(shè)立有助于航行的其他改進(jìn)措施和預(yù)防、減少和控制海洋環(huán)境污染這兩個方面進(jìn)行合作。[14]《公約》還規(guī)定了打擊海盜的國際合作義務(wù),但是其將海盜行為定義為發(fā)生在公海的行為無疑不利于打擊專屬經(jīng)濟(jì)區(qū)內(nèi)同類性質(zhì)行為的國際合作,鑒于此,馬六甲海峽沿岸國必須為打擊武裝搶劫船只行為自謀出路。
印尼主要采用三種方式和新加坡、馬來西亞合作對馬六甲和新加坡海峽進(jìn)行管轄。一是2002年,三國締結(jié)三邊協(xié)定,合作事項多達(dá)十一類,包括反恐、打擊武裝搶劫船只行為等等。二是2004年6月17日,印度尼西亞提議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三國各派出5到7艘軍艦組成聯(lián)合海軍巡邏部隊在馬六甲海峽執(zhí)行巡邏任務(wù),這一倡議得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積極回應(yīng)。[15]2004年,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開始對于馬六甲海峽和新加坡海峽進(jìn)行聯(lián)合巡邏,這種巡邏是協(xié)調(diào)或合作式的,而非共同巡邏。三是2007年,三國建立關(guān)于提升航行安全和防治海洋環(huán)境污染的合作機(jī)制,主要合作形式有合作論壇,項目執(zhí)行協(xié)調(diào)委員會和更新維持導(dǎo)航設(shè)備基金。
四、結(jié) 語
印度尼西亞解釋和運用《公約》有兩點基本考慮:首先,實現(xiàn)其國家利益,增進(jìn)人民福祉。[16]其次,捍衛(wèi)對群島水域的主權(quán)及相關(guān)海域的權(quán)利。對于這兩點考慮的過度關(guān)切,印尼在國內(nèi)立法和海洋管轄實踐中或多或少偏離了《公約》的正常運行軌道,帶有合法性缺失。這體現(xiàn)了國內(nèi)立法和實踐與國際法的矛盾,也體現(xiàn)了國家捍衛(wèi)主權(quán)完整性和向在某項具體事務(wù)上向國際組織讓渡主權(quán)權(quán)利的矛盾,反映了所有國家在處理國際法問題上的微妙心理。主權(quán)完整性與否涉及國家的合法性問題,這使得國家實體在捍衛(wèi)自身主權(quán)和主權(quán)權(quán)利的時候必須嚴(yán)陣以待,以保持政權(quán)的合法性。在處理國際關(guān)系事務(wù)時,國家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觀意愿行事,國際法的約束性便可見一斑。把主權(quán)國家身份和國際組織成員國或國際協(xié)定締約國身份置于天平兩端,國家會向這邊或那邊傾斜。印尼獲得獨立后將現(xiàn)代國際海洋法意義上的群島水域視為領(lǐng)土所在地,對這一水域的絕對管轄權(quán)的關(guān)切使之明知故犯,在指定群島海上航道時僭越正常法定程序。印尼在海域劃界和表達(dá)海域權(quán)利訴求等事務(wù)中必須依靠《公約》以獲得法理支持。這表明要求國家實體在任何時候無條件服從國際法成了一個難題,印尼解釋和運用《公約》的實踐印證了這一難題。無論如何,印尼在爭取群島國家地位和權(quán)利中付出的努力及體現(xiàn)的精神值得借鑒。
參考文獻(xiàn):
[1]Donald R. Rothwell,Tim Stephens, ed..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M].Hart Publishing, 2010:356 .
[2]Arthur H.Dean.The Second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the Sea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60,(4):751-789.
[3]Robert W. Smith.the Indonesian Exclusive Economiv Zone by the Grace of Go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laims, an Analysis and Primary Documents[M].Nijhhoff Publishers,1986,(5):231-233.
[4]董治良, 趙中社, 張軍.海南省海洋執(zhí)法工作手冊[M].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海南省海洋與漁業(yè)廳,2013:201.
[5]Bun Toro K.An Analysis of Legal Issues Relating to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through and over Indonesian Waters[J].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2010:35-190.
[6]Brown, E.D..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J] .Volume I Introductory Manual,Dartmouth, 1994:259-261.
[7]劉暢.印度尼西亞海洋劃界問題:現(xiàn)狀、特點與展望[J].東南亞研究,2015,(5):36-39.
[8]李榮珍,吳一亮.海事行政處罰聽證程序的初步研究[J].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3,(6):90-97.
[9]Puspitawati D.The Development of Indonesias Maritime Claims[J].Perspektif Hukum,2010:75-90.
[10][馬]拉姆利﹒多拉,萬·沙瓦魯丁·萬·哈桑,著,文一杰,譯.印度尼西亞海洋邊界管理中的挑戰(zhàn):對馬來西亞的啟示[J].南洋資料譯叢,2015,(1):28-35.
[11]Agoes ER. Current Issues of Marine and Coastal Affairs in Indonesia[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1997,(2):201-224.
[12]Donald R. Rothwell.Law of the Sea[M].Chel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3:473.
[13]James Kraska,Paul Pedrozo.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Law[M].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231.
[14]Sam Bateman, Maritime Security.Regional Concern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in William T. Tow ed.,Security Politics in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al-Global Nexus[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235-250.
[15]張杰.冷戰(zhàn)后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海峽安全模式選擇[J].東南亞研究。2009,(3):6.
[16]曲波.海洋法與人權(quán)法的相互影響[J].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3,(4):89-95.
(責(zé)任編輯 秋 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