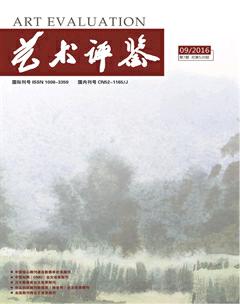論張愛(ài)玲小說(shuō)的情節(jié)藝術(shù)
馮碧華 杜慧
摘要:張愛(ài)玲像一朵凄艷的花以她獨(dú)特的魅力給世人以“蒼涼的啟示”。翻開(kāi)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撲面而來(lái)的便是震撼人心的人物生活情節(jié),在那個(g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普通的凡人承受的時(shí)代重負(fù)最能反映時(shí)代生活的艱難可怕的狀貌。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能夠最直接把握到時(shí)代最真實(shí)、基本的變化,從而表現(xiàn)出時(shí)代的本質(zhì)。然而只有少數(shù)作家像張愛(ài)玲這樣把視角投向那些普通凡人的日常生活。本論文通過(guò)探究張愛(ài)玲小說(shuō)情節(jié)藝術(shù)的分析、內(nèi)容體現(xiàn)及藝術(shù)表現(xiàn),深入而系統(tǒng)地挖掘張愛(ài)玲小說(shuō)的情節(jié),并從中體會(huì)張愛(ài)玲留給世人的“蒼涼的啟示”。
關(guān)鍵詞:張愛(ài)玲 小說(shuō)情節(jié) 人物刻畫(huà) 悲劇色彩
一、緒論
有人說(shuō):“只有張愛(ài)玲才可以同時(shí)承受燦爛奪目的喧鬧與極度的孤寂”。翻開(kāi)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撲面而來(lái)的便是震撼人心的蒼涼悲劇。從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中,人們能發(fā)掘出身為一代女性代表的她,對(duì)生命、對(duì)生活、對(duì)人的性格來(lái)自不同方面的剖析,她的小說(shuō)情節(jié)就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體現(xiàn)。筆者選擇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情節(jié)藝術(shù)作為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通過(guò)對(duì)張愛(ài)玲小說(shuō)進(jìn)一步的研究了解,從小說(shuō)情節(jié)內(nèi)容中發(fā)掘更加具體的人物生活及性格各方面較深層次的不同東西,以期引起更為廣泛的對(duì)生活、對(duì)人的全面認(rèn)識(shí)。
1985年出版的錢(qián)理群等四人所撰《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三十年》使張愛(ài)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陸文學(xué)史排行榜。從1987年起,張愛(ài)玲研究論文明顯增多且研究日漸細(xì)致深入,研究范圍也更加廣泛。此后還有許多從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角度把握張愛(ài)玲的文章,如宋家宏《張愛(ài)玲的“失落者”心態(tài)及其創(chuàng)作》和潘學(xué)清《張愛(ài)玲家園意識(shí)文化內(nèi)涵解析》等。他們都試圖解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這位作家的獨(dú)特人格和文風(fēng)。這些對(duì)我們研究張愛(ài)玲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根源有很重大的啟示和參考借鑒價(jià)值。在國(guó)外,1961年美國(guó)哥倫比亞大學(xué)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出版時(shí),張愛(ài)玲第一次被寫(xiě)進(jìn)文學(xué)史。夏志清認(rèn)為“張愛(ài)玲該是今日中國(guó)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他認(rèn)為張愛(ài)玲小說(shuō)的特色在于“強(qiáng)烈的歷史意識(shí)、豐富的想象、對(duì)人情風(fēng)俗的熟練處理、對(duì)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發(fā)等”。
二、“封鎖”的小說(shuō)情節(jié)模式、蒼涼的藝術(shù)手法
張愛(ài)玲自1943年登上小說(shuō)文壇以來(lái),便以絕塵的姿態(tài)在小說(shuō)長(zhǎng)廊上鐫刻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她的悲哀與蒼涼,她筆下的上海、香港都不可復(fù)制。她獨(dú)有的對(duì)“人間無(wú)愛(ài)論”的詮釋?zhuān)忌钌畹卮蛏狭藦垚?ài)玲的烙印。這一切都與她獨(dú)特的小說(shuō)情節(jié)模式有關(guān)。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大多在一個(gè)封鎖的圈子里展開(kāi),在這個(gè)封鎖的圈子里,人們建構(gòu)愛(ài)情,展開(kāi)所有對(duì)美好的追求,然而,無(wú)一例外,無(wú)論是對(duì)于情,對(duì)于金錢(qián),對(duì)于權(quán)勢(shì)乃至種種欲望的追求,都一一破滅。
這一情節(jié)模式不單是張愛(ài)玲極端化的感情體驗(yàn)的一種折射,更是她蒼涼決絕的愛(ài)情婚戀觀的重要縮影。它的形成受到其家庭背景、人生遭際、特定地點(diǎn)的真實(shí)歷史事件等因素的影響,亦有心理學(xué)上的依據(jù)。這一切反映在小說(shuō)情節(jié)中,即是“封鎖”的小說(shuō)情節(jié)模式的建構(gòu)以及蒼涼藝術(shù)手法的渲染。
準(zhǔn)確說(shuō)來(lái),“‘封鎖下愛(ài)情的建構(gòu)與破滅”這個(gè)情節(jié)模式的關(guān)鍵就在于“封鎖”二字。
張愛(ài)玲以愛(ài)情為描摹對(duì)象,以“封鎖”作為情節(jié)模式,依次展開(kāi)敘事。張愛(ài)玲的這些小說(shuō)正是通過(guò)對(duì)心理“封鎖”下愛(ài)情獲得過(guò)程的描繪和對(duì)歷史上戰(zhàn)爭(zhēng)中封鎖事實(shí)的借用來(lái)展開(kāi)敘事的。陳怡在《“封鎖”下愛(ài)情的建構(gòu)與破滅——論張愛(ài)玲1943年小說(shuō)的情節(jié)模式》中曾經(jīng)指出,“‘封鎖這種心理狀態(tài)的形成包含著三個(gè)層面:不佳的個(gè)人境遇為張愛(ài)玲筆下的主人公們創(chuàng)造了第一層‘封鎖,家庭氛圍的壓抑加深了第二層‘封鎖,經(jīng)濟(jì)利益的糾葛完成了核心的第三層‘封鎖”。
張愛(ài)玲以“封鎖”為背景,建構(gòu)了一段段或美麗或沉重,或丑陋或壓抑的愛(ài)情。無(wú)一例外,這些掙扎在“封鎖”圈子里的人都曾經(jīng)對(duì)美好充滿(mǎn)過(guò)憧憬。然而,現(xiàn)實(shí)的封鎖,人生遭際的困頓一步步將其捆綁,“封鎖”越來(lái)越甚,到最后,愛(ài)情已經(jīng)不復(fù)最初的遐想,而是淪為想要掙脫“封鎖”的工具,只是,殊不知,最后卻將其引入更黑暗的深淵。
困頓的境遇,加之來(lái)自家庭環(huán)境的逼迫,早已使他們的心靈變得殘缺。當(dāng)愛(ài)情來(lái)臨時(shí),她們的心中有著深深的不安與隱憂(yōu)。飽受困頓之后的她們已經(jīng)變得自卑多疑——當(dāng)白流蘇遇上范柳原,也許是有心悸,但更多的該是尋找一個(gè)脫離那個(gè)“封鎖”而壓抑的家的出路。因此,這樣早已病態(tài)的她們,縱而當(dāng)愛(ài)情來(lái)臨時(shí)也藏著深深的隱憂(yōu),這樣的隱憂(yōu)與“封鎖”的環(huán)境注定了她們無(wú)論如何去努力建構(gòu)愛(ài)情,都無(wú)可避免愛(ài)情破滅的結(jié)局。
張愛(ài)玲筆下的婚姻是無(wú)愛(ài)的、晦澀的,帶有強(qiáng)烈的悲劇色彩。正是這種悲涼的家庭經(jīng)歷和奇特的求學(xué)經(jīng)歷,使她格外注重實(shí)際,她對(duì)時(shí)代的觀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種高度上,而且思考程度也是另一個(gè)層次的,并且?guī)в幸环N失落感,這種失落感一直在她不同的小說(shuō)中滲透著。她的作品,常常讓讀者感受到隱藏在背后那種對(duì)人生的絕望,平淡的敘述中,往往又透露著悲涼感。可以說(shuō),自張愛(ài)玲走向文壇開(kāi)始,“封鎖”背景下愛(ài)情的建構(gòu)與破滅就一直伴隨著她。“人間無(wú)愛(ài)”,建構(gòu)與破滅是她對(duì)愛(ài)的決絕感知,也是她蒼涼孤寂身世的一種折射。家對(duì)于她而言,即使有,也是孤獨(dú)的。家與親情乃至愛(ài)情,其實(shí)都是一道封鎖。家給人以無(wú)形的壓力,而誕生于家的封鎖之下的愛(ài)情企圖去打破家的封鎖,從一開(kāi)始就注定了它的悲劇結(jié)局。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就這樣帶著這份決絕,挑戰(zhàn)了以往小說(shuō)大團(tuán)圓的經(jīng)典模式,蒼涼的情感基調(diào)與藝術(shù)表現(xiàn)模式,沒(méi)有十分的厚重,卻也是有著張愛(ài)玲的獨(dú)特思考以及那份不容置疑的深度。
三、“封鎖”情節(jié)模式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中以悲劇故事見(jiàn)長(zhǎng),作品彌漫著濃厚的悲劇色彩。她的性格中聚集了眾多的矛盾,她人生經(jīng)歷中充滿(mǎn)著悲涼,以至她對(duì)人生處境充滿(mǎn)了悲劇意識(shí)。她清醒地意識(shí)到時(shí)代的悲哀,人生的殘缺,同時(shí)又不放過(guò)發(fā)現(xiàn)和細(xì)細(xì)地品味人生“可親可愛(ài)”的那一面,但卻并不陷入絕望。于是,在張愛(ài)玲的筆下,“封鎖”的情節(jié)模式是一種人生的無(wú)奈,時(shí)代的悲哀。而借著這“封鎖”的模式,人物命運(yùn)的“蒼涼”,人性本質(zhì)的剖析,悲劇色彩的渲染都被描摹得淋漓盡致。
張愛(ài)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說(shuō):“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méi)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壯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色,是一種強(qiáng)烈的配色,但它的刺激性還大于啟發(fā)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zhǎng)的回味,就因?yàn)樗裉壹t配蔥綠,是一種參差的對(duì)照。”
作為張愛(ài)玲的代表作,《傾城之戀》充滿(mǎn)了蒼涼、抑郁而哀切的情調(diào)。白流蘇是一個(gè)怯弱的女兒,離婚后的白流蘇寄居在娘家,受到兄嫂的奚落與排斥,而自己的母親卻無(wú)力為她撐腰,她是給家人逼急了才開(kāi)始一個(gè)冒險(xiǎn)的愛(ài)情故事。白流蘇在心靈上與無(wú)家可歸的孤兒無(wú)異,但她拋下親人,遠(yuǎn)離家園,跟隨男主人公范柳原到了香港。第二度來(lái)到香港的時(shí)候,白流蘇卻成為了范柳原的情婦。其實(shí)像范柳原般的男人,又有些什么價(jià)值呢?“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wàn)盞燈的夜晚,拉過(guò)來(lái)又拉過(guò)去,說(shuō)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wèn)也罷。”
這一種“蒼涼”感也來(lái)自于張愛(ài)玲自身的感受,時(shí)代變遷帶給她的是失落與荒涼,貴族文化沒(méi)落帶來(lái)的濃厚的末世情調(diào),與時(shí)代動(dòng)亂的流離感、戰(zhàn)亂時(shí)期的強(qiáng)烈危機(jī)感交織在一起。
張愛(ài)玲筆下的人物,他們?cè)诜饨ㄊ浪椎膲浩认拢裆n白,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在物欲、情欲等誘惑下,人性也早已變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們?nèi)恰安 绷说娜恕垚?ài)玲從人的“虛偽性”來(lái)揭露“人性惡”,以及人的“靠不住”。
《金鎖記》刻畫(huà)的是一個(gè)心理變態(tài)的女性——曹七巧。原本一個(gè)麻油店站柜臺(tái)的年輕姑娘,是自由潑辣的,可以站在街上和賣(mài)肉的朝祿調(diào)情,是處于社會(huì)中下層的小井市民身份,但卻為了金錢(qián),她以青春和婚姻為代價(jià),嫁進(jìn)了姜家這個(gè)封建貴族大家庭。雖然她如愿成了少奶奶,但同時(shí)也失去了真正的愛(ài)情,她的一輩子為金錢(qián)而殉葬了。她對(duì)金錢(qián)的焦慮,本質(zhì)上是一種強(qiáng)烈的生存危機(jī)感。為錢(qián),可以揉碎自己女兒的自尊心,將自己的家庭幸福如掐螞蟻般毀滅;為金錢(qián),可以隔斷一切親情,棄兒女的婚姻幸福于不顧,以致喪失了人性。
無(wú)論是從張愛(ài)玲的美學(xué)宣言,還是從她的作品中,都能看的出她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一位獨(dú)特的,帶有濃濃悲劇色彩的女作家。她內(nèi)省、孤傲的性格以及都市人的優(yōu)越感與孤獨(dú)感交織起來(lái)形成她對(duì)時(shí)代“悲劇”特色的心理感受。她對(duì)人性的悲觀,自身積淀的太多否定性感情又使她終身處于一種哀怨、憂(yōu)愁、悲觀的境地。因此,她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悲劇感敘述了一個(gè)個(gè)悲涼的傳奇故事。
在“封鎖”的情節(jié)模式下,小說(shuō)的人物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演繹著自己的悲劇。他們的悲劇很難說(shuō)清楚是哪個(gè)人或事,但卻總是發(fā)生的不可避免,自然而然的。甚至在他們自己經(jīng)受悲劇命運(yùn)的同時(shí),還在為旁人制造著新的悲劇。這也是“封鎖”情節(jié)模式強(qiáng)大的表現(xiàn)力,人們?cè)谶@個(gè)圈子里不停地掙扎,乃至陷入絕望,悲劇在不停地上演。
四、結(jié)語(yǔ)
張愛(ài)玲,這位曾經(jīng)在二十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以言情小說(shuō)風(fēng)靡文壇的民國(guó)才女,縱使她的創(chuàng)作如曇花一現(xiàn),僅僅在上海灘文壇絢爛了兩年,但是對(duì)她作品的解讀一直在繼續(xù)著。張愛(ài)玲的小說(shuō),為什么到現(xiàn)在還能得到讀者的青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將生活藝術(shù)化了,又把藝術(shù)生活化了,她以現(xiàn)實(shí)的目光去剖析人性、冷眼看待時(shí)代的腐朽。這種“現(xiàn)實(shí)”也是對(duì)我們?nèi)缃襁@個(gè)新社會(huì)現(xiàn)象的寫(xiě)照,張愛(ài)玲通過(guò)對(duì)市民日常生活的描述,闡釋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一種法則——活在當(dāng)下。在“封鎖”情節(jié)模式下,人物的悲涼,性格的缺陷,時(shí)代的無(wú)奈,世事的滄桑一一呈現(xiàn)。這亦是張愛(ài)玲小說(shuō)深度之所在。
參考文獻(xiàn):
[1]傅雷.論張愛(ài)玲小說(shuō)風(fēng)格[M].逸海書(shū)城出版社,2003:25-46.
[2]張愛(ài)玲.張愛(ài)玲典藏全集[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3:101-111.
[3]魏可風(fēng).臨水照花人——張愛(ài)玲傳奇[M].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2001:20-30.
[4]張愛(ài)玲.張愛(ài)玲文集(精讀本)[M].北京:中國(guó)華僑出版社,2002:4-30.
[5]張愛(ài)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華出版社,2005: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