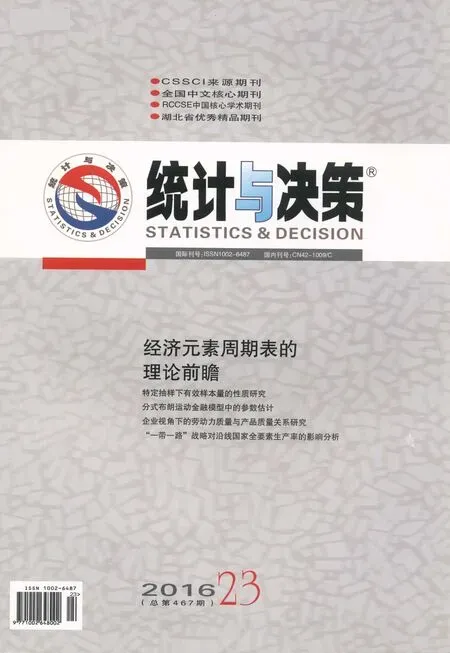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研究
李 琳,戴姣蘭
(湖南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長沙 410079)
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研究
李 琳,戴姣蘭
(湖南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長沙 410079)
文章以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為研究對象,解析三大因素對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影響機制;并在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上,運用協同學的哈肯模型,對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進行序參量識別。結果表明:創新比較優勢(CIA)是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序參量;整體而言,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尚處于初級階段,初步形成中心—外圍的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結構。
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序參量;哈肯模型
0 引言
城市群作為一種特殊的區域形態,其本質是跨城市-區域系統,相對于一般的區域形態,能夠產生巨大的集聚經濟效益,是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載體。因此,研究以城市群為空間載體的跨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打造城市群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能,對于推進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新型城鎮化、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此,本文以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為研究對象,在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理論基礎上,運用協同學的哈肯模型,對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進行序參量識別,以揭示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演化的主要推動力,旨在為相關決策以及實施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戰略提供理論支撐。
1 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分析
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是指在相對獨立而聯系緊密的城市集合內部,多元創新主體以城市為載體通過城際關系互動,針對城市間以及城市內知識與技術的再創新和再利用,形成的知識流、技術流、信息流與物質流的循環創新型網絡。在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中,資源稟賦的差異形成各城市的創新比較優勢,引發以優勢互補為目的的創新合作在城市間和多元創新主體間展開,帶動創新要素流動,進而使城市子系統間以及多元創新主體之間的關系結構產生變化,形成以多種要素流為主要枝干的交叉網絡,多維協同關系網絡產生[1,2]。因而,城市群協同創新的演化主要受到創新比較優勢、創新要素流動和創新網絡形成的影響,三大因素既獨立運作又彼此交互作用于城市群協同創新過程,共同驅動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由低級向高級演化。
1.1 主要驅動因素
(1)創新比較優勢(CIA)。創新比較優勢是指城市本身具備的創新資源優勢與創新環境優勢,是其參與協同創新的依據,屬于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基礎,是系統演化初級階段的特征。在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發展初級階段,創新比較優勢主要體現為以人力、資金等初級要素為依托的低級、靜態的創新資源稟賦差異,引致以優勢互補為目的的創新合作在城市群內城市間與多元創新主體間有序展開。
(2)創新要素流動(IEF)。創新要素流動是指創新要素在城市群內不同城市間與創新主體間的流動與整合,反映了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中子系統間的能量交換,是在創新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實現創新要素在城市群內部整體配置均衡的途徑。以優勢互補為目的的創新合作會帶動創新要素在城市間雙向、多向流動,實現城際多元創新主體間的要素互換與共享,使不同城市的資金、技術等要素比例結構重新達到一個整體均衡的比例結構。
(3)創新網絡形成(INB)。城市群協同創新要求城市群內多元創新主體有機聯系并實現要素共享,通過以多元主體互動關系為基礎的創新網絡來強化城市群內部創新主體的聯系,形成高效的運作紐帶。城市群創新網絡的形成從根本上打通創新要素流動以及創新效應擴散的通道,提高系統的運轉效率,城際多元創新主體通過創新網絡進行頻繁聯系與交流,推動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的演化。成熟的創新網絡是實現創新要素快速流動、創新主體行為有效耦合、創新效應高效擴散的關鍵因素,是系統演化高級階段的特征。
1.2 驅動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機制
創新比較優勢、創新要素流動與創新網絡形成三者的協同交互作用形成了城市子系統間的有序運動。資源稟賦差異形成各城市創新比較優勢,引發以優勢互補為目的的創新合作在城市間和多元創新主體間展開,帶動創新要素流動,促進形成多維協同創新網絡結構;同時,各城市子系統間多元創新主體間合作的拓寬與深化會逐步打通創新要素的流動渠道,加速創新要素的重新分配,促進各城市低級創新比較優勢向高級比較優勢轉變。如此循環往復,產生協同創新效應。因此,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強調系統內部各城市子系統間相互協作并有機地整合成有序演變狀態,最終會以協同創新機制為牽引,形成覆蓋整個城市群的協同創新關系網絡,實現創新要素的高速流動與創新效應的高效擴散,實現各城市子系統的創新績效同步于整體創新績效,從而使整個協同創新系統實現初級-中級-高級的協同演變。
2 城市群協同創新驅動因素序參量識別
2.1 哈肯模型
哈肯模型由協同學創始人哈肯提出,主要運用于研究系統的自組織演化過程,是衡量系統有序度的重要模型[3]。根據哈肯提出的自組織原理,系統中各子系統與參量會對系統產生差異化、不平衡影響,當控制參量的改變將系統推過線性失穩點,差異化影響凸顯,從而慢變量支配快變量,消去快變量,得到支配系統的序參量方程[4,5]。假設q1為某子系統及參量的內力;q2被該內力所控制,系統所滿足的運動方程為:

λ1和λ2代表兩個子系統的阻尼系數且至少相差一個數量級,且λ2>0被稱為該運動系統的“絕熱近似假設”[6,7]。若“絕熱近似假設”成立,突然撤去q2,q1來不及變化。令求得:

q1即序參量,進而解得序參量演化方程,也即系統演化方程:

為了保證系統演化方程最后存在非零實解,應滿足:λ1λ2ab<0。對的相反數積分可求得系統勢函數,能有效的判斷整個系統所處狀態:

由于哈肯模型最初運用于物理學研究,運動方程是針對連續型隨機變量設定的,此處將其進行離散化處理運用至經濟分析,即:

2.2 指標選取
(1)創新比較優勢(CIA)。創新比較優勢是通過對創新使能指數改進得來。創新使能指數(IDI)由直接投入指數與創新環境指數合成,體現城市的創新資源優勢與創新環境優勢兩個方面,分別取權重0.7與0.3[8]。直接投入指數反映的是創新的人力資本與科技資金,分別用科研人員比例與政府財政支出中R&D比例兩個指標來反映,考慮到兩種要素的重要性,各取0.5的比重;創新環境指數為實際使用的外商投資額占本地區GDP的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γ1=0.7,γ2=0.3;α=β=0.5。
由于協同指標需要反映城市群內城市之間的聯系,體現出城市群內每個城市在創新資源稟賦方面的比較優勢,故將創新使能指數IDI進行處理得出改進后的創新比較優勢指數CIA。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DIi表示城市i的創新使能指數值,IDIj表示城市j的創新使能指數值,n表示研究對象個數。CIAi值越大,說明城市i與其他城市間的創新資源稟賦差距越大,越有利于城市間創新資源優勢互補。
(2)創新要素流動(IEF)。創新要素的流動IEF主要從人員流動與資金流動來體現。考慮到兩種要素的重要性,各取0.5的權重合成綜合指標IEF。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CFi為城市i的資金流動度,用城市i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R&D外部支出占城市i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R&D總支出比重衡量;DMi為城市i的人員流動度,用城市i的科研人員的流動量占年末科研人數比重衡量。a=b= 0.5,下文中出現的a、b取值同此。
(3)創新網絡形成(INB)。基于數據可獲得性,創新網絡的形成由聯合專利指數與技術相近性指數兩個指標合成。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階段越高,城市群協同創新網絡的形成就越成熟。因此,創新網絡形成屬于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高級階段的特征,其表現為較高的協同創新效應水平和技術協同水平。聯合專利指數可以直接衡量城市協同創新效應水平,而技術相近性指數可以衡量城市間技術差距。因此上述兩個指標的合成指標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創新網絡形成的成熟度。基于兩者的重要性,各取0.5的權重。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NBi為創新網絡形成指數,JPIi為聯合專利指數,是城市i的企業與本市以及其他城市高校、企業的聯合專利數占城市i的三類專利總量的比重;TCIi則為技術相近性指數,可以衡量城市i與其他城市間的技術差距,數值越小,技術差距越小,城市間技術協同水平越高。故計算時逆向處理取倒數。TCIi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OVHTi表示城市i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OVHTj表示城市j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ASIOVi表示城市i的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ASIOVj表示城市j的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n表示研究對象個數。
2.3 研究對象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中三角城市群的地級市為研究對象。中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武漢‘1+8’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和長株潭‘3+5’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共23個地級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剔除宜春、上饒和吉安,最后以中三角城市群的20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數據主要來自于2004—2013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湘鄂贛三省《統計年鑒》、各市《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及各市科技局官網。鑒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外部研發支出”指標的數據獲取難度較大,通過《統計年鑒》、統計公報及科技局網站仍無法獲取完整數據,部分缺失數據為2014年項目啟動階段通過實地走訪部分城市統計部門獲取的內部數據,僅更新至2012年,受限于數據來源,難以再次通過實地走訪的方式更新數據,故研究期未更新至截止發稿前的最新年份。
3 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序參量識別的實證分析
3.1 序參量識別
哈肯模型一般針對兩個變量進行序參量識別,此模型共有CIA、IEF、INB三個變量,三個變量既獨立影響又交叉影響,因此對三個變量進行兩兩分析,基本步驟為:(1)提出模型假設;(2)構造運動方程并判斷方程是否成立;(3)求解方程參數并判斷其是否滿足“絕熱近似假設”;(4)判斷模型假設是否成立,得出系統序參量。模型方程均利用EVIEWS6.0軟件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求得,兩兩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三角城市群2003—2012年變量間兩兩分析結果
表1分析結果顯示,在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驅動因素中,CIA為系統的序參量。
3.2 勢函數求解
由表1中方程①可得:

系統演化方程為:

系統勢函數為:

根據方程(9)可得系統勢函數圖像如圖1所示,系統演化方程的求解結果為A(-0.0281,0)、B(0.0281,0)和C(0, 0)。由于哈肯模型最初運用于物理學研究非線性動力學,特別是振諧系統研究,類比于物理學當中的球體下落運動,由于重力勢能的作用,小球總會回落至系統低點。因此,根據系統演化方程求解結果可知,得出系統穩點為A與B,C不是系統穩點。

圖1 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勢函數圖形
在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中,由于CIA的值均大于零,因而勢函數圖像僅考慮q>0的部分。依據勢函數的三個解可得,系統的穩定點為B(0.0281,-0.00001),任意一點D與穩定點B的距離決定了其所處的狀態:

狀態點與系統穩點距離越大,表明狀態點越不穩定。因此d值越大,表明系統越不協同,反之,d值越小,系統協同度越高。

運用方程(11)的方法對d值進行正向化處理,并將其轉換為(0,1)之間的正向指標,得出協同創新發展值,見表2。

表2 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得分值
3.3 結果分析
通過對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驅動因素CIA、IEF、INB進行系統序參量識別,得出CIA為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演化的序參量,并且系統演化進程同時受到CIA與IEF的影響,CIA為系統慢變量,IEF為系統快變量。
根據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的運動方程,可知系統演化過程中快慢變量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其各自對系統演化進程的影響。①控制參量a>0和b>0,說明當城市群內各城市創新資源稟賦存在較大差異,城市體現出各自的創新比較優勢,會提升城際間創新合作動力,使創新要素在城際間流動。但現階段創新要素水平較低,不能通過創新要素的充分快速流動,使城市的創新比較優勢由低級靜態的比較優勢向高級動態的比較優勢轉化,進而促進城市群整體協同創新水平的提升。②控制參量λ1<0和λ2>0,表明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內部已經建立了創新比較優勢CIA不斷增長的正反饋機制和創新要素流動IEF遞減的負反饋機制,即城市群內各城市通過創新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生,并通過創新要素的流動推動低級靜態的比較優勢向高級動態的比較優勢轉變,但是由于目前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尚處于演化的初級階段,創新網絡形成不成熟,要素流動壁壘仍未完全打破,當現有的要素流動渠道飽和時,創新要素流動就會放緩。
根據表2數據顯示,可知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狀況。從整體分析,2003—2012年間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發展的十年平均得分值(0.2985)高于2003年得分值(0.1716),低于2012年得分值(0.4117),說明中三角城市群整體協同創新水平在2003—2012年間是呈上升趨勢的,且2012年較2003年得分值上升幅度約為139.84%,說明十年間中三角城市群整體協同創新水平上升幅度較大。從局部分析,2003年與2012年各城市得分值比較,在中三角城市群內部,除黃岡市外,其他城市的協同創新水平均呈上升趨勢,上升幅度均為50%以上。從2012年得分值分析,中心城市得分值分別為長沙(0.9612)、武漢(0.7933)、南昌(0.3955),其中長沙和武漢分別高于所在城市群的周邊城市,而南昌(0.3955)低于新余(0.4353)和撫州(0.4414),說明長株潭城市群與武漢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聚效應明顯,大量創新資源聚集,協同創新水平較快提高。長株潭城市群、武漢城市群已形成中心-外圍協同創新結構,而鄱陽湖經濟圈的南昌的創新要素集聚功能較弱,中心-外圍的協同創新結構不顯著。此外,中三角城市群十年協同創新均值僅為0.2985,整體而言尚處于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初級階段。
4 結論
(1)中三角城市群2003—2012年協同創新系統序參量識別結果表明,創新比較優勢(CIA)為中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序參量;且系統演化進程同時受到創新比較優勢(CIA)與創新要素流動(IEF)的影響。
(2)創新比較優勢(CIA)為系統慢變量,創新要素流動(IEF)為系統快變量;且系統內部已建立了CIA不斷增長的正反饋機制和IEF遞減的負反饋機制。
(3)中三角城市群整體仍處于以CIA為序參量的協同創新系統演化的初級階段,此階段IEF創新要素流動水平較低,城市群內大部分城市的創新比較優勢仍體現為低級的靜態比較優勢。
(4)中三角城市群整體協同創新水平在2003—2012年間呈上升趨勢,但各城市協同創新水平不一,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相對差距較大,中心-外圍的城市群協同創新結構初顯。
[1]解學梅.都市圈協同創新機理研究:基于協同學的區域創新觀[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11,28(1).
[2]解學梅.協同創新效應運行機理研究——一個都市圈視角[J].科學學研究,2013,31(12).
[3]Haken H.Synergetics:An Introduction[M].Berlin:Spring-Verlag,1983.
[4]Frenken K F.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mplexity Theory[J].Eco? 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6,(15).
[5]Jadesadalug V,Ussahawanitchakit P.The Impacts of Organizational Synergy and Autonomy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Mindset and Innov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2008,8(3).
[6]陳勁,王方瑞.再論企業技術和市場的協同創新——基于協同學序參量概念的創新管理理論研究[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2(2).
[7]趙玉林,魏芳.基于哈肯模型的高技術產業化過程機制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7,24(4).
[8]涂振洲,顧新.基于知識流動的產學研協同創新過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3,31(9).
(責任編輯/劉柳青)
F425
A
1002-6487(2016)23-0119-0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4FJL01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1&ZD012)
李 琳(1965—),女,湖南漣源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城市創新與區域發展。
戴姣蘭(1990—),女,湖南長沙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創新與區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