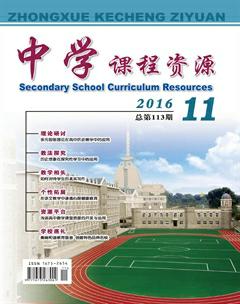歷史想象在探究性學(xué)習(xí)中的運(yùn)用
吉衛(wèi)偉
摘 要:“想象”是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教師應(yīng)重視歷史想象在探究性學(xué)習(xí)中的重要作用。這種想象應(yīng)建立在學(xué)生已有知識(shí)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課堂教學(xué)可從歷史背景的共性想象、個(gè)人際遇的個(gè)性想象、多樣性的推理想象這三個(gè)方面著手,使學(xué)生深刻感悟歷史時(shí)代背景、真切感受歷史人物情感、辯證評(píng)析歷史史實(shí),從而使學(xué)生形成正確的歷史觀,推進(jìn)歷史探究性學(xué)習(xí)的開(kāi)展。
關(guān)鍵詞:歷史想象 探究性學(xué)習(xí) 運(yùn)用
“想象”在歷史研究與教學(xué)中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yàn)榻裉煳覀兯芤罁?jù)的史料是有限的,可能只是歷史遺存的一小部分,如果不運(yùn)用合理的歷史想象,就很難構(gòu)建出比較完整的歷史圖景。陳寅恪認(rèn)為,歷史學(xué)家要有藝術(shù)家的想象力,才能對(duì)歷史有真正的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shuō)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
歷史想象到底該如何運(yùn)用?我認(rèn)為,想象應(yīng)該建立在學(xué)生已有的歷史知識(shí)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不能憑空想象,否則就成為無(wú)本之木、無(wú)源之水。雖然這種知識(shí)與經(jīng)驗(yàn)很有限,但只有從已知出發(fā),學(xué)生才能建立起一定的學(xué)習(xí)自信,才能更好地去感悟歷史。學(xué)生學(xué)習(xí)歷史的過(guò)程就像戲劇表演,既需要一個(gè)仿真的歷史舞臺(tái)——情境;同時(shí)也需要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通感,從而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獲得最具有真實(shí)觸感的歷史。我在教學(xué)實(shí)踐中,把歷史想象按照其依據(jù)來(lái)源與運(yùn)用方式大體分為三種形態(tài):
一、歷史背景的共性想象
葛兆光在《中國(guó)思想史》中提出了一個(gè)觀點(diǎn):“一種近乎平均值的知識(shí)、思想和信仰,作為底色或者基石而存在。”推而廣之,作為整體的歷史,不僅在文化層面,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jì)等各個(gè)方面都會(huì)有這樣一種基本而普遍的水準(zhǔn),它們共同搭建了歷史舞臺(tái),前人的活動(dòng)不可能超越此限度,而后人也可以借此限度來(lái)充分想象,從而重構(gòu)前人的歷史活動(dòng)。
錢穆先生在推演八卦起源就巧妙運(yùn)用了歷史想象。八卦大體出現(xiàn)在游獵文明年代,彼時(shí)人類尚無(wú)文字記載,只能作畫以記事。錢穆先生設(shè)想遠(yuǎn)古時(shí)代有一隊(duì)牧民,外出放牧,走了很遠(yuǎn)很遠(yuǎn),來(lái)到了一片不毛之地,人、畜干渴難耐,到處尋找水源,終于在一個(gè)山丘上,找到了一股清冽的泓泉。隨即在下山時(shí)做了一個(gè)醒目的圖畫作為記號(hào),表明“山上有水”,這樣在下次放牧經(jīng)過(guò)此地時(shí),就可以很快地找到水源。隨著時(shí)間的推演,后人已經(jīng)忘記了是哪位前人做了這一記號(hào),再加上當(dāng)時(shí)明智未開(kāi),就認(rèn)為“彼見(jiàn)此卦象可以告我以外物,以謂必有類我而神明者主之,而敬畏之心漸起”。后來(lái),圖畫逐漸抽象成了符號(hào),“”便成了“山水蒙”卦,象征啟蒙奮發(fā)之意。先生用歷史想象彌合了斷裂之處,給了八卦起源一個(gè)相對(duì)合理的解釋。
高中歷史教學(xué)已出現(xiàn)的像帕帕迪、二毛故事等虛構(gòu)史實(shí),雖然講述的是個(gè)人遭遇,但這些人物在歷史中的思維和行為卻體現(xiàn)了群體性,即那個(gè)時(shí)代大部分人的共同行為模式,這恰恰是由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所構(gòu)成的歷史大背景所決定的。我在教選修四《儒家文化創(chuàng)始人——孔子》一課時(shí),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探究性活動(dòng)——孔子求職記,讓學(xué)生分別扮演孔子和君主,相互詰難批駁。
甲方:作為孔子,你有哪些優(yōu)勢(shì)和特長(zhǎng)?想謀求什么樣的職位?
乙方:作為君主,你會(huì)給孔子職位嗎?為什么?
通過(guò)這種方式讓學(xué)生感受到:孔子受君主尊崇,但不受君主重用。這是由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所構(gòu)成的歷史大背景所決定的。春秋時(shí)代,禮崩樂(lè)壞,早已不是西周初年郁郁乎文哉的王道時(shí)代,而是群雄角力的霸道時(shí)代,孔子的主張顯得不合時(shí)宜,其不受重用,時(shí)勢(shì)使然。但孔子不曲學(xué)阿世,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又足見(jiàn)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精神。
二、個(gè)人際遇的個(gè)性想象
每個(gè)人都有自己個(gè)性化的東西,如出身、才能、意志、經(jīng)驗(yàn)、性格等,都會(huì)在自己參與的歷史事件中留下烙印,甚至決定著個(gè)別歷史事件的走向。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心理學(xué)上的通感共情和換位思維來(lái)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從而更好地理解人物行為。當(dāng)然,個(gè)人際遇必須與歷史背景相互動(dòng),純粹的心理游戲是不真實(shí)的。
“王國(guó)維之死”是中國(guó)近代文化史一段公案,其死因眾說(shuō)紛紜,莫衷一是,其中陳寅恪的“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說(shuō)法最為后人論道。他認(rèn)為,王國(guó)維先生蹈湖自殺,不是糾結(jié)于個(gè)人的恩怨(家庭變故),也不是一個(gè)王朝的滅亡(殉清說(shuō)),而是以死明志,體現(xiàn)其獨(dú)立自由的個(gè)人意志,因?yàn)檫@些追求具有超越時(shí)空的價(jià)值和生命力。近代中國(guó)處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王國(guó)維作為中國(guó)第一代受到現(xiàn)代訓(xùn)練的知識(shí)分子,既受四書五經(jīng)的熏陶,又有歐風(fēng)美雨的浸染,其一生以傳承中國(guó)文化為己任,又格外珍視現(xiàn)代式學(xué)術(shù)自由,而當(dāng)時(shí)恰又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式微,新文化有很強(qiáng)的功利性,要服務(wù)于改造社會(huì)。再聯(lián)系其遺言“經(jīng)此世變,義無(wú)再辱”,當(dāng)時(shí)南方革命軍已經(jīng)打來(lái),尤其是湖南名士葉德輝被農(nóng)民軍所殺,使其感同身受。王國(guó)維所傳承的傳統(tǒng)文化自當(dāng)被革命,王國(guó)維所捍衛(wèi)的學(xué)術(shù)自由恐怕也在劫難逃。故王國(guó)維自謂“永抱悲觀者”,其自殺是可以理解的,是王國(guó)維的志業(yè)性格與社會(huì)巨變的互動(dòng)產(chǎn)物。
在高中歷史教學(xué)中,基于歷史人物心理的想象會(huì)經(jīng)常不自覺(jué)地用到,譬如教學(xué)《戊戌變法》時(shí),改革最后被慈禧太后所扼殺,有的學(xué)生激動(dòng)說(shuō):“光緒帝為什么斗不過(guò)慈禧這個(gè)老太婆呢,要是我就和她去拼了。”其實(shí),教師只要把光緒帝的個(gè)人際遇(光緒皇帝為慈禧抱養(yǎng)才做了皇帝,慈禧從小對(duì)他嚴(yán)加管教,動(dòng)輒呵斥并體罰,光緒見(jiàn)慈禧如見(jiàn)獅虎,會(huì)害怕得瑟瑟發(fā)抖,慈禧不叫他起身,他就會(huì)一直跪著等歷史細(xì)節(jié))告訴學(xué)生,他們聽(tīng)后會(huì)有所感悟的。有的學(xué)生說(shuō):“性格決定命運(yùn),光緒年輕銳意進(jìn)取,對(duì)慈禧的管教和束縛有叛逆之心,同時(shí)也對(duì)慈禧的養(yǎng)育也有感恩之情,所以光緒可以忤逆慈禧意圖去改革,但絕對(duì)不敢生弒殺之心。”
三、多樣性的推理想象
高中歷史教學(xué)往往把已發(fā)生的歷史事件看作某種歷史必然的產(chǎn)物,混淆了實(shí)然與應(yīng)然的界限,最終從唯物歷史主義走向了唯心宿命主義,不承認(rèn)歷史發(fā)展存在著第二種可能性。其實(shí)歷史本由人創(chuàng)造,而人可以在多重可能性之間做出抉擇。所以“必然性并非天生的,而是由可能性轉(zhuǎn)化而來(lái)的。最初,歷史是向各種可能性開(kāi)放的,歷史可以向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但最后只有一種可能性變?yōu)楝F(xiàn)實(shí)性”。因此,利用“歷史想象”來(lái)進(jìn)行“歷史可能性”研究,既彰顯了人的歷史主體地位,又有助于加深我們對(duì)歷史實(shí)際進(jìn)程的理解。
李澤厚在《告別革命》中提出了一個(gè)有趣的歷史命題:“中國(guó)當(dāng)年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huì)好得多。”他認(rèn)為,歷史發(fā)展有多種可能性而不是像宿命論所認(rèn)為的只有一條道路。多種道路之間相比,改良要比革命對(duì)社會(huì)破壞小,另外改良可以在現(xiàn)有的政府框架內(nèi)進(jìn)行,而選擇革命就必須要在革命后再建立一個(gè)政府,而這一過(guò)程是漫長(zhǎng)的。細(xì)觀其論述,可以用社會(huì)學(xué)“選擇成本”理論來(lái)考量,改良是比較經(jīng)濟(jì)的做法,對(duì)社會(huì)的破壞較小,故而有“告別革命”一說(shuō),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fā)人們對(duì)百年中國(guó)史的反思和再認(rèn)識(shí)。
我在日常教學(xué)中遇到過(guò)類似的問(wèn)題,在講授《從蒸汽機(jī)到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小論文來(lái)引導(dǎo)學(xué)生探討科技革命的影響,題目為《假如沒(méi)有電》。學(xué)生充分發(fā)揮了想象,有的說(shuō):“煮不了飯,洗不了衣服。”有的說(shuō):“吃不到冰淇淋。”有的說(shuō):“夜晚將會(huì)漆黑一片,人們將重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shí)代。”更有甚者不無(wú)幽默地說(shuō):“終于晚上可以不上自習(xí)了。”顯然,這種可能性的想象是反事實(shí)的,但卻給學(xué)生提供了一個(gè)機(jī)會(huì),即用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去感悟歷史事物。這比那種平鋪直敘、一味說(shuō)教“科技革命如何重要”要更加真切,更加感同身受。
柯林伍德說(shuō):“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只要以基于歷史背景的共性想象來(lái)構(gòu)建舞臺(tái),以基于個(gè)人際遇的個(gè)性想象來(lái)塑造角色,以多樣的可能性來(lái)推演劇情,讓過(guò)往的歷史像一幕幕戲劇一樣呈現(xiàn),歷歷在目感同身受。通過(guò)想象來(lái)重構(gòu)歷史,可以加深對(duì)歷史的認(rèn)識(shí)。在高中歷史教學(xué)中,“歷史想象”也是一種重要的教學(xué)手段,只要我們用之得當(dāng),就會(huì)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xiàn):
[1]王家范.中國(guó)歷史通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
[2]葛兆光.中國(guó)思想史導(dǎo)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7.
[3]錢穆.國(guó)學(xué)概論[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2004.
[4]王國(guó)維.王國(guó)維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4.
[5]王學(xué)典.述往知來(lái):歷史學(xué)的過(guò)去、現(xiàn)狀與前瞻[M].濟(jì)南: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2003.
[6]房德鄰.評(píng)“‘假如史學(xué)”[J].近代史研究,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