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人跡罕至的地方
■謝絡繹
去往人跡罕至的地方
■謝絡繹
好的文論一定不會教授,而是啟發,是哲學性的,是對基本規律的發現,因為文學本身就是寫基本規律的,人是什么,這個世界是什么,探討的是本質上的東西。交流也是這樣。我們今天的討論就有一定的座談意味,是一種脫離文本的綜合性討論,是俯觀文學進行觀念提練的討論,我希望更多的在意識層面上與大家進行碰撞,談談文學的基本問題,規律性的問題,而不是具體的技能,那樣貌似提供了一種解決辦法,實際上會形成更大的限制,讓人無措。接下來我就從小說創作者普遍熱衷的技能上的討論出發,談談我的反技能觀念。
人跡罕至,顧名思義就是去的人少,一般人很難企及的地方。文學自然要追求這個。人云亦云的作品是平庸的,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是一種消耗,文學最大的作用是提供一種力量,認識生命本質的力量,平庸之作不可能產生力量,只能產生廢氣,污染環境。但是我們摒棄平庸的手段必然是追求奇詭嗎,它似乎指向的正是人跡罕至。當然不是這樣。
一、語言
語言是一個人的思想、經歷和情感模式的集合體,某種程度來說,它比體貌更能反映一個人的本真。有的人的語言浪漫,有的人的語言樸實,這都只是風格問題,是一種形式美,它們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你應用這種語言在說什么,是否準確,是否得心應手,不幼稚和生硬,它們的習成有一部分是天生的,有一部分是后天閱讀趣味塑造的,還有一部分得益于長期寫,所謂無他,熟而生巧爾。因此來說,語言方面,順應個人條件,不刻意追求新奇和浪漫才為好。
《菜根譚》有言:文無奇巧,人亦本然。意思是說,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恰好,體現在語言上就是純粹、自然、不寧巴。你看魯迅和王小波,文章就是他們的個性。這一點在虛構文學上似乎有一定的遮掩性,也不然,你看丁玲和蕭紅,某種程度上她們都活得灑脫,但丁玲有矩,她對人性和世事有更為理性和深入的領會,蕭紅也有她的領悟,但更超脫,用世俗的眼光看就是不融,在個人生活上,她對世間的洞察仿若未洞察,因為并不能指導她的生活。也因此她們二人的作品風格大不同,前者有理性成分,后者更為恣肆。
不能因為看到其他人作品中呈現出某種特殊的語言質地,你就去追求,想要自己也寫成那個樣子。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須順應自己的身體和思想要求,讓自己最自然地表達,方能應運自如,抵達那片只屬于你的,無人可以登頂的語言天地。

謝絡繹,河南西平人,現居武漢。湖北作協文學院簽約作家。作品有長篇小說《外省女子》等三部;中短篇小說集《到歇馬河那邊去》;中篇小說《舊新堤》、《倒立的條件》等;短篇小說《他的懷仁堂》、《父母準入制》等。獲第七屆湖北文學獎。
二、故事
我聽過很多寫作者感嘆自身經歷平淡,仿佛有了奇特的經歷是寫出好作品的必然條件。他們還會到處找尋他們以為的奇特的故事。然而,太陽底下無新事。所有聽起來生猛的故事,本質上是我們身邊發生的尋常之事的極端,然而無論是尋常還是極端都只是形式上的一種呈現,重要的是故事的精神意義。既然一體兩面,我們就沒必要費工夫從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尋找故事,學會從日常,從身邊找故事是一種能力。
《繁花》是近年來特別火的一部長篇小說,它寫的都是微小的事件,但寫出了利益與信仰的角斗,寫出了世態,這些都是與人心緊緊相連的東西,自然共鳴者眾多。前幾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國外一個老太太連續殺害了十幾個房客,看著不爽就殺,用各種方法處理尸體,隱瞞了這么多年。有朋友轉發這個消息說這真是一個好的小說啊。像這樣的故事,變態、血腥,當然難得一見,但根本上,它也只是世態的一部分,寫這種遠離日常的世態,可以,但不能追求這個,因為那種極端體驗只對很少的有一定心理問題或是特殊經歷的人有效,對大眾只造成一定程度的感官刺激,稍縱即逝,不可能引起更為普遍和長久的情感共鳴。
我最近發表了一個小說叫《他的懷仁堂》,寫的是父子關系,就是一般的瑣事,這當中最重的一點是這對父子不能進行身體接觸,他們做不到,這在我國傳統的父子關系中太常見了,我就寫他們為什么會這樣,并且寫了他們不能突破的痛苦、想要突破的愿望和嘗試,他們后來雖然做到了那么一點,但為時已晚。或者說,要不是為時已晚,他們也不會邁出關鍵的一步——他們擁抱了,在父親咽下最后一口氣的時候。這當中就有對生活極致的觀察和在此之上的對生活的體諒。
故事本身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是載體,所有理想都是建立在首先有這個載體在的基礎上的,但是發現才是真正的源泉。在故事的選擇上,我更傾向于作者去理解最尋常的人情世故,將這種理解發揮到極致。這當然很難做到,這會是另一個人跡罕至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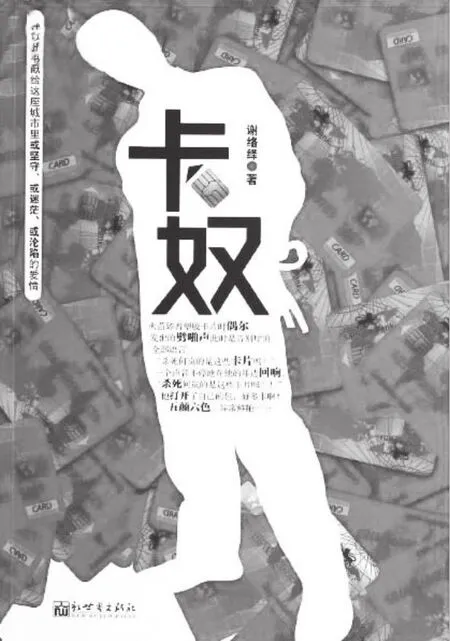
《卡奴》/謝絡繹著
三、結構
《百年孤獨》經典的“許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的時候,奧雷良諾·布恩迪亞上校一定會想起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成為倒序的典范。《我的名字是紅》,一個人寫一章,且是以他們各自的視角展開,很厲害。這些都是常常被重視小說結構的作家拿來做例子的優秀范本。但是,如果剔除這兩部作品的結構不談,看其內容,你會發現,那種出色依然令人驚嘆。
結構在一部作品中的輔助意味其實是最強的,真正讓一部作品偉大的還是它的內容,某方面來看,結構其實只是內容的一部分,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我的經驗是,你寫的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決定了你怎么去寫,順敘還是倒敘,等等,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過程。刻意的在結構上的出其不意有時候會壓制住你的表達,并且,如果太過于追求結構上的設計,它反倒會變成一個框框,限制你的表達。在這個方面,不去追求大概才是最好的追求,是一種無招勝有招的奇絕境界,需要寫作者具有敏銳分析和處理寫作素材的能力。當我們吃透了我們要寫的東西,便會自然地賦予這個東西一個合適骨骼,就如我們的人體一樣,我們被支撐,但是我們并不能直接看到它。
綜上,平庸絕非平常,而是對平常參不透。寫作的高超在于進入對平常頂級的參悟上,而不是說,從形式上拋棄平常追求奇特。一切都是表象,只有內在深淺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