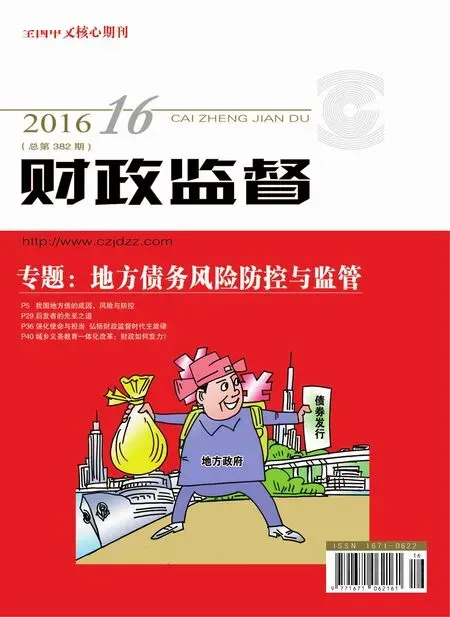后發(fā)者的先至之道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
●本刊記者 柳光強 阮 靜
后發(fā)者的先至之道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
●本刊記者 柳光強 阮 靜

上了一整天課、處理完相關管理事務、接受筆者采訪,在北京最暑熱的季節(jié)里鄭秉文教授依舊繁忙。即使是如此密集的工作節(jié)奏,面對每件事情時的鄭秉文都有著十分的熱情和飽滿的精神,加之東北人的豪爽和學者的那份謙遜智慧,這位剛過花甲之年的學者給人的第一印象便極富感染力和親和力。作為社會保障研究領域的名家翹楚,鄭秉文45歲起才開始搞研究做學問,是學術界的“后發(fā)者”,但他自踏足社保研究領域的那一刻起便筆耕不輟、而今亦已著作等身,成為國內(nèi)享有較高聲譽的社保專家。
鄭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中國新興經(jīng)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咨詢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社會保險標準化技術委員會(SAC/TC474)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院、國家行政學院、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等十幾所高校兼職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福利國家,福利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企業(yè)年金基金等。本期大家專訪鄭秉文教授,以其人生經(jīng)歷和治學歷程向讀者詮釋“后發(fā)者的先至之道”。

接受媒體采訪
文藝青年的“黃金時代”
至今鄭秉文還保留著青少年時拉小提琴自己手抄的五線譜。格尺刻下的五線、手繪的音符,搬家多次,連法國朋友贈送的名貴小提琴都已不知所蹤,但這一疊疊手抄的曲譜猶埋在箱底,足以見它在鄭秉文心中的“價值”。
1955年,鄭秉文生于遼寧省遼陽市,幾年后轉(zhuǎn)到鞍山市,父親是鞍鋼的一般干部,母親是工人,家庭經(jīng)濟條件尚可且家教氛圍開明。在鄭秉文很小的時候,父母就為其買各種樂器“拜師學藝”。少年時的他就有竹笛二胡等民樂演奏基礎,后來在“寄賣行”花15元買了一把小提琴,專門拜師演奏小提琴。“文革”期間,以管弦樂為主要配樂的樣板戲?qū)W習班招收學員,鄭秉文就以拉小提琴的專長考入劇團。1971年起鄭秉文正式在樣板戲樂隊里擔綱起一名小提琴手。與同代人“上山下鄉(xiāng)”的經(jīng)歷不同,因文藝特長考入劇團的鄭秉文16歲到23歲的“黃金時代”就在文藝的熏陶和訓練中度過。上文化課、學音樂理論、苦練小提琴,還自學日語,鄭秉文的青年時代譜寫了一曲不一樣的青春之歌。

在“2014中國養(yǎng)老金論壇”上演講

在“2013·中國企業(yè)年金高端論壇”上演講

除了會演奏樂器,畫畫也是鄭秉文“黃金時代”的愛好特長之一,中學時學校正門前的毛主席畫像都出自他的畫筆,用當今的時髦話來講彼時的鄭秉文是地地道道的“文藝青年”。此后工農(nóng)兵學員推薦上大學,表現(xiàn)出色的鄭秉文曾被推薦至沈陽音樂學院指揮系,卻因故錯失機會。而正當他為這關上的一扇窗而滿懷不平的時候,時代的變遷又為他開啟了新的一扇門。
1977年,高考恢復,有著一定文化課和日語基礎的鄭秉文以鞍山地區(qū)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遼寧大學,后來轉(zhuǎn)入英語系,從此開始了系統(tǒng)的理論知識學習。畢業(yè)后的他在遼寧省出版局工作了一年半,于1983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盡管此后的人生路與“文藝”不再有太多關聯(lián),但那些刻印著歲月痕跡的手抄樂譜卻似一段看得見的人生記憶留在了身邊,無聲勝有聲地“訴說”著屬于文藝青年鄭秉文的“黃金時代”。
“半路出家”的社保大咖
談及社會保障研究領域,鄭秉文在當今國內(nèi)可謂是非常知名的學者大家。但他并不像其他學者有著一以貫之的學習研究經(jīng)歷,而先是留校以管理工作為主,然后是“半路出家”搞研究。
1986年6月,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作為學生會主席的鄭秉文留校作團委書記,后兼任學生工作處副處長。這期間鄭秉文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而是團的工作和學生工作,這期間的經(jīng)歷讓他有很多感悟。為此,他開始讀博,1992年9月,已獲社科院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的鄭秉文飛赴法國進修,在法國巴黎第十一大學讓·莫內(nèi)學院做博士后14個月繼而又受聘于法國Marne la Vallée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微觀經(jīng)濟學和亞太經(jīng)濟。在法國教書一年多后回國的鄭秉文在經(jīng)過多種選擇的認真權衡后最終決定繼續(xù)留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

與龍永圖電視“論道”
實際上,早在國內(nèi)做博士論文和在巴黎留學進修時,鄭秉文認識到,社會保險是矯正“市場失靈”的一個主要領域,需要國家出面舉辦“社會保險”,以替代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企業(yè)保險”,這是個大趨勢,并意識到了研究社會保障問題大有前途,意識到社會保障研究很重要,在國外是成熟的領域,在中國是朝陽領域,并初涉該領域的研究,還在法國搜集了一些法文的資料。但自1995年2月至2000年10月回國后的這段時間,他在研究生院“二次留校”之后,根據(jù)工作需要,先后任培訓中心主任、題庫考試中心主任、院長助理、副院長等教學行政管理職務,無暇進行系統(tǒng)的學術研究;自2000年10月到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履職后才真正啟動社保問題的研究生涯,從研究生院的管理崗位到研究所的研究崗位,工作環(huán)境一下子“冷清”下來,這正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坐冷板凳”的時間和空間,提供了人生轉(zhuǎn)型的重要機遇,抓住它,一切都還來得及。因此,他徹底改變了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話說“45歲才開始真正做學問,而在此前做些研究和寫些東西也是在評職稱的壓力下,目的性很強”。



2005年,與美國波士頓學院的約翰·威廉姆森教授

2011年,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奧利維亞·米切爾教授

2002年與美國經(jīng)濟學家、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教授

2006年與英國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的尼古拉斯·巴爾教授
可即便是“半路出家”,鄭秉文以“把以前14年管理工作的時間補回來”的心態(tài)做科研工作,靠著一天當兩天用的刻苦勤奮步步為營,成為當今社會保障研究領域的名家,不僅發(fā)表論文、文章、內(nèi)參等300多篇、英文論文十幾篇,著述和譯著也已有十幾部,發(fā)表文字共計700多萬字。鄭秉文常常是相關部門決策議政的“座上賓”,十幾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中央領導在他研究報告上做出批示,幾乎參與了2000年以來社保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論證和頂層設計。鄭秉文東北人的性格是快人快語,敢言敢當,甚至在這幾年來的學術爭論中也是如此,他“經(jīng)常是少數(shù)派,經(jīng)常得罪人”。他也是一直以來媒體競相追逐的“社保大咖”,不論是在央視等主流媒體上解讀社保改革新規(guī)還是在相關論壇演講普及社保知識,理性且不乏激情的鄭秉文讓他始終有著旁人少有的學術感染力。
自然,這位“社保大咖”的個人影響力已無需多言,作為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的鄭秉文,他所帶領的這一團隊近年來的學術貢獻也可圈可點:每年完成的《中國養(yǎng)老金發(fā)展報告》系列著作已成為社保研究領域的權威之作,連續(xù)五年召開的社會保障論壇也已成為社保領域的重要平臺,這些舉措不僅促進了產(chǎn)、學、研、政各界的廣泛交流,也在為政府決策建言獻策、為學術研究拓疆擴土、為業(yè)界發(fā)展提供咨詢等方面形成影響力,打造出了有著社會高知名度的學術品牌。而這些成績的得來當然與這一團隊的領導者鄭秉文的帶領和打磨密不可分。
“‘半路出家’只有全力以赴”,鄭秉文如是想也如是做。難怪社科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這么評價他:“我相信,即使他當時不選擇研究社保領域,研究其他領域,亦或是做其他的事情,都會和今天一樣有成就,他就是這種人。”


“要建立以民族價值觀為支撐的社保模式”
2016年,推進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成為我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關鍵詞,在“去產(chǎn)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部署之下,“幫助企業(yè)降低成本”成為重要的一環(huán)。而把社會保險費率降下來、切實為實體經(jīng)濟讓利則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是決策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作為社保問題的研究者,鄭秉文從供給側(cè)改革對降費提出要求出發(fā),走向問題的背面和縱深,在考察社會保險費率高企的現(xiàn)狀和原因的基礎上,對降費后面臨的潛在風險和挑戰(zhàn)進行分析,并對降費倒逼社會保險制度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意義展開探討。他在今年6月份剛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供給側(cè):降費對社會保險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意義》中寫道:
“社會保險降費,在表面上是供給側(cè)的階段性改革舉措,但在新常態(tài)下,要有中長期的心理準備;從深層次看,借用降費作為契機進行制度結(jié)構(gòu)性改革,將會在中長期內(nèi)成為支撐降費的基礎。換言之,降費率與調(diào)結(jié)構(gòu)不要偏廢,要相互促進。”

2009年在丹麥社會福利部門前

2013年在薩爾瓦多召開的第27屆美洲國際社會保障大會上發(fā)表演講

2014年,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亨利·阿倫教授
在鄭秉文看來,不應僅從降費的表象去理解其政策含義,不應一“降”了之,而應借此機會改革制度,增強制度的收入能力,改善制度供給的質(zhì)量,推進整個社保體系的結(jié)構(gòu)性改革。所以,他認為,降費是表面的,制度改革是本質(zhì)的,否則,降費難以真正實現(xiàn),過幾年又回到原點。他反對社保改革中將主要精力放在“找錢”上,而忽視了社保結(jié)構(gòu)性改革,認為社保結(jié)構(gòu)性改革才是提高財務可持續(xù)性的根本,這應為此次供給側(cè)改革的實質(zhì)。采訪中鄭秉文表示,當前的養(yǎng)老保險制度缺的不是錢,而是正確的機制,解決了機制問題就解決了制度的可持續(xù)性難題,“否則,社保改革還停留在十年前‘找錢’的階段,那就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zhì),因為時代變了,條件變了”。
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研究風格,對待社保問題從不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探討,對制度的可持續(xù)性、深層次的模式選擇、政策背后的博弈、文化的支撐等等,鄭秉文都等同視之,“跳出社保研究社保”,讓他一直葆有了對于相關問題的前瞻認知。
作為最早譯介、引入和研究名義賬戶制的國內(nèi)學者,鄭秉文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引入和建立名義賬戶制是解決我國社保制度困境的一把鑰匙。所謂名義賬戶制是“名義繳費確定型”的簡稱,其本質(zhì)是在融資方式上是現(xiàn)收現(xiàn)付,而在給付方式上采取繳費確定型,就是多繳多得。長久以來,在“統(tǒng)賬結(jié)合”的根本制度之下,我國養(yǎng)老保險制度采取的是“真金白銀”的積累型個人賬戶制度,2001年做實賬戶試點以來,“做實賬戶”一直是既定政策的大政方針。但鄭秉文經(jīng)過多年對名義賬戶制度的研究,始終認為做實賬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在他看來,這并非決策層在主觀上喜不喜歡的問題,而是在客觀上能不能實現(xiàn)的問題,如果強行實施,最終必將流產(chǎn),“因為它違背了‘阿倫條件’(編者注:阿倫教授現(xiàn)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見照片),或說違背了“生物收益率”的原則,各級政府在做實賬戶時就不可能真心實意地支持它!”為此,鄭秉文當時提出了一整套適用于我國國情的完整與變形的名義賬戶改革方案。鄭秉文的這些思想在2007-2008年受原勞動和保障部委托的課題研究時集中做了表達并提交給主管部門。由于歷史條件等原因,做實賬戶試點一直進行著,但效果不好,隨著時間的推移,空賬規(guī)模越來越大,2006年是10957億,到2013年就高達30955億,而做實的個人賬戶在2013年僅為4154億元。2013年在人社部邀請國內(nèi)四個單位參加養(yǎng)老保障制度頂層設計,其中有三個主張實行名義賬戶,鄭秉文的團隊也在這三個單位之中,這說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做實賬戶是不可能的。在這樣一個氛圍下,2013年年底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提出“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取代了“做實個人賬戶試點”的一貫提法。鄭秉文堅持十幾年的名義賬戶政策主張終于取得共識,作為發(fā)展趨勢和客觀規(guī)律終于形成高層決策。名義賬戶制重回決策者視野,當然離不開學術界的鼓與呼,與鄭秉文等一眾社保研究者的努力密不可分,而支撐鄭秉文進行持續(xù)研究的也是那份學者的社會責任感。


這種責任感體現(xiàn)在他率真直言的性格上,體現(xiàn)在他對研究的執(zhí)著和“不折不從”的學術堅持上。十年前受某部委的委托做課題,得出的結(jié)論不是做實賬戶,與當時的主張和該部門的意見完全相反,直接導致了這一課題的終止。去年受托為某部門做課題,得出的結(jié)論也不完全與該部門一致,經(jīng)過磨合,仍存在較大距離。
由此,鄭秉文經(jīng)常屬于“少數(shù)派”,但往往也是“關鍵的少數(shù)”,無論是在人數(shù)很少的內(nèi)部征求意見會上,還是在社會媒體上,或是在公開與半公開的學術爭鳴當中,只要他認為是正確的,他就堅守,有時在發(fā)言中甚至只有他一個人,是“絕對的少數(shù)”。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社保改革進入深水區(qū),改革的領域都是“硬骨頭”,在內(nèi)部討論時,在發(fā)表內(nèi)部研究報告時,在公開演講時,對某些存在重大理論爭議并十分尖銳的問題往往是難以回避的,比如,對泛福利化的看法,問題的本質(zhì)是否效法歐洲福利國家模式;當前制度的根本問題是再分配功能弱化,還是個人激勵性弱化;當前改革中是否應該強調(diào)多繳多得的原則,是否強調(diào)個人積極性與激勵性;個人賬戶比例是擴大有利于可持續(xù)性和長期利益,還是縮小個人賬戶;社保制度設計中是應該強化精算技術的重要性,還是弱化精算技術的重要性,即應如何看待堅持精算平衡原則,等等,這些爭論還在繼續(xù)……


在很多領域,他的看法和提法都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獨到之處,最終受到采納。比如,他是最早提出制度碎片化概念的學者,并在分析碎片化制度弊端的基礎上指出建立統(tǒng)一社保制度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他認為,中國社保制度的碎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橫向上是地域割據(jù),這是統(tǒng)籌低下的表現(xiàn),縱向上還是以人群劃分為特征,引發(fā)不公平,比如機關事業(yè)單位獨立于大制度,所以,在七、八年前,他堅決反對為農(nóng)民工獨立建立一個制度,在很多會議上,他都旗幟鮮明地反對有關部門這一動議,甚至在會上公開說“如果中國真的出現(xiàn)農(nóng)民工養(yǎng)老保險制度,在歷史上將是罪人”,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最終證明,2009年底有關部門最終放棄了農(nóng)民工沒有建立單獨制度的決定是正確的。他是首次提出堅持、推動、普及DC型信托制年金發(fā)展路線圖的學者,而堅決反對采取DB型制度,認為DB型制度不適合中國,企業(yè)生命周期太短,既不利于保護工人的合法權益,還有可能將國家也綁架進來,他的這一研究報告受到總理的批示,我國一直堅持401k模式的DC型信托制年金制度,與此有關,這也不利于個別的部委利益,他們感到“不爽”。與此同時,鄭秉文一直主張在中國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養(yǎng)老金管理公司”,認為這是推動年金基金投資、擴大年金參與率、推動職業(yè)年金發(fā)展甚或是推動基本養(yǎng)老保險基金投資體制改革的一個“牛鼻子”,對此,鄭秉文早在2007年就開始撰文倡導建立中國版的養(yǎng)老金管理公司并一直呼吁至今。去年底,中國第一個養(yǎng)老金管理公司終于呱呱落地了。此外,鄭秉文一直認為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體制要改革,是主張養(yǎng)老保險基金投資體制改革的鼓吹手,認為養(yǎng)老保險基金存銀行收益率太低,不利于養(yǎng)老保險的可持續(xù)性,不利于提高職工的替代率,也不利于資本市場的建設,并襟懷坦白,勇于公布自己學術觀點發(fā)生變化的心路歷程和原因——在12年前為什么主張國債投資模式,不久為什么改變觀點、主張證券投資模式,都公開發(fā)表文章,更正自己的觀點,坦誠自己學術思想的變化及其原因。其實,鄭秉文的學術興趣比較廣泛,由于他分別在歐洲所、拉美所和美國所工作過,所以,對這幾個地區(qū)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保障也有深入的研究,例如,對歐洲福利模式的研究很深入,尤其對法國福利體制研究頗多,網(wǎng)上公開能看到的研究法國的大篇幅文章幾乎都是他所寫;對拉美的研究中涉獵到城市化、反貧困、貧民窟和社會保障等,并有不少著述,尤其是,他將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國家來研究,并利用拉美所的平臺,首次將“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傳播給相關拉美國家,例如巴西和阿根廷,傳遞給有關國際機構(gòu),比如拉美經(jīng)委會,泛美開發(fā)銀行等,由此形成拉美本土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學術領域;對美國的研究以前就涉及到奧巴馬醫(yī)改等,到美國所工作后主要集中在美國多層次養(yǎng)老金制度的特征與資本市場等等,例如,美國養(yǎng)老保險制度第一支柱OASDI的研究,美國第二支柱401k和DB型制度的研究,美國第三支柱IRA的研究,是國內(nèi)最熟悉美國養(yǎng)老制度的專家。此外,鄭秉文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已有六、七年的歷史,寫作不少相關文章,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例如,他上月在《人民日報》撰文《從國際經(jīng)驗看如何長期保持增長動力》,就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如何保持強勁發(fā)展動力提出了國際比較分析和借鑒,這篇文章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引起海外媒體的注意。于鄭秉文而言,對現(xiàn)實問題的思考和解決也往往伴隨著理念和思想的升華。他的視野是廣闊的,思考也不乏深邃性,在不同場合就具體的問題談論再多最終都會歸結(jié)到國家的福利模式選擇上來,在他看來,社保改革要遵循理性追求,要有明確的制度目標,要選擇符合本國基本國情的福利模式——
“福利模式的選擇事關重大,涉及一個國家未來經(jīng)濟發(fā)展?jié)摿蜕鐣l(fā)展彈性等重大問題,最終決定這個國家能走多遠。因此要盡早確立起自己的追求目標,凝聚社會共識,以立法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以便在制定各項政策時能夠一以貫之,不以政府換屆和領導人的變更而隨意變化”,采訪中鄭秉文強調(diào),“要建立起符合國家文化傳統(tǒng)、以民族價值觀為支撐的社保模式選擇。”


“只要大家承認我是個學者,這就夠了”
“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親身經(jīng)歷和參與了改革開放。作為學者,尤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在理論上能夠有所建樹,就更為幸運。如果在實踐上能夠有所參與并對某些改革有所推動,就會獲得極大的滿足。”

鄭秉文在2014年出版了三卷本的《鄭秉文自選集》,共計150多萬字,在“自序”中他如是寫道,以平實而真摯的語言道出了作為一介學者的樸素情懷。在社保領域耕耘近二十年,鄭秉文忘我的研究熱情始終不減。不論是早年間一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就要去學習了解當?shù)氐纳鐣U锨闆r,還是近年來一些媒體人表示常常在凌晨3、4點鐘收到鄭秉文的稿件,即使年過花甲、雙鬢斑白,熟悉他和初見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旺盛的精力和飛揚的神采。采訪中他興致勃勃地向筆者介紹即將出版的關于加拿大1997年社保投資體制改革的譯著。鄭秉文初次了解到加拿大的這一改革還是十多年前讀到的一篇學生論文,此后他念念不忘這場改革,終于在近年通過一位律師輾轉(zhuǎn)拿到了書寫這一改革的原版書籍。鄭秉文花了兩三天一口氣讀完這本書,當即拍板要將它翻譯過來向國人推薦。

“在加拿大的這次改革設計中,為建立資金池而提高繳費率所做的測算,為減輕子孫后代繳費壓力而建立投資體制所預測的投資收益,為提高收益率和減少市場風險設計的投資體制所做的制度創(chuàng)新等,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鄭秉文說到加拿大1997年改革滔滔不絕,“當然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制度確立的過程、改革背后的博弈。財長力主改革,副財長全面設計,與總理進行斡旋;改革方案數(shù)易其稿,持續(xù)多年,不僅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和咨詢智庫,還與各省多次協(xié)商,甚至到省里進行專題講解和路演。這一過程也是極有意義值得探研的。”
然而與我們?nèi)巳讼⑾⑾嚓P的社保問題,鄭秉文還是時不時覺得在國內(nèi)重視程度不夠,此前他在電視節(jié)目中與龍永圖論道“明天我們?nèi)绾勿B(yǎng)老”時就說道“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已經(jīng)迫切到應該要唱國際歌的時候了”,形象且飽含憂思地表達了養(yǎng)老改革已經(jīng)到十分緊迫的程度;他時常呼吁要秉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和開放的姿態(tài)讓更多的人了解社保現(xiàn)狀、參與到制度設計中來,作為社保專家的他也始終不遺余力地向社會對社保問題作解釋宣傳。
而在公共視野背后的鄭秉文,已在社科院的本職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工作了幾十年。從研究生院轉(zhuǎn)到研究所后,先是2000年10月至2004年7月在歐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長,緊接著2004年7月至2014年5月到拉丁美洲研究所任所長兼書記,再到如今的美國研究所所長,鄭秉文始終堅持學術第一、學術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要藝術地平衡,始終頭腦清晰地處理好個人研究與領導的研究所研究主題之間的關系,始終孜孜不倦做學問、在社保研究領域細作深耕。
在中國社科院國際研究學部有8個研究所,他曾在3個研究所工作過;作為所領導,他是“另類”,因為他的研究領域“很小”,并非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等主流;但17年來,他一直恪守這一原則,即將社會保障和社會問題作為個人科研和發(fā)表成果的主陣地,對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等主流研究領域,他以參加學術活動、帶領做課題等履行所長職務出發(fā),但不署名發(fā)表著述。在他眼里,這樣做,才是一個學者出成績應堅守的學術之道,尤其作為后發(fā)者,更應專注而堅持,否則學科相差很遠,極易變成“萬金油”。
“只要大家承認我是個學者,這就夠了”,采訪的最后鄭秉文說道。更使他津津樂道的是,在他60歲生日時,有學生建議搞一個簡單的慶生,但他并沒有同意,而是把一些畢業(yè)和沒畢業(yè)的學生共計有四、五十人都召集在一起,當時,針對鄭秉文的一項研究報告,總書記剛剛做了大段批示,總理和兩位副總理也接著分別給予大段批示,這次聚會最終變成一個學習中央四位領導批示的學習會和社保改革的小型研討會,有著特殊的意義。

如果說扎實的外語和經(jīng)濟學專業(yè)功底、留學訪問的經(jīng)歷以及治學方向的準確把握等都為鄭秉文獲得學術研究上的 “后發(fā)優(yōu)勢”筑牢根基,那么堅定的學術目標、理性的治學態(tài)度和持續(xù)的研究熱情和努力則是鄭秉文行穩(wěn)致遠的源泉和保障。這大概就是“后發(fā)者的先至之道”,值得吾輩感悟借鑒。
(本欄目責任編輯:阮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