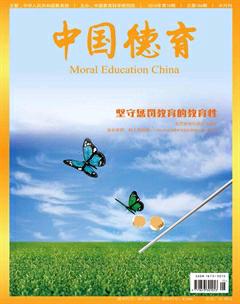懲罰教育的價值與實現
在實際教育教學工作中,我們認為,簡單地責難或貶低懲罰教育的應有意義,不僅背離了懲罰教育的初衷,而且難以達成立德樹人的育人目的。
隨著基礎教育改革的縱深挺進以及以人為本教育思想的倡導與貫徹落實,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深刻地領悟到褒獎、勉勵或頌贊在學校教育中的至關重要,不少教師不敢、不愿或不屑使用懲罰。那么,在實際的教育教學情形中,懲罰教育有無存在的價值?究竟該不該使用懲罰?如何合理有效運用懲罰?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確證懲罰在學校教育中的應有地位和理性對待懲罰教育的邏輯前提。
一、懲罰:一個綿亙古今且飽受爭議的
重要教育命題
《新華詞典》將“懲罰”解釋為通過懲罰使人警備。懲罰教育是對個體過錯行為的糾偏、否定與制裁,旨在遏制某種不良行徑,使人改過自新。縱觀人類教育發展史,不難發現,對懲罰教育的論辯貫穿于教育的整個發展過程。
在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中尊崇懲罰的教育思想源遠流長。在我國古代,《易經》中就有“利用刑人,以正法也”的記載,《學記》中也有“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等對學生進行懲罰的字句描述。先秦時期的法家如韓非子、李斯等人也強調通過懲罰的方式壓制人們無限膨脹的私欲,以達到“化性起偽”。南宋的朱熹更是希望通過“存天理、滅人欲”的懲罰手段,以探究“窮理盡性”之要。進入現代以來,不少一線教育工作者也在實施懲罰的過程中積累了眾多經驗,維護了課堂紀律,穩固了學校的教育教學秩序;在西方,夸美紐斯在《大教學論》中專設一章“論學校的紀律”詮釋懲罰及懲罰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來,犯有過失的學生應該接受應有的懲罰,要通過嚴格的紀律規范學生的行為,“使他們日后不去再犯。”[1] 在赫爾巴特那里,訓育和管理被視作培養學生遵守秩序并順利進行教學的基本前提。“教育而不注重兒童不守秩序的行為,即兒童本身也不認為是教育。此外,如果不堅強而溫和地抓住管理的韁繩,任何功課的教學都是不可能的。”[2]涂爾干在《道德教育》中也極力推崇懲罰的重要性,他認為,遵守紀律是一種美德,維護紀律嚴肅性和權威性的有效手段是懲罰。“懲罰具有補償作用,可以糾正因過錯而產生的惡”,[3]進而培養學生遵守法紀的良好品性。
然而,與提倡懲罰及懲罰教育截然相反的是,一些研究者對懲罰及懲罰教育口誅筆伐。他們認為,懲罰既不是一種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手段。我國古代宋明理學家王守仁反對封建高壓的、強迫的、簡單粗暴的、鞭撻繩縛的懲罰教育,強調對學生實施愉快教育,讓學生在愉悅的教育氛圍中明人倫、致良知。在西方一些極力倡導自由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學者眼中,拒絕懲罰是教育的“金科玉律”。如薩特認為,人是絕對自由的,任何外在的懲罰均是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僭越了人自由選擇的權利,理應遭到鄙視與唾棄,甚至發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悲壯宣言。無獨有偶,部分人本主義者也認為懲罰的規約特征與天賦人權的法則相違背,實施懲罰教育是對做人價值的吞噬等。
與以上兩種觀點有所不同的是,近現代以來,一些“價值中立者”既不簡單地主張運用懲罰,也不拒絕懲罰。他們既反對“防邪近正”的懲罰教育,也反對“放任自流”的自然教育。在他們看來,教師的任務不是通過懲罰的方式告知學生何為對錯、何為是非,而應保持中立。這是因為,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教師不應將自己的思想以紀律或規則的懲處方式強加于學生,要在教育過程中培養學生自我選擇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教育者一定要記住,“我們無法也不可能交給學生一套固定的、絕對的價值標準,但我們卻可以交給他們一種更有效的學問,那就是教給他們通過自己的反思來獲得自己價值的方法。”[4]
對懲罰及懲罰教育的不同聲音,從不同方面佐證了懲罰是教育教學難以割舍的一個研究場域,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研究視域,而且賦予我們進行深化研究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已成為現代教育不容回避的重要議題。
二、懲罰教育的價值意蘊
在實際教育教學工作中,我們認為,簡單地責難或貶低懲罰教育的應有意義,不僅背離了懲罰教育的初衷,而且難以達成立德樹人的育人目的。合理的懲罰與賞識是有效教育的一體兩翼,二者缺一不可。迷戀賞識教育而貶低懲罰教育,易使人滋生盲目優越感和自我中心的不良心態,刻意抬高懲罰教育而弱化賞識教育,易導致個體的不滿情緒或抵觸心理,是一種抱殘守缺的錯誤行徑,均無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對于賞識教育的價值,閃耀著研究者睿智的風采與真知灼見,這里不再贅述,僅對懲罰教育的應有效用作詮釋與說明。
(一)懲罰教育是合乎人性吁求的價值指引
作為人的基本屬性,人性的善惡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范疇,也是研究者孜孜不懈探求的研究領域,在歷史上形成了性善、性惡、性無善無惡或有善有惡等多種觀點。總結歷史,反觀現實,我們更加認同霍布斯“人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的人性預設。人本身具有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的雙重屬性,也對此作了注解。“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它一方面是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是人生而固有的社會本性。”[5]人集善惡于一身。人具有的自然屬性,表明人并不總是道德的、理智的、趨善的,而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諸如貪婪自私、利己排他的愿望和行為。在這種情境下,懲罰教育可以為人性的健康發展提供價值指引,使個體理解善惡的真實內涵,懂得向善、向上的重要意義,知羞恥,明榮辱,從投機主義、利己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泥潭中解脫開來,學會過一種道德的、積極向善的生活方式,實現利己與利他的有機結合。“我們人類在各種年齡階段有不同的欲望,這不是我們的錯處。我們的錯處是在不能使我們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規范與約束。這中間的區別不在有沒有欲望,而在有沒有管束的能力與不為欲所獲的功夫。”[6]借助懲罰這種約束與管理手段,可克服人性的固有缺陷,充分發揮人性的閃光點,激發學生改過向善的上進心,激勵和鞭策學生避惡趨善,循著人性光輝之路,指引他們朝著完善人性的軌道穩步前行,成為充盈人性、豐富人性、健全人性與發展人性的重要標尺。
(二)懲罰教育是遵循道德發展規律的必然抉擇
道德教育發展的規律表明,個體道德的發展經歷了從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轉變過程。“他律道德是自律道德的基本前提與條件保障,自律道德是他律道德的拓展延伸與凝練升華。”[7]對于辨別能力較弱、自主能力不強的小學生和部分中學生而言,必要的制度約束和紀律懲罰可糾正學生認知上的偏差,使之明確行為的邊界,阻止或遏制不良行為,形成教育秩序,培養學生的道德責任感,為個體道德的自主建構提供基礎條件和外在支撐。反之,倘若學生違背日常行為規范和道德規則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不僅會模糊學生的道德認知,不利于他們持續地、一貫地踐行道德,而且易使他們習得一些不良的習慣,如遲到早退、曠課、說謊直至挑釁鬧事等,將道德置于九霄云外,中斷了道德發展階段的連續性。按照柯爾伯格長期跟蹤研究得出的結論,中小學生的道德判斷經歷了習俗前水平、習俗水平和習俗后水平三個水平,每一個水平又分為兩個階段,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若在習俗前水平和習俗水平缺乏有效的懲罰教育,個體的不良行為得不到有效的收斂與矯正,則難以達到習俗后水平——道德自律。因此,懲罰教育是契合學生道德發展規律的理性訴求。
(三)懲罰教育是促進個體社會化的有力支撐
生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要經歷社會化的發展過程。懲罰是一種強有力的教育力量,可將個體從錯誤中解救出來,懂得敬畏規則,提升明辨是非和識別對錯的認知能力,逐步成為社會所預期的、積極的社會成員,以幫助個體沿著社會化的方向前行。倘若對犯有過錯的個體或聽其自然,或包庇縱容,或一味妥協,致使過失行為得不到有效的懲處,必然會助長他們投機取巧、明知故犯的畸形心理,表現出眾多違紀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人的合法權益勢必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與保障。實際上,對犯有過失行為的個體進行懲罰的過程,也是對其他人進行提醒、警戒的過程。在學校教育中,懲罰教育會使學生深刻地認識到不良行為的嚴重后果,從被訓誡學生的身上汲取深刻教訓,銘刻在心,從內心建立心理防衛意識,處處提防,引以為戒,有效避免學生從違紀越軌行為滑向違法犯罪行為的深淵,引導學生從被動接受懲罰到主動建構道德。一如馬卡連柯所指出,得當的懲罰制度不僅合理,而且合法,對于學生的成長與發展重要而迫切,卓有成效的懲罰有益于培養他們堅韌的性格特征,有助于提升他們抵御外界不良刺激以及戰勝誘惑的實際本領,這對于學生了解社會、走向社會、適應社會進而服務社會是大有裨益的。
三、懲罰教育的有效運用
懲罰教育對于個體的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缺失懲罰的教育是一種單一的教育,是一種殘損的教育,是一種脆弱的教育。但懲罰教育并不總是有效的,為避免懲罰的濫用、低效或無效,增強懲罰教育的科學性、指向性、自覺性與有效性,需要我們認真做好幾方面的工作。
(一)精準定位,尊重學生
在運用懲罰教育時,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有明確的認識與判斷:懲罰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達成教育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倘若定位不準或偏狹,不僅無以實現懲罰的應有價值,而且加劇了人們對懲罰教育的懷疑態度與抵制情緒,無論是對于懲罰教育本身的良性運作,還是對于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均會產生不容小覷的負面效應。為此,一方面,要確立完善人性的懲罰觀。懲罰教育既非宣泄教師負面情緒的方式,也非讓學生聽話、馴服學生的利器,而要“治病救人”,將學生的錯誤言行扭轉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喚醒學生的道德良知,塑造學生健全的道德人格,逐步構建堅不可摧的道德大廈;另一方面,要凸顯人文關懷。懲罰不應傷害學生的尊嚴,打擊學生的自尊心,侮辱學生的人格,而要引導學生從內心認同紀律,內化規則,進而達到道德自覺。這在蘇霍姆林斯基那里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在《和青年校長的談話》一書中精辟地寫道,懲罰也是一種善舉,實施懲罰是為了學生更好的成長,教育工作者不僅要保護學生自尊、自立和自強的心理,同時也要對他們心靈里滋生蔓延的一切紕繆的傾向采取毫不退讓、毫不放任的態度。如此,既體現了對學生的尊重,又發揮了懲罰教育的應有作用,而且會使受到懲罰的學生從內心深處認可懲罰,并進行自我反省,自覺體認道德,外化于行,最終實現道德的自主成長。[8]
(二)把握分寸,堅持適度
在懲罰教育中,掌握分寸是一種重要的管理藝術。當學生有過失行為時,采取的懲罰并非越多越好,也非越重越好。一些教師僅憑個人的主觀意愿用事,過多地運用懲罰,或是引發學生的焦慮心態、疲憊和恐懼反應,或是誘發學生等閑視之、“破罐子破摔”的自我作踐與甘于墮落心理,甚至走上歧路,走向了懲罰教育的反面,與教育規律背道而馳。[9]為此,在懲罰教育中應把握分寸,堅持適度,特別需要糾正教育工作者的兩種錯誤行為,一是將懲罰作為唯一有效的甚或主導的教育手段。眾所周知,“表揚為主,批評為輔”是中小學的基本原則。因此,切不可將批評或懲罰人為地擴大,更不能將其視為整治“問題學生”的“尚方寶劍”。在教育教學中,如果依靠明理導行的教育勸導能引導學生改正過失的,不必大動干戈采用嚴厲的懲罰。只有那些明知故犯、屢教不改、品性頑劣的學生,才慎重地選用適合的懲罰方式;二是將懲罰等同于體罰或心罰。一些教師在懲罰教育中濫施淫威,將懲罰與體罰、心罰混為一談。媒體報道的諸如在學生臉上刻字、在學生身上扎針等便是鮮明表征。此外,一些教師用羞辱、恐嚇的方式進行懲罰,給學生起外號、譏諷學生、挖苦學生,也是教師心罰學生的表現。此種行為,嚴重地違反了《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不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的規定,逾越了懲罰的界限,損害了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而且極易誤導社會各界對懲罰教育合理性的認知,勢必導致懲罰教育的挫敗。
(三)區別對待,有序推進
在運用懲罰時,一定要堅持分類指導,有針對性地實施。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法國啟蒙思想家洛克的做法。他在《教育漫畫》一書中寫道,我們應理性看待懲罰,既不能丟棄懲罰,也不能千篇一律地、模式化地運用懲罰。第一,要依據學生的不同年齡特征和心理承受能力實施相對應的懲罰。如對于小學生而言,盧梭在《愛彌兒》提出的自然后果懲罰法便是很好的例證。這種“冷處理”的方式會使小學生深刻地體驗到,來自師長的懲罰是基于自身不良行為或過錯行為的自然后果,這對于可塑性極強的小學生而言,成效自然不言而喻;第二,要根據學生所犯錯誤的嚴重程度進行分層實施。一些有不良行為如偷盜、酗酒、參與非法組織等屢教不改的學生,要尋求社會的幫助,必要時移交相關行政機構;第三,要保證懲罰教育的一貫性與連續性。在懲罰教育過程中要力戒松緊不一、虎頭蛇尾等短期行為,要增強懲罰教育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推進懲罰教育的可持續發展,使懲罰成為學生健康成長不可或缺的有益教育資源。另外,教師在有序推進懲罰的過程中一定要公平、公正,力戒對犯有過錯的“特殊學生”特殊對待。
(四)統整協調,多方聯動
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表明,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持久性、反復性、多向性、變遷性、整合性的典型特征。聚焦于懲罰教育領域,亦不例外。倘若缺乏來自社會、政府、學校和家庭之間的配合與互動,懲罰教育必將在各方對峙或沖突的不良情形中陷入僵局,嚴重地削弱懲罰教育實施的整體效果。為此,首先,各方應緊扣時代脈搏,協同攻關。政府要提供必要的懲罰教育政策支持,家庭、學校與社會要緊密結合懲罰教育暴露的新問題與前沿動態,與時俱進地推進懲罰教育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推進,為其提供堅實的理論根基與實踐路向;其次,社會各界要統一教育要求,步調一致地探討如何有效開展懲罰教育。我們必須從“該不該懲罰”這個毫無實質意義的爭論中擺脫出來,總結經驗,不斷提升懲罰的品味與層次。一如盧梭所言,“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與集體的共同體,以代替每個訂約者的個人”;[10]最后,要建立懲罰教育的專門網站,交流信息,互通有無,為多方聯動搭建平臺,在改革創新中不斷打破固有思維和原有定勢,將懲罰教育推向新的發展境界。
參考文獻:
[1]夸美紐斯.大教學論[M].傅任敢,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198.
[2]張煥庭.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267.
[3]涂爾干.道德教育[M].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3.
[4]Simon S,Olds S.Helping Your Child Learn Right From Wrong:A Guide to Values Clarification[M].New York:Schuster,1979:17.
[5]王海明.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1.
[6]洛克.教育漫話[M].傅任敢,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21.
[7]馮永剛.制度建構:兒童道德啟蒙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礎支撐[J].中國教育學刊,2016(4):16-20.
[8]馮永剛.規則教育的偏失及匡正[J].中國德育,2015(7):33-37.
[9]戚萬學.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公民道德教育的使命[J].教育研究,2015(11):14-19.
[10]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21.
【馮永剛,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黃蜀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