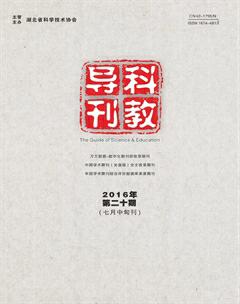從微觀角度看柏林大學的優秀傳統
李殿民
摘要 19世紀初,被譽為“現代大學之母”的柏林大學的建立引發了德國高等教育領域的變革,也給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柏林大學成立于國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際,卻能夠自成立起在世界大學中獨領風騷近百年,幾乎沒有一所大學可以與之媲美。那么,柏林大學究竟是憑借什么創造出了引領世界高等教育的輝煌?追尋柏林大學的優秀傳統,發現柏林大學的魅力,從微觀角度探索柏林大學的優秀傳統,發現柏林大學的魅力。
關鍵詞 微觀角度 柏林大學 優秀傳統
中圖分類號:G64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l.cnki.kjdkz.2016.07.003
在19世紀初的洪堡大學改革中,被世界譽為“現代大學之母”的柏林大學誕生了。柏林大學自1810年成立起在世界大學中獨領風騷近百年,幾乎沒有一所大學可以與之媲美。柏林大學的建立代表著一種富有強大生命力的新模式在德國大學中產生。正因如此,德國大學在19世紀的歐洲高等教育中獨占鰲頭,高居歐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盟主地位。那么,柏林大學的巨大魅力究竟何在?本文旨在從微觀角度挖掘柏林大學的優秀傳統以期找到對于今天我國大學發展來說具有借鑒意義的東西。
1 獨特的辦學理念
1.1 教學與科研合一
盡管大學的科研功能肇始于哈勒大學,但是在那時科學研究只是大學的“副業”,不占主流地位。洪堡大學改革下的柏林大學建立時,“教學與科研合一”的理念被首次明確地提出。從此,西方大學除教學功能外被賦予了一個新職能:科學研究。大學的科研功能首先在柏林大學確立起來。在柏林大學,科研是首要的任務,其次是教學。但是,這并非意味著不重視教學。這種理念源于洪堡的獨到的“學問觀”,他認為,“‘學問不是繼承文化傳統,而是要求大學經常把學問作為一個問題來處理,對問題尚未獲得解決必須時時致力于研究。”因此,大學教學必須與科研結合起來,教學內容因該是科研活動的成果。只有教師經過創造性的研究活動取得的成果才能作為知識傳授給學生,也只有這樣的“教學”才能稱得上是大學教學。柏林大學在選擇教授時,要求只有對學問有貢獻、有獨創能力的學者才有資格當選,而不一定要能言善辯。學校堅決反對教師重復教條,提倡鼓勵思想自由和思想創新;要求學生一定要掌握科學原理、科學的思維方法,要能夠從事創見性的科學研究,而不必博學多識。柏林大學師生共同追求真理、一起致力于學術研究的風氣樹立了起來,濃厚的研究氛圍得以營造起來。從此,大學里不再有學者們的高談闊論、照本宣科、拾人牙慧或是人云亦云。“教學與科研合一”的理念為柏林大學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使之煥發出勃勃生機。“洪堡認為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就必須將教學與研究結合起來,時間證明他是正確的。”教學與科研合一的這一理念極大地推進了西方大學的現代化,并成為了西方現代大學的一個永久的原則。
1.2 自由和寂寞
“自由”是由“教學與科研合一”決定的一個重要理念。進行科學研究必須要以自由為保障,自由是大學實現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政治上政績的取得和科學上成績的取得遵循的是不同的規范,因此,來自政府方面的影響會阻礙科學研究的進展。柏林大學的自由理念主要體現為: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如果說學術是大學的生命,那么學術自由就是大學生命的“守護神”。“政府不能對科學研究下令規定,其作用是提供科研工作所需要的設備和條件。”在這種意義上講,政府的職責是設法保障柏林大學的研究自由。教師應該自由地選擇教授內容,可以教給學生所有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在教學中,教師各講各的,不要求有統一的認識或標準。學生應該享有很大的學習自由:在決定去哪里學、學什么以及學習多長時間這些問題上,學生不應受到限制,他們可以自行安排學業,可以選修各種課程,可以從一所大學轉到另一所大學,原來取得的學分仍然有效;學習自由甚至還包括什么也不學的自由。大學中允許各種學派存在,教師除了得到固定工資外,還可以獲得學生的聽課費,這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了各學派的自由競爭。
“寂寞”既是柏林大學建立之初的又一重要辦學理念,也是對當時柏林大學及其師生的生存狀態和活動方式的一個極好的寫照。“寂寞”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柏林大學自治的實現,使柏林大學與政治、經濟和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被來自大學之外的各種力量左右。“在18世紀,大學教授的生活中心并不一定在大學中,他們通常與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教授從事第二職業的現象屢見不鮮、司空見慣。柏林大學建立后,教授的待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慢慢地就對現實的政治經濟生活疏遠了下來,開始安心靜居于“象牙塔”之中,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在其中盡情地享受著“寂寞”帶來的自由,“精神和心靈在寂寞中會變得寬廣、活躍、聰穎和強健。”柏林大學的教授們逐漸形成一種潛心研究高深學問的高貴氣質,他們這種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一批致力于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才俊前來匯聚于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學生要潛心于學習和研究以實現其知識和智慧的增進及其思維能力的發展,這就要求學生必須甘于寂寞,不被現實世界的名利誘惑,不受喧囂的世界紛擾,因為“紛擾的社會生活會使人失去精神的獨立性。”
2 獨特的組織制度
2.1 學院與課程設置
柏林大學在中世紀大學的學院設置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變動,把原來的文學院改為哲學院,即由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學院四個學院組成。哲學院取代了以往神學院的地位,居于各學院之首,成為大學的中心:哲學院的課程成為了大學諸門課程的核心;哲學院的職能不再只是純粹的教學機構,開始肩負起研究的使命。這是由哲學是科學的統一這一特性決定的,哲學是“科學之王”,是各學科發展和進步的基礎。柏林大學建校之初,“哲學院的總課程數約為78門,幾乎囊括當時除神、法、醫之外所有的高級學問。”根據知識的性質,課程被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與歷史知識相關的部分(如歷史學、地志學、語言學、人文類學科等);一是與純粹理性認識相關的部分(如純粹數學、純粹哲學以及有關自然或道德的形而上學等)。這兩個部分相互關聯,使得哲學院所涉及的領域覆蓋人類知識的全部。哲學院的所有課程都側重于各學科領域中基礎理論的研究,并不強調實際操作和應用。課程不僅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內容,而且引入了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
2.2 教學組織形式
2.2.1 習明納和研究所
習明納(研討班)和研究所也是柏林大學區別于傳統大學的根本所在。柏林大學建立初期設立的研討班只面向少數高年級學生,就某個特定的領域進行學術研究訓練。19世紀中期以后,研討班從一種教學形式轉變為了一種普通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盡管在當時的德國,研討班出現于柏林大學不是先例,但是之前的那些研討班“多側重于語言、哲學等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很少涉及近代自然科學學科,而且這些研討班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性的教學手段,并沒有在大學中將教學與科研真正結合起來。”研究所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和教學單位,擁有全部必要的人員和設備,例如實驗室、資料室、討論室和教室等等。在柏林大學,研討班和研究所是教學與科研結合的重要載體。在柏林大學的研討班或研究所,教授必須是學問淵博的而且“多產”的。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在交流中進行的是激烈的爭論和探討,進而產生出新的觀點,獲得新的科學發現。
2.2.2 講座教學和實驗教學
講座教學作為近代德國大學首創的教學方法,在19世紀初的柏林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柏林大學的講座按學科和專業進行設置,每一講座由一名講座教授全權負責,諸如組織考試,負責學生的錄取、人員招聘、自主研究、經費的管理等等。教授可以自由選擇論題舉辦演講,可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當作講義而不拘泥于固定的教材。為使學生有主動獲取新知識的能力,教師重在對學生進行思維方法的訓練。柏林大學的講座制賦予教授充分的權力,保障大學教學與研究的自由。實驗教學也是柏林大學將教學與科研合一的重要體現。原來學生們掌握科學基本原理僅僅是通過教師的講授這一單一途徑,而柏林大學采用實驗教學形式,實驗室研究成為教學的重要程序,學生們在親身操作實驗的過程中學習與研究。
2.2.3 管理模式
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模式被稱為“教授大學”,因為大學的自我管理權被教席教授壟斷,這種管理模式又被稱為“教授治校”模式。在柏林大學中,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是分開的,行政事務為學術事務服務。在學術事務中,教席教授享有廣泛和強大的權力:“大學一學部一研究所\講座”是柏林大學的組織結構形式,其中研究所\講座是中心,是大學的基本組織單位,其唯一負責人是教席教授,他們享有經費預算、儀器設置的權力,在其所在的領域中,研究和教學由他們負責,他們由國家聘任,薪水由國家發放;(教授中除教席教授外還有編外教授,他們在大學自我管理中沒有實際權力,處于從屬地位。)校長由全體教席教授會議選舉產生;最高的決策機構——學術評議會由全體教席教授會議委任;各學院的院長每年從全體教席教授中選出,院長代表學院執行有關博士學位和教授資格證書的頒發事宜,并管理學院的財政;各學院的院長還是該學院的學術管理機構的負責人,學術管理機構也由教席教授組成;學院有關教學人員的招聘、教授資格考試、教授資格評定等權力通常由該學院的教席教授組成的教授大會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