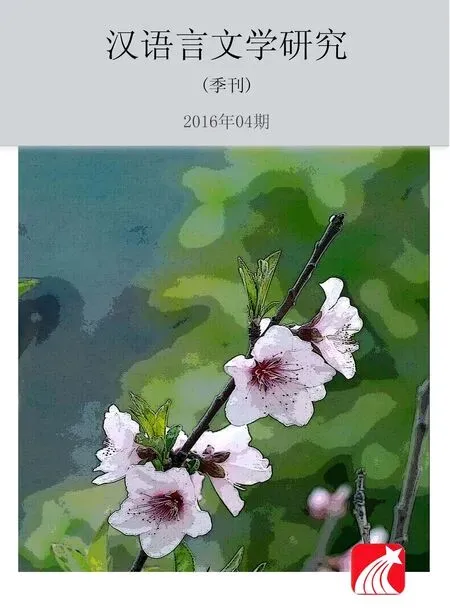地方性、民族形式與國家想象
季劍青
地方性、民族形式與國家想象
季劍青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文學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往往被視為一種美學風格,相關的討論經常只停留在形式層面。李松睿的新著《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卻注意到,在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和批評家的筆下,地方性作為一種自覺的追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對地方性的關切,顯然已經突破了形式和技法的范圍,而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因而,盡管這部著作仍以小說文本的分析為主體,但分析過程本身卻包含了自覺的理論視角和問題意識,從而使得全書獲得了一般小說研究著作所不具備的分量,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文學研究之外的歷史學領域,就會發現地方的視角一直貫穿于中國歷史的編纂和研究之中。且不說源遠流長且延續至今的地方志的編撰傳統,近代以來興起的新史學也非常重視地方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地方史的研究。當代歷史學者更是在域外理論的刺激下,在“國家/社會”“中心/邊緣”等框架下挖掘地方視角的潛力。無論是在王朝國家的大一統格局下,還是在中國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地方的意義往往是在與中央政府或國家權力的參照和互動下凸顯的。在這樣的視野下,20世紀40年代的特殊性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全面抗戰的爆發和國民政府的內遷,政治權力一體化運作的空間不復存在,中國形成了國統區、淪陷區和解放區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央的失墜使得地方的重要性急劇上升,抗戰時期地方性成為包括文學界在內的文化界和知識界討論的核心話題。
作者顯然注意到了抗戰的具體歷史語境之于地方性問題的意義,正是抗戰所造成的生活境遇的改變,“使得地方風光、地域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帶有地方性特征的事物,真正進入到20世紀40年代作家、批評家的生活之中”①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尤為重要的是,抗戰在打破舊的權力中心的同時,也在召喚新的國家想象。從這個角度,作者對“民族形式”論爭這一老問題,以及民族形式與地方性問題的關系,作出了新的闡釋。書中數次引用黃芝崗《論民族形式》中那段著名的話:“抗日的內容是火”,地方性的“舊形式”則是“薪炭”;而“‘民族的形式’則是烈火鍛煉成的”,因此“薪炭”的作用就在于“使內容的火燃燒得更其猛烈”。②同上,第10、33、102頁。地方性為民族形式的鍛造提供了材料,而民族形式又關涉著“抗戰建國”的構想:“在文藝‘民族形式’論爭背后,隱藏著的是不同的對于民族國家未來的構想與理解”。③同上,第92頁。
發生在國統區文壇的“民族形式”論爭,不僅展開了對地方性與民族形式之間關系的討論,更進一步延伸出民族形式如何獲得“國際性”和“世界性”的問題。在世界的舞臺上,中國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地方”。如果說只有在地方性的基礎上才能創造出民族形式,那么也只有通過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民族形式,中國的文學藝術才能在世界文壇上獲得一席之地。這就是蕭三那句著名的“愈是民族的東西,它便愈是國際的”④同上,第107頁。背后的邏輯,也是胡風強調五四新文學是“世界進步文藝傳統的一個新拓的支流”的真正用心所在。作者敏銳地指出,地方性與民族性,民族性與世界性,“這兩組概念實際上處于同構關系。正是這樣一種‘地方—民族—世界’的遞進關系在文藝的‘民族形式’論爭中被反復確認,并成為20世紀40年代文藝理論界的基本共識”①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第103頁。。也許可以補充的是,這種遞進關系包含著反向的辯證運動。正是對民族和國家的關切,使得地方性的材料和敘述上升為全民族的寓言,獲得了某種普遍性,這在作者專章分析的老舍40年代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同樣,也正是40年代左翼文藝理論家自覺的國際主義視野,正是他們對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地位的強烈關切,賦予民族形式以深刻的時代內涵,這也把他們所呼喚的民族形式與晚清以來建立在對傳統的體認的基礎上的文化民族主義,以及30年代國民黨官方的民族主義運動,鮮明地區分了開來。
民族形式問題在解放區也是一個核心問題。與國統區文藝界經由與地方形式的接觸而展開民族形式的討論這一路徑有所不同,解放區首先關心的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通過民族形式加以本土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②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在毛澤東這里,由馬克思主義來保證的普遍性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通過民族形式來取得本土化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而當時的延安文藝界受到國統區的影響,追求的是借助地方性特征來獲得“世界性”和“普遍性”,因而也就不難理解,這種追求會在受到1942年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批評后突然中斷。③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第110頁。毛澤東在《講話》中要求文藝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去,改造自己的階級立場,寫出真正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作品。《講話》沒有專門討論民族形式和地方性的問題,貫穿其中的始終是階級性這一普遍的尺度。然而當像周立波這樣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努力按照《講話》的要求去表現邊區人民群眾的生活時,他的作品卻表現出鮮明的地方色彩來,其中特別顯眼的便是他對方言土語的自覺使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解放區文藝中的地方性特征乃是階級話語支配的結果,“階級性成了衡量文學的地方性特征的價值尺度”④同上,第113頁。。
有趣的是,周立波的這種努力卻并未受到解放區文藝理論家的認可,他作品中的地方色彩不僅沒有為他贏得榮譽,反而成為他未能真正改造自己獲得“無產階級立場”,從而思想感情方面存在缺陷的標志。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趙樹理,這位后來被追認為山西“山藥蛋派”鼻祖的小說家,當時備受解放區文藝理論界的推崇,卻從沒有人強調他作品中的地方性色彩。為了解釋這種意味深長的現象,作者巧妙地引入認知“裝置”的概念,非常精彩地分析了解放區批評家如何在這種認知“裝置”的支配下,“自動地把這位作家(按:指趙樹理)筆下的方言土語‘過濾’為‘群眾的語言’或‘人民的語言’”⑤同上,第200—201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趙樹理的小說也不像老舍的小說那樣提供了具有民俗學意味的標本,而是刻畫了以整體形象出現的“人民大眾”。⑥同上,第232頁。趙樹理小說中地方性的“隱退”,確實是作者的獨到發現,對于理解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是具有癥候性意義的。這表現出作者銳利的眼光,他基于文本細讀對這一現象及其背后的機制的分析,也令人拍案叫絕。
概括地說,主導40年代解放區文藝理論界的主要是階級性的觀念,其次是民族性,地方性即便有所表現,也往往是批評的對象。在解放區的話語體系中,民族性是在和階級性的糾纏中,而不是通過對地方性的提升來呈現的。賀桂梅曾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構想中,“新的民族形式必須在兩個緯度上展開,一是相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普遍話語的民族性,一是相對于國內文化民族主義話語的階級性”①賀桂梅:《革命與“鄉愁”——〈紅旗譜〉與民族形式建構》,《文藝爭鳴》2011年第4期。。為了調和階級話語的普遍性與抗戰中建立 “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之間的緊張,毛澤東把由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組成的“人民大眾”,界定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②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5-856頁。,使其在具備階級代表性的同時,也獲得了代表全民族的資格。正是著眼于“人民大眾”在中華民族中的主體地位,毛澤東給延安根據地的抗日敵后斗爭,賦予了“領導中國前進”的歷史任務。他批評有些來自國統區的作家,因為對延安生活不熟悉而生出“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想要為“大后方”的讀者寫作,以為這樣才有 “全國意義”。毛澤東告誡這些作家,大后方的讀者也希望讀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愈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愈有全國意義”。這句話很像“愈是民族的東西,它便愈是國際的”,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可實際上討論的是延安這一特定環境的“地方性”如何具有“全國意義”的問題。毛澤東的邏輯不是從地方性本身提升到民族性,而是強調延安根據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力量,內在地就體現了“全國性”和“民族性”,因為“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③同上,第876-877頁。。這其中實際上也包含了中國共產黨對未來中國的展望,對新的國家的想象。它將是一個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而非簡單地建立在民族共同體基礎上的民族國家。
與作者對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討論相比,書中關于淪陷區作家對地方性的認知和處理的討論稍顯薄弱。在作者看來,由于淪陷區高壓的政治氛圍,“淪陷區文藝理論家對鄉土文學的大力倡導、對地方色彩的反復強調,其最終目的在于讓作家真實地寫出他們所身處的現實生活”,“借助于意義略顯含混的地方性特征,使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戰爭年代淪陷區人民真實的生存狀況,在言論動輒得咎的淪陷區,或許已經是那些正直的文藝理論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④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第126頁。作者以東北淪陷區作家梁山丁的長篇小說《綠色的谷》為例,具體分析了小說中東北地方風物描寫,如何最大限度地容納了復雜的政治環境不允許直接表達的諸多意義。這樣的論述自然是非常有啟發性的,但似乎還有進一步深入展開的空間:在這種復雜曖昧的政治氣候下,民族和國家議題是不是有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呈現?如果是的話,這種呈現方式與地方性又是怎樣的關系?
這里不妨以書中沒有涉及的周作人作一點提示性的探討。1945年7月,抗戰即將取得勝利之際,周作人寫了一篇題為《談胡俗》的文章,其中特別談到北京的少數民族習俗。考慮到北京歷史上曾多次成為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的都城,而在日偽政權統治下的北京,民族關系又是極為敏感的話題,周作人撰寫此文的用心頗值得玩味。他在文中提出北京的所謂“胡俗”不過是北方一地的風俗,“我們翻閱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點心有薩齊瑪是滿洲制法。此外也還多是古俗留遺,不大有什么特殊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并沒有什么,雖然有些與別處不同的生活習慣,只是風土之偶異而已”。⑤周作人:《談胡俗》,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6冊,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頁。用“風土之偶異”造成的地方性特征,來淡化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入侵所帶來的創傷體驗,消解種族對立的意味,隱隱有為自己淪陷時期的附逆辯解的用心。周作人煞費苦心的表述提醒我們,淪陷區作家的地方性書寫,是不是也隱含著化解民族認同危機的心理動機呢?在偽滿洲國和華北日偽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作家,借由地方風物的描寫,是不是也在曲折地表達某種民族意識和國家想象呢?
當然,我們不必要求作者在一本以“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為主題的著作中,充分地討論甚至解決地方性、民族形式與國家想象之間的復雜關系所包含的諸多問題。重要的是,這部既有細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又不乏深刻見地的出色論著,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地方性的概念包含著多么豐富的理論潛力,如果加以充分地開掘,將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帶來怎樣的突破。在這個意義上,說《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一書開辟了一個新的問題域亦不為過。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該書將激發更多研究者去思考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地方性問題,從而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我們對地方性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的認識。
【責任編輯 穆海亮】
季劍青,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