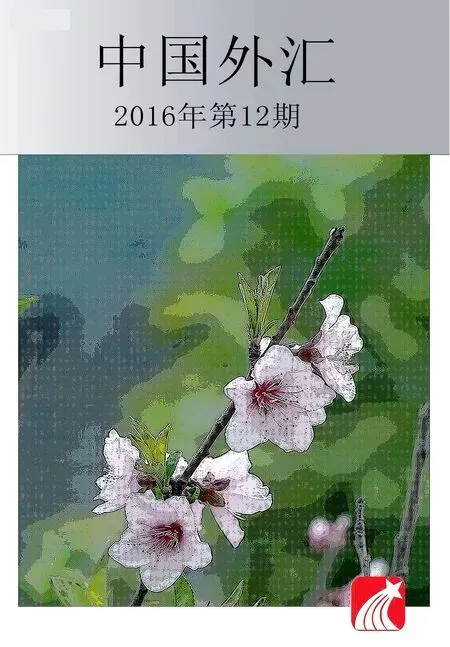有理有據(jù)應(yīng)對海運延遲
文/袁斌 溫莉 編輯/劉麗娟
有理有據(jù)應(yīng)對海運延遲
文/袁斌 溫莉 編輯/劉麗娟
國內(nèi)貨主在安排海運過程中應(yīng)積極關(guān)注船公司網(wǎng)站,并保持與船公司的溝通,詢問貨物流轉(zhuǎn)情況,及時將貨物遲延或船公司其他違約可能導(dǎo)致的后果告知船公司。這些是后續(xù)協(xié)調(diào)或索賠中的有力證據(jù)。
中國企業(yè)80%以上的出口貿(mào)易通過海運方式完成。海運實踐中,延遲交付是僅次于貨損貨差的主要風(fēng)險,也是出口企業(yè)頻繁遇到的一種情況。而一旦發(fā)生延遲交付糾紛,出口企業(yè)向船公司索賠也是一個頗為復(fù)雜的過程。在寧波出口貿(mào)易企業(yè)A(以下簡稱“A企業(yè)”或“國內(nèi)貨主”)2015年起訴馬士基公司(即船公司)延遲交付貨物導(dǎo)致其貨款損失的案例中,相關(guān)各方對貨物到港時間晚于正常運輸可能需要的時間均無異議,但對于是否構(gòu)成《海商法》第50條規(guī)定的遲延交付以及承運人可否引用《海商法》第57條享受責(zé)任限制的爭議較大。最終,綜合考慮貨物貶值原因、貨主應(yīng)承擔(dān)的減損義務(wù)及馬士基公司應(yīng)預(yù)見的延誤風(fēng)險,寧波海事法院一審判定,船公司按貨主損失金額50%的比例對貨主進行賠償。本案中A企業(yè)應(yīng)對延遲交付糾紛的經(jīng)驗,可供其他出口企業(yè)借鑒。
案情回放
2014年12月,A企業(yè)為出口一批提花布至非洲貝寧,委托貨代公司向馬士基公司訂艙。2014年12月28日貨物裝船,次日馬士基公司簽發(fā)提單。提單列明的主要信息如下:裝貨港為寧波,卸貨港為貝寧科托努港,收貨人為Oumarou Souley Dan Gara Passport,貨物價值為248872.32美元。
該批次貨物系收貨人為在當(dāng)?shù)?015年3月的銷售季節(jié)銷售而采購的,因此要求貨物必須于2015年2月到港。然而,A企業(yè)在查詢馬士基船公司網(wǎng)站后發(fā)現(xiàn),該批次貨物實際于2015年3月11日被卸至喀麥隆杜阿拉港。鑒此,A企業(yè)多次催索船公司盡快將貨物運抵目的港科托努,但直至2015年5月18日,船公司才安排該批次貨物從杜阿拉港起運。5月29日,貨物運達科托努港;6月25日,貨物清關(guān)完畢被收貨人憑正本提單提走。因貨物到港遠遠超出預(yù)定時間,收貨人先是明確拒收。后經(jīng)協(xié)調(diào),最終由A企業(yè)承擔(dān)了50%的貨款損失。就此,A企業(yè)以船公司違約導(dǎo)致其貨款損失為由,將馬士基公司訴至寧波海事法院。
馬士基公司委托律師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下稱《海商法》)關(guān)于遲延交付的規(guī)定為核心思路,提出以下抗辯理由:第一,作為貨權(quán)憑證的正本提單已流轉(zhuǎn)至收貨人,且貨物在目的港已被收貨人提走,貨主并未持有正本提單,因而沒有訴權(quán);第二,《海商法》第50條規(guī)定,構(gòu)成遲延交付須事前約定交付時間,但貨主在交付運輸當(dāng)時并未對到港時間提出明確要求;第三,即使構(gòu)成遲延交付,因享有訴權(quán)的收貨人未在提取貨物后60日內(nèi)向承運人提出主張,依據(jù)《海商法》第82條的規(guī)定,作為承運人也不承擔(dān)遲延交付損失的賠償責(zé)任,且即使承擔(dān),按《海商法》第57條規(guī)定,賠償限額也僅限貨物運費;第四,貨主無客觀證據(jù)能證明其所遭受的損失。
確定爭議焦點
寧波海事法院初始歸納爭議焦點為貨主是否有訴權(quán)、船公司是否遲延交貨、是否享受責(zé)任限制以及貨主損失是否真實、合理;但A企業(yè)的代理律師認為,上述爭議點主要適用于延遲交付類案件,但本案并非單純因海上風(fēng)險或者承運人可免責(zé)事項導(dǎo)致的遲延。
貨物遲延到港并遲延交付給收貨人確系事實,但為何不是《海商法》意義上的延遲交付?這是由于A企業(yè)與船公司在承運貨物之初并未約定到港時間,不符合《海商法》第50條規(guī)定的遲延交付要件;此外,從海商法意義上看,其對遲延交付進行責(zé)任限制的立法本意是基于海上正常航行的風(fēng)險或者其他客觀因素,而本案中導(dǎo)致延遲的原因則可能是船公司的主觀過錯。
A企業(yè)的代理律師提供了充分的證據(jù)證明,馬士基船公司在貨物運輸過程中存在以下方面的過錯疑點:一是貨主與馬士基船公司往來郵件顯示,涉案貨物在杜阿拉港停留了兩個多月之后才安排運送至目的港科托努;二是在杜阿拉港安排貨物轉(zhuǎn)運時,船公司卻要求提供貨物發(fā)票,并稱貨物需要清關(guān)才能轉(zhuǎn)運,這不符合一般運輸流程;第三,馬士基網(wǎng)站顯示,從寧波港到約定的目的港貝寧科托努港航線時間為35天,而寧波到杜阿拉港正常的船期是41天,且對比兩條航線路徑就會發(fā)現(xiàn),從寧波到杜阿拉港的航線途經(jīng)科托努港,按常理應(yīng)先行到達科托努港,但船公司卻直接將貨卸在了杜阿拉港。此外,A企業(yè)在與收貨人溝通時也強調(diào),遲延是船公司貨物運錯港口所致。
關(guān)于國內(nèi)貨主是否有訴權(quán)的問題,A企業(yè)的代理律師指出,除審查合同法律關(guān)系及是否可訴訟之外,判斷是否享有訴權(quán)的關(guān)鍵,在于確定提起主張的一方主體是否存在實質(zhì)損失且由其提訴是否會導(dǎo)致被告雙重賠償?shù)目赡堋1景笩o異議的是貨主與承運人之間成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關(guān)系,提單只是運輸合同的證明,提單流轉(zhuǎn)后國內(nèi)貨主托運人的法律身份并未喪失;遲延到港導(dǎo)致的損失經(jīng)協(xié)調(diào)最終確認由國內(nèi)貨主承擔(dān),損失承擔(dān)主體是貨主;且馬士基公司也確認,收貨人并未在法律規(guī)定期限內(nèi)就涉案同一事由向其主張權(quán)利,貨主主張索賠不會加重馬士基的法律責(zé)任,更不會導(dǎo)致其雙重賠償;更進一步,馬士基公司確認,與馬士基公司聯(lián)系的始終為貨主,在收貨人提貨之前,雙方就已對遲延會導(dǎo)致貨主損失且全部責(zé)任均需貨主承擔(dān)事宜進行過溝通,雙方糾紛提貨之前即已產(chǎn)生。由此,作為托運人的A企業(yè)當(dāng)然有權(quán)以馬士基公司違反運輸合同項下承運人的相關(guān)義務(wù)而追究其違約責(zé)任,并主張遲延交付損失。
基于上述事實,法院也注意到本案并非單純的遲延交付。本案承運人是否承擔(dān)責(zé)任的關(guān)鍵在于除遲延交付之外,承運人是否違反了《海商法》規(guī)定的義務(wù),從而需承擔(dān)責(zé)任。由此,該案的爭議焦點就變成馬士基公司是否違約。根據(jù)A企業(yè)提供的證據(jù),承運人在運輸過程中,尤其在中轉(zhuǎn)港停留兩個多月存在明顯過錯;船公司對為何在杜阿拉港卸貨及其所稱是在進行中轉(zhuǎn)自始至終未能給出任何明確合理的答復(fù)。因此,法院雖未明確認定港口卸錯,但實質(zhì)上并未排除船公司卸錯港口的可能,從而認定,本案不適用《海商法》僅支付運費款的責(zé)任限制。
損失認定是關(guān)鍵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件中,無論是貨損貨差、遲延交付還是任何違約或侵權(quán)事由,國內(nèi)貨主主張承運人賠償損失的關(guān)鍵均在于認定其主張的損失是否成立,是否合理有據(jù)。
涉案貨物是提花布產(chǎn)品,貝寧科托努屬于非洲熱帶地區(qū),季節(jié)差異不大,而且可以確定的是,布料產(chǎn)品并沒有因為遲延而導(dǎo)致實質(zhì)性的損壞。那么該批價值24萬多美元的貨物錯過當(dāng)?shù)劁N售季節(jié)后的零散銷售又會發(fā)生多大的實際損失呢?按照一般理解,布料產(chǎn)品在不同的時間銷售,有多大可能出現(xiàn)跌價以及出現(xiàn)多大程度的跌價是很難判斷的,查詢類似判例也可以發(fā)現(xiàn),大部分案件均因為損失缺乏真實合理性且無客觀依據(jù)支撐而被法院駁回。由此,本案除前述兩個法律難題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難題,就是損失該如何舉證和判斷。
還原國內(nèi)貨主與國外買方自貿(mào)易合同訂立至雙方最終協(xié)調(diào)賠付的全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貨主與船公司往來記錄中將貨物遲延交付可能導(dǎo)致的貨主損失告知的全部往來情況,可明確以下事實:其一,涉案貿(mào)易合同簽署當(dāng)時,買方即明確了提花布產(chǎn)品是為2015年3月的節(jié)日準備的,并對花色、布料提出了特殊要求,且強調(diào)必須在2月初到港才有可能趕上節(jié)日。其二,貨物于2014年12月28日報關(guān)出運之后,貨主一直跟蹤,并在2月發(fā)現(xiàn)貨物未按預(yù)定時間到港,3月發(fā)現(xiàn)貨物被卸在杜阿拉港,后貨物在杜阿拉港被安排再次出運并清關(guān)交付。其三,國外買方在此過程中多次要求務(wù)必盡快安排,否則將做棄貨處理;3月份之后,經(jīng)貨主積極協(xié)調(diào),買方要求務(wù)必在5月前到港以趕上另一個銷售季,但貨物實際到港時間為5月29日,且因遇當(dāng)局調(diào)查貨物被拉至尼日利亞,直至6月25日才清關(guān)完畢;買方為此堅決棄貨,經(jīng)協(xié)調(diào)后稱,即使提貨也僅支付其中20%的貨款,但最終同意支付50%的貨款。再查詢貝寧科托努當(dāng)?shù)毓?jié)日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月3日是開齋節(jié),5月25日是耶穌升天節(jié),此后直至8月才會有節(jié)日。一審法院由此確信,貨物銷售確有季節(jié)性,貨主主張的貨物貶值率基本合理,未明顯高出市場行情,對主張的損失事實予以確認。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屬貿(mào)易合同領(lǐng)域其中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而海上貨物運輸各環(huán)節(jié)也直接影響貿(mào)易合同的履行效果。作為貿(mào)易賣方的國內(nèi)貨主,在安排運輸過程如訂艙、貨物出運前后,應(yīng)積極關(guān)注船公司網(wǎng)站,并保持與船公司溝通,詢問貨物流轉(zhuǎn)情況(尤其是貨物存在非正常運輸可能情形時),及時將貨物遲延或者船公司其他違約可能導(dǎo)致貨主承擔(dān)的法律后果告知船公司,并催索船公司安排落實。這些,無論是對后續(xù)與船公司之間的協(xié)調(diào),還是向船公司索賠費用損失,都是有力的證據(jù)。此外,即使船公司違約,作為守約方,國內(nèi)貨主也應(yīng)當(dāng)積極履行減損義務(wù),將可能將損失降到最低,并保留損失證據(jù),如外方的索賠函、雙方的溝通聯(lián)系記錄、匯付憑證、發(fā)票等,以利于法院做出支持判決。
作者單位:北京大成(寧波)律師事務(w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