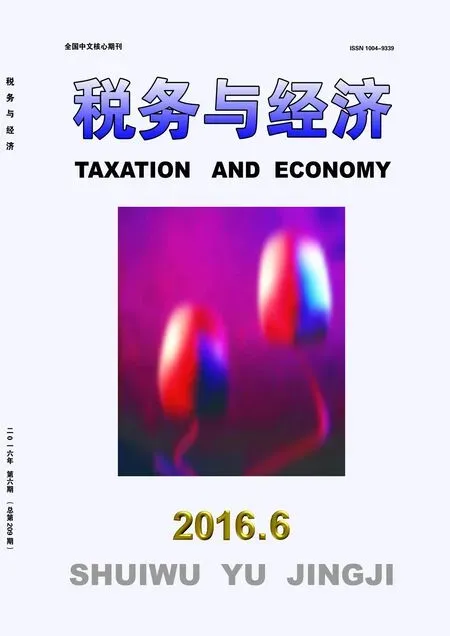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法律問(wèn)題研究
胡元聰,稅夢(mèng)嬌
(西南政法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法學(xué)院,重慶 401120)
一、娛樂(lè)業(yè)稅制及其改革的法律問(wèn)題概述
(一)娛樂(lè)業(yè)的界定及其現(xiàn)行稅制
娛樂(lè)業(yè)作為“供給側(cè)改革”的重要領(lǐng)域,是指為娛樂(lè)活動(dòng)同時(shí)提供場(chǎng)所和服務(wù)的行業(yè)。具體包括歌廳、舞廳、夜總會(huì)、酒吧、臺(tái)球、高爾夫球、保齡球、游藝(包括射擊、狩獵、跑馬、游戲機(jī)、蹦極、卡丁車、熱氣球、動(dòng)力傘、射箭、飛鏢)。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全面推開(kāi)營(yíng)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diǎn)(以下簡(jiǎn)稱“營(yíng)改增”),屬于營(yíng)業(yè)稅稅目的娛樂(lè)業(yè)也被納入改革范圍,且劃入為滿足城鄉(xiāng)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各類服務(wù)活動(dòng)的生活服務(wù)之中。根據(jù)相關(guān)規(guī)定,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應(yīng)當(dāng)繳納的稅費(fèi)包括增值稅、文化事業(yè)建設(shè)費(fèi)、城市維護(hù)建設(shè)稅、教育費(fèi)附加和企業(yè)所得稅。其中,增值稅的征收稅率為6%,教育費(fèi)附加的計(jì)征比率為3%,文化事業(yè)建設(shè)費(fèi)為營(yíng)業(yè)額的3%,以及除少數(shù)小型微利企業(yè)適用20%的稅率以外,其余娛樂(lè)企業(yè)征收25%的企業(yè)所得稅,還有不同地區(qū)分別收取7%、5%、1%的城市維護(hù)建設(shè)稅。
(二)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法治邏輯
娛樂(lè)業(yè)的稅收法治化思考緣起于“十三五”規(guī)劃建議提出的以擴(kuò)大服務(wù)消費(fèi)為重點(diǎn)帶動(dòng)消費(fèi)結(jié)構(gòu)升級(jí),健全促進(jìn)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現(xiàn)代財(cái)政制度,建立稅種科學(xué)、結(jié)構(gòu)優(yōu)化的稅收制度等邁向稅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宏偉構(gòu)想。因此,作為我國(guó)市場(chǎng)化程度最深、大眾消費(fèi)核心場(chǎng)所的娛樂(lè)業(yè),其稅制模塊設(shè)計(jì)及結(jié)構(gòu)優(yōu)化應(yīng)有現(xiàn)代化的思維和理念。由稅收公平原則演變而來(lái)并使社會(huì)公平與公眾福利相結(jié)合的量能課稅思想,其根據(jù)納稅義務(wù)人的負(fù)稅能力公平分?jǐn)偠愘x,是探尋娛樂(lè)業(yè)稅制法治改革路徑中財(cái)政民主化之公共性立場(chǎng)的表達(dá)。以?shī)蕵?lè)業(yè)納稅人的捐稅能力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為公共物品融資,是將稅收國(guó)家的財(cái)源建立在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基礎(chǔ)上的理性選擇。伴隨著“客觀負(fù)擔(dān)稅捐能力”標(biāo)準(zhǔn)理論的濫觴,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客觀給付能力可以根據(jù)該娛樂(lè)行業(yè)所具有的社會(huì)化功能加以考量,而并非僅憑借實(shí)際消費(fèi)來(lái)衡量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稅負(fù)能力。現(xiàn)代財(cái)稅法治理念下,稅收早已不再是國(guó)家通過(guò)“掠奪之手”強(qiáng)制性籌集資金的外生性機(jī)制。娛樂(lè)業(yè)稅制優(yōu)化是當(dāng)前國(guó)家在完善科學(xué)財(cái)稅體制背景下,實(shí)現(xiàn)“外生稅收機(jī)制內(nèi)生化”,“內(nèi)生功能機(jī)制公平化”,保證娛樂(lè)業(yè)稅收“扶持之手”功能發(fā)揮的必然趨勢(shì)。公共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行使應(yīng)當(dāng)以納稅人權(quán)利保護(hù)為中心,最大程度地保障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整體利益。將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限定在公平、合理范圍之內(nèi),避免因?qū)蕵?lè)業(yè)課以重稅而導(dǎo)致的稅收風(fēng)險(xiǎn),抑制國(guó)民精神生活質(zhì)量的提高。
(三)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基本定位
踐行財(cái)稅法治理念與優(yōu)化娛樂(lè)業(yè)稅制結(jié)構(gòu)功能之回歸,矯正我國(guó)現(xiàn)行不甚公平、合理的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制度,根據(jù)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稅捐負(fù)擔(dān)能力實(shí)現(xiàn)量能課稅,尤其是以各娛樂(lè)業(yè)不同的社會(huì)功能對(duì)稅賦進(jìn)行合理分?jǐn)偅M(jìn)而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改革法治化的五維定位:一是推進(jìn)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提出落實(shí)“稅收法定原則”的宏偉構(gòu)想,而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征收并未上升至法律。因此,使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改革回歸法律理性,加快完成娛樂(lè)業(yè)稅收的法律化進(jìn)程,是邁向稅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必然要求。二是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權(quán)利的保護(hù)。我國(guó)一直以來(lái)對(duì)娛樂(lè)行業(yè)采取歧視性態(tài)度,使得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稅賦重,稅收發(fā)展權(quán)、納稅救濟(jì)權(quán)難以真正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改革便是以財(cái)政民主為稅收國(guó)家的治理基礎(chǔ),探尋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權(quán)利保護(hù)的實(shí)現(xiàn)機(jī)制。三是促進(jìn)娛樂(lè)業(yè)稅捐正義。娛樂(lè)行業(yè)的重稅以及娛樂(lè)行業(yè)內(nèi)部并未再針對(duì)各行業(yè)對(duì)社會(huì)所產(chǎn)生的不同作用進(jìn)行課稅,忽視了某些大眾娛樂(lè)業(yè)對(duì)民生福利增進(jìn)的影響,難以使娛樂(lè)業(yè)稅收在稅捐正義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財(cái)稅法治。因此,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改革應(yīng)立足于建構(gòu)平等的稅收法治環(huán)境,從而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不同行業(yè)之間稅賦的公平正義。四是規(guī)范政府理財(cái)行為。我國(guó)各省級(jí)政府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稅、定稅和用稅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導(dǎo)致公共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取得缺乏正當(dāng)性基礎(chǔ)。因而從夯實(shí)稅收正當(dāng)性基石的思維出發(fā),防止國(guó)家課稅權(quán)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侵犯,制約政府的征稅權(quán)、定稅權(quán)和用稅權(quán)是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法治化改革的理性選擇。五是彰顯娛樂(lè)業(yè)的量能課稅原則。“營(yíng)改增”以前,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的稅率明顯重于同樣作為文化業(yè)部門的體育行業(yè),明顯與量能課稅原則相悖。因此,我國(guó)未來(lái)的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制度改革應(yīng)當(dāng)引入稅收扶持理念,根據(jù)各娛樂(lè)行業(yè)在社會(huì)上的不同作用公平、合理地分?jǐn)偠愘x,進(jìn)而在真正意義上實(shí)現(xiàn)量能課稅理念。
二、我國(guó)現(xiàn)行娛樂(lè)業(yè)稅制存在的問(wèn)題
(一)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問(wèn)題
1.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位階不高
“營(yíng)改增”之前,《營(yíng)業(yè)稅暫行條例》規(guī)定,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收5%~20%的營(yíng)業(yè)稅。2016年3月23日,財(cái)政部和國(guó)家稅務(wù)總局發(fā)布《關(guān)于全面推開(kāi)營(yíng)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diǎn)的通知》(以下簡(jiǎn)稱《通知》),《通知》中包含的《營(yíng)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diǎn)實(shí)施辦法》規(guī)定,我國(guó)全部營(yíng)業(yè)稅納稅人由繳納營(yíng)業(yè)稅改為繳納增值稅,并規(guī)定增值稅稅率為6%。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財(cái)政廳(局)和國(guó)家稅務(wù)局可以根據(jù)情況確定本地區(qū)適用的起征點(diǎn)。從娛樂(lè)業(yè)來(lái)看,對(duì)娛樂(lè)業(yè)縱向稅權(quán)的配置缺乏整體思路[1],并由此導(dǎo)致一系列問(wèn)題。新修訂的《立法法》第八條規(guī)定了我國(guó)稅種的設(shè)立、稅率的確定及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應(yīng)依法而定。此處的法律只能是由全國(guó)人大及其常委會(huì)制定的狹義的法律。顯然,由國(guó)務(wù)院或財(cái)稅主管部門制定的娛樂(lè)業(yè)稅收行政法規(guī)或稅收通知,以及行政主導(dǎo)式的娛樂(lè)業(yè)“營(yíng)改增”試點(diǎn)均存在合法性方面的缺陷。
2.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授權(quán)紊亂
雖然《立法法》第八條有落實(shí)“稅收法定原則”之意,但《立法法》第九條又授權(quán)國(guó)務(wù)院對(duì)于娛樂(lè)業(yè)稅收問(wèn)題可先行制定行政法規(guī)的空間。結(jié)合《稅收征管法》第三條規(guī)定,不僅稅收的開(kāi)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等稅收征管基本權(quán)可以授權(quán)國(guó)務(wù)院制定,而且關(guān)于稅率稅額調(diào)整權(quán)、稅收規(guī)章制定權(quán)、稅收法規(guī)解釋權(quán)等,國(guó)務(wù)院還可以授權(quán)其他機(jī)關(guān)、單位和個(gè)人,使得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權(quán)和稅收政策調(diào)整權(quán)存在隨意性的行政管理,由此導(dǎo)致“稅收法定原則”因稅收立法授權(quán)而沒(méi)有得到完全的落實(shí)。并且,娛樂(lè)業(yè)稅收授權(quán)立法大多屬于空白授權(quán),授權(quán)的目的、事項(xiàng)和范圍不明確,也沒(méi)有制定相應(yīng)的合憲性審查標(biāo)準(zhǔn)給予正當(dāng)性約束。此外,《立法法》規(guī)定國(guó)務(wù)院不得將該項(xiàng)權(quán)力轉(zhuǎn)授給其他機(jī)關(guān)。因此,財(cái)稅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均無(wú)權(quán)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出臺(tái)部門規(guī)章和政府規(guī)章。而我國(guó)現(xiàn)行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規(guī)范性文件中存在大量沒(méi)有“經(jīng)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的表述、甚至僭越上位階法規(guī)等嚴(yán)重違背禁止轉(zhuǎn)授權(quán)規(guī)定的情形。
(二)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負(fù)擔(dān)問(wèn)題
1.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負(fù)擔(dān)不公平
在我國(guó)當(dāng)前“清費(fèi)減稅”的大背景下,娛樂(lè)業(yè)納稅人不僅需單獨(dú)繳納區(qū)別于其他文化部門的銷售額之3%的文化事業(yè)建設(shè)費(fèi),并且還被征收重于其他文化企業(yè)的城市維護(hù)建設(shè)稅和教育費(fèi)附加,明顯違背稅收負(fù)擔(dān)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法治理念。從過(guò)去我國(guó)“營(yíng)改增”在部分行業(yè)的試點(diǎn)來(lái)看,部分行業(yè)的稅負(fù)不但沒(méi)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從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關(guān)系來(lái)看,生活性服務(wù)業(yè)提供的服務(wù)處于消費(fèi)終端,其服務(wù)費(fèi)的支付具有一次性或非連續(xù)性的特點(diǎn),無(wú)所謂上下游關(guān)系,由此增值稅的鏈條機(jī)制難以在娛樂(lè)行業(yè)中發(fā)揮其特有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優(yōu)勢(shì)。[2]此次全面“營(yíng)改增”之后,購(gòu)進(jìn)的娛樂(lè)服務(wù)不能抵扣進(jìn)項(xiàng)稅額,便難以實(shí)現(xiàn)消除重復(fù)征稅、打通增值稅抵扣鏈條等娛樂(lè)業(yè)實(shí)行“營(yíng)改增”之目的。所以,如何克服娛樂(lè)企業(yè)由于制度和自身業(yè)務(wù)等因素不減反增稅收負(fù)擔(dān)之難題,是未來(lái)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改革試點(diǎn)應(yīng)當(dāng)突破的核心問(wèn)題。
2.娛樂(lè)業(yè)稅制結(jié)構(gòu)不合理
按照量能課稅原則,給付稅捐能力相同者應(yīng)同等征稅,負(fù)擔(dān)稅捐能力不同者應(yīng)區(qū)別課稅。而我國(guó)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收稅費(fèi)一直采取“一刀切”模式,并未重視娛樂(lè)業(yè)內(nèi)部不同行業(yè)之間的量能課稅、稅負(fù)公平以及稅捐正義問(wèn)題。根據(jù)我國(guó)稅法規(guī)定,納稅的娛樂(lè)業(yè)包括經(jīng)營(yíng)音樂(lè)茶座、歌舞廳、KTV、網(wǎng)咖、電子競(jìng)技、臺(tái)球、高爾夫球、保齡球、游藝等娛樂(lè)場(chǎng)所,以及兼營(yíng)歌舞表演的餐廳、酒吧、咖啡廳等為顧客進(jìn)行娛樂(lè)活動(dòng)提供服務(wù)的行業(yè)。在上述行業(yè)中,部分行業(yè)屬于有利于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下“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wàn)眾創(chuàng)新”、拉動(dòng)消費(fèi)升級(jí)、大眾普遍消費(fèi)以及豐富民眾精神生活的娛樂(lè)項(xiàng)目,例如音樂(lè)茶座、KTV、電子競(jìng)技、臺(tái)球、保齡球、游藝等。但由于我國(guó)一直以來(lái)對(duì)娛樂(lè)業(yè)的行業(yè)性質(zhì)給予的負(fù)面定位,因而并沒(méi)有將那些隨著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變得日漸大眾化、具有普惠性的娛樂(lè)行業(yè)與高檔消費(fèi)的娛樂(lè)業(yè)進(jìn)行分行業(yè)、分類別征稅。
(三)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問(wèn)題
1.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的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問(wèn)題
“稅式支出和稅收優(yōu)惠是一枚硬幣的兩個(gè)方面,稅式支出是從政府的角度來(lái)看待稅收優(yōu)惠,稅收優(yōu)惠是從納稅人角度來(lái)看稅式支出”。[3]我國(guó)在優(yōu)化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制度的改革中,如果將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的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下放至地方政府,那么要保障“稅收法定原則”貫穿至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行使的全過(guò)程,就不僅需要在結(jié)構(gòu)上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的利益平衡性,還需要通過(guò)總量控制進(jìn)而排除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確認(rèn)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行使的隨意性,這是重塑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的關(guān)鍵。從以往稅式支出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的濫用情況來(lái)看,我國(guó)缺乏落實(shí)稅式支出法治化的規(guī)范措施是其重要根源。一些地方政府以規(guī)范性文件的形式擅自設(shè)定稅收優(yōu)惠,使得諸多脫法的稅收優(yōu)惠得以存在。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財(cái)稅部門規(guī)避中央稅收減免的禁止性規(guī)定,通過(guò)先征后返等方式變相減稅、免稅,形成稅收優(yōu)惠的惡性競(jìng)爭(zhēng)態(tài)勢(shì)。[4]由于沒(méi)有將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納入預(yù)算中進(jìn)行預(yù)算審查和財(cái)政監(jiān)管,政府也不用為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的濫用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由此導(dǎo)致的財(cái)政越位、錯(cuò)位現(xiàn)象非常普遍。
2.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稅收優(yōu)惠權(quán)問(wèn)題
由于稅收優(yōu)惠也具有公共需求的公益性和非排他性[5],因而國(guó)家應(yīng)將此種制度性的公共產(chǎn)品公平分配至納稅義務(wù)人。稅收優(yōu)惠權(quán)則是每一個(gè)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應(yīng)有的正當(dāng)性稅收權(quán)利。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視野下,一些有利于大眾共享和刺激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新興娛樂(lè)產(chǎn)業(yè)不斷涌現(xiàn),例如,電子競(jìng)技、游藝、音樂(lè)茶座等。但這些帶有普惠性、具有創(chuàng)意特性的娛樂(lè)產(chǎn)業(yè)在我國(guó)并沒(méi)享有企業(yè)所得稅、增值稅等稅種的稅收優(yōu)惠,只有極少數(shù)小型微利企業(yè)享有稅收優(yōu)惠,適用20%的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從而使不同娛樂(lè)企業(yè)納稅人之間稅收負(fù)擔(dān)極不平衡,背離了“量能課稅原則”。在《稅收征收管理法》中,納稅人權(quán)利包括了依法申請(qǐng)稅收優(yōu)惠權(quán)。同時(shí),納稅人稅收優(yōu)惠權(quán)也是憲法意義上納稅人的一項(xiàng)基本權(quán)利。因此,在保證娛樂(lè)業(yè)納稅人公平分?jǐn)偠愘x的基礎(chǔ)上,也應(yīng)當(dāng)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的公平性,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稅捐正義基礎(chǔ)上的量能課稅。而我國(guó)的稅收優(yōu)惠沒(méi)有惠及有利于擴(kuò)大服務(wù)消費(fèi)、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新興文化娛樂(lè)產(chǎn)業(yè),不利于國(guó)家提出的推動(dòng)社會(huì)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以及建設(shè)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宏偉構(gòu)想。
三、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法治化要求及進(jìn)路
(一)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法治化要求
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必須堅(jiān)持稅收法定、量能課稅原則,踐行財(cái)稅法治理念,進(jìn)而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遵循從“有法”到“良法”、再到“善治”的國(guó)家稅收法治化行使方向。
1.稅收法定原則下的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
國(guó)家在規(guī)定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法定化租稅之義務(wù)以及賦予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產(chǎn)業(yè)性租稅之優(yōu)惠中,納稅主體、征稅主體、征稅客體、稅目、稅基及其稅率等征稅實(shí)體要件,以及稅務(wù)稽征中的程序要件都必須由最高立法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律進(jìn)行規(guī)范。即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娛樂(lè)業(yè)稅收負(fù)擔(dān)、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事項(xiàng)只能以法律定之。在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方面,落實(shí)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原則,規(guī)范娛樂(lè)業(yè)稅收授權(quán)立法,厘清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權(quán)的配置和歸屬,理順立法機(jī)關(guān)和行政機(jī)關(guān)的關(guān)系。[6]在娛樂(lè)業(yè)稅收負(fù)擔(dān)法定方面,應(yīng)當(dāng)契合國(guó)家“清費(fèi)減稅”的稅收法治化理念,凈化娛樂(lè)業(yè)濫收費(fèi)環(huán)境,通過(guò)促進(jìn)“稅收法定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的有機(jī)融合,消除歧視性的稅費(fèi)制度對(duì)娛樂(lè)行業(yè)持續(xù)發(fā)展所帶來(lái)的嚴(yán)重弊端。從過(guò)去我國(guó)實(shí)施稅收優(yōu)惠政策的效果來(lái)看,稅收優(yōu)惠機(jī)制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娛樂(lè)業(yè)稅費(fèi)制度改革只有設(shè)計(jì)遵循“稅收法定原則”的稅收優(yōu)惠機(jī)制,才能達(dá)到立法者制定優(yōu)惠政策背后的利益安排,矯正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機(jī)制的負(fù)外部性,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權(quán)衡基礎(chǔ)上的量能課稅原則。
2.量能課稅原則下的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
當(dāng)前我國(guó)優(yōu)化稅制結(jié)構(gòu)應(yīng)當(dāng)重視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降低流轉(zhuǎn)稅比重,推進(jìn)減少經(jīng)濟(jì)不平等的累進(jìn)稅制,真正彰顯“量能課稅原則”。[7]在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方面, 以“量能課稅原則”作為娛樂(lè)業(yè)稅收規(guī)范之核心取向,并受財(cái)政憲法拘束(主要指中央、地方權(quán)限劃分),及以財(cái)產(chǎn)保障為主的自由與平等基本權(quán),并受法治國(guó)家之要求,與社會(huì)國(guó)之社會(huì)形成任務(wù)[8];在娛樂(lè)業(yè)稅收負(fù)擔(dān)方面,以財(cái)政收入為目標(biāo),應(yīng)符合“量能課稅原則”,每個(gè)人按其負(fù)擔(dān)能力平等分擔(dān)公共財(cái)政需求[9];在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方面,租稅優(yōu)惠雖屬于“量能課稅原則”之例外,但如果是基于財(cái)政政策、國(guó)民經(jīng)濟(jì)政策、社會(huì)政策等公共利益的理由或稽征技術(shù)上的考量,則仍然不違背實(shí)質(zhì)平等原則。[10]然而,國(guó)家很難準(zhǔn)確判斷每一個(gè)納稅人的稅捐負(fù)擔(dān)能力,單純以該娛樂(lè)業(yè)的銷售額或其納稅人的經(jīng)濟(jì)支付能力作為衡量娛樂(lè)業(yè)納稅人負(fù)稅能力的指標(biāo),已經(jīng)不能適應(yīng)國(guó)家稅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以各娛樂(lè)行業(yè)之“社會(huì)化功能”作為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收“量能”征收的法治化思維考量。
(二)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法治化進(jìn)路
1.完善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機(jī)制
(1)落實(shí)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原則。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改革法定化路徑應(yīng)從三個(gè)維度出發(fā),即稅收立法、稅權(quán)配置和分成比例。第一,落實(shí)娛樂(lè)業(yè)征稅法定。我國(guó)當(dāng)前稅收領(lǐng)域僅有四部稅收法律,分別為《企業(yè)所得稅法》、《個(gè)人所得稅法》、《車船稅法》以及《稅收征管法》,其余均是由行政機(jī)關(guān)制定的稅收規(guī)范性文件。其中,增值稅作為最有利于減輕稅負(fù)和我國(guó)目前最大的稅種,僅由國(guó)務(wù)院以暫行條例來(lái)規(guī)定,與我國(guó)全面落實(shí)“稅收法定原則”之宏偉構(gòu)想相悖。因此,娛樂(lè)業(yè)等行業(yè)“營(yíng)改增”試點(diǎn)全面推開(kāi)后,應(yīng)當(dāng)盡快由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及其常務(wù)委員會(huì)啟動(dòng)增值稅立法,通過(guò)稅收立法鞏固娛樂(lè)業(yè)稅收改革成果。第二,明晰中央與省級(jí)政府的稅權(quán)配置事項(xiàng)。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收增值稅、消費(fèi)稅、企業(yè)所得稅均屬于與企業(yè)、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密切相關(guān)、稅基易轉(zhuǎn)嫁、具有再分配性質(zhì)的中央稅收或共享稅收,而不屬于區(qū)域性的地方稅種。因此,娛樂(lè)業(yè)稅收基本制度也應(yīng)當(dāng)專屬于最高立法機(jī)關(guān)立法和解釋,不適宜將稅權(quán)下放至地方,建議以此解決娛樂(lè)業(yè)稅收存在的合法性缺陷,理順中央和地方的娛樂(lè)業(yè)稅權(quán)關(guān)系。第三,調(diào)整娛樂(lè)業(yè)增值稅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改革的重要問(wèn)題之一便是娛樂(lè)業(yè)增值稅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目前我國(guó)增值稅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配,建議未來(lái)增值稅中央與地方收入實(shí)行五五分成,以保障改革后中央和地方的財(cái)力格局總體穩(wěn)定。
(2)規(guī)范娛樂(lè)業(yè)稅收授權(quán)立法機(jī)制。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應(yīng)體現(xiàn)規(guī)范公共財(cái)產(chǎn)權(quán)和稅收立法法律化的法治精神,以完全規(guī)范的娛樂(lè)業(yè)稅收“人大立法”取代當(dāng)前混亂的娛樂(lè)業(yè)稅收“授權(quán)立法”。[11]筆者建議:第一,應(yīng)當(dāng)加快收回全國(guó)人大稅收立法權(quán),娛樂(lè)業(yè)稅收基本制度不得授權(quán)立法。逐步修改《立法法》和《稅收征管法》對(duì)稅收基本制度以及稅收征管制度允許授權(quán)國(guó)務(wù)院之規(guī)定,完整地落實(shí)稅收法定原則的法治化要求。第二,禁止中央進(jìn)行新的稅收政策調(diào)整權(quán)授權(quán)。《關(guān)于全面推開(kāi)營(yíng)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diǎn)的通知》(財(cái)稅〔2016〕36號(hào))是經(jīng)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授權(quán)財(cái)政部和國(guó)家稅務(wù)總局制定頒布的。在某種程度上,“營(yíng)改增”試點(diǎn)違背了“國(guó)務(wù)院不得轉(zhuǎn)授權(quán)”之規(guī)定。根據(jù)私人財(cái)產(chǎn)課稅法治化的要求,納稅人將財(cái)產(chǎn)讓渡給國(guó)家是為了實(shí)現(xiàn)自身的權(quán)利保障及生存發(fā)展。而國(guó)家對(duì)納稅人應(yīng)當(dāng)提供的最基本的保護(hù)便是依據(jù)經(jīng)過(guò)人民同意、具備合法性要件的法律進(jìn)行課稅。未來(lái)應(yīng)當(dāng)保障“營(yíng)改增”試點(diǎn)主體法定,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試點(diǎn)權(quán)只能由最高立法機(jī)關(guān)行使,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稅制改革的社會(huì)可接受性。第三,提高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的實(shí)質(zhì)正當(dāng)性。由于納稅人權(quán)利保護(hù)是娛樂(lè)業(yè)稅收授權(quán)立法回歸全國(guó)人大的核心意旨。所以,應(yīng)當(dāng)將“量能課稅原則”貫穿至娛樂(lè)業(yè)稅收實(shí)體法和稅收程序法之中,在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捐稅能力與娛樂(lè)業(yè)稅收立法之間尋求平衡與協(xié)調(diào),營(yíng)造公平的娛樂(lè)業(yè)稅收法治環(huán)境。
2.完善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負(fù)擔(dān)機(jī)制
(1)保障娛樂(lè)業(yè)稅負(fù)公平。通過(guò)促進(jìn)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與量能課稅的有機(jī)融合,憑借契合稅捐正義的娛樂(lè)業(yè)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安排,從而祛除娛樂(lè)業(yè)歧視性的稅費(fèi)負(fù)擔(dān)對(duì)娛樂(lè)行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所滋生的抑制性因素。筆者建議:第一,完善娛樂(lè)業(yè)稅負(fù)調(diào)整機(jī)制。國(guó)家通過(guò)推動(dòng)有利于娛樂(lè)業(yè)結(jié)構(gòu)性減稅政策、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增值稅起征點(diǎn)等措施以減輕娛樂(lè)業(yè)納稅人負(fù)擔(dān)。此外,降低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繳納的城市維護(hù)建設(shè)稅和教育費(fèi)附加的稅費(fèi)率,限制娛樂(lè)業(yè)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產(chǎn)業(yè)且并未具備稅捐實(shí)質(zhì)正當(dāng)性差異事由的歧視性稅制,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實(shí)質(zhì)平等和量能課稅價(jià)值理性之回歸。第二,清理娛樂(lè)業(yè)行政收費(fèi)。促進(jìn)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負(fù)擔(dān)公平,需要合理控制娛樂(lè)業(yè)稅收規(guī)模,凈化娛樂(lè)業(yè)的收費(fèi)環(huán)境,取消在生活服務(wù)業(yè)中單獨(dú)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收的文化事業(yè)建設(shè)費(fèi),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清費(fèi)減稅”之構(gòu)想,全面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設(shè)計(jì)在我國(guó)“營(yíng)改增”背景下與財(cái)稅法治功能建構(gòu)的無(wú)縫對(duì)接。第三,建構(gòu)規(guī)范的娛樂(lè)業(yè)消費(fèi)型增值稅制度。消費(fèi)型增值稅作為最有利于保持稅收中性的增值稅類型,其對(duì)稅前扣除更合理,能有效解決對(duì)娛樂(lè)業(yè)征收增值稅抵扣項(xiàng)目不完整的問(wèn)題。實(shí)現(xiàn)對(duì)娛樂(lè)業(yè)由征收營(yíng)業(yè)稅改征增值稅的目的,徹底解決娛樂(lè)業(yè)的重復(fù)課稅問(wèn)題,保障“營(yíng)改增”之后,娛樂(lè)業(yè)稅負(fù)只減不增。
(2)優(yōu)化娛樂(lè)業(yè)稅制結(jié)構(gòu)。筆者建議:第一,構(gòu)建促進(jìn)實(shí)質(zhì)公平的大眾娛樂(lè)業(yè)稅收與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以各娛樂(lè)行業(yè)之“社會(huì)化功能”作為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收“量能”征收的法治化思維考量,按照各娛樂(lè)業(yè)差異化的社會(huì)功能將娛樂(lè)業(yè)稅收劃分為大眾娛樂(lè)業(yè)稅收和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12]大眾娛樂(lè)業(yè)稅收是以大眾共享的功能定位為主,豐富公眾精神生活的娛樂(lè)行業(yè)的稅收。例如射擊、狩獵、跑馬、游戲機(jī)、蹦極、卡丁車、熱氣球、動(dòng)力傘、射箭、飛鏢等娛樂(lè)項(xiàng)目的稅收。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則是為滿足少數(shù)自身納稅能力強(qiáng)的課稅對(duì)象的消費(fèi)需求所產(chǎn)生的娛樂(lè)行業(yè)的稅收。例如高爾夫球、高檔會(huì)所、私人游艇等為富人娛樂(lè)活動(dòng)提供服務(wù)的高消費(fèi)娛樂(lè)項(xiàng)目的稅收。通過(guò)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收進(jìn)行內(nèi)部行業(yè)細(xì)化,在分業(yè)課稅的基礎(chǔ)上以“量能課稅”打造激發(fā)娛樂(lè)企業(yè)活力的公平稅收平臺(tái)。第二,將高檔消費(fèi)的奢侈娛樂(lè)業(yè)納入消費(fèi)稅征稅范圍。大眾娛樂(lè)業(yè)適用與一般生活服務(wù)業(yè)相同的稅制,在“營(yíng)改增”背景下仍然繳納6%的增值稅,而對(duì)并非滿足城鄉(xiāng)居民一般生活需求的奢侈娛樂(lè)業(yè)則可單獨(dú)征收消費(fèi)稅。同時(shí),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制度的建構(gòu)應(yīng)當(dāng)遵循“漸進(jìn)式稅制改革”的法治化路徑,將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的征稅范圍框定在少數(shù)具有必要合理性的娛樂(lè)項(xiàng)目之內(nèi)。對(duì)大眾娛樂(lè)業(yè)與奢侈娛樂(lè)業(yè)稅收進(jìn)行合理的區(qū)別對(duì)待,不但不違背起點(diǎn)公平、實(shí)質(zhì)平等的稅收法治理念,反而有利于發(fā)揮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與娛樂(lè)業(yè)量能課稅之間關(guān)聯(lián)耦合特性的功能。
3.完善我國(guó)娛樂(lè)業(yè)稅收的優(yōu)惠機(jī)制
(1)完善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的規(guī)范管理機(jī)制。筆者建議:第一,保障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的法律化。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法律化是為落實(shí)娛樂(lè)業(yè)稅收法定之立法意旨,使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導(dǎo)入公共預(yù)算框架之中[13],將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行業(yè)、優(yōu)惠環(huán)節(jié)等事項(xiàng)的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交由最高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行使。即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應(yīng)當(dāng)以公益原則作為正當(dāng)性依據(jù),且必須由法律定之,以強(qiáng)化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政策的規(guī)范管理。雖然基于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法定化的考量,不賦予地方娛樂(lè)業(yè)稅收減免權(quán)限,但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財(cái)政返還”等方式補(bǔ)貼新興娛樂(lè)企業(yè)。第二,完善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效益評(píng)估機(jī)制。根據(jù)娛樂(lè)業(yè)不同行業(yè)的性質(zhì)及作用,對(duì)各娛樂(lè)行業(yè)稅式支出進(jìn)行成本效益分析,并且通過(guò)對(duì)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評(píng)估程序的正當(dāng)性約束,使娛樂(lè)業(yè)的稅收優(yōu)惠兼顧公平正義與比例原則,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制度的設(shè)計(jì)遵循合法性與合理性原則,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制度形式公平與實(shí)質(zhì)公平的統(tǒng)一。第三,完善娛樂(lè)業(yè)稅式支出的監(jiān)督機(jī)制。通過(guò)將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列入預(yù)算,并按照預(yù)算支出的要求進(jìn)行監(jiān)督。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以便于公眾全面監(jiān)督的方式將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決策公開(kāi)。強(qiáng)化財(cái)政部門濫用稅式支出的確定權(quán)和調(diào)整權(quán)的法律責(zé)任,從而構(gòu)建覆蓋娛樂(lè)業(yè)財(cái)政收入、支出、監(jiān)管的綠色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制度。
(2)完善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的稅收優(yōu)惠權(quán)保障機(jī)制。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稅收優(yōu)惠權(quán)的保障機(jī)制設(shè)計(jì),一方面要有基于量能課稅產(chǎn)生的合理稅負(fù)差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各娛樂(lè)行業(yè)稅負(fù)逆向運(yùn)行可能帶來(lái)的負(fù)外部性。筆者建議:第一,調(diào)整娛樂(lè)業(yè)納稅人所負(fù)擔(dān)的增值稅、企業(yè)所得稅等稅種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可以對(duì)電子競(jìng)技、游藝、音樂(lè)茶座等大眾娛樂(lè)業(yè)適用20%的企業(yè)所得稅優(yōu)惠稅率,并通過(guò)免稅額、扣除額、稅額扣抵、免稅項(xiàng)目等實(shí)現(xiàn)稅捐正義的減免方式,保障娛樂(lè)業(yè)納稅人享受平等的稅收優(yōu)惠權(quán)。第二,完善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政策的適用目錄。可以向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方向引導(dǎo),使一些附加值高的娛樂(lè)產(chǎn)業(yè)在總產(chǎn)值中占更大比重,增強(qiáng)稅收優(yōu)惠的產(chǎn)業(yè)導(dǎo)向作用,從而促進(jìn)娛樂(lè)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以及文化娛樂(lè)業(yè)和戰(zhàn)略性新興娛樂(l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扶持和促進(jìn)小微娛樂(lè)企業(yè)發(fā)展。第三,完善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實(shí)施程序機(jī)制。建立保障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實(shí)施程序化的協(xié)調(diào)運(yùn)作機(jī)制、檢查機(jī)制和備案機(jī)制,通過(guò)財(cái)稅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有效銜接和合力管理,從而遏制政府職能部門之間出現(xiàn)彼此推諉、扯皮現(xiàn)象。還應(yīng)當(dāng)健全高效率的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審批機(jī)制,避免復(fù)雜的優(yōu)惠審批環(huán)節(jié),降低娛樂(lè)企業(yè)稅捐優(yōu)惠的獲取難度及遵從成本,從而提升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的執(zhí)行效率,既避免造成娛樂(lè)業(yè)稅收的扭曲,促進(jìn)娛樂(lè)業(yè)稅收優(yōu)惠扶持功能有效發(fā)揮,也有利于實(shí)現(xiàn)娛樂(lè)業(yè)納稅人稅收優(yōu)惠權(quán)利的保障。
[1]馬海濤,李升.縱向稅權(quán)配置的改革建議及評(píng)估:基于現(xiàn)狀的思考[J].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6):21.
[2]龐鳳喜,凌瑜明.中國(guó)服務(wù)業(yè)“營(yíng)改增”理論效應(yīng)分析與制度設(shè)計(jì)[J].稅務(wù)與經(jīng)濟(jì),2015,(3):72.
[3]李旭鴻.稅式支出制度的法律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6.
[4]熊偉.法治視野下清理規(guī)范稅收優(yōu)惠政策研究[J].中國(guó)法學(xué),2014,(6):163.
[5]張富強(qiáng).論稅收國(guó)家的基礎(chǔ)[J].中國(guó)法學(xué),2016,(2):171.
[6]劉劍文.落實(shí)稅收法定原則的現(xiàn)實(shí)路徑[J].政法論壇,2015,(3):21.
[7]許多奇.論稅法量能平等負(fù)擔(dān)原則[J].中國(guó)法學(xué),2013,(5):67-75.
[8]葛克昌.稅捐實(shí)質(zhì)正當(dāng)性與違憲審查[J].月旦法學(xué)雜志,2014,(3):195.
[9]Birk, Das Leistungsfahigkeitsprinzip als Mabstab der Steuernormen, 1983, S.167; P. Kirchhof, Die deistungstatigkeit, StuW, 2011, 365.
[10]陳清秀:量能課稅與實(shí)質(zhì)課稅原則:上[J].月旦法學(xué)雜志,2010,(8):89.
[11]劉劍文,王樺宇.公共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概念及其法治邏輯[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14,(8):145.
[12]劉劍文.“大消費(fèi)·娛樂(lè)業(yè)·優(yōu)化稅制”研討會(huì)綜述(2016年1月10日)[EB/OL]. http://www.cftl.cn/ArticleInfo.aspx?Aid=48813&LevelId=002003001.
[13]王霞.稅收優(yōu)惠法律制度研究:以法律的規(guī)范性及正當(dāng)性為視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