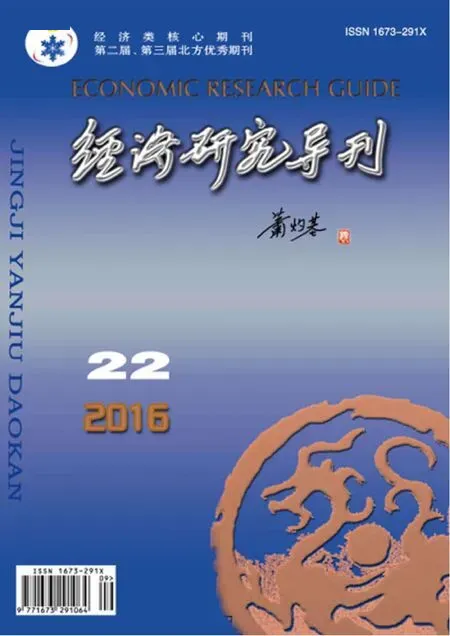勞動異化邏輯的解構與科學唯物史觀的建構
——馬克思《評李斯特》中的唯物史觀考析
王媛媛
(福建社會科學院,福州 350001)
勞動異化邏輯的解構與科學唯物史觀的建構
——馬克思《評李斯特》中的唯物史觀考析
王媛媛
(福建社會科學院,福州 350001)
《評李斯特》寫于1845年3月,恰逢馬克思舊唯物主義觀念的解構和科學唯物史觀逐步建構的時期,內容上批判了李斯特國民經濟學的理論部分,主要是生產力理論等。更重要的,它還體現了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延續和蛻變,一方面,馬克思批判德國式的唯心主義,揭示德國資產者以唯心主義的方式粉飾其追求財富的本質,還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在對新舊唯物觀的解構和建構方面,馬克思此時并未完全擺脫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勞動異化邏輯,但其中也包含了關于歷史的、實踐的唯物主義觀念的萌芽,是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異化勞動;唯物史觀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19世紀40年代不僅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時期,更重要的,它還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形成時期。在這一時期,馬克思先后創作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年夏天)、《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末至1844年1月)、《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5—8月)、《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4月)以及《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年11月至1846年5月)等重要著作和文本。正是這幾個著作文本奠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觀點,其中《德意志意識形態》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標志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科學體系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845年3月,馬克思創作了《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簡稱《評李斯特》)一文,它雖然是以批判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為目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其唯物史觀的萌芽,多少呈現了馬克思舊唯物主義觀念的解構和科學唯物史觀的建構軌跡,成為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目前,國內對馬克思《評李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馬克思對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批判(杜寶寬,2009;李淑梅,2010;周海飛,2014),以及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對馬克思本身的生產力理論及唯物史觀產生的影響上(馮景源,1984;崔永和,1994;吳學琴,1998;張雪魁,2005;郭杰忠,2005;姜海波,2007,2010;王峰明,2009;史小寧、常娟娟,2011;趙華靈,2012;楊喬喻,2013)。也有學者對馬克思與李斯特有關貿易自由與保護關稅觀點的異同展開討論(黃瑾,2011)。還有學者采用文本研究方法對《評李斯特》進行解構(馮景源,1984;張一兵,1995;胡大平,2005)。
本文試圖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對馬克思《評李斯特》中的唯物史觀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并通過與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的主要文本著作的比較研究,揭示馬克思舊唯物主義觀念的解構和科學唯物史觀的建構軌跡,以及《評李斯特》一文在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二、《評李斯特》的寫作背景及文本情況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時代的德國相較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一個封建農奴制國家,地主掌握國家政權,德國各邦及其內部各個省區都存在地方稅率,大大妨礙了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全國市場的形成。為消除國內的關稅壁壘,李斯特等人在1819年建立了德國工商協會,1934年成立了德國關稅同盟。作為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李斯特除了與國內的封建主義做斗爭外,還面臨著保護德國新興的產業資本利益,他主張用國家的力量來保護國內的生產力量,擺脫來自英法等相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競爭威脅。1841年李斯特發表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一卷——國際貿易、貿易政策和德國的關稅同盟》一書,立即在德國引起巨大反響,“儼然成了追求財富、渴望統治的年輕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宣言書,成了在政治經濟上推動德國的‘福利、文化和力量’的良方。”[1]
1844年11月,從哲學走向經濟學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剛剛完成批判鮑威爾兄弟的《神圣家族》,不約而同地想到要批判離現實更近的李斯特[2]。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德國資產階級……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壞,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氣十足、不那么徹底、不那么巧妙罷了……只要一有時間,我就寫幾本小冊子,特別是反對李斯特的小冊子。”[3]1845年2月15日,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批判李斯特把德國資本家對保護關稅的渴望變成了體系。1845年3月17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他從皮特曼那里及時知道馬克思也有批判李斯特的想法,“……我是想從實際方面對付李斯特,闡明他的體系的實際結論……你批判他的理論前提會比批判他的結論更著重一些。”[3]1845年3月,馬克思寫了《評李斯特》一文,正如恩格斯所言,馬克思主要批判了李斯特的“理論前提”。
馬克思《評李斯特》一文并沒有付印,現存的手稿是不完整的(這篇評論李斯特的草稿是在馬克思的長女燕妮·龍格的孫子長期保存的馬克思遺稿中發現的)。手稿一共24印張,缺少其中的第1印張、第10—21印張以及第23印張。文本內容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李斯特的一般綜述”(由于手稿第1頁遺失,第一部分的標題是前蘇聯編譯學者加的),共有4節。第1節和第2節的開始部分遺失,第3節和第4節相對完整;第二部分標題是“生產力理論和交換價值理論”,但后面部分因為手稿遺失,內容并不完全;第三部分標題是“論地租問題”(由于手稿第10-21頁遺失,第三部分的標題也是前蘇聯編譯學者加的),因前面大部分遺失,內容大致剩下一個片段;第四部分標題是“李斯特先生和費里埃”,內容相對完整。
三、解構與建構: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形成的解析
馬克思《評李斯特》寫于其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思想蛻變和升華時期,前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等重要著作,后有《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里程碑式的著作。根據張一兵[4]的觀點,馬克思在1843年完成其第一次重大思想轉變,即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實現從唯心主義到一般唯物主義的轉變。在其后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肯定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并以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勞動異化邏輯來重新詮釋黑格爾。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繼續通過肯定費爾巴哈來批判黑格爾,但其中已經含有超越費爾巴哈形而上學、直觀的唯物主義的觀點。1845年4月,馬克思寫作了“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批判了費哈巴哈抽象的、脫離實踐的人本主義世界觀,標志著馬克思第二次思想轉變,即由人本主義勞動異化邏輯向科學的唯物史觀的轉變,《德意志意識形態》則標志著這一轉變的基本完成。《評李斯特》介于馬克思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轉變之間,也即處于人本主義勞動異化觀的解構和科學的唯物史觀的建構時期,其中必然存在著“承前”和“啟后”的觀點。
(一)對唯心主義的徹底批判
對唯心主義的批判是馬克思建立科學的哲學體系的第一個重要任務。《評李斯特》中,馬克思繼續批判德國式的唯心主義。文中第一部分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妨礙德國資產者追求工業財富的一個巨大障礙,是他迄今為止信守的唯心主義。”[1]接著,馬克思批判了李斯特等德國“庸人”以唯心主義的方式粉飾其追求財富的目的。他說,德國資產者“以真正德國人的矯揉造作的方式、以唯心主義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來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財富而又否認財富,他把無精神的唯物主義裝扮成完全唯心主義的東西,然后才敢去獵取它”[1]。進而在批評李斯特想要證明的原理和要達到的目的時論述:“工業資產者不得不表明,他們絕不是追求物質財富,他們所想的無非是為了精神本質而犧牲交換價值,犧牲物質財富。因此,說到底,問題只在于自我犧牲,在于禁欲主義,在于基督教的崇高靈魂。”[1]
在評論李斯特批判世界主義的國民經濟學時,他說:“李斯特先生大概永遠也不會想到,現實的社會組織是無精神的唯物主義……他永遠也想不到,國民經濟學家只是給這一社會制度提供相應的理論表現。否則他就應該把矛頭指向現在的社會組織,而不是指向國民經濟學家……他從未批判過現實社會。他作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對這個社會的理論表現進行批判,指責說它所表現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幻象。”[1]這里我們應該注意,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等“真正的德國人”時說“他從未批判過現實社會”,這里表明馬克思不僅僅局限于批判唯心主義,也在批判一切脫離現實社會的實踐的理論。
另外在第二部分,即生產力理論和交換價值理論部分,馬克思還批判李斯特將生產力本質看成是唯心主義的。他批評說:“……力量的感覺世界便代替了交換價值的物質世界……力量則表現為獨立的精神本質——幽靈,表現為純粹的人格化,即上帝,人們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國人為幽靈犧牲惡的交換價值!”[1]
(二)對異化勞動邏輯的遵守與剝離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異化勞動的概念,具體分析了產品的異化、生產活動的異化、類本質的異化以及人與人的異化,并認為異化勞動的概念可以“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在《評李斯特》第二部分里,馬克思繼續將人(工人)的活動(勞動)視為“異化”的勞動,“借助于工資可以確定,他的活動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現,而毋寧說是把他的力量售賣給資本,把他的片面發展的能力讓渡給資本……談論自由的、人的、社會的勞動,談論沒有私有財產的勞動,是一種最大的誤解。‘勞動’按其本質來說,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會的、被私有財產所決定的并且創造私有財產的活動。”[1]但此時,馬克思并沒有在語境上對“異化勞動”大書特書。馬克思此時沒有用“異化勞動”,而是用打著雙引號并且加注了著重號的“勞動”,馬克思硬是“剝去了‘異化’‘類本質’這樣的語言外殼”,雖然沒有造成人本主義邏輯的解構,但是“一種新的方法無意識地被呈現了”[2]。此后,馬克思有意識地去除語境中的“異化”“類”等,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論述共產主義消滅分工時說:“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后才會消滅。”[5]他這里用加了引號的“異化”,以及括號中的解釋——“用哲學家易懂的話”,說明馬克思此時已有意識地放棄了“異化”這個“語言外殼”。
在《評李斯特》中,馬克思總體上尚未完全擺脫費爾巴哈勞動異化的思想。他從人本主義角度出發,批判資產階級不是為了人的發展,而實際上是否定人的。“……人同馬、蒸汽、水全都充當‘力量’的角色,這難道是對人的高度贊揚嗎?在現代制度下,如果彎腰駝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發展和加強等,使你更有生存能力,那么……這就是一種生產力……”[1]“難道資產者、工廠主關心工人發展他們的一切才能,發揮他們的生產能力,使他們像人一樣從事活動而同時發展人的本性嗎?”[1]“把人貶低為一種創造財富的‘力量’,這就是對人的絕妙贊揚!資產者把無產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創造財富的力量。資產者還可以把這種力量同其他的生產力——牲畜、機器——進行比較。”[1]這都說明此時馬克思還是從人本主義角度、從人的發展的角度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對人本性的踐踏和否定。
另外,馬克思還從人的發展的角度看待工業的發展,認為當前作為資產階級牟利工具的工業最終將滅亡。他說:“對工業的這種評估同時也就是承認廢除工業的時刻已經到了,或者說消除人類不得不作為奴隸來發展自己能力的那種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時刻已經到了,因為一旦人們不再把工業看作買賣利益而是看作人的發展,就會把人而不是把買賣利益當作原則,并向工業中只有同工業本身相矛盾才能發展的東西提供與該發展的東西相適應的基礎。”[1]
(三)科學唯物史觀建構的萌芽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經包含有超越費爾巴哈機械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觀點。例如,他在評論對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批判時指出,它們“并不是什么在人類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所進行的真正的人類活動……這里面不僅體現著他們的思維,并且更主要是體現著它們的實踐活動”[6]。在這里他不僅僅局限于談抽象的人和實踐,而是作為人類的體現實踐活動的人。在批判埃德加爾的哲學觀時說:“因為哲學過去并沒有真正獨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對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決,未能對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鑒別力,……未能實際地干預事物的進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滿足于抽象形式的實踐。”[6]
在《評李斯特》中,馬克思批判李斯特這類德國“庸人”“暴露出他的‘民族’特點”:一方面,“認為整個經濟學不外是研究室中編造出來的體系。”[1]另一方面,認為李斯特不去研究現實的歷史,而是“探求個人的秘密的惡的目的”[1]。他認為,經濟學的發展“是同社會的現實運動聯系在一起的”[1]。國民經濟學的實際出發點就是:“‘市民社會’,而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以探討。”[1]這里,馬克思一方面批判脫離現實社會的德國的經濟學理論;另一方面,馬克思沒有將“市民社會”看作是一個僵化不變的固有形式,而是從歷史的、發展的、實踐的角度看待“市民社會”及其“各個不同發展階段”,這里折射出馬克思已經用歷史的唯物主義觀念看待和剖析現實社會。
另外在分析工業的發展時,馬克思撇開“骯臟的買賣利益的觀點”,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工業的發展,認為:“工業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對象化,為自己創造人的生活的條件。如果這樣看待工業,那就撇開了當前工業從事活動的、工業作為工業所處的環境,那就不是處于工業時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業目前對人來說是什么,而是按照現在的人對人類歷史來說是什么,即歷史地說他是什么來看待工業;所認識的就不是工業本身,不是它現在的存在,倒不如說是工業意識不到的并違反工業的意志而存在于工業中的力量,這種力量消滅工業并為人的生存奠定基礎。”[1]這里可以明確地看出,馬克思已經在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來看待工業的發展了。即撇開當前的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站在工業發展的歷史之上,認為工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工業使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工業催生了擺脫作為剝削手段的工業本身的力量。他還指出:“打破工業羈絆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擺脫工業力量現在皆以活動的那種條件、那種金錢的鎖鏈,并考察這種力量本身。這是向人發出的第一個號召:把他們的工業從買賣中解放出來,把目前的工業理解為一個過渡時期。”[1]即表明所要消滅的并不是工業本身,而是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把資本主義工業看成是一個過渡時期。總之,這里的論述明顯超出了之前人本主義的邏輯框架,預示著馬克思向唯物史觀的過渡。
(四)揭示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必然趨勢
《評李斯特》中有關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觀念與其同期的其他著作文本一脈相承。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就已經揭示了資產階級和私有制走向滅亡以及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必然趨勢,“私有制在自己的經濟運動中自己把自己推向滅亡,但是它只有通過……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的產生,才能做到這點……隨著無產階級的勝利……私有制都趨于消滅。”[6]他還指出:“無產階級必須能夠而且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它不是白白地經受了勞動那種嚴酷的但是能把人鍛煉成鋼鐵的教育的……它的目的和它的歷史任務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狀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最明顯地無可辯駁地預示出來了。英法兩國的無產階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任務,并且不斷努力使這種意識達到完全明顯的地步……”[6]
在《評李斯特》一文中,馬克思繼續論述道:“法國和英國的資產者已經看到即將實際消滅一貫被稱為財富的那種東西的真實生命的風暴就要來臨,而還沒有取得這種惡的財富的德國資產者卻試圖對這種財富作新的‘唯靈論的’解釋。”[1]對于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必然趨勢,他寫道:“工業用符咒招引出來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對工業的關系,同無產階級對工業的關系完全一樣,今天,這些力量仍然是資產者的奴隸,資產者無非把它們看作是實現他的自私的利潤欲的工具;明天,它們將砸碎自身的鎖鏈,表明自己是會把資產者連同只有骯臟外殼和工業一起炸毀的人類發展的承擔者……這些力量將炸毀資產者用以把它們同人分開并因此把它們從一種真正的社會聯系變為社會桎梏的那種鎖鏈。”[1]
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更明確地指出,實現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他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并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1]
四、結論及現實意義
《評李斯特》是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建立過程中,體現其思想蛻變的一系列作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雖然在重要性、理論性及系統性方面不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及《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但介于其寫作的時間恰在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建立的“前夜”,能從其中明顯看到馬克思思想蛻變的脈絡,《評李斯特》是研究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建構不可或缺的文本材料。《評李斯特》中,馬克思雖然沒有完全擺脫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勞動異化的邏輯思想,但還是有意識地使自己從歷史的、發展的、實踐的角度看待和剖析現實社會,這就具備了歷史唯物主義邏輯的萌芽,進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系統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標志著科學唯物史觀的建立。
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是永不過時的,對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前,我國正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關鍵的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一方面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另一方面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面臨著經濟發展速度降低、資源環境束縛壓力大、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優勢趨于消失、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如果罔顧這些現實發展條件的阻礙,制定不合理的發展規劃將付出代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豐富與完善,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的發展運動有著一般的固有規律,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五大發展理念是從我國現階段的社會存在和物質條件的總和出發,從系統的、科學的、發展的、普遍的視角出發而得出的,指導我國今后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其中閃耀著馬克思科學唯物史觀的理論光芒。因此,我們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們當前的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等各項工作不斷向前推進。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0-505.
[2]張一兵.人本主義邏輯的亞意圖顛覆[J].江蘇社會科學,1995,(6).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0.
[4]張一兵.馬克思走向哲學新視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J].哲學研究,1996,(2).
[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3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195.
[責任編輯吳高君]
B03
A
1673-291X(2016)22-0008-04
2016-05-16
王媛媛(1982-),女,江蘇連云港人,助理研究員,博士,從事世界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