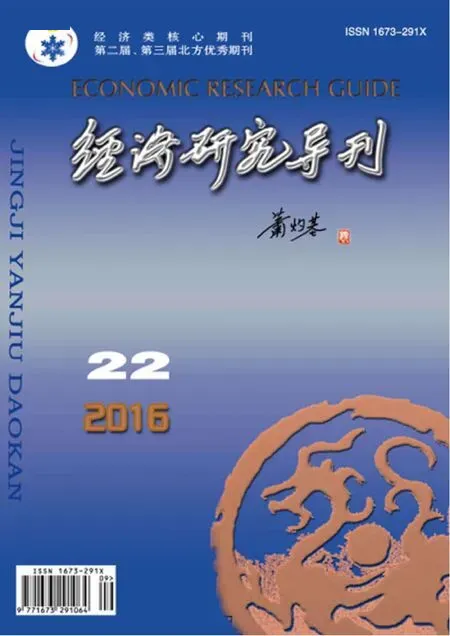健康的呈現與社會團結
——基于K健身APP的網絡社區考察
朱晨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北京 100872)
健康的呈現與社會團結
——基于K健身APP的網絡社區考察
朱晨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北京 100872)
通過對K健身APP的網絡社區的考察,發現社區內成員重新定義了健康,將作為軀干的身體視為健康本身而加以追求且將其在互動過程中語言化。同時,網絡社區內的互動也在展示與參觀中進一步展開,且通過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使文化資本得以碰撞,從而維系并鞏固社區作為健康共同體的團結形式。
健康身體;網絡社區;社會團結
一、問題的提出
健康,是同人之身體相伴相生的概念。從醫學角度來看,健康同其所相對的疾病、損傷等概念一樣,均是以身體作為生物性載體而存在于人的屬性。當社會學加入到有關健康議題的探討之后,健康的社會性得以呈現,并開始在身體之外去尋找健康及其作用的社會機制。人之身體并未從傳統醫學定義下的生物性中走出,而是作為健康議題的隱含前提而維持著相對隱性的狀態——無論是生物性或是社會性的身體,均已被高度抽象,健康與疾病等主觀體驗同身體相分離。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開展深刻地改變了原有以工業為經濟基礎的社會形態,使得互聯網成為進行社會交往、延展關系網絡的新平臺。信息革命所帶來的震蕩最集中地體現在經濟層面,網絡經濟已引發社會總體的變遷,健康領域也概莫能外。在疾病的診療方面,“互聯網+醫療”應運而生,為實體醫療提供巨大便利,并催生出諸如網絡問診等全新的醫患互動方式;在保健方面,互聯網也誕生了許多新經濟形式,其中較為深刻的改變發生于健身行業,體現在健身作為業態、生活方式、互動形式、文化資本等方面,并對健康定義本身帶去改變。
在本文中,筆者通過對K健身APP的網絡社區考察,試圖探討在虛擬時代的背景下,健康定義是如何經由身體而被再定義的;通過身體被呈現出的健康表象又是如何在互聯網的基礎上型塑出一種社會團結形式的。這一社會團結形式如何通過社區的規則創設來得以維系并鞏固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
二、網絡社會與健康的再定義:身體的呈現
不同視角對于健康概念會得出不同的定義闡釋;而社會學的介入則在根本上強調了健康及其相關要素的社會建構意義。其中Talcott Parsons對健康做出了較為清晰的概述,即已社會化的個人完成角色和任務能力的一種最佳狀態。這種功能主義的思路將健康置于人的社會行動中,彰顯其社會屬性;而健康社會學也順延“健康的社會性”而行進——身體是基礎性的存在、是健康不言而喻的前提條件。因而在社會學的宏大敘事中,有關健康的探討實則并未進入身體本身。
當我們將身體置于社會健康議題的中心時,關注的視角往往始于身體能夠做出怎樣的展現,因而疾病的、健美的、殘障的身體以及行動的、實踐的身體等不同狀態的呈現得到了關注,且這一系列的身體存在均指向健康內涵的某種變異。在此基礎上,對于身體探討開始推至這些不同身體狀態的社會體驗及資本創造,進入身體的行動、身體的實踐等將身體能動化的范疇。而在身體由個體性向社會性邁進的過程中,互聯網為身體的呈現與延展提供了平臺,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基于身體的健康所指代的社會意涵。在網絡的建構下,社會成員開始更新對健康的認識并重新理解健康所代表的狀態。從傳統的意義上來看,健康是一種身體內部的完好狀態,是身體作為生物有機體而發揮的正向的生理性功能。當信息時代降臨,身體在更大程度上是軀干肉體層面的存在,其主體在長期過程中扮演或展示或參觀的社會角色。社會成員逐漸開始形成對身體的評判并進而推至身體所代表的健康狀態評判的意識,即有意識地認為某種身體呈現意味著良好的狀態,且這種狀態直接指向健康本身。這一轉變過程中,身體作為健康的本質地位并未改變,但互聯網強大的延展性卻重構了對于這一系列概念的認知與想象。
本文所選取的K網絡社區是當前網絡中身體呈現的一個縮影,其背后是在這一再定義過程后社會成員基于身體的行動與實踐及其在組織層面所促成的主體間聯結的契機。當社會成員作為K平臺的一員而參與到社區中時,事實上包含著對于自我狀態的追求,且這些追求往往同各自的生活體驗相關聯:
希望通過健身見證全新的自己(成員Y)。
胖了這么多年想知道自己瘦下來是什么樣(成員N)。
走在亂世中,還不被欺負(成員J)。
進入K社區的每一成員都能被看作各自生活的經歷者,其身體也體驗著生活本身。這種對自我狀態的追求體現為兩點:一是個體在主觀體驗及客觀指標下的健康狀態,二是作為外在軀干所呈現出的良好體態;二者不可分割,且主體試圖在經由二者相結合的體驗過程中而導向更令自我滿意的生活狀態。這種相對趨同的集體信念體現出這一健康共同體中健康與身體間模糊的關系,成員將二者相等同,并潛在地認為二者互為表里。
三、身體的展示與參觀:他者眼中的健康
互聯網之于身體的革命性意義在于為身體提供了最大程度上展示與參觀的機會。展現與參觀是網絡空間的社會互動規則,是成員們基于相互間的空間區隔及匿名處理所進行的不同類型的社會行動。在這兩種行動的基礎上,人們展開了對對象諸如消費、欣賞等進一步行動。
在K社區中,對身體的展示與參觀是最為基本的互動形式。不同于其他網絡社區平臺,以健康為紐帶而形成的社會聯結改變了身體為衣物及流言所遮蔽的狀態,在這一過程中試圖將身體作為一種社會存在而日常化,并使其成為社區內相互溝通的語言;而這種身體語言在K社區中可以同文字語言并存來使互動發生。K社區中,成員間很大一部分的互動依賴于以圖片形式所呈現的身體語言,進行展示的社區成員通過身體傳達信息,而參觀者則對信息進行主觀解碼——身體語言可以獨立于甚至取代文字語言而維系溝通的進行。
因此,當作為軀干肉體的身體得以展示并被參觀之時,健康的內涵在這一群體中被進一步書寫。健康及其所代表的身體狀態不再是個體性的滿足程度,更大程度上體現為他者眼中的情感賦予。社會成員為了獲得群體認同而進行身體的展示,而參觀者則在另一方面主導著互動的進行,通過語言的問詢、引導來擴展溝通的維度。從這一角度上來看,展示者與參觀者之間的互動并非在傳統意義上的主客關系中進行,每一名社區成員均是各自互動范圍內的主體,均擁有展示及參觀的角色扮演可能性。
四、線上生活的線下實踐:健康生活方式的契約
網絡社會同現實社會并非處于相分裂的狀態,其事實上是作為虛擬和現實的續譜。當身體在線上線下兩種情境下為其主體所實踐時,這一過程本身是兼具虛擬性與現實性的。K社區同已有的網絡社區研究對象的很大不同在于其虛擬性與現實性的相互轉化,即主體的線上生活同其線下實踐是密不可分的。以往的網絡社區研究關注主體在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中的雙重生活體驗;而本研究中,K社區成員線上與線下的生活卻呈現出趨同的狀態。K社區在容納成員互動的同時,事實上構建起了一套屬于社區內部的契約體系,使社區內的成員各自行使“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通過各種非正式規則加以維系。
五、文化資本的碰撞:健康社區的社會團結
Durkheim對社會團結的定義相對擱置了空間之于關系紐帶建立的影響,將社會團結置于廣闊的情境之下,因而無論是探討工業文明中基于充分社會分工的有機團結、抑或本研究中的虛擬社區,均具有極強的適應性。互聯網所呈現的社會團結并未脫離其原本的定義;虛擬社會中社會成員所維系的是一種缺場狀態下的團結形式。K網絡社區事實上也維系著社會團結,這種團結是在身體的實踐、資本的碰撞以及群體意識的一致性之上所達成的;同時,其達成也離不開互聯網本身對于團結的型塑。
基于健康的關系聯結早已有之,然而其存在囿于一定的空間、年齡、稟賦等要素。在互聯網的運作下,健康團體的凝結突破了必須在場的限制,相對缺場的條件使社會人口學特征不再成為制約參與的因素。在K社區中,成員的準入條件僅限于對智能手機的使用,為相關人員的聯結創造較為寬松的條件。這一特征是互聯網獨特的社會建構結果,為網絡社區內的社會團結帶去了獨特的影響。
K社區成員集聚的契機依賴于身體的實踐及各個情景下的人際互動。在前文中,健康的定義在主體間或展示或參觀的社會行動中被重塑,在這一群體表象之下,社會成員通過身體進行的線上及線下行動將自身置于社區之中;而另一方面,社區本身則通過吸納多方文化資本而將這種團結維持下去。以K社區為代表的健康導向社區,其資本的碰撞往往呈現為身體化形態,即在社區中文化資本的累積是在大量的時間、消費基礎上而“慣習化”的過程。在本研究中,這種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體現在那些格外擅長于健身、飲食等領域的社區成員之中,他們是權威的享有者,受到其他成員的尊敬與好評。這些成員在數量上往往較少,但卻面臨著大量的咨詢需求;同時,社區內的文化資本也處于一種高度流動的狀態——隨著參觀者不斷加入到展示者的行列中,越來越多的身體及其技術得以成為具有文化資本的符號。在不同文化資本相互作用的格局下,基于健康的團結形式得以進一步鞏固。
六、小結
健身作為一種保健手段,在現階段常指向健身這一行為。當進入一個基于健康這一集體信念而聚集的網絡社區時,社區內成員所做的是回到身體本身去重新定義健康,同時將物質性的身體作為實踐方式來進行展示或參觀的互動,并這一過程中身體成為成員間互動的語言;在社區及其成員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中,文化資本在社區內充分碰撞、流動。在此基礎上,社區得以維系團結的形式。
[1]文軍.身體意識的覺醒:西方身體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及其反思[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6).
[2]夏學鑾.網絡社會學建構[J].北京大學學報,2004,(1).
[3]朱偉玨.“資本”的一種非經濟學解讀——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J].社會科學,2005,(6).
[責任編輯周沖]
G811.4
A
1673-291X(2016)22-0160-02
2016-07-08
朱晨聰(1994-),男,福建廈門人,本科,從事城市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