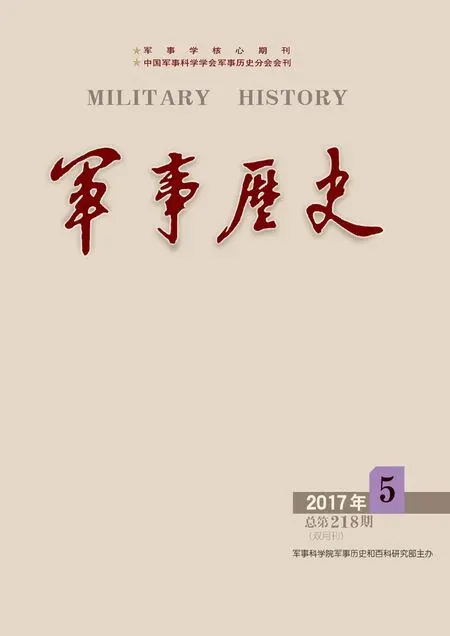從漢字看中國古代戰爭觀
★
漢字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漸創造出來的,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是音、形、義的結合體,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時空性。與戰爭有關的漢字,帶有對戰爭問題及戰爭相關因素的認識,蘊含和記載了中國古代對戰爭的根本看法。據統計,甲骨文中與戰爭有關的字,如兵器的戈矛、方國的夷羌、戰時的射衛、俘虜的囚殺等,占總字數的8%,大大超過了有關衣(1.7%)、住(6%)、行(3.6%)方面的字數*李蘇鳴:《軍事語言研究》,106頁,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漢字寫下了中華文明的過去,也融入金戈鐵馬、縱橫捭闔的較量中,考察漢字中戰爭的“痕跡”,探尋戰爭史上的漢字源流,對于認識中國古代戰爭觀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漢字中的疆域觀
斯大林指出:“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漢字與其他文字一樣,與國家相伴而生,在誕生時自然而然地承擔了表達國家疆界范疇的功能,也反映了疆域與戰爭的關系。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或”字。“或”是“域”和“國”的初文,《說文解字》中提出:“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也就是說,“或”至少包括三方面要素:“口、戈、一”,從根本上反映了古人的國家(邦)觀與“戈”的關系密切,“口”用來聲索疆域(一,土地),而倚重的則是“戈”。另外,“域,從土,或(yu)聲”“堡,從土,保聲”,等等,都說明了疆土是國家存在的物質基礎和心理基礎。“守土”“衛國”需要“戈”(軍事手段)來作為基礎和達成目標的手段。除此之外,漢字中沒有用到其他更為明顯的字形形式。也就是說,漢字在 “國”“域”等表示疆域方面上,充分反映了古人“兵者,國之大事”的思想,有“戈”則有疆,無“兵”則無國。
縱觀世界戰爭史,引發戰爭的因素多種多樣,包括領土爭端、掠奪資源、爭奪勢力范圍、宗教沖突、意識形態斗爭、民族矛盾等,其中,地緣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戰爭的起因從根本上來說,多是由爭奪疆域和自然資源引起的。漢民族自古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土意識,保衛“王土”的完整和安全,需要在邊境地區進行防衛和管理。在保衛疆域方面,有護“城”衛“邑”之說。“城,從土從成”,本義是土筑墻垣,“所以盛民也”,用于防御外來入侵;“邑”,上為口,表疆域,下為跪著的人口,偏重于指規模較小的村落、城鎮。《吳子·應變第五》指出:“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反映了“城”“邑”雖大小不同,但對于保衛疆域都具有支撐作用,都是戰爭中爭奪的焦點。
二、漢字中的攻防觀
漢字中,“伐”與“戍”,均“從戈”,也就是說,這兩者都與“兵者”直接相關。伐者,左人右戈,人持戈也;戍者,下人上戈,人何戈也。《說文解字》中有:“伐,擊也”,《廣雅》認為:“伐,殺也”,一擊一刺為一伐;《說文解字》又有:“戍,守邊也”,人持戈以抵擋,戍守止寇賊是其本意。以上兩個漢字的“一攻一守”,從字形上就生動展現了敵對雙方你擊我擋的戰斗場景,也反映了古人對戰爭形式的樸素認識,擴展起來還體現了爭奪土地、疆域的戰爭目的。
攻防作為作戰的基本形式,還明顯地反映在“矛”“盾”這兩個漢字中。“矛”,象形字,一頭帶尖的長柄武器,柄上有扣環,為進攻之具,操戈執矛,用以刺敵;“盾”,象形字,《說文解字》認為:“盾,瞂也。所以捍身蔽目。”手持護牌,舉在頭上,保護眼睛和腦袋。古戰場上,無論是兵車對壘,還是短兵相接, 士兵一手持盾保護自己,一手持矛進攻敵人,都形象地表明,中國古代的兵家已認識到“消滅敵人”與“保存自己”這對辯證統一的關系,并通過兵器的制造和使用來統一這對關系以實現戰爭的目的。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二版)將戰爭定義為:“國家、政治集團和民族之間為了一定的政治、經濟等目的而進行的武裝斗爭。”*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二版)·戰略》,500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雖然戰爭的發起往往是政治家、軍事家,但戰爭都是要組織武裝人員開展武力對抗的,“武”是戰爭最為重要的代名詞之一。從這個代名詞出發,如何來理解戰爭?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為武。”意指能止息戰爭的,才能叫做具有武力。這是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將“武”看成是“從止從戈”的會意字。事實上,甲骨文中的 “止”,是腳趾的象形,表行進,在“武”中與“戈”組合,表示持戈而行、出征作戰。又如《漢書·弄法志》中有:“當斬左止者”,顏注:“止,足也”。 古漢語中,“止”都代表足趾,也就是人的足跡,幾乎都有前進、進取之義,而絕非中止、制止。*趙弼:《從漢字看古代戰爭——析窮“兵”黷“武”》,載《時代報告》,2012(1)。因而,從漢字的本源來看,“武”的原始本意并非后世會意而生的 “止戈為武”,而是象形義的“出征、進攻、征戰”。也就是說,“武”中“攻”的意味更重。沒有進攻,就沒有武力的對抗。進攻是戰爭的開端,更是戰爭最為重要的方面之一。甲骨文中征伐類動詞共有征、伐、敦、執、捍等14個,侵擾類動詞共有侵、出、啟、至等7個*韓劍南:《甲骨文攻擊類動詞詞義研究——兼論商代的戰爭觀》,載《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2)。,與之對應的防御類動詞則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重攻”思想,依稀可見“進攻是最好的防御”思想萌芽。
三、漢字中的策略觀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無非是擴大了的搏斗”*[德]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上卷,12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64。,在甲骨文中稱為 “伐”“爭”,其他古籍中稱為“戎”“兵”“征”“斗”等,后多稱為“戰”,而“戰爭”作為一個合成詞,最早出現在兵書《吳子·料敵第二》,《史記·秦皇本紀》也有:“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指導戰爭是人類最艱難的一種活動*李際均:《論戰略》,1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那么,從“戰爭“的構詞理據來看待古人對于戰爭的態度,會對其中的艱難有一些新的認識。從“戰爭”中的“戰”來說,繁體字為“戰”,從單從戈,其中,戰之聲符為“單”,新近的研究傾向于動物象形,認為單與鼉是同源字,都是指龍中的一個品種——鼉鱷、鼉龍,并且,單與獸、獸(古獸、狩同字)也有內在聯系*何新:《龍:神話與真相》,146~14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對應著獸性的沖動和殘殺,這些與《說文解字》中的“戰,斗也”也基本一致。而從“爭”的字形上看,為兩手奪一物,可會意為爭奪資源與地位而征戰不休。而從隱義來看,兩股力量的爭奪,其結果不是一敗一勝,就是兩敗俱傷。而后者為爭斗雙方所竭力避免的。*羅建平:《戰爭的語言理據及其政治意味》,載《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5(4)。因此,“爭”最好能形成一種平衡,古人造出的“靜”“箏”等一系列字也含有和諧、穩定之義,與“爭”的動態平衡暗合。“自古多征戰,由來尚甲兵。”“戰爭”二字,融入人類發展史中,既有“戰”投射的非理性沖動,還有“爭”展現的敵對雙方力量對峙, 以及升華而成的維持平衡的格局。對戰爭暴力性和平衡策略共生互補關系的認識,是漢字中蘊含的最大的戰爭策略。
除了在暴力與平衡之間控“勢”的大策略之外,中國古代的策略觀還少不了“計”“謀”二字。
《說文解字》認為:“計,會算也。”《廣雅》認為:“計,較也。”計,從言從十,本意是“數數、計算的意思”,引申為比較、謀劃。《孫子兵法·計篇》有:“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文中明確提出,“計”即“算”,“廟算”是制定策略的基礎,也是戰爭勝利的基礎。
《說文解字》有:“謀,慮難曰謀。”《孫子兵法》將《謀攻》與《計篇》并列,杜牧《孫子注》中有:“廟算之上,計算已定……可以謀攻。”謀攻中,首先是慎戰,《論語·述而》認為:“子之所慎:齋,戰,疾。”對待戰爭,在中國古代即已認為兵法的最高藝術是“無為而戰、不戰而勝”“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也反映了中國軍事文化的核心是以道立國而不是以兵立國。若不得不戰,最好慎重首戰,謀定后戰,以謀為本,一戰而勝。相比于西方人注重技術,東方人更注重謀略。具體的謀略內容,“快” 如“兵貴神速”,“準”如“權敵審將”,“全”如“算無遺策”,“活”如“柔能制剛”,更重要的是“奇”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最終實現“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劣勝優”。
四、漢字中的情報觀
從古至今,情報一直對戰爭勝負起著關鍵性作用。早在商代,掌握占卜、祭祀的卜巫之官,就負有情報分析的職能,甲骨文獻中更是充斥著對敵情的求索。到了周朝,“觀”卦就是要掌握各部族邦國的情況,主張既要“觀我生”,又要“觀其生”,還要考察大國的政績(“觀國之光”),以此決定自己的進退方針和內政外交方略。*儲道立、熊劍平:《中國古代情報史論稿》,1頁,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無論是“觀”卦還是“觀”情,“童觀”還是“窺觀”,“觀”都是獲取情報、輔助決策的重要方式。《說文解字》中有:“觀,諦視也。”意即仔細看、全面看、反復看,“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盡可能獲得全面情報,服務于戰爭的籌劃與組織實施。在情報工作中,與“觀”類似的表述和行動還有“相”“因”。《說文解字》中還有:“相,從木從目,省視也。”“省視”義同“諦視”,全面仔細地查看;“因,從囗(wei)從大。就也。”“因”的“囗”類似于“國”的“囗”,意即把“囗”內因素放大,便于更為全面、透徹、準確把握情況。綜合對以上漢字的分析,可以說,古人早已認識到,觀情而定、相機而動、因敵而變,才有可能獲得戰爭的主動權。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與軍事情報相關的最常用漢字還有“知”,即獲取與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軍事斗爭有關的情況和資料,這也是獲情的目的。《易傳》認為,戰爭勝負、宮廷政變、人事吉兇等社會現象的初始跡象和征兆稱為“幾”,“知彼知己”要“知幾”“極深而研幾”;《老子》在量變推動質變的樸素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知常閱明”;還有《管子》認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直觸情報工作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呂氏春秋》著眼“先識”“知化”“長見”,把高度的預見性和有效的預警作為情報工作的根本要求,進而探討了情報工作的規律——“知道”。《孫子》則主張“先為不可勝”,并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開始完全脫離早期的卦辭思想,強調情報工作中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
在具體的情報觀方面,《孫子》中的“道”“天”“地”“將”“法”的大情報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具體的情報方式方面,可概括為“料敵”“用間”“審察”等,這些門類都與具體的漢字相對應。“問”“算”“識”“測”等漢字,表示“料敵”的不同環節,用以達到“測深探情”的目的;“目”“候”“間”“諜”“斥”等漢字,均有軍事情報偵察人員之義,“凡欲征伐,先用間諜”“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且可肩負“分散其眾,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的更大作用;“望”“目”“見”等漢字,都是審察、觀望的意思,表示對敵方的軍情進行偵察,“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也反映了古人對戰前情報極端重要性的認識。
五、漢字中的裝備觀
通常來說,西方重實力,中國重謀略。在崇尚智慧、兵法的文化氛圍中,對武器裝備的硬實力的強調似乎弱化了。其實不然,中國古代人和現代人一樣,極為重視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只不過“器勝”的思想因為漢字中的戰爭概念通常以兵器類字來表達,將強調裝備實力擴大為強調軍事能力了,從而在形式上弱化了單純的裝備觀。“兵” 本意為兵器,引申為士兵,并被廣泛用作與軍事或戰爭有關事物的統稱,類似的文字和例子使得原本的裝備思想泛化為軍事思想了。比如,《司馬法》中強調,“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本是在強調要加強裝備建設,但又由因“馬車、甲兵”可被賦予借代意義,而可擴大理解成“軍備齊全,乃強國之道。”
反觀古代軍事裝備的狀況,在漢字中得到充分體現,《說文解字》所收的有關兵器類的字很多,而且分類很細。比如,長兵器有殳、祋、杸、戈、戟、矛、矠、钑、鋌、鈗、錟等,短兵器有刀、戚、斤、斧、鉞、鏌、釾等,弓矢類有弓、弴、弭、弧、弩等,護身兵器有盾、瞂、櫓、鎧、甲、釬、櫂、科、渠、铔鍜、兜鍪等。正如語言學家蘇新春先生所指出的:“分析漢語中兵器類基本詞的構成與發育情況,我們仿佛看到了一幅古代社會兵戎相見的全景圖。”*蘇新春:《漢字文化引論》,40頁,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而且,隨著漢字的發展,不但有表示主戰兵器的文字,還出現了表示軍馬戰車類、軍鼓軍樂類、旌旗徽幟類、兵器配飾類等漢字,比如旌旗類的有旌(旍)、綏(緌)、旟、旐、旂、常、旗、旃(旜)、麾、翳、幢等,旗幟的材料不同、配鈴不同、柄制不同、顏色不同、等級不同、用途不同、所繪之物不同,都有對應的漢字來表示。這些體現了我國古代武器裝備門類多、分類細的特點,也反映了古代人對兵器的倚重。
我國古代武器裝備不但在實體上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從思想上來說也極其豐富。《管子》中指出:“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古代軍事家們更是深知“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重器”的思想表現在三個主要方面:在兵器制造方面,為了提高性能,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十分注重吸收和運用當時先進的技術;在兵器使用方面,要求因時、因地、因敵、因器、因戰的不同,選擇使用不同的武器裝備;在兵器的制造與管理方面,早在春秋時期古人就走上了裝備制式化的道路,并且在后續朝代,開始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官職,注重把握發展武器裝備的時機及相應的政策,還注意吸引和招募“天下之良工”,給予優厚的待遇,“因能利備,則求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