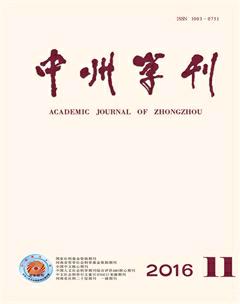“距離”在文學創作中的意義
楊暉+肖成
摘要:距離在文學創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心理距離”理論要求作家控制好與生活、情感、語言等方面的距離;“小說距離”理論強調敘述手法對讀者距離的控制,內聚焦、外聚焦及零聚焦敘述方式能產生獨特審美效果;現代主義主張以“變形”等藝術手法制造與生活的距離,后現代主義則主張填平距離。在藝術創作中,距離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距離的消失意味著藝術獨特性的消失,也意味著藝術的消失。
關鍵詞:文學創作;距離;元素
中圖分類號:I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1-0163-05
“距離”以其獨特的魅力,在藝術創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布洛的“心理距離”關注創作主體在創作過程中涉及的諸多距離問題;布斯的“小說距離”重視敘述手法對讀者距離的影響;而不同的創作觀念在處理距離問題上存在著差異。總之,在藝術創作中,距離無處不在,距離的消失意味著藝術獨特性的消失,也意味著藝術的消失。
一、創作主體與心理距離
在創作中,作家要控制好藝術與生活、情感之間的距離,以及語言收放等問題,促使審美效果的最大化,這些都與心理距離密切相關。
1.作者與生活
作者與生活的距離控制表現了“出”與“入”的統一。作者既要呈現對生活的真實體驗,又要充分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控制好自己與生活的距離。
蘇軾在《送參寥師》中提到,詩人既要“閱世走人間”,又要“觀身臥云嶺”,也就是既要深入生活,又要超越生活。正如朱光潛所說:“創造和欣賞的成功與否,就看能否把‘距離的矛盾安排妥當,‘距離太遠了,結果是不可了解;‘距離太近了,結果又不免讓實用的動機壓倒美感,‘不即不離是藝術的一個最好的理想。”①也就是說,藝術與生活應保持“適當”的距離,“太遠”或“太近”都不是“最好的理想”。
那么作家應如何控制這一距離呢?王國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②“入乎其內”就是要深入生活,對審美對象有深刻體悟。辛棄疾在《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中對“愁”的體悟很能有代表性:“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詩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這里正好說明詞人早期對“愁”缺乏體驗,有了一定閱歷后才發現“實愁”與“虛愁”的距離。“出乎其外”就是不囿于生活表面,深入生活。王國維評周邦彥《蘇幕遮》的“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云:“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③,又說:“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鳥共憂樂。”④“輕視”與“重視”的距離調節正好體現了“入”與“出”的關系。可見,唯有“出”與“入”統一,
2.作者與情感
情感距離控制分為兩種:一是作家的情感參與度;二是生活情感與藝術情感的差異度。這里討論的情感距離控制主要是前者。
藝術創作離不開作家的情感參與。劉勰曾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文心雕龍·知音》),梅堯臣說“憤世嫉邪意”(《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西方也有“憤怒出詩人”之說。這些都說明創作與情感的相關性,因為“參與藝術家或作家創作活動的想象之最重要特點是它的明顯情緒性。作家頭腦中產生的形象、情境、情節的意外轉折似乎是透過一架特殊的‘不斷充實的機器,進行創作的個人情緒方面就是這樣一架機器”⑤。而想象中的情緒(情感)又摻雜理性,情感與理智間的距離調節影響著創作。布洛認為藝術家須處理好“心理距離”的矛盾,最合適的便是“最大限度盡量減少距離而不使之消失”⑥。
肆意宣泄情感會使創作難以控制。朗吉努斯認為:“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沒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為自己的盲目、輕率的沖動所操縱,那就會象一只沒有了壓艙石而飄流不定的船那樣陷入危險。”⑦托馬斯·曼也認為:“生糙的熱烈的情感向來是很平凡的不中用的……強烈的情感并無藝術的意味。藝術家一旦還到人的地位來在情感中過活時,就失其為藝術家了。”⑧這些都說明創作須限制情感,正如狄德羅所說:“你是否趁你的朋友或愛人剛死的時候就作詩哀悼呢?不,誰趁這種時候去發揮詩才,誰就會倒霉!”⑨哈代《德伯家的苔絲》的結局,就是作家情感與理智的距離喪失的典型例子,柯林伍德評論其毫無節制的情感宣泄,“就像一個起訴律師講完一席話之后,朝囚犯臉上吐了一口唾沫一樣”⑩。因此,作家既要有積極的情感參與,又不能為情感所蒙蔽,“不能同時在這種情感中過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觀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觀的觀賞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經驗放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所以情感盡管深刻,經驗盡管豐富,終不能創造藝術”。情感的放任易導致感染力減弱,過度控制又易造成情趣的失缺。
3.作者與語言
語言的距離控制是指作家須運用語言,縮小“言”與“意”的距離,以言傳意。對于作家而言,語言是表達“心中之意”的載體。然而,語言與表現對象存在“距離”。
《周易·系辭上》有“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表達了追求以言盡意的美好希冀。莊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表明既想以“言”傳“意”,又不拘泥于“言”。陸機說:“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文賦》)這里指出語言常不能準確反映作者心中所想。文學創作中,若言不盡意,作家會遺憾無窮;若言能盡意,作品又失去回味空間。作者要對語言距離進行控制,以有限之“言”表達無窮之“意”。因此,“為了盡可能縮小言意之間的差距,就要注重‘文外之意,利用語言所能夠表達、可以直接描繪出來的部分,去暗示和象征語言所不能表達、難以直接描繪出來的部分,盡可能擴大藝術表現的范圍,并且充分利用讀者的聯想能力”。
可見,藝術家的藝術創作離不開距離的元素,如果與生活、情感、語言之間的距離太近,不利于充分發揮藝術的想象性特征,流于淺顯;距離太遠,又難以激發藝術想象,流于晦澀。
二、創作手法與距離效果
作者在創作中常以某種藝術手法來調節受眾與作品之間的心理距離,以達到理想的審美效果。作家的藝術手法極為豐富,這里僅以敘述為例,分析其帶來的“距離”上的差異。
1.敘述視角
何謂“敘述視角”?托多洛夫指出:“構成故事環境的各種事實從來不是‘以他們自身出現,而總是根據某種眼光,某個觀察點呈現在我們面前。”“視角”原指畫家作畫時的視線出發點,后被移植到文學,指選擇或者不選擇某個受限制的視點。荷蘭學者米克·巴爾認為:“不言自明的是,事件無論何時被描述,總要從一定的‘視覺范圍內被描述出來,需要選挑一個觀察點,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無論所涉及的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還是虛構的事件。”可見,敘述視角在文學作品中無處不在,它表現了作家選擇誰來敘述,用什么方式來敘述的問題。
敘述學關于敘述視角的概念和分類并不統一,但熱奈特在對弗里德曼的八分法進行歸納和簡化的基礎上提出的三分法最有代表性。“他的三分法是對三種聚焦模式的劃分:(1)‘零聚焦或‘無聚焦,即無固定視角的全知敘述(包括弗氏的前兩類),它的特點是說出來的比任何一個知道的都多,可用‘敘述者﹥人物這一公式來表示。(2)‘內聚焦,其特點為敘述者僅說出某個人物知道的情況,可用‘敘述者=人物這一公式來表示……熱內特區分的第三大類為外聚焦(包括弗氏的最后兩類),其特點是敘述者所說的比人物所知的少,可用‘敘述者﹤人物這一公式來表示。”不同的聚焦敘述方式對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產生不同的距離,“一般地說,內聚焦敘述能夠拉近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外聚焦敘述則疏遠了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的距離;而零聚焦敘述者由于具有絕對權威,因而使敘述者和人物之間總保持很大的距離”。換言之,敘述者知道的多少影響著讀者與作品人物之間的距離。
內聚焦敘述指敘述者直接參與事件,敘述顯得可靠,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如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陌生人以自己的口吻敘述,使讀者與人物心理接近,易贏得共鳴。外聚焦敘述指敘述者充當旁觀者,易給讀者造成一定的距離感。如《孔乙己》以咸亨酒店的小伙計為敘述者,造成心理距離,從而引導讀者思考。零聚焦敘述指敘述者擁有全知全能視角,讀者接觸的是距離化的人物,易摻雜作者的主觀情緒或對讀者的突然干預。如托爾斯泰時常跳出故事情節,發表道德議論,讀者接觸的是作者評價后的人物,由此拉大了讀者與劇中人物的距離。
敘述視角影響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在作者主導的敘述文本中,讀者體會作者對人物的情感;在凸顯人物心理的敘述文本中,讀者跟隨人物的思想和感知。無論何種敘述,作者的話語都將調節著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
2.敘述時態
敘述時態也是調節距離的有效手段。熱奈特將敘述分為四種類型:“事前敘述(常見于過去時敘述);事后敘述(預言性敘事,一般用將來時,但也可用現在時);同時敘述(與情節同時的現在時敘事)和插入敘述(插入到情節的各個時刻之間)。”這些敘述類型又可概括為三種敘述時態,即現在時敘述、過去時敘述、將來時敘述。
現在時敘述就是敘述正在進行的事件,它能使讀者如臨其境,縮短敘述和讀者的距離。“故事與敘述完全重合在一起,排除了各式各樣的相互影響和時間上玩的花樣。”比如閱讀“你把左腳放在了銅槽口上,正用你的右肩費勁地想把滑動板再推開些,卻怎么也推不動”,就是把敘述者與讀者自然地銜接在一起,主體間的距離縫隙很小。現在時敘述在日記體小說中運用廣泛,由于“敘述階段與被敘述階段相匹配,共同限定話語和被報道情境的重合的‘現在狀況。因此所報道或記載之事便是所體驗之事,用貝克特的話來說,‘我看,故我說”。因此,閱讀《少年維特之煩惱》時,言語和事件仿佛同時展開,讀者幾乎忽視了敘述的距離。
過去時敘述就是敘述發生在事件以后,如張愛玲《金鎖記》的開頭“30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就表明了敘述與故事之間的距離。關于過去時敘述,米勒曾說:“在敘述中采用常規的過去時是表達敘述者與他所描繪的文化相分離的一種方式。敘述者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種文化。這種保持距離的做法削弱了小說中人物分享的那些設想和價值觀念。”過去敘述包含了一種導致讀者與小說人物相分離,使讀者以局外人的視角閱讀。這種分離的結果之一就是審美的誕生。朱光潛認為:“‘從前兩個字可以立即把我們帶到詩和傳奇的童話世界。甚至一樁罪惡或一件壞事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不那么令人反感。”過去時的敘述通常過濾掉道德利害,給人以獨立思考的機會,使對象的意義呈現出來。
將來時敘述就是敘述將發生之事,具有預言性質。完全采用將來時敘述的作品頗為罕見,但在有關宗教、夢、詛咒等內容的作品中通常有這種方式。如《俄狄浦斯王》敘述了一個預言成真、命運難逃的故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敘述與讀者之間存在距離。
相比而言,過去時敘述和將來時敘述比現在時敘述更能使讀者感覺到故事的遙遠。需要指出的是,敘述并不明顯標記時間距離,敘述時態的變化,會帶來相應的距離變化。在《魯濱遜漂流記》中,作者主要運用過去時敘述,而結尾處敘述視角的變化又使故事呈現出現在時的距離特點。其實,在創作中,單一時態敘述并不常見,多數作品會綜合運用幾種時態,隨之帶來與讀者距離的相應變化。
三、創作觀念與距離表現
不同創作觀念下的文學作品顯示出的距離效果也是有差異的,如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在其創作中表現出明顯的距離差異。
1.現代主義的距離“消蝕”
“現實主義小說的創作目的在于表現普通讀者眼中的生活和社會環境,引導讀者產生這樣的意識,即小說中的人物可能是真的存在,小說中的事情可能真的會發生。”因而,現實主義強調拉近與生活的距離,取材于日常生活,易造成距離的消失。而現代主義,正如西班牙的奧爾特加·加塞特所認為的:“現代藝術家不再笨拙地朝向實在,而是朝與之相對立的方向行進。他明目張膽地把實在變形,打碎人的形態,并使之非人化。”現實主義的創作容易為人理解,但也易于喪失審美距離,因而遭到現代主義的拋棄。
現代主義打破現實主義傳統,通過想象、虛構,甚至荒誕的情節、人物,以及陌生化手法去表現抽象東西,“距離”化特征明顯。如卡夫卡的《變形記》運用變形、荒誕的手法描寫了主人公變形前后的心理感受,表現了這類人的孤獨絕望,折射出人在哲理意義上的生存狀態。
然而,現代主義文學反叛過度的傾向又帶來了與現實距離過大的弊病。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表達了對現代主義的拒絕,認為理性正在為人們的刻意求新所破壞,現代主義小說變得愈發難以理解。但他并不反對距離的設置,認為“一旦藝術與現實的縫隙完全彌合,藝術就將毀滅。但是直到本世紀,人們才開始真正承認,使我們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的人為的力量可能是一種優點,而不僅僅是達到充分現實主義的不可逾越的障礙”。與現實距離過小,藝術將毀滅;過大,藝術又晦澀難懂。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分析現代主義藝術時,提出現代主義對理性的反叛帶來距離“消蝕”。他認為傳統藝術最講究距離,“按照現代之前的傳統觀點,藝術基本上是沉思的工作;藝術的觀照者因與經驗保持審美距離而持有支配這種經驗的‘力量”。在貝爾看來,現代主義藝術比之于古典藝術有“距離的消蝕”的特征。他認為古典藝術的原則,第一是遵循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理性宇宙觀;第二是遵循距離觀念的摹仿理論,而這種蘊含審美距離的關系被現代主義打破,“在體裁上,產生出一種我稱之為‘距離的消蝕現象,其目的是為了獲得即刻反應、沖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動性。審美距離一旦消蝕,思考回味也沒了余地,觀眾被投入到經驗的覆蓋之下……距離消蝕法則一舉打破了所有藝術的原有格局:文學中出現了‘意識流手法,繪畫中抹殺了畫面上的‘內在距離……”正因為如此,現代主義不再是藝術家沉思的工作,欣賞者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審美經驗,讀者所慣常依據的審美經驗也不能起到足夠的作用,因而讀者會感到一種“震驚”的感受。可見,在大眾文化的背景下,貝爾不同于其他的現代主義者,他看到了現代主義文學距離“消蝕”的一面。
2.后現代主義的距離“消失”
現代主義文學強調“確立邊界,生成鴻溝”,后現代主義則偏重“跨越邊界,填平鴻溝”。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的:“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風格,它以一種無深度的、無中心的、無根據的、自我反思的、游戲的、模擬的、折中主義的、多元主義的藝術反映這個時代性變化的某些方面,這種藝術模糊了‘高雅和‘大眾文化之間,以及藝術與日常經驗之間的界限。”艾布拉姆斯也認為:“后現代主義還通過依靠‘大眾文化中的電影、電視、報紙卡通和流行音樂等模式,顛覆了現代主義‘高雅藝術中的精英主義。”可見,后現代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藝術與生活的界限模糊化,藝術與現實的距離逐漸喪失,正如杰姆遜所說的:“在19世紀,文化還被理解為只是聽高雅的音樂、欣賞繪畫或是看歌劇,文化仍然是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而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距離正在消失。”后現代主義文學提倡日常生活的審美化,高雅藝術變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后現代主義文學正以各種姿態滲入現代社會,大眾化文學也趨向“零距離”的文學,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內容世俗化。作家“以日常的人生經驗作為敘事依托,以現實生存的客觀秩序作為敘事的真實參照,不斷地在大眾經驗的平臺上從事簡單的話語虛構,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現實生存的邏輯規則進行話語營構”。如新寫實小說就具有后現代主義的傾向,他們宣稱“感情的零度寫作”,主張“純粹客觀地對生活本態進行還原”,以達到“毛茸茸”的程度。正如池莉稱自己的《煩惱人生》,“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輯,不動剪刀,不添油加醋地,是當時此時的真實”,展示了一個平凡人一天的平淡生活。文學是想象的、審美的藝術,讀者通過審美活動超越現實,而“大眾文化文學的實質上是非文學的、反文學的,因為它在語言等形式層面和精神審美層面是趨零距離化的,其文學性也在距離的消失中而逐漸消解”。它似乎在反叛道路上走得過遠,忘記了文學超越生活的一面。
第二,語言日常化。文學語言的陌生化逐漸喪失,趨于生活大眾化和粗俗化。傳統文學講究語言的“距離化”效果,通過語言的距離和張力,吸引人們去揣摩。唐代詩人盧延讓“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苦吟》),賈島曾為一個字,反復推敲,費盡腦筋。現代泛化的文學,語言的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也使得文學與生活的“距離”喪失。
第三,手法淡漠化。文學表現手法也逐漸被取消,修辭手法、藝術技巧被輕視。正如布魯姆所說:“人們誤以為,想象性文學與其他藝術相比較,只要較少的知識和技能就能被生產和被理解……當我試圖閱讀憎恨學派選為經典之替代的眾多作品時,我思忖,這些胸有抱負的作者必然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講故事,或者他們誠摯感情本身就已經是詩,只需稍加修飾就行。”由于藝術手法的缺失,后現代主義的一些文學作品顯得平庸、粗劣。創作的“零距離”趨向使得后現代主義文學被廣為詬病。
可見,作家的創作觀念與創作距離休戚相關。文學創作如果落入日常化的描述,容易蛻化為非藝術,導致作家忽略文學的審美性、想象性和虛構性特征,失去對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距離的控制,喪失藝術的深度。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距離的消失意味著藝術獨特性的消失,也意味著藝術的消失。
注釋
①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頁。②③④王國維:《人間詞話》,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35、19、35頁。⑤[蘇]彼得羅夫斯基主編:《普通心理學》,孫曄等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85頁。⑥[英]愛德華·布洛:《作為藝術要素和審美原理的“心理距離”》,章安祺編訂:《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四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79頁。⑦伍蠡甫等:《西方文論選》(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117頁。⑧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9頁。⑨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16頁。⑩[英]喬治·科林伍德:《藝術原理》,王至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26—127頁。朱光潛:《談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1—32頁。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8頁。張寅德:《敘事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65頁。[荷]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2版),譚君強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67—168頁。申丹:《敘事學與小說文體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7—198頁。白春香:《小說敘述距離的審美本質及藝術生成》,《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50、151頁。轉引自王先霈、王又平等:《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0、371頁。程錫麟、王曉路:《當代美國小說理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年,第259頁。朱光潛:《悲劇心理學》,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1頁。[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吳松江等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21、337頁。[西]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藝術的非人化》,米歇爾·福柯、尤爾根·哈貝馬斯等編:《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8頁[美]W·C·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36頁。[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三聯書店,1989年,第95、31頁。[英]特雷·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幻象·前言》,華明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62頁洪治綱:《想象的潰敗與重鑄》,《南方文壇》2003年第12期。王萬森:《新時期文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2頁。曾洪偉:《文學終結·審美終結·距離終結——試論哈羅德·布魯姆關于當前文學危機的觀點并與希利斯·米勒比較》,《文學評論叢刊》2011年第2期。[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37頁。
責任編輯: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