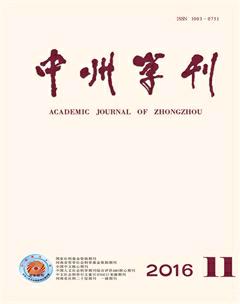網絡風險事件中的集體行動研究
湯天甜+劉聰
摘要:風險事件中,集體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發“集體維權”“集體抗議”等群體性事件。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表現出與傳統集體行動不同的特點,風險事件的爆發是網絡集體行動的邏輯起點,網絡相對自由的環境和平臺為公眾提供了發泄不滿情緒的空間。群體成員通過構建共同身份、集體造勢等情感動員的方式聚集起來,以集體行動為抗爭劇目,通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方式,影響網絡輿論的走向以達成其行動的預設目標,并將該影響從網絡延伸到現實,最終建構社會成員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集體行動;情感動員;網絡環境;風險事件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1-0168-05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集體行動開始轉向互聯網,并呈現出與傳統集體行動不同的特點。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以何種方式動員,其內部存在著怎樣的機制,是當前互聯網媒介生態下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中國正處于轉型期,社會的階段性、不穩定性等導致群體性事件的頻發,而網絡為群體性事件提供了新的發生場所。本文旨在考察當前的互聯網背景下,風險事件的集體抗爭如何動員,其行動方式有什么特點以及產生了什么樣的社會影響。
一、風險事件的抗爭劇目:集體行動
Koopmans認為,大眾媒體在運動動員和運動擴散中,甚至替代了社會運動參與者和組織者的很多工作①。由此可見,媒介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革也必將對社會運動的進行產生影響。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傳統的集體行動開始出現與互聯網結合的傾向,并出現了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讓個人的力量不再微薄”“溝通、自由、平等”“圍觀改變生活,圍觀就是力量”等,這些門戶網站的宣傳口號,體現出互聯網對現代人交流、溝通方式所帶來的改變。網絡風險事件涉及自然、政治、科技、社會等方面,既包括與大多數百姓相關的公共事件,也包括小范圍的個體性事件,它以互聯網為行動的基礎架構,打破了空間的界限,在更大的范圍內將人們聚集起來,使社會成員在意見表達過程中獲得參與感和社會認同感。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表現出兩種行動方式:一是在線集體行動,即以網絡為載體的集體行動,如網上簽名、網絡反腐等;二是離線集體行動,即緣起于互聯網的集體行動在現實空間中進行。
1.風險事件:網絡集體行動的邏輯起點
在風險事件中,由于集體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發“集體維權”“集體抗議”等群體性事件。西德尼·塔羅、布魯默、蒂利等是集體行動學說的代表人物。顧名思義,集體行動是以集體的力量進行的行動,集體行動中的個體有著共同的集體目標,這個目標通常是抵制或者支持某種社會變遷;集體行動既包括沖突性運動,也包括共意性運動。據此定義,群體性事件、集體維權、集體抗議等社會現象都屬于集體行動。②國內目前研究風險社會視域下的集體行為的學者主要有秦強、郭星華、鄭杭生等。秦強、
郭星華認為,轉型社會的過渡性、階段性和不穩定性特征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頻頻發生。從法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群體性事件的本質是發生在風險社會中的一種集群行為。該視角強調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景,即風險社會。風險社會是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根源,集群行為是群體性事件的本質特征。③鄭杭生、郭星華則指出,當各種問題和矛盾相互交錯、相互影響、日趨激化,社會運行機制不能及時有效地進行調整和控制,就必然會導致大量社會失范行為的發生,嚴重時引發群體性事件。④群體性事件的引發與一定的社會環境有關,在風險事件中,主客體及周圍環境等多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中,被卷入對象有相對剝奪感,這種不穩定狀態一旦激發即會導致集體行動的發酵和激化。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新舊交替的轉型過程中,存在著各類矛盾和沖突,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不穩定性為風險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必要條件。一般認為,特定的環境因素、社會角色的改變與行為的失范以及利益的相對剝奪感是集群行為產生所需要的條件。風險是一種社會建構,它“部分地是一種客觀的傷害威脅,部分地是文化和社會經驗的結果”⑤。因此,可以認為,風險社會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源,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存在著諸多的沖突和矛盾,潛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具備風險社會的特征。面對醫療、住房、腐敗等社會風險問題,由于社會成員在現實生活中缺乏及時有效地表達渠道,網絡所提供的虛擬空間為社會成員的意見表達和行動組織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平臺,使其在相對自由的表達過程中滿足在現實生活所不能獲得的社會認同感。
近年來,出現了許多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突發性事件,社會成員通過互聯網集結,以產生網絡輿論等形式為爭取相關利益進行抗爭和博弈,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網絡集體行動的產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風險事件的突發性以及不確定性能夠極大地刺激人們的集體意識,當發起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之時,或者說他們明確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并決定采取集體行動維護自己權益之時就爆發了集體行動。⑥可以說,風險事件的爆發導致了網絡集體行動,是網絡集體行動產生的邏輯起點。
2.離線集體行動與在線集體行動
網絡空間中的集體行動不僅延續了傳統集體行動的方式,并且能夠利用網絡的力量在更大的范圍內集結人群,使行動的范圍擴大化。此外,離線集體行動的方式,使得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同傳統集體行動一樣,不僅在網絡中進行,而且延續到現實空間中來。從現實到網絡再到現實,網絡作為集體行動的中介和連接點使事件發酵,再回到現實的抗爭或稱集體行動不再是真實的事件反應,而是社會成員對經過網絡加工后的事件的反應,這種反應作用于現實社會,在現實社會中進行,對傳統媒體行為方式和現實世界產生著影響。
與傳統集體行動相比,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離線集體行動一方面能夠通過互聯網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號召最多的人參與其中,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發生在現實世界,需要公眾的真實參與,其行動的進行方式和本質與傳統的集體行動無異。如2012年10月,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發生PX項目事件,網絡上掀起了對PX項目的討論,討論的焦點集中于對PX生產裝置是否會引發環境問題的擔憂。10月25日和26日鎮海區民眾進行了大規模的抗議,27日和28日在網絡的作用之下,抗議活動由鎮海區蔓延到寧波市中心,事件的影響一度擴大。這次抗爭引發了大量的媒體報道,吸引了全社會關于PX與環境問題的關注。最終,寧波市政府做出讓步,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并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⑦在寧波PX項目事件中,網絡發揮著運動組織者和影響擴大者的角色,與鎮海區少數村民利益相關的事件通過網絡的傳播影響擴大化。其過程是鎮海區村民的集體上訪引起了政府以及寧波市民的關注,寧波市民則通過網絡媒體、人際傳播等方式對鎮海區村民的集體上訪進行了解,最終演變成更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相比于傳統媒體在風險事件發生時的失語狀態,網絡媒體的即時性、互動性等特點發揮著更高的動員力,成為風險傳播中的強大力量。
在線集體行動是一種完全顛覆傳統集體行動的抗爭方式,它緣起于網絡,在網絡中進行,是一種發起于互聯網、進行于互聯網、真正通過互聯網實現的抗爭。互聯網的匿名性、跨地域性等特點為風險事件的抗爭提供了有利的發生條件,它能夠使群體在更大的范圍內集結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采取共同行動。如2015年5月3日,一段網友上傳的男司機街頭暴打女司機的視頻,上線半小時內點擊量過百萬,引發了網友的熱議與圍觀。縱觀整個事件的發展,在網絡群體壓力的作用下,輿論幾度急轉,由被打女司機視頻剛曝光時對男司機的譴責,到第二段行車記錄儀視頻曝光時指責女司機盧某,再到對盧某進行人肉搜索、人身攻擊直到盧某發表致歉,網絡暴力的聲音才逐漸趨于緩和。網絡所構建的虛擬空間使公眾在不明真相且匿名的狀態中更樂于發表自己的言論,并在“法不責眾”的心理驅使下做出種種宣泄,在網絡環境中主要以網絡言論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在線集體行動不是脫離現實環境而存在的,它受到現實環境的影響,同時反作用于現實環境,網絡輿論、網絡暴力影響事件的發展進程,事件的真相被掩蓋,網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網民是整個事件的主角,網絡群體性事件是網民的集體狂歡。
二、網絡集體行動的新特點
作為對社會現實的一種抗爭,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并不單純以在線集體行動或離線集體行動的方式進行,通常是兩種方式綜合的結果。不同于西方社會集體行動在制度上的合理性,在當前中國社會,集體行動被視作一種非制度化的行動,社會成員在表達意見的過程中缺乏暢通的渠道或面臨一定的阻礙。相比于純粹在現實環境中進行的集體行動,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能夠為群體成員提供更為便利的渠道,有效地降低了可能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因此,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現代集體行動也表現出新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行動范圍的擴大
互聯網的發展為群體性事件提供更大的便利性,這種便利性體現在其能夠打破空間的界限,使每一個網民無論身處何處都可以被動員起來。綜觀近幾年的群體性事件,都是借助網絡發揮著更大的影響。上文中提到的PX事件,非事發地的群眾也能夠通過互聯網,以“保護環境”“維護生存權益”等動員框架被納入到抗爭的體系中來。可見,互聯網作為動員的工具,擴大了行動的影響力和范圍。
2.成員間互動性的增強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組織渠道,網絡的虛擬空間為集體行動提供了一個虛擬的組織和活動平臺。集體行動的能量在于群體成員共意的達成,通過成員之間的互動、協商從而制定行動策略,采取行動,以達到預設的目的。相比于傳統的集體行動需要在現實空間中進行,這種基于新技術平臺形成的組織模式,使得群體成員通過微博、微信等通信工具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地展開協商和辯解,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進行互動和意見的交換,有助于集體意見的達成。
3.行動影響力的擴散
卡斯帕森認為,新聞媒體等社會放大站會對風險信號進行放大或者弱化。⑧互聯網是由文字、視頻、圖片等符號所構成的信息系統,群體成員通過這些符號進行交流和互動。基于互聯網的開放性等特性,群體成員的這種交流和互動能夠得到數量可觀的轉發及關注,這種呈數字級增長的影響力是傳統集體行動無法想象的。成都女司機被打事件本是關于當事者雙方的小規模事件,由于互聯網的連續發酵擴大了事件的影響范圍,網絡輿論甚至一度影響了事件的發展方向。互聯網作為話語平臺的提供者介入到事件的發展中來,它的傳播特性極大地擴散了集體行動的影響力,我們已經無法忽視互聯網的傳播力量及其可能產生的漣漪效應。
三、風險事件集體行動的動員機制:情感動員
當前網民的數量如此龐大,網絡不僅是信息傳播的工具,也成為網民情感交流與情感共鳴的場域。人們受情感的驅動在網絡虛擬世界抗爭,并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行為,而是社會沖突的道德語法的直接表現,其本質是爭取承認的政治或者說認同的政治。⑨集體行為的關鍵在于行動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人們的共鳴度,共鳴度越高,越能引發大家的圍觀關注和參與回應,也越能占據輿論中心,形成強大的社會影響力。⑩當前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認同危機,貧富差距加大,仇富、仇官等心理情緒普遍存在,社會中充滿了不信任、擔憂和焦慮。與西方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抗爭不同,中國社會的抗爭是一種體制外的抗爭,而網絡公共空間為公眾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民間輿論場,在此社會成員更傾向于表達意見,而且是一種情緒放大的表達。一旦某個風險事件經過網絡的傳播引起部分人的關注和討論,因社會性矛盾的存在而激發另一部分網友內心的認同和共鳴,這部分網民迅速集結起來構建集體身份,激發悲情、戲謔等情感,這些情感以網絡公共話語等形式表現并傳播,引發更大規模人群的認同和參與,形成網絡抗爭性行動。有些網絡話語抗爭會擴展到現實之中,形成線下的具體行動,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
1.網絡風險事件的情感動因
勒龐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集體行動中的非理性因素,認為個人作為個體時是理性、有教養、有文化的,但隨著聚眾的發展,個體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會逐漸變得野蠻和非理性化,人們有時會殘暴無情,整個群體行為會趨向于一種非理性的方式,集體行動主要是非理性的產物。國內學者對群體事件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強調了情感在群體性事件中的重要性。應星從“氣”和“氣場”來解釋集體行動中暴力如何產生,認為“維權行動激發出一個“氣場”。沙蓮香對群體心理進行研究后指出,典型的群體心理表現在群體成員的“我們”的情感上,也就是用“我們”的心理構成區別于其他群體的心理構成。“我們”的情感,就是反映了群體成員對共同心理的意識。楊國斌在對網絡事件動員機制進行研究時指出網絡事件的動員所依賴的是能夠激發網民的嬉笑怒罵、喜怒哀樂等情感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網絡事件的發生是一個情感動員的過程。綜上,本文認為,集體行動是體制外的,有非理性的成分,網絡風險事件的集合動因來自于情感的表達,群體成員受到感染和動員參與其中,風險事件的爆發是集體行動的邏輯起點。因此,如何揭示網絡風險事件的抗爭劇目和動員機制,是厘清網絡風險事件社會影響的關鍵所在。
當前中國的社會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尚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由于在現實生活中缺乏有效暢通的意見表達渠道,網絡相對自由的環境和平臺為公眾提供了發泄不滿情緒的空間,仇富、仇官等心理引發的網絡事件時有發生。霍耐特認為,社會秩序的維持依賴人們之間的相互承認,而這種承認有著不成文的規則。當這些規則受到侵犯時,也即一方沒有遵守規則時,受侵犯者的個人尊嚴和個人價值便受到了損害,導致感情受傷害。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之中,“劫貧濟富”為正義之舉,對弱者的同情、對強者的痛恨是在“情理之中”、符合“人之常情”的。因此,涉及特權階層、強弱力量對比的事件總能引發大范圍的關注,網友通過網絡平臺的調侃諷刺甚至破口大罵都能左右網絡輿論。
2.共同身份建構與集體造勢
社會運動中情感動員的主要方式是情感的表達。情感表達依賴各種載體和象征手段,如話語、音樂、漫畫、詩歌、順口溜、口號等。在互聯網和新媒體時代,這些傳統的表達方式被賦予新的能量,傳播面廣、速度快、發布管道多,同時也出現了視頻、短信、閃客、播客、博客等新的表達方式。網絡空間中進行的集體行動多通過網民發表言論即形成網絡輿論的方式進行,話語是網民集體抗爭的主要武器,而情感動員在網絡事件的發生機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1994年的朱令案件隨著2013年4月復旦黃洋案再次浮出水面,引發了社會的熱議,受害人同樣是有前途的名校學生、同樣被投毒。時隔近20年,朱令案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復旦投毒案發生后,當年的懷疑對象孫某也再次遭到網絡輿論的審問。天涯和新浪微博不斷有網友蓋樓發帖,要求制裁孫某;甚至數十萬網民集體向白宮情愿,要求美國政府遣回孫某并對其進行調查。在朱令案件中,孫某與朱令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是激發網友憤怒的重要導火索,孫某的高官家庭背景與朱令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對比,孫某事業成功、生活幸福與朱令躺在病床上、智商只有十多歲、需要父母服侍的對比。在這個事件中,社會成員通過共同身份的構建集合起來,使社會成員有共同的情感歸屬。這種情感一是來自于對弱者的同情,二是對所謂的“逍遙法外者”及其家庭背景的集體憤怒。在集體行動中網民通過發表自己的言論和意見宣泄情感,這種臨時構建起來的群體在意見表達中體現集體歸屬感,他們期望通過群體的力量發出共同的聲音,改變事件的進程。
3.構建群體成員的集體記憶
在風險事件的集體行動中,網民是主要的參與者。上文分析的朱令案件通過網民的集體行動和反復提起構建了網民的集體記憶。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看,集體記憶是由群體或現代社會所共享、傳承和建構的。網絡建構了一個虛擬社會并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保存的信息建構起現代人關于當代社會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依賴媒介、圖像或各種集體活動來保存、強化或重溫,一旦有相似事件發生,朱令案件就會重出水面引發社會的討論并使公眾重新集結起來。這些相似的事件平時淹沒于海量的網絡信息之中,但它們已經通過某種關聯被連接了起來,同類事件的發生必然掀起一連串關于此類事件的討論,這種連鎖反應是人們從互聯網中所獲得的集體記憶。
四、結論與反思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著諸多的風險問題,互聯網改變了整個社會運行的基礎架構,基于互聯網的新媒介的出現為風險事件提供了新的滋生土壤。相比于傳統的集體行動,網絡風險事件中的集體行動必然存在著新的動員機制及抗爭方式,具體而言,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風險事件的頻發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各方面存在著力量不均衡的狀況,具備風險社會的特征。一般認為,特定的環境因素、社會角色的改變與行為的失范以及利益的相對剝奪感是集群行為產生所需要的條件。群體性事件的爆發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風險事件的爆發是群體性事件產生的邏輯起點。
第二,集體行動開始出現與互聯網結合的傾向。網絡為集體行動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相比于傳統的集體行動,互聯網的開放性、匿名性等特點更能滿足社會成員的意見訴求。與西方制度化的集體行動不同,中國的集體行動是一種體制外的行動,網絡空間為網民提供了較為自由的言論平臺。
第三,在網絡這個平臺中,語言是網民的主要武器,而情感的動員能夠有效地刺激網民的集體意識,使網民在網絡空間內迅速集結起來。他們不歸屬于任何組織卻能夠表現出組織力量,能在意見表達中產生驚人的影響,通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方式,左右網絡輿論的走向以達成行動的目標,并將其影響從網絡延伸到現實,最終建構社會成員的集體記憶。
總體而言,風險事件的爆發是群體性事件產生的邏輯起點,然而,與西方制度化的集體行動相比,當前的中國網絡生態環境下,公眾缺乏表達意見的有效途徑,往往通過情感動員的方式聚集起來,并渴求通過集體的力量發出共同的聲音,改變事件的進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體制外的參與表現出公眾意見表達的強烈愿望。因此,關注底層人民需求,安撫公眾情緒,逐漸建立制度化的意見表達渠道,塑造良好的網絡語言環境是規范網絡集體行動的必要途徑。
注釋
①參見R. Koopmans.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Waves: West Germany,1965 to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3, Vol.58, No.5, pp.637—658.②參見蔡前:《以互聯網為媒介的集體行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頁。③參見秦強、郭星華:《風險社會中的集群行為——法社會學視閾中的群體性事件及其解決機制》,《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第2期。④參見鄭杭生、郭星華:《中國社會的轉型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浙江學刊》2004第2期。⑤R. E. Kaspers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Progress in Develop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Risk. in Sheldon Krimsky, Dominic Golding (eds.).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Westport, CT:Praeger, 1992, pp.153—178.⑥參見李華俊:《網絡集體行動組織結構與核心機制研究——組織動員理論視角的引入》,上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48—55頁。⑦筆者整理于網絡資料。⑧參見[英]皮金、[英]卡斯帕森、[英]斯洛維奇編:《風險的社會放大》,譚宏凱譯,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0年,第10—23頁。⑨轉引自謝金林:《情感與網絡抗爭動員——基于湖北“石首事件”》,《公共管理學報》2012第1期。⑩參見楊江華、鄢佩:《集體行為視野下的網絡走紅現象探析》,《中州學刊》2015年第10期。參見[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6—38頁。參見應星:《氣場與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兩個個案的比較》,《社會學研究》2009第6期。參見沙蓮香:《社會心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3頁。參見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第9期,2009年出版。參見[德]阿克塞爾·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胡繼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0頁。
責任編輯:沐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