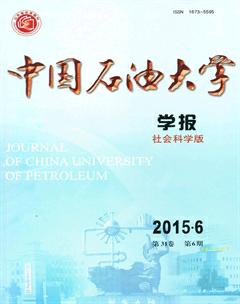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演進
張永寧+沈霽華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演進可以歸結為形成、發展、修正和融合四個階段,整體呈現出政策內容逐漸細化、政策結構逐漸系統化、政策工具逐漸多元化、政策層次和法律效力不斷提升的特征。面對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的趨勢,政府需進一步利用后發優勢,提升政策的整體性和協同性,發揮市場型和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作用。
關鍵詞:節能減排;政策演進;政策文本;政策工具
中圖分類號:X-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6)06-0001-05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針對節約能源和減少污染排放的公共政策陸續出臺。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時期的節能減排政策呈現出不同的結構特征,形成了政策演進的不同階段。系統梳理各個階段的政策及其特征,并在公共政策相關理論框架指導下進行分析,有助于進一步理解節能減排政策的制定及作用規律,預測其發展趨勢,提出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優化路徑。
一、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演進過程
節能減排的本質是節約能源,減少環境有害物的排放。節能減排政策的產生,源自解決資源、能源消費的環境外部性及稀缺性問題。[1]《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將節能減排政策界定為“節能節水、減少SO2和COD排放、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以及發展或使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2]。中國現行的節能減排政策,可分為法律法規和財稅政策兩大類。其中,法律法規包括國家發展規劃、節能減排相關法律和法規條例;財稅政策包括節能減排稅收優惠政策和財政補貼等。另外,圍繞節能減排政策而進行的管理體制改革,節能減排技術和標準的推廣應用,也屬于節能減排政策的范疇。[3]1978年以來,中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節能減排相關政策。根據政策的出臺時間、時代背景和內容特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節能政策與減排政策并行的政策形成階段(1978—1988)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相比1978年版憲法,1982年版憲法明確了環境保護的范圍和內容,突出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普通法律的根本依據。依據憲法,1979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三十二字方針”,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環境保護的專門法律。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能源緊缺逐漸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1980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節約能源工作的報告》和《關于逐步建立綜合能耗考核制度的通知》,將節能減排的重要意義提高到“不僅影響著國民經濟,更是代表了社會發展的程度”,確立了“節約與開發并重,充分發揮資源的可利用率”的政策方針。國家成立了專門管理機構,把節能作為一項專門工作納入國家宏觀管理范疇,從而確立了節能在能源發展中的戰略地位。為了進一步推廣節能技術,自1982年起,國務院相繼發布了《對工礦企業和城市節約能源的若干具體要求(試行)》《超定額耗用燃料加價收費實施辦法》《關于按省、市、自治區實行計劃用電包干的暫行管理辦法》和《中國節能技術政策大綱》。在此基礎上,1986年《節約能源管理暫行條例》進一步完善了節能技術政策,提出了對工業企業實行合理用能、合理布局的原則。同時條例重視節能技術的開發和推廣,對節能技術改造和應用科研采取扶持政策,重大節能技術納入國家重點科研計劃;加快節能法規、標準和規范的制定。本條例有效促進了中國能源的合理開發和使用。
為了減少污染物排放、治理環境污染,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標準管理辦法》對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制定了相應標準。198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防治水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的法律,是水污染防治領域的專項法律,全面規定了水污染治理的管理體制和基本制度。1985年《工業企業環境保護考核制度實施辦法(試行)》,明確了各工業企業要以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協調發展為目標,充分利用一切能源資源,盡可能地采用無污染工藝,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二)節能減排上升為基本國策的政策發展階段(1989—1999)
1989年全國人大修訂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該法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實施十年來的經驗教訓,確立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原則,推動了單行環境法律法規的創制,標志著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進入了法制化階段。[4]1990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開篇強調:“保護和改善生產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加大城市環境監護力度,治理工業污染。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針對大氣污染做出了相關規定,明確大氣污染的范圍和內容,提出防治大氣污染的更高要求和目標,要求地方政府運用多種手段來保證本地區的大氣質量。1996年《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抓緊建立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指標體系和定期公布制度,實行環境質量行政領導負責制。
鑒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1995年《關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報告》《1996—201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綱要》鼓勵開發風能、太陽能和地熱能等新能源,使新能源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明確節約資源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國家實施節約與開發并舉、把節約放在首位的能源發展戰略,制定節能標準與能耗限額,淘汰落后高能耗產品,加強重點用能單位的管理,完善節能優惠政策、技術政策,要求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盡可能減少單位產值能耗和單位產品能耗,努力建設資源節能型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確定了節能在中國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使節能工作有法可依,為節能行動提供了法律保障,有效促進了節能減排工作的發展。1999年《重點用能單位節能管理辦法》規定了重點用能單位每年最大限度使用能源的數量,要求促進節能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減少環境污染。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政策修正階段(2000—2008)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環境保護、能源安全的壓力越來越大,節能減排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00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把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同時,市場機制在節能減排中的作用得到重視。2000年《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交通行業實施節能法細則》《關于加強工業節水工作的意見》體現了這一點。2004年《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04—2020年)》(草案),提出堅持和實施節能優先的方針,制定和實施統一協調的促進節能的能源和環境政策、促進結構調整的產業政策、強化節能的激勵政策,加大依法實施節能管理的力度,加快節能技術開發、示范和推廣,推行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節能新機制。2005年《關于做好建設節約型社會近期重點工作的通知》,提出圍繞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這一核心,重點發展循環經濟,鼓勵節能、節水、節材、節地與資源的綜合利用,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2007年《國務院批轉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及考核實施方案和辦法的通知》建立了全套的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和審核三大體系,標志著中國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得到了落實。
面對中國重大水域嚴重污染的嚴峻事實,2000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進一步強調對水污染的監督管理,細化法律責任,加大處罰力度。隨后國務院相繼批復了太湖流域、巢湖流域、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十五”計劃。2008年環保部出臺《關于加強重點湖泊水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要“以污染物減排為核心,以保障飲用水安全為重點,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堅持不懈地推進全面、系統、科學、嚴格的污染治理”。200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進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的責任,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并且進一步保障公眾參與的權利。
(四)發展生態文明的政策融合階段(2009至今)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主題是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與之相對應,中國節能減排政策法規增加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內容。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為引導,節能減排工作的重點轉向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促進生態保護和修復。2011年《“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明確了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要求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大力推進節能降耗,加快建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體系,大力推動全社會低碳節能行動。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布局中,實行“五位一體”,這是中央報告首次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大建設并列,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報告倡導“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理念,旨在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對后續的節能減排政策產生深遠影響。2014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和2016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都體現了十八大的精神和要求。
《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要求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發展低能耗低排放產業,優化能源消費結構;狠抓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節能降碳;從價格、財稅、綠色融資等方面進行政策扶持,推行市場化節能減排機制,加強監測預警和監督檢查,落實各級目標責任。2016年的《工業節能管理辦法》要求重點做好節能管理、節能監察、落實企業主體地位和重點抓用能大戶等工作,提升工業企業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業綠色低碳發展和轉型升級。
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第十篇強調,“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要求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其中規劃第四十三章提出“樹立節約集約循環利用的資源觀,推動資源利用方式根本轉變”,第四十四章提出“創新環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強化排污者主體責任,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這些理念將直接影響下一階段節能減排政策的走向。
二、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演進特征
從政策特點、政策結構、政策工具及其法律效力的視角進行分析,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發展軌跡呈現出四個特點和趨勢。
(一)政策內容:從宏觀到具體,節能減排的措施和指標逐漸細化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節能減排政策起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多見于《中國節能技術政策大綱》等較為宏觀的文件中。其中對節能減排的相關規定也基本是粗線條的,規定中國節能減排工作采用政府管理體制。進入20世紀90年代第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實施細則》等相關文件對節能減排的規定開始呈現細化的傾向,并明確了大氣污染的范圍和內容,提出了大氣污染防治的標準和目標。進入21世紀后的修正階段,以《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等形式出臺的政策,對排放種類、數量、排污費的征收和使用標準,以及處罰方法等的規定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十二五”規劃以來,國家有關節能減排相關政策規定更加細化,地方層面也相繼出臺政策并制定具體措施,如《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重點行業大氣污染限期治理方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等。實踐證明,具體細化的政策內容,有助于政策的落實和責任的追究。
(二)政策結構:從并行到整合,節能與減排的目標逐漸系統化
20世紀80年代初期關于節能的相關政策比較集中,而減排政策相對較少,符合當時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問題尚不突出的客觀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頒布后,控制排放、防止污染的政策文件數量增加。總體來看,節能政策與減排政策盡管都上升為國策地位,但基本上屬于各自并行分立,各自頒布實施和考核。進入21世紀以后,政府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節能政策和減排政策開始融合,如《國務院批轉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及考核實施方案和辦法的通知》涵蓋能源消耗考核方案和減排政策考核辦法,《2014—2015年節能減排低碳發展行動方案》要求發展低能耗低排放產業,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另外,與早期政策相比,2000年以來節能減排政策進入國家發展規劃和黨代會報告,節能減排政策逐漸呈現出系統化態勢,同時表明政策決策層次逐漸提升。
(三)政策工具:從規制型逐漸走向規制型、市場型和信息型的復合
政策工具是政府有效治理的途徑和手段。[5]能否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政策工具的選擇至關重要。在節能減排政策的形成和發展階段,政府主要使用規制型政策工具,運用直接供給和管制的方式實現政策目標,如1986年的《節約能源管理暫行條例》。進入第二階段后,政府開始采用市場型政策工具,通過市場機制、價格杠桿來影響組織和公眾的行為方式選擇,如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提出完善節能優惠政策。進入第三階段,市場型政策工具得到普遍采用。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公眾環境意識的普遍提高,政府開始重視信息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通過環境信息公開、環境標志和公眾參與來實現預定的政策目標。如2007年《節能減排統計監測及考核實施方案和辦法》關于節能減排的統計監測、2011年《“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關于溫室氣體排放的統計核算。目前,中國政府基本形成了規制型、市場型和信息型三種政策工具復合使用的工具體系,其中規制型工具仍然占據主導地位。2016年“十三五”規劃提出“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預示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在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的過程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政策效力:從經濟和環保領域走向政治領域,政策層次和法律效力不斷提升
鑒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帶來的能源枯竭和環境污染雙重壓力,加之近年來極端氣候現象頻發、大范圍空氣污染的嚴峻形勢,節能減排政策逐漸從早期的經濟領域和環保領域逐漸向政治領域轉移,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并出現在黨代表大會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等重要的政治文件中,表明節能減排政策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地位逐漸提升。特別是亞運會、奧運會、世博會、APEC等重要會議期間,相關區域內的地方政府出臺并執行緊急狀態下大氣污染防治措施,采取超常規手段保障會議期間空氣質量,將節能減排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升至政治的高度,實踐效果十分明顯。同時,節能減排政策的法律效力也呈現逐漸提升的態勢。特別是節能、大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等相關法律規范的多次修訂,以法律形式進一步強化了節能減排政策的法律效力和執行力。整體來看,中國的節能減排政策由行政命令主導向經濟手段、法律法規為主導的方向逐漸轉變。[1]
三、結論與反思
政策分析過程具有能動性,需要借助客觀而精確的處理方法來提高分析的解釋力。
[6]同時政策分析又是一個系統、復雜的科學,政策分析者要運用多元的方法、政策模式,以形成政策知識和主張。[7]
分析發現,中國節能減排政策呈現正態的發展軌跡,依據政策特點、結構、政策工具及其法律效力的分析框架,可以將這一發展軌跡總結為:政策內容從宏觀到具體逐漸細化,政策結構從并行到整合逐漸系統化,政策工具從規制型為主到規制型、市場型和信息型三者的有機結合,政策層次和法律效力不斷提升。這一軌跡與西方發達國家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節能減排政策的發展軌跡存在較高的相似性。從“政策情境—政策表達—政策結局”的視角出發,這一變遷軌跡回應了中國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進程中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壓力逐漸增大的現實情境。[8]盡管本文主要基于政策內容文本挖掘,未涉及政策效果評價,但結合前期文獻研究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在遏制高能耗、高污染這一問題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效是值得肯定的,節能減排政策對遏制高能耗和高污染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樹立節能減排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等政策目標對節能、減排和經濟效果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值得關注的是,防治污染目標和產業升級目標對經濟效果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9]
盡管中國節能減排政策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整體能耗和環境治理績效仍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所致,另一方面要反思政策的有效性。首先,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充分重視后發優勢和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探索發達國家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能耗和污染的一般規律,并著力思考如何跳出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軌跡。其次,要跳出“各自為戰”的碎片化模式,實現政策協同。資源協同與服務協同、政策協同與管理協同,是打破治理結構碎片化、實現協同治理的核心要素。[10]為此,要加強不同政策部門、不同地方政府的統籌規劃與協調配合,增強不同政策之間的協同性、減少“政策打架”是建立協同節能減排模式的關鍵。再次,要進一步推進政策工具的多元化與多樣性,特別是進一步增加市場激勵型政策工具和信息型政策工具的比重。只有充分發揮規制型政策工具、市場型政策工具和信息型政策工具的協同作用,調動企業和公眾節能減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才有利于實現社會各個層面從“被動節能”向“主動節能”、從“不敢排污”向“不想排污”的轉變,從而全面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曾凡銀. 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理論框架與實踐分析[J]. 財貿經濟,2010(7):110-115.
[2] 張國興,高秀林,王應洛,等.中國節能減排政策的測量、協同與演變——基于1978—2013年政策數據的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12):63.
[3] 林艷.我國節能減排政策的優化策略研究[J].理論月刊,2016(3):162-167.
[4] 王曦,陳維春.論1989年《環境保護法》之歷史功績與歷史局限性[J].時代法學,2004(4):3-7.
[5] 甘黎黎.我國環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及其優化[J].江西社會科學,2014(6):199-204.
[6] 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5:5-6.
[7] William N Dunn.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3:62-63.
[8] 張永寧,李輝,叢男,等.“情境—表達—結局”框架下中國減排政策變遷與反思——以“五年規劃”為線索的文本挖掘[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33(20):109-114.
[9] 張國興,張振華.我國節能減排政策目標的有效性分析——基于1502條節能減排政策的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5,29(11):88-95.
[10] 李輝.協同型政府: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100-107.
責任編輯:張巖林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the evolu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policies in China can be generalized as four stages: formation, development, mod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general, it shows the following change tracks: the policy content is gradually refined; the policy structure becomes systematized; the policy tools become diversified; and the policy level and legal effect upgrades continuously. Faced with repaid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further use of late-mover advantages, improve the integrity and synergy of polic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licy tools both of incentive and information.
Key wo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text; policy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