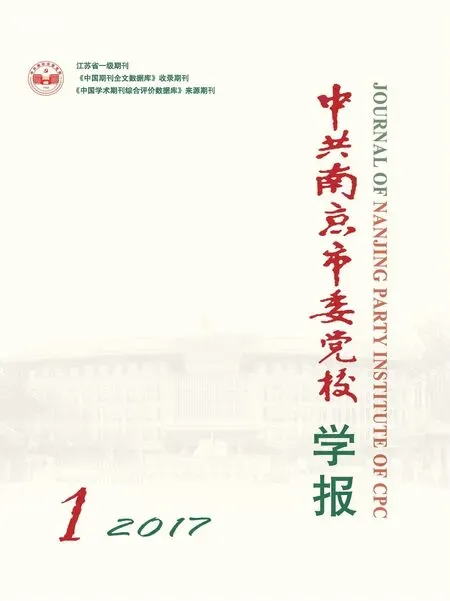論政治領導過程中的非制度性約束*
夏慶宇
(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 上海 楊浦 200433)
論政治領導過程中的非制度性約束*
夏慶宇
(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 上海 楊浦 200433)
既往的政治學研究較為關注政治制度對政治行為的監督、制約作用,并未對行政主體在領導過程中受到的非制度性約束進行集中的理論表述。這種研究現狀反映了一種認識盲區,即未曾注意到任何政治領導者都會受到并未成為明確的制度設計的制約因素的約束。這些非制度性的約束因素可分為主觀因素(如中國古代社會中存在的“天命觀”、“仁政觀”)、客觀因素。客觀的非制度性約束因素主要包括:客觀現實對政治領導者所構成的約束、被領導者對政治領導者所構成的約束。這些非制度性的約束因素在現實政治中發揮著切實而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政治治理趨于“善治”而非“虐政”。研究政治現象時應注意到這些因素及其作用。因此在衡量不同政治體制的“法治”化水平時,不能僅僅以制度性約束的指標的高低為衡量標準,而應將非制度性約束的強度納入指標體系之中。
約束;制約;制衡;制度;領導
一、引言:本論文的研究意義
美國社會科學界對社會科學論文的意義的一般理解是:論文必須揭示前人并未闡明的、社會現象背后的因果機制(即提出某種理論)。然而,屬于人文學科的歷史學科則一般不要求論文必須對社會現象背后的運行機理進行解釋,而只要求論文對前人未曾厘清的歷史事實進行陳述。也就是說,社會科學論文以提供“理論”為宗旨,人文學科論文以提供“知識”為宗旨。
綜合以上兩種論文寫作規范,似可以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論文的共同的意義作這樣一個比喻:論者看到了其他人未看到的事物并將其告訴給其他人的過程,便是寫作論文的過程。所謂“其他人未看到的事物”,既包括現象、也包括現象背后的機制。
本文的寫作主題,即是迄今為止其他人并未充分闡述過的、關于政治領導過程的一些現象——即:在任何政治領導過程中不僅存在著對政治領導者的制度性約束,而且存在著大量的非制度性約束;從古至今,非制度性的約束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政治領導者的行為,使政治領導者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善治并使所有政治領導行為都呈現出某些跨時空的共性。
例如,傳統上人們認為法治誕生于近代西方社會。法治的本質含義是:政治機構、政治過程受到成文的(即明確的)規定(即憲法、行政法等關于政權設置、運作的法律)的制約、約束。(一般而言,“法”包括民法、商法、刑法、國際法等法律,而“法治”的基本含義是政治機構、政治過程受到“法”的約束而不是非政府行為如民事行為受到“法”的約束,因此本文認為用“憲政”來代替“法治”能夠更恰當地體現中文中“法治”一詞的本義。)但是在近代之前,不論在東方、西方,政治領導者歷來均受到多種束縛,這些束縛雖然并一定來自明文的規定、明確的制度,但的確發揮著不可否認的現實約束力。
例如在中世紀時期的西歐,日耳曼人實行封建制度,各級封建領主之間實際存在著“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契約關系,上級封建主將封地封給封臣之后,封臣有義務忠于封建主,在戰時派兵隨封建主作戰,但是封建主一般不能也不會干預封臣領地內部的事務。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的這種傳統習慣約束了日耳曼族領導人,使國王的權力受到極大的削弱,因此西歐國家在中世紀呈現出各地封建割據嚴重、一盤散沙、王權衰落、治權不斷下移的局面。
又如中國古代并未出現西方的“三權分立”思想——“三權分立”的本質是讓三種不同的權力相互制約,因此在三權分立制度下,實際上一個國家并無最高掌權者(例如美國總統只是最高行政長官,而不是最高司法長官或立法長官),這種思路與中國古代主流的大一統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盡管如此,中國古代也有“制約與平衡”的觀念,例如《元史·列傳·卷六十三》記載:“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由此可見中國的先人們明白:一個部門的權力過大則會出問題,因此要通過合理權力分工限制某個部門權力過大、濫用權力。又如朱元璋曾明確指出各衙門之間要實行制約與平衡:“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1]
盡管中國古代的主流政治文化認為只有一個最高領導者將更有利于國家,但是中國古代的最高領導者也不是可以為所欲為的,他的行為至少要符合當時人們的是否觀念。例如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明確指出:“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與這種觀念相似,《北史·本紀·卷二》描述北魏世祖拓跋燾“明于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著針對統治者的不成文但又切實存在的評價標準,如果皇帝的行為背離這種標準也會遭到臣民的非議。
中國古代的許多皇帝甚至自覺地形成了法治觀念。拓跋燾就“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另外《元史·列傳·卷六十三》記載謝讓的事跡:“讓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圣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朱元璋也指出:“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平康。”[2]由此可見,中國古代不是不存在法治——至少存在法治因素。
另外,中國古代也有分權的思想——例如六部各司其職,權限分明。盡管刑部須要受皇帝管理,但“刑部,天下持平”(《元史·列傳·卷七》)的理念難道不是“司法權獨立”的理念嗎?因此,認為“司法權獨立”的概念是孟德斯鳩首先提出來的,似乎并不準確。
由此,本文認為,在古今中外任何政治領導過程中都存在不成文的、非制度性的對領導者的制約因素。隨便翻翻歷史書就會發現:高高在上的掌權者們很不自由。不論是居于“至尊”之位的皇帝還是手握兵權的梟雄,不論是國王還是蘇丹,在執政過程中都在事實上受到許多掣肘。盡管中國古代尚沒有后來從西方舶來的“三權分立”的觀念,但是掌權者也不是為所欲為的,都是在一定的“規范”內活動。有些“規范”形成了明確的制度設計或成文的規定,例如中國古代歷史悠久的史官、言官、諫官制度,歷朝歷代的“祖宗之法”;有些規范則未成為明確的制度設計但卻現實地存在著。非制度性的規范、制約因素可以大致分為主觀的約束因素、客觀的約束因素兩類。
二、政治領導過程中的主觀的非制度性約束因素
這類因素包括兩類:第一,能夠起到約束政治領導者的行為的作用的物議性、社會輿論性因素。例如,周厲王之所以令人民道路以目,是因為人民的物議在一定程度上對周王起著制約作用。最終周厲王因為人民暴動而被流放,這顯示了人心是能夠對封建統治者構成強力的約束的。又如,中國古代的“德治”、“以正治國”、“天命”、“天道”、“德配天地”觀念自周初以來就成為了君、臣、民都認可的政治共識,這種共識使統治者的“失德”的政治行為受到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的否定,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統治者的行為。第二,能夠約束政治領導者的思想、進而能夠約束政治領導者的行為的因素(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會影響其行為)。例如,中國古代統治者一般相信天人感應,天子代表天統治人民,因此天子的行為必須符合天的意志,例如不能驕奢淫逸、要愛民如子。這種思想會對封建帝王形成約束,例如當大旱、蝗災等天災發生時,封建帝王一般會反躬自省、考慮自己的行為有哪些失德的地方、下“罪己詔”、改變失德之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封建帝王在行為時也會有所顧忌。
從形式上說,上述兩類制約因素是主觀的,從有關制約因素的客觀存在和其發揮的現實作用方面來說,上述制約因素又是客觀的。下面以中國古代的“天命”觀念對統治者所產生的約束作用為例進行剖析。
中國古代的“天命觀”指的是一個王朝的興替是由天意所決定的,而天決定讓一個王朝興、亡的標準是統治者的行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是否符合德治的標準。如朱元璋就明確指出:“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受天之眷顧。若生怠慢,禍必加焉,可不畏哉?”[3]其實,這類“天命觀”的具體內容是封建王朝對客觀現實進行認識、總結之后形成的產物。往往在實行暴政的王朝滅亡之后,新興的朝代會看到前朝的經驗教訓,這時統治集團內部的“天命”意識會最為強烈。因此,“天命”是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治國理政進行的經驗總結、是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經驗教訓,是反映社會的客觀需要的一種觀念,它事實上反映的是人民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統治者過于殘暴,人民將推翻統治者,從而統治者便失去了“天命”。按照上述理解,“天命觀”也不是中國獨有的,西方的“自然法(natural law)”觀念與“天命觀”相通,都是人對自身所受到的客觀世界的現實約束的一種認識——但是“天命觀”帶有濃厚的道德觀念和神秘主義色彩,這是“自然法”觀念所不具備的。
所謂“天命”必然是某種高尚的東西,因此“天命觀”內含著統治者必須推崇道德的含義,這就意味著統治者不能“無道”、不能“缺德”,要仁民愛物、克己復禮、修齊治平。“天命觀”中的“以德配天”、“天命不常”思想主要是對統治者提出的道德、行為要求。因此可以說,“天命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法治觀念。“天命觀”要求任何人——特別是統治者——都不能違背“天命”,這也就意味著天子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范、政治權力要受到約束。因此,“天命觀”無疑會對中國古代統治者形成約束。道德、法律都能夠約束人的行為,“天命觀”本身體現了對統治者的約束,本身就發揮了行政法的作用。盡管“天命觀”在約束執政者的行為方面屬于一種軟約束,但有時也能變成硬約束。例如意識里深植了“德治”觀念的大臣直言進諫、面折廷爭、以死明志,有時候是能夠對皇帝構成很強的約束的,這類令皇帝收回成命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俯拾皆是。
“天命觀”植根于中國古代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的思維之中,連最底層的庶民都有這樣的觀念:皇帝是“有道”還是“無道”,官員“為不為民做主”。這無疑反映出中國古代社會都認為皇帝必須“循道而行”,官員必須“為民父母”,這種觀念乃是一種洋溢于全社會的正能量,形成了一種制約政權的社會文化氛圍。至于進入統治階層的、受到這種思想熏陶的、有良知、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在維護善治方面發揮的作用會更大,因為他們更接近權力、更能夠直接約束統治者的不良行為。與其它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古代士大夫階級的“義”與“非義”的觀念非常強烈,成為中國傳統官僚的一種顯著特點。
三、政治領導過程中的客觀的非制度性約束因素
這類因素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領導者受到客觀現實的約束。例如不論是奴隸主階級統治者還是封建主階級擔任國家的統治者,只要國家發生了水災,都必須組織救災,這是因為:有了被統治者,統治者的存在才有意義;如果被統治者出現了生存危機,那么統治者的好日子也不會長久。而后,在治理水災的過程中,領導者的行動還必須符合水利工程的原理——不論誰當領導者,最終所能采取的行動都必須是符合水利原理的而不能違背有關客觀規律,不論誰當統治者都必須遵循有關水利原理、最終做出相同的決策。由此就可以看出客觀現實、客觀世界的現實規定性對領導者的行為所構成的約束。
可以說,客觀現實決定了所有政權都必須遵守一些盡管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又真實存在的規范。這種規范意味著統治者在行動時必須避免一些禁忌、必須完成一些工作、必須照顧到一些情況、必須符合客觀規律,否則政權的統治或治理就會出現問題。
閱讀歷史可以看出,不論何人“坐天下”,有些“規范”是必須遵守的。比如不能搞得民不聊生,否則就是自取滅亡;相反還要發展生產、改善民生,因為政權的經費來源于民間,來源于人民創造財富。政府必須承擔起一些公共職能、提供一些公共產品,比如敵國來犯不能不應對、社會秩序不能不維護、生產不能不予以鼓勵、統治機構自身的穩定不能不維持、在文化教育領域政府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發生天災不能不管,等等。如朱元璋曾告誡子孫:“四方有水旱等災,當驗國之所積,于被災去處優免稅糧。”[4]
統治其實也是一種重擔,統治也不能只取不予,統治的同時也要承擔責任。要想統治得越久,須要承擔的責任、完成的事業就越多,統治者就越不自由。對自己負責任的掌權者、明智的掌權者會活得非常累——累了一輩子的康熙、“累死”了的雍正就是典型例子(雍正長年勤于政事、身體每況愈下,最終吃了術士煉的丹藥而暴斃)。例如朱元璋如此自述勤政的情況:“察情觀變,慮患防危,如履淵冰,心膽為之不寧。晚朝畢而入,清朝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也。”[5]
在面對“天下”時,統治者須要處理許多涉及人民生計的事情;在管理統治集團時,統治者則要付出更多的辛勞。最危險的敵人往往就在身邊,統治者不僅要防范統治集團內部的陰謀家,也要注重統治集團內部的平衡。例如皇帝要想任命一名官員,通常也要考慮某官吏的資歷能不能降服下屬、其他官員會不會有意見等情況再作出任命;要想冊封一名嬪妃,也不能不考慮其它嬪妃背后的勢力會有什么反應、該決定是否會對統治帶來不利影響。
因此可以說,現實中就客觀地存在著一些針對統治者的不成文的“規范”,明智的統治者能感受到它們并會順從它們。即便是統治者也不能打破這種天然存在的“規范”,否則統治集團內部、外部就會出問題。這些就是本文所謂的“客觀環境對政治領導者的行為的規范”。這是一種普世性的約束,一切政權只要顧及到相應的利害,都會遵守這些規范。這類規范永遠存在、永恒發揮作用,這是因為“統治”本身就不是自由的,世界上也沒有什么人是完全自由的,最高封建統治者亦不例外。這些規范也決定:不論是何種政權,都不能過度侵害被統治者的利益,否則這個政權必然垮塌。因此,古今中外都不可能出現暴政長期維持的狀況。
值得指出,客觀環境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的行為,但是也有例外,例外之一是政治領導者不一定能夠意識到客觀環境決定他應當做的、對他來說最有利的行為是什么;例外之二是政治領導者有時可能會做違背自己利益的事。與客觀環境相比,更加直接地決定人的行為的是人的思想、想法。如果客觀環境決定了一個領導者采取一種行動會對自己有利、反之就有害,但是這個領導者認識不到這種客觀現實或者執意不按照這種客觀要求去做,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沿著客觀現實所規定的道路行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最終自取滅亡。因此非制度性約束因素并不總是能夠約束政治領導者的行為,但如果政治領導者執意不受非制度性約束因素(如民意)的約束,那么其政治領導就有可能很快結束——例如在民不聊生時爆發農民起義。由此可見,社會本身具有對暴政的約束機制,當暴政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滅亡,因此任何政府的行為都面臨著潛在的限制。
第二,領導者受到被領導者的約束。可以說,領導者領導被領導者的過程,其實也是被領導者“領導”領導者的過程。這句話的意思是,任何一個領導者的位置都不是天然能夠維持下去的,從根本上說,領導者必須符合被領導者的期望,才能成為領導者并維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因此,不論是否實行民主政體,領導者一定會受到被領導者的束縛,只不過在民主制下,被領導者對領導者的束縛表現得比較明顯而已。但在君主制等制度下,被領導者會對領導者構成不那么明顯但同樣強大的約束。
被領導者往往有擺脫被領導地位、自己成為領導者的意圖。因此領導者必須防范被領導者鬧獨立或暗地里架空自己。例如有著作對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后其領導力難以貫徹到地方的情況作了如下描述:“由于那時地方政府中傳統的回避制度被徹底地破壞了,全國各省差不多都被當地的軍頭所盤踞,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通統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6]手握重兵的袁世凱尚無法對地方實行真正的領導,可想而知中央政府要想如臂使指地領導地方其難度有多大了。
廣義的被領導者中還包括除最高領導人之外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內部往往也會形成相互之間的強烈制約關系,而且擁有權力的領導集團中的成員往往比普通被領導者能夠對其他領導者形成更強烈的制約。例如趙匡胤取代柴宗訓、趙光義又取代趙匡胤成為皇帝,中國古代經常出現外戚及宦官的干政等等,就表現出領導集團中的人會對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領導者形成強力的制約。如果最高領導者無德無能,很容易被其他人取代。
四、領導者的素質與非制度性約束因素的關系
成為領導者并不須要具備相同的素質,但是擔任領導者則須要具備一些相同的素質,其原因在于在擔任領導者的過程中要受到基本類似的非制度性約束因素的束縛。
(一)成為領導者所須具備的素質
無論古今中外,都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現象。人群中存在領導者這一現象,雖然不像猴群中要有一位猴王、羊群中要有一個領頭羊之類的現象表現得那樣明顯,但是在任何人群中,不同的人在群體中發揮的作用很難保持絕對相同:往往自然地會有些人在人群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些人則較少發揮自身的影響力。發揮更大影響力的人,雖然可能并不具備領導者的名義,但事實上就是領導者。
那么為什么有些人會成為領導者?須指出,在這里討論的是自然地出現的領導者,而非已經有了行政機構、由有關機構任命的領導者(或者更籠統地說,由既有的產生領導者的機制產生的領導者,也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法理型領導者)。自然出現的領導者與法理型領導者的產生過程是存在差異的:后者有整套的行政機構、強力機關作為被任命的領導者開展領導活動的后盾;而自然地出現的領導者則是依靠自身的素質、自身的素質和自身的活動對群體中的其他人產生的影響而成為領導者的。
在討論一個潛在的領導者所應具備的素質之前,應看到的一個現象是“時勢造英雄”。也就是說,不同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會要求領導者具備不同的素質,因此,在一個非領導者成為領導者的過程中,并不須要有關人員具備相同的素質。可舉簡單的例子對此進行說明:在風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賀龍曾經憑借兩把菜刀鬧革命,由此成為革命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賀龍具備的素質是擁有比一般人更強烈的革命精神;而諸葛亮成為劉備的重要助手、蜀軍的領導者之一,則主要是因為其謀略過人。因此,成為領導者的人,并不須要具備相同的素質。
但是能夠憑自己的素質成為領導者的人具備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至少其某一方面的素質超過一般人,二是其所具備的素質適合了時代(或者說客觀形勢)的需要。
與上述自然形成的領導人不同,一些人是在已經形成了一套產生領導人的機制的情況下成為領導者的。相對而言,這些人自身的素質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外界的因素、非領導者個人素質的因素會在這些人成為領導者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君主制下,要想成為君主,重要是天生的血統;在今天的美國要想成為總統,必須擁有大筆資金開展競選活動。
(二)擔任領導者所須具備的素質
前已述及,要想成為領導者,有關人員所須具備的素質并不一定相同,但是擔任領導者的人須要相同的素質,這是因為領導的過程帶有一定的共性,領導者往往須要處理相同的事務。在此處,主要討論在政治領導現象中領導者所須具備的素質。
第一,處事公允。在領導過程中,往往須要分配利益。在分配利益時,領導者要能夠服眾。被領導者之所以不會對領導者作出的分配決定提出質疑,主要是因為被領導者能夠感到領導者的分配大體符合公平原則。(當然,有時領導者在自己領導的團體內部所進行的分配并不公平,例如封建主把獲得的主要的財富分給騎士,依靠騎士的忠誠來維持對普通百姓的統治。但是在騎士集團內部,封建主的分配也要做到公平,不能使騎士因分配不公而起來反對自己。)而且在領導過程中,領導者往往須要對下屬進行激勵或約束,因此領導者在賞罰過程中更要注意做到處事公允。因此可以說,任何人擔任領導,在進行分配、賞罰時都不是自由的,他必須按照下屬心目中普遍認同的公平原則行事。任何一個團體、國家所制定的分配、賞罰機制必然要體現、符合這個團體、國家的人民心目中所認可的公平原則。例如,《元史》對元成宗皇后卜魯罕的最重要評價是:“大德之政,人稱平允”,可見即使是在古代為政的客觀標準之一也是平允,要想做到平允統治者就不能隨意作為。又如慈禧太后之所以能長期統治清政府,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能夠處事公允,讓滿族宗室成員、漢族大員基本上能夠對她的行事感到心服。
要做到處事公允,就須要領導者具備一定的智慧,能夠對下屬的功過作出正確的評價并作出相應的賞罰,領導者還要掌握下屬的心理、對賞罰的決定所能引發的反應有所判斷。例如由于項羽未封田榮為王,田榮大為不滿并起兵反對項羽,這一事件在劉邦擊敗項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如果是一名合格的領導者,即使不能使田榮感到自己受到了公平對待,項羽也應當預見到封王的決定可能引起的田榮的反應,從而提前采取措施防止田榮反叛事件的發生。
第二,決策高明。任何一個團體往往是因為某一或某些原因而存在的,因此團體往往會有自己的目標。為了實現目標,領導者要帶領團體采取行動。在此過程中,領導者要及時給團體指明方向。一般情況下,團體內部圍繞團體所應采取的行動這一問題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意見,這個時候領導者必須能夠對不同的意見進行辨析、明確哪種意見更高明并作出取舍。在此過程中,領導者不僅要有果斷作出決策的能力,還要有聽取不同意見的習慣(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更要有對不同意見進行科學判斷的智慧。總之,領導者要能夠作出最高明的決策——如果領導者的決策不如團體中的其他人的意見高明,那么這個領導者的位置是難以長期維持的。例如,毛澤東曾分析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歷史上領導多頭總是要失敗的。太平天國的時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廣西,楊秀清說他回到天國了。洪秀全回來時,將領們都是擁護楊秀清的。其實那時楊秀清更年輕有為些,洪秀全應該服從楊秀清的領導。但洪秀全是創教者,是領袖。兩權對立,所以失敗了。”[7]也就是說,在太平天國發展過程中,楊秀清的決策能力逐漸顯得比洪秀全高明,因此許多將領開始擁護楊的領導,洪秀全的領導地位已經動搖了。
領導者決策高明這一點可以體現為兩種情況:一是領導者本人具備最高的智慧(例如毛澤東在紅軍反圍剿和長征過程中顯示出了比其他領導人更高超的軍事才能,由此中央其他領導人才認可他的領導地位);二是領導者能夠采納其他聰明人的建議,從而作出高明的決策(例如劉邦)。
由于正確的決策必然是符合客觀需要的決策,因此領導者在作出決策時也是不自由的,必須尊重客觀規律、符合客觀現實。
第三,嚴于律己。領導者受到的有形的約束似乎要比普通人小,但事實上領導者注定受到許多無形的約束,這類約束突出表現在:如果領導者的決策不符合客觀要求,集體的事業就會遭遇失敗,從而動搖領導者的地位;同樣地,如果領導者恣意妄為,會嚴重影響被領導者對其領導地位的認可。例如歷史上著名的“止謗”的周厲王最終遭遇民變:“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因此,領導者要想維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必須有很強的自制力,能夠自行約束自己的行為,而且其自制力要比普通人更大,這是因為手中握有權力的領導者要比沒有權力的普通人更有條件恣意妄為。
第四,善于服眾。領導過程中,最根本的是要能夠得到下屬的服從。有的領導者善于得到下屬的愛戴,有的領導者善于維護自己的權威,但在多數情況下領導者都要做到恩威并施。此外,領導者的位置往往是眾人所覬覦的,因此領導者要足夠機警且能夠采取措施消除他人對自己的地位的威脅。
正是由于任何領導者在領導過程中均須面臨基本類似的、非制度性制約因素,因此所有領導者才都須要具備上述四種素質。
總之,任何政治領導者都會受到客觀的、主觀的非制度性約束的束縛。這些約束因素表現得沒有制度性約束因素那樣明顯,但在研究政治現象時必須注意到這些無形的約束力量所發揮的實際作用。由此,政治學研究就可以擺脫僅僅關注政治構架中的正式的制約性制度設計的狹隘做法,更全面地認識不同的政治體制在不同的社會中所受到的制約,從而更加全面地評價不同政治體制的優劣。
此外,任何政治體制都處在具體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中,有關社會環境、文化環境會對政治體制構成某些非制度性的約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體制本身不能決定政府的治理績效,政治體制與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結合在一起才共同決定政治績效。例如,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提倡仁政,由此營造出的社會氛圍對王朝政權的行為構成了明顯的約束,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古代實行皇族統治就認為古代王朝在任何時候都在推行暴政。又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文化強大,因此盡管教會本不應該屬于政治機構,但教權在當時還是對王權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因此,政治學的研究要避免僅僅關注正式制度而忽視其它現實影響因素、非制度性影響因素的傾向。
[1][2][3][4][5] 楊一凡點校.皇明制書(第三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784、783、785、786、788.
[6] 唐德剛.袁氏當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109.
[7] 陳晉:毛澤東之魂(修訂本)[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370.
(責任編輯: 育 東)
本文為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資助基金項目“東歐諸國與兩次世界大戰的關系研究”(16JHQ025)階段成果。
2016-12-15
夏慶宇(1981—),男,遼寧鞍山人,法學博士,復旦大學政治學流動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為政治學。
D0
A
1672-1071(2017)01-00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