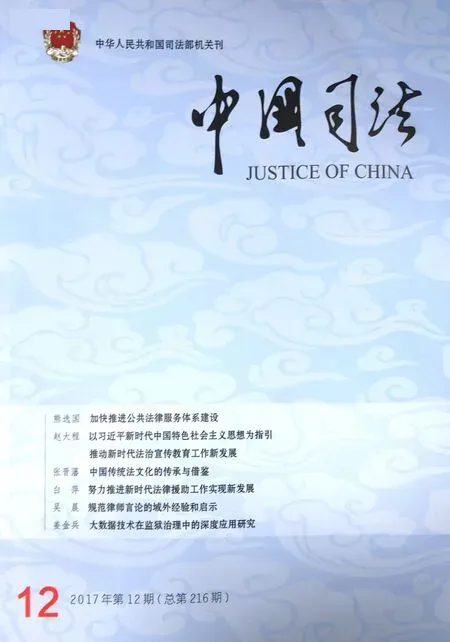為什么要給當事人選擇律師的權利
——一個關于法律援助的重要話題
桑 寧(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為什么要給當事人選擇律師的權利
——一個關于法律援助的重要話題
桑 寧(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2002年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國際會議上,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觀點—“當事人不應該具有選擇律師的權利”,其理由很簡單,國家負擔不起。時隔十五年,2017年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國際律師協會組織的一個關于法律援助原則的專家討論會上,再次聽到了這個熟悉的觀點—“不應由當事人自己選擇律師”,但理由與布達佩斯聽到的不同了,這次的理由是因為當事人不具備作出正確選擇的能力。坦率地講,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時的感覺是有些無奈,但第二次聽到這個觀點時的感覺是有點似是而非。
是否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是一個國家法律援助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公民享有的權利越多,就意味著國家的責任越大,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看,國家的整體實力決定一些社會政策的水平,不僅是合理的,也是讓政策變得切實可行的科學前提。
一個基本事實
在分析是否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的權利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受援人的權利很容易受到傷害。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因素影響:第一個因素是信息不對稱。法律服務是一個嚴重信息不對稱的領域,當事人很容易被掌握著絕對信息優勢的服務提供者牽著鼻子走,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時也渾然不知。從一些調查數據和典型事例看,侵害當事人利益的事件時有發生,有些甚至還很嚴重,而當事人總是處在一種被動的地位。第二個因素是公共服務的屬性。公共服務的作用是保基本、兜底線,基本需求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含糊的概念。國際法庭一個著名的判例稱,當事人在法律援助服務中享有的權利是有限的;英國認為法律援助應確保提供符合最低標準的服務;加拿大認為法律援助服務應是中等收入者所能購買的服務;國際律師協會的觀點是最低限度應按職業行為守則行事,在合理的情況下可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我國《法律援助條例》規定律師應提供符合標準的服務。可以看出,盡管有不同的表述,但都把法律援助定位于滿足最基本需求,與法律服務追求卓越的目標有所不同。事實上我們看到的也是如此,很少有國家會明確法律援助受援人實際享有哪些權利,也鮮有起身理直氣壯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受援人。第三個因素是法律服務市場的逐利性。市場是具有逐利性的,而法律援助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律師報酬普遍偏低,由于缺乏吸引力和足夠的動機,優質服務資源無法聚集于法律援助的領域,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無意貶低律師行業服務公益的優良傳統,但把一項法律制度建立在良知基礎上也是靠不住的。這些對當事人不利的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法律援助發展面臨的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服務質量普遍偏低,而且缺乏有效的治理。
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的好處
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的第一個好處是讓法律援助服務提供者認清誰才是自己真正的客戶,應對誰負責任。由于政府在法律援助中承擔著支付者的職責,所以政府往往會橫亙在法律援助的提供者和法律援助的消費者中間,遮擋住提供者對消費者需求關注的視線。法律援助作為提供者尋求的一種市場,第一個要打交道的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法律援助消費者而是政府機構。換句話說,就是法律援助提供者要從政府那里獲取法律援助的機會,與真正的法律援助消費者并無多大關系,這會在很大程度上誤導法律援助提供者,使他們以為政府才是自己需要謹慎應對的客戶,而真正法律援助客戶——法律援助受援人就變得沒那么重要了。在這樣的關系下,政府能否有效地代表法律援助受援人,切實維護法律援助受援人的合法權益,就成為法律援助受援人實現自己訴求的基本途徑。大量事實證明,政府總是很難扮好這個角色。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的權利,讓政府退到當事人后面做一個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者和簡單的支付人,由當事人直接面對提供者,就像法律服務中的關系一樣,當事人自己選擇某一個合適的提供者,這不僅使法律援助的法律關系從表面上看變得更加簡單,而且可以使提供者更清楚地認識到他是在為誰服務,誰才是決定其服務的人。當事人有了選擇的權利,才有可能理直氣壯的對律師進行監督。
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的第二個好處是政府代表當事人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投入壓力會有所減輕。由政府機構指派、任命律師,隨之而來的一個責任就是應確保所指派、任命律師為當事人提供的服務是合格、有效的,為此政府需要采取多項措施來監督法律援助提供者服務的質量。從聯合國全球法律援助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出,由于影響法律援助質量的要素繁多,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途徑方法也十分復雜,而且需要綜合實施才可見效,面對法律援助資源的普遍匱乏、質量管理機會成本高昂的現實,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輕松應對由此形成的財政負擔。讓當事人自己選擇律師,就是把機會還給真正的市場,讓無形之手發揮作用,效果不遜于政府的管制。
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的第三個好處是可以提高法律援助的可獲得性,改善法律援助提供者和受援人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當事人在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中最關注的三個問題是:不好找、等候時間長和服務不專業。如果由當事人自己選擇律師可以取得一舉三得的功效。不好找和等候時間長與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設置和程序的復雜性有關。從一些國家便利當事人改革的成功經驗看,在當事人獲得法律援助服務過程中,唯一無法實現便捷化的就是找律師,就像人生病必須要去醫院找醫生一樣,這一環節是無法省略的。讓當事人自己選擇律師,就如同人生病直接去醫院就可以了,到那里以后所有的程序都由律師代理去辦,當事人不僅可以免去許多來回奔波之苦,由專業人員面對程序還可以提高效率,縮短等候時間,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站式”服務。另外,當事人自己選擇的律師和政府指派的律師在相互關系的認同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別,通常人們總是相信自己選擇的才是最好的。
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的第四個好處是可以防止法律援助機構的腐敗和徇私。當法律援助成為律師尋求的市場時,誰來指派、任命律師就變成一種實實在在的權力,既然是權力就有腐敗和徇私的風險。預防這一風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變成當事人的權利。
可能存在的風險
任何事物都存有另一面,好處的另一面就是壞處。分析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可能存在的風險,是為了讓人們在決定是否為此值得一試的決策當中進行全面的考量。管理學中有一個論斷,成功往往不決定于有多少有利因素,而是取決于有多少不利因素。下面就分析一下賦予當事人選擇律師權利可能存在的風險。
第一個風險就是對法律援助是律師普遍義務這一原則的影響。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律師,就意味著法律援助在實踐中可能變化為不再是律師的普遍義務。法律援助實際成為一部分律師的“業務”,與法律援助律師的普遍義務的規定在實踐中是否存在張力,還需認真研究。但它可行的前提必須是多勞多得。被當事人選中次數多的律師,在經濟上應該得到更多的正相激勵,至少不能是做的越多,律師失去的越多。在一些經濟欠發達、仍需靠律師履行普遍義務來滿足法律援助需求的地方,就很難做到讓當事人自主選擇律師,我們曾在欠發達地方看到的一些“點援制”做法,往往是一種附條件的選擇律師權,實際自由度并不太高。在發達的東部省份,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律師尋求的市場,“點援制”則表現的相對成熟,當事人有了更多的選擇自由。提高律師的補貼,讓律師參與法律援助變成正相激勵,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但不應將其視作一種風險,而是責任所在。
第二個風險是可能當事人無法做出正確選擇。法律援助服務是典型信息不對稱領域。當事人很可能會受掌握信息優勢一方的暗示和影響,自愿做出一些并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導致不良后果。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任命律師,在可行能力方面明顯優于當事人,對提供者的把握也更加客觀全面,不足之處前面已經說過了。如何防范、降低這種風險,國際經驗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一是政府應把好提供者的資質準入關,讓不符合能力標準的人不能進入。二是認真履行信息披露義務,讓當事人全面掌握法律援助提供者的職業信息,幫助當事人做出合適選擇。
第三個風險是管理機構權力改變或喪失帶來的影響。指派、任命律師,是法律援助管理機構一項傳統權力,在法律援助管理權力結構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失掉這部分權力,對管理系統會產生連鎖性的影響。管理的邏輯起點變了,從管理理念到路徑、方法都會跟著起變化。歐洲有許多國家是由當事人自己選律師,管理模式表現出一種多元化的態勢,最典型的是德國,因為不需政府機構指派、任命律師,所以連專門的法律援助管理機構都沒有設立,目前運作的也十分良好;荷蘭也是由當事人自己選擇律師,所以荷蘭法律援助辦公室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提供者的把關上。再看國際上在法律援助管理方面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做法和經驗,德國、荷蘭真可謂是“大道至簡”。
朱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