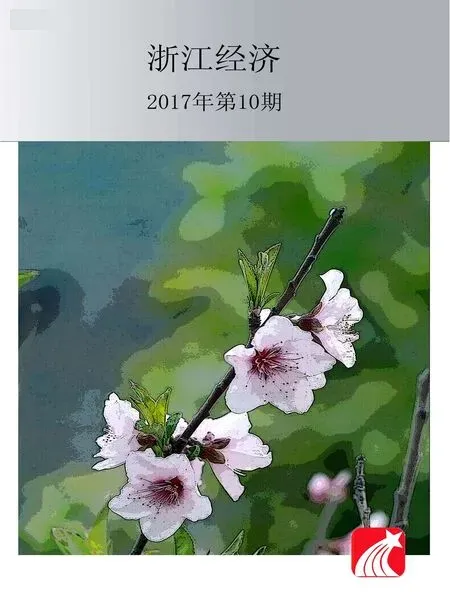復(fù)雜適應(yīng)理論(CAS)視角的特色小鎮(zhèn)評(píng)價(jià)
□國(guó)務(wù)院參事、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原副部長(zhǎng) 仇保興
復(fù)雜適應(yīng)理論(CAS)視角的特色小鎮(zhèn)評(píng)價(jià)
□國(guó)務(wù)院參事、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shè)部原副部長(zhǎng) 仇保興
浙江人創(chuàng)造的特色小鎮(zhèn),彌補(bǔ)了城市的一些不足,起著城市修補(bǔ)、生態(tài)修復(fù)、產(chǎn)業(yè)修繕的功能。
特色小鎮(zhèn)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優(yōu)于其他城市模式,就是小鎮(zhèn)的人和外部環(huán)境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超越傳統(tǒng)的偏見:從老三論、新三論到復(fù)雜適應(yīng)理論(CAS)
發(fā)源于上個(gè)世紀(jì)50年代的控制論、信息論和一般系統(tǒng)論簡(jiǎn)稱“老三論”。“老三論”解決了兩個(gè)問題,一是把基建系統(tǒng)的控制延伸到生物系統(tǒng),二是把線性系統(tǒng)延伸到非線性系統(tǒng)。這兩大系統(tǒng)的打通,促進(jìn)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我們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產(chǎn)生了新的飛躍。到了上世紀(jì)60年代,人們發(fā)現(xiàn)“老三論”還不足以來描述客觀世界,這時(shí)便誕生了“新三論”。“新三論”包括伊里亞·普里戈金提出的耗散結(jié)構(gòu)論、托姆的突變論和哈肯的協(xié)同學(xué)。“新三論”解決了系統(tǒng)不確定性結(jié)構(gòu)的問題。將不確定與確定性之間打通是“新三論”的突出貢獻(xiàn)。如現(xiàn)在科幻片里講到奇點(diǎn)、黑洞就是“新三論”的創(chuàng)造。直到現(xiàn)在人類還是用“新三論”來指導(dǎo)科學(xué)和世界觀的改造。但人類的認(rèn)識(shí)是無止境的,到上世紀(jì)90年代,人們覺得用“新三論”來描述事物仍然存在缺陷。這時(shí),美國(guó)科學(xué)家霍蘭和幾位諾貝爾物理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共同推出了第三代系統(tǒng)論,即復(fù)雜適應(yīng)理論(CAS)。“老三論”與“新三論”描述的都是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認(rèn)為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是天然的,對(duì)主體活動(dòng)跟系統(tǒng)演變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不到位。復(fù)雜適應(yīng)理論與前兩代理論的最大區(qū)別就是把主體對(duì)環(huán)境的主動(dòng)適應(yīng)性、學(xué)習(xí)能力、應(yīng)對(duì)能力、挑戰(zhàn)能力看成是整個(gè)系統(tǒng)演變的動(dòng)力源。該理論最主要的核心是主體。在特色小鎮(zhèn)這個(gè)系統(tǒng)中,主體就是人。特色小鎮(zhèn)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優(yōu)于其他城市模式,就是小鎮(zhèn)的人和外部環(huán)境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從特色小鎮(zhèn)1.0版到特色小鎮(zhèn)4.0版
第一代特色小鎮(zhèn),即小鎮(zhèn)1.0版,我們把它歸納為“小鎮(zhèn)+一村一品”。小鎮(zhèn)是為周邊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服務(wù)的。這種小鎮(zhèn)的模式延續(xù)了兩千年,與農(nóng)耕文明的歷史同樣悠久。進(jìn)入改革開放后的30年,浙江省由于缺少國(guó)家投資、蘇聯(lián)援助和大工業(yè)的機(jī)制約束,創(chuàng)造出“小鎮(zhèn)+企業(yè)集群+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模式,我們歸結(jié)為第二代特色小鎮(zhèn),即小鎮(zhèn)2.0版。小鎮(zhèn)里進(jìn)行專業(yè)化的分工與協(xié)作,人們之間緊密合作構(gòu)成一個(gè)高效率的生產(chǎn)體系,即塊狀經(jīng)濟(jì)。由于受各種外部條件限制,浙江省特色小鎮(zhèn)反而走出了一條創(chuàng)新的路子。小鎮(zhèn)2.0版是整個(gè)浙江省經(jīng)濟(jì)從落后到先進(jìn)、從前工業(yè)化進(jìn)入后工業(yè)化的推動(dòng)力和鑒證者。到上世紀(jì)80年代末,人們意識(shí)到,有些保留獨(dú)特歷史文化的小鎮(zhèn)還沒有被塊狀經(jīng)濟(jì)所覆蓋,而這些小鎮(zhèn)獨(dú)特的文化、奇特的建筑和獨(dú)有的地形和諧融合,成為旅游資源,發(fā)展旅游的同時(shí),可以帶動(dòng)其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由此誕生了第三代特色小鎮(zhèn),“小鎮(zhèn)+服務(wù)業(yè)”,即小鎮(zhèn)3.0版。在近30年的城市建設(shè)過程中,出現(xiàn)了成片大學(xué)城、產(chǎn)業(yè)城、工業(yè)城在空間上硬湊在一起的現(xiàn)象,切斷了城市天然有機(jī)的聯(lián)系,產(chǎn)生了一系列問題。浙江人創(chuàng)造的特色小鎮(zhèn),彌補(bǔ)了城市的這些不足,起著城市修補(bǔ)、生態(tài)修復(fù)、產(chǎn)業(yè)修繕的功能。由此產(chǎn)生以“小鎮(zhèn)+新經(jīng)濟(jì)體”為特征的第四代特色小鎮(zhèn),即小鎮(zhèn)4.0版。
從CAS視角看特色小鎮(zhèn)演變需要堅(jiān)持的四項(xiàng)原則
原則一:任何復(fù)雜的系統(tǒng)總是動(dòng)態(tài)變化的。這種變化不僅是數(shù)量上的,更是參數(shù)上的。這種變化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文化或者制度的顛覆性創(chuàng)新,注重個(gè)體能動(dòng)性的恢復(fù)。從這個(gè)角度來看,是人的變化導(dǎo)致了特色小鎮(zhèn)的變化。
原則二:多樣性是特色產(chǎn)生的動(dòng)力,特色是任何經(jīng)濟(jì)變遷的重要特征。第四代特色小鎮(zhèn)中新產(chǎn)品、新結(jié)構(gòu)、新創(chuàng)業(yè)業(yè)態(tài)的形成,取決于企業(yè)家的能動(dòng)性、創(chuàng)造性,是城市所提供的無數(shù)正向公共品疊加的結(jié)果。特色小鎮(zhèn)影響力的大小在于特色的唯一性。小鎮(zhèn)特色從浙江唯一到全國(guó)唯一,再到世界唯一,是三個(gè)不同的跨度。如果能將特色做到極致,特色小鎮(zhèn)必然會(huì)發(fā)展好。
原則三: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體的復(fù)雜性。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體是復(fù)雜的,企業(yè)家們的能動(dòng)性具有廣泛的不確定性,這樣的不確定性甚至形成一種混沌狀態(tài)。在這種混沌狀態(tài)中,有五個(gè)確定性的要求,只有遵循這五個(gè)要求,特色小鎮(zhèn)的“特色”才能凸顯,定位才能準(zhǔn)確。第一,特色小鎮(zhèn)發(fā)展的產(chǎn)業(yè)必須跟周邊的產(chǎn)業(yè)有差異,有差異才能互補(bǔ),互補(bǔ)才能協(xié)調(diào)。第二,特色小鎮(zhèn)必須有新奇的產(chǎn)業(yè),有內(nèi)發(fā)的新東西。第三,特色小鎮(zhèn)必須是綠色發(fā)展的,不能損害周邊環(huán)境。第四,特色小鎮(zhèn)要跟周邊的產(chǎn)業(yè)園區(qū)或大學(xué)園互補(bǔ)。第五,特色小鎮(zhèn)應(yīng)該是可體驗(yàn)的,可居住、可旅游、可就業(yè)。
原則四:經(jīng)濟(jì)組織主體的適應(yīng)性造就了復(fù)雜性。特色小鎮(zhèn)產(chǎn)業(yè)和空間的活力來源于個(gè)體的自主性。小鎮(zhèn)本身就具有企業(yè)孵化器的功能,對(duì)小鎮(zhèn)的管理就和對(duì)一般產(chǎn)業(yè)的管理完全不同。政府對(duì)小鎮(zhèn)應(yīng)采取激勵(lì)措施而不是取代小鎮(zhèn)的管理權(quán)。政府應(yīng)簡(jiǎn)政放權(quán),為小鎮(zhèn)護(hù)航而不是包辦小鎮(zhèn)事務(wù)。對(duì)于特色小鎮(zhèn)的評(píng)價(jià),既可以按照GDP總量、財(cái)政、稅收、投資、就業(yè)等指標(biāo)進(jìn)行評(píng)估,又要有新的理論來描述特色小鎮(zhèn)這種新鮮事物。CAS理論正好可作為描述特色小鎮(zhèn)評(píng)估體系的理論支撐。
用CAS理論評(píng)價(jià)特色小鎮(zhèn)的10個(gè)標(biāo)準(zhǔn)
標(biāo)準(zhǔn)一:自組織。按照CAS理論,自組織是自下而上依據(jù)某種基礎(chǔ)或某種愿望形成的,但他組織是根據(jù)從上到下的規(guī)定塑造出來的。任何一個(gè)有活力的組織必須是自下而上自己組織出來的。只要是自發(fā)的組織,就具有無比的活力。自組織和他組織二者效果完全不同。
標(biāo)準(zhǔn)二:共生性。共生性是指,特色小鎮(zhèn)是否與原本的產(chǎn)業(yè)和環(huán)境是共生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鎮(zhèn)就是和當(dāng)?shù)貧v史、生態(tài)環(huán)境共生得很好的例子。當(dāng)?shù)厥悄纤喂俜皆鞄诺氐臍v史背景使小鎮(zhèn)發(fā)展金融業(yè)早有淵源。八卦田等歷史遺跡的保留,使得當(dāng)?shù)氐慕ㄖ@林化,與自然環(huán)境和諧共生。相比之下,差的小鎮(zhèn)就會(huì)出現(xiàn)同質(zhì)化,如主城搞工業(yè)小鎮(zhèn)也搞工業(yè),主城搞居住小鎮(zhèn)也搞居住,甚至小鎮(zhèn)跟主城是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這樣的小鎮(zhèn)自然無法發(fā)展起來。
標(biāo)準(zhǔn)三:多樣性。多樣性是主體突變的基礎(chǔ)。一個(gè)地方擁有多樣性,活力就強(qiáng),地方創(chuàng)新就能成功。例如成都的德源鎮(zhèn),曾因房地產(chǎn)開發(fā)過度被譽(yù)為鬼城、空城。當(dāng)?shù)氐霓r(nóng)民把房產(chǎn)重新收購回來,根據(jù)青年人創(chuàng)業(yè)的需要進(jìn)行改造。青年人需要星巴克,就在當(dāng)?shù)匾M(jìn)星巴克;青年人需要風(fēng)險(xiǎn)投資就在當(dāng)?shù)馗慊穑磺嗄耆诵枰行W(xué)幼兒園,就在當(dāng)?shù)卦黾优涮住_@樣一步步根據(jù)創(chuàng)業(yè)者需求把德源鎮(zhèn)變成了著名的創(chuàng)業(yè)孵化基地。
標(biāo)準(zhǔn)四:強(qiáng)連接。連接是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jì)與新經(jīng)濟(jì)一個(gè)最基本的特點(diǎn),連接有強(qiáng)有弱。例如京津冀地區(qū)最大的缺點(diǎn)就是二級(jí)城市跟北京連接弱,新產(chǎn)業(yè)一經(jīng)培育起來,就被北京吸納走了,有去無回,使得京津冀協(xié)同作用發(fā)揮得并不好。相比之下,成都邊上的德源鎮(zhèn),把成都人愛玩的刺繡、染布、釀酒、木刻等地方性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集聚起來,建成私人博物館35所,打造為成都也是四川最大最齊全的文創(chuàng)基地。在文創(chuàng)這個(gè)連接線上強(qiáng)大的、獨(dú)一無二的連接,產(chǎn)生了強(qiáng)大的反磁力,把成都市這部分人才吸引回德源鎮(zhèn)去,使德源在成都邊上很好地發(fā)展起來。
標(biāo)準(zhǔn)五:產(chǎn)業(yè)集群。產(chǎn)業(yè)集群是一種高效率的、相互連接的、專業(yè)化分工非常細(xì)密的企業(yè)集群。每個(gè)企業(yè)的進(jìn)入都帶來了與本企業(yè)配套的其他企業(yè)。哈佛大學(xué)彼特教授所作的《國(guó)家的競(jìng)爭(zhēng)力》一書中指出:“一個(gè)國(guó)家或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活力和競(jìng)爭(zhēng)力,不取決于當(dāng)?shù)氐暮暧^數(shù)據(jù),而是決定于那些地理上不起眼的‘馬賽克’”,也就是眾多中小企業(yè)結(jié)合在一起形成的產(chǎn)業(yè)集群。如宜興的丁蜀鎮(zhèn),形成了四萬多從業(yè)人員、6000多配套人員、一萬兩千紫砂家庭作坊的產(chǎn)業(yè)集群。產(chǎn)業(yè)集群帶動(dòng)了旅游和其他收入。
標(biāo)準(zhǔn)六:開放性。柳市鎮(zhèn)原是溫州的一個(gè)電器小鎮(zhèn)。其中有兩位修自行車的聰明小伙子,合辦了一個(gè)儀表廠,在電器之都里曾是骨干企業(yè)。儀表廠后來分離出來成為“正泰集團(tuán)”和“德力西集團(tuán)”,正泰集團(tuán)一以貫之地做高精尖電器,德力西集團(tuán)則跟法國(guó)全球最大的電器制造商施耐德合資,合資工廠每年提供利潤(rùn)六個(gè)億。他們的生產(chǎn)基地都在柳市鎮(zhèn),因此柳市鎮(zhèn)的生產(chǎn)廠家可以融入到全球產(chǎn)業(yè)鏈中去。現(xiàn)在柳市鎮(zhèn)已經(jīng)成為全國(guó)最大的電器專業(yè)鎮(zhèn)。
標(biāo)準(zhǔn)七:超規(guī)模效應(yīng)。華北地區(qū)在雄安新區(qū)附近也有好的小鎮(zhèn)。因?yàn)槿A北地區(qū)是一個(gè)土地流轉(zhuǎn)非常快的地區(qū),需要大型、先進(jìn)、大碼力的農(nóng)機(jī)。而這些農(nóng)機(jī)需要有一個(gè)鎮(zhèn)來推銷和提供零配件,需要1000多個(gè)工廠為農(nóng)機(jī)生產(chǎn)零部件。這些農(nóng)機(jī)損壞后維修的需求,就可以形成一個(gè)不受規(guī)模制約、非常專業(yè)化的小鎮(zhèn)。
標(biāo)準(zhǔn)八:微循環(huán)。特色小鎮(zhèn)使用的能源是分布式的能源,用的水是分布式供水,這些都是綠色環(huán)保措施。特色小鎮(zhèn)的很多東西都必須要采用有別于城市的分布形式,采用小型的、分散的能量微循環(huán)模式。通過微循環(huán)可以成功創(chuàng)建新的產(chǎn)業(yè)集群。
標(biāo)準(zhǔn)九:自適應(yīng)。特色小鎮(zhèn)的活力全部來自于企業(yè)家對(duì)外部強(qiáng)大的觀察能力和自適應(yīng)能力。有很多小鎮(zhèn)或在東莞、或在順德,或是機(jī)器人小鎮(zhèn)、或是數(shù)控機(jī)床小鎮(zhèn)。而這些小鎮(zhèn)中的技術(shù)人員全部來自東三省。東三省的這些能工巧匠到南方去,為南方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xiàn)。建議東北的領(lǐng)導(dǎo),應(yīng)該在哈爾濱工業(yè)大學(xué)邊上搞幾個(gè)特色小鎮(zhèn),將當(dāng)?shù)厝瞬帕糇。瑬|北就可以振興了。
標(biāo)準(zhǔn)十:協(xié)同涌現(xiàn)。生產(chǎn)和銷售的協(xié)同效應(yīng)是非常強(qiáng)大的。義烏是一個(gè)特色的商業(yè)鎮(zhèn),旁邊四個(gè)省、1000多個(gè)小鎮(zhèn)為它提供配套服務(wù),形成協(xié)同。甚至在義烏有些村專門做鑰匙、有些村專門生產(chǎn)水晶,為整個(gè)市場(chǎng)配套服務(wù)。這種協(xié)同涌現(xiàn)的效應(yīng)比單槍匹馬強(qiáng)大無數(shù)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