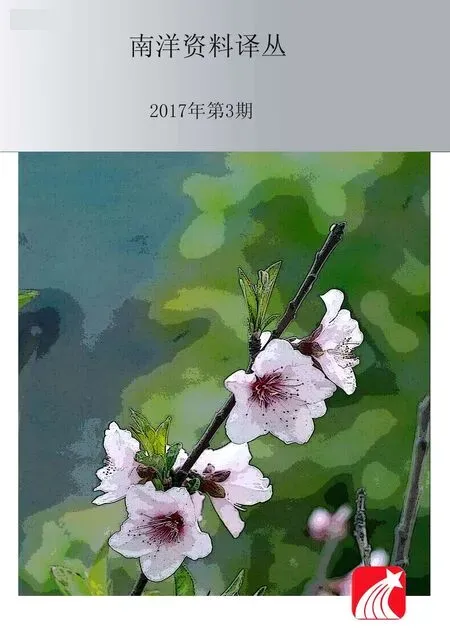“海洋界限”第143號報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
美國國務院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海洋與極地事務辦公室
“海洋界限”第143號報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
美國國務院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海洋與極地事務辦公室
編者按:近年來,美國頻繁介入南海爭端。2014年12月5日,美國國務院網站發布了“海洋界限”系列第143號報告,標題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該報告對中國的南海斷續線的法律效力問題曲解、妄斷。現將此報告內容全文譯出,供批駁參考。
該報告是國務院海洋、國際環境和科學事務局海洋與極地事務辦公室所發布的系列報告之一,該系列報告之目的是審查沿海國家的海洋主張和∕或邊界以及評估其主張與國際法規是否一致。該文件僅在所討論的特別問題上代表了美國政府的觀點,并不意味接受有關國家所聲稱的海洋界線。
引 言
該報告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特別是對環繞南中國海島嶼和海域的“斷續線”主張。
2009年5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兩份照會,要求在所有聯合國成員國之間傳閱。在該照會中,中國表達了對越南與馬來西亞一起和越南單獨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文件的不滿。照會聲明如下: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并對相關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見附圖①本譯文略去了原文中的所有地圖。)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上述立場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也為國際社會所周知。”
中國照會中所指地圖(本報告所復制的第1號地圖)描繪了環繞南中國海海域、島嶼及其他地物的九個線段(斷續線)。越南、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隨后對中國2009年照會的內容提出了抗議,聲明斷續線地圖反映的中國主張不具備國際海洋法依據。2011年,在向聯合國成員國提交的另一份照會中,中國重申了前述文字的第一句話,照會強調指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和相關權利以及管轄權有充分的歷史和法律證據支持。”
中國并沒有通過立法、宣言或其他官方聲明來明確其有關斷續線主張的法律基礎或性質。因此,這份“海洋界限”的報告主要考察關于斷續線主張的幾種可能解釋,并闡明上述主張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國際海洋法。
斷續線地圖
緣起與演變
盡管中國政府沒有提供一個官方解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華民國政府在1947年出版了第一號斷續線地圖,并為當時的學者和評論者廣泛提及。這張顯示11條斷續線的地圖在本報告中被稱為第2號地圖。學術研究表明,這張題為“南海諸島圖”的1947年地圖,源于更早的一張名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島嶼圖”(漢語拼音為“中國南海島嶼圖”),由中華民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在1935年出版,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版的中國地圖“似乎遵循了這張過去的地圖”。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地圖卻刪除了兩條最初劃在東京灣的斷續線,雖然在2009年地圖(第1號地圖)上已不可見,但至少在1984年以來的中國現代地圖,包括中國在2013年和2014年出版的豎式定向地圖上,還包括了一段位于臺灣東部的第10條斷續線。
地理描述
中國 2009年外交照會中的地圖包含了環繞該海域、島嶼的九段線和南中國海的其他地貌。中國沒有公布這些斷續線的具體地理坐標及位置。因此,本報告中有關斷續線的計算只能是粗略的估計。
該斷續線之內的海域大約有200萬平方公里,有中國22%的陸地面積那么大,這占據了大部分的南中國海。除臺灣和普拉塔斯島(中國稱之為東沙群島)外,斷續線內大約有13平方千米的陸地面積。這片陸地區域包括南中國海域的3組群島:(1)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2)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和(3)斯卡伯勒礁(中國稱為黃巖島)。在這些島嶼中,最大的是帕拉塞爾群島的永興島,面積達2.4平方千米。該斷續線內同樣有大量的水下地物,比如馬科斯菲爾德沙洲(中國稱為中沙群島)和詹姆斯淺灘(中國稱為曾母暗沙)。
本報告中的第3號地圖繪制的斷續線旁的數字僅僅是出于描述目的而加注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在每條斷續線上標明數字。斷續線之間距也不是等距離的,譬如說,在第7條和第8條斷續線之間有106海里,而在第3條和第4條斷續線之間卻有274海里。斷續線位于比較靠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和沿海島嶼的南中國海沿岸國家。第1條斷續線距越南大陸海岸有50海里,距越南的沿海島嶼離山島36海里。第3條斷續線距最靠近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色卡通島(Pulau Sekatung)有75海里。第4條斷續線距馬來西亞婆羅洲島的海岸有24海里。第5條斷續線距菲律賓島東南部最近的海岸有35海里。第9條斷續線距菲律賓呂宋海峽北部的雅米島26海里。
本報告的第4號地圖顯示,與距離上述斷續線內的島嶼相比,斷續線通常離周邊國家的海岸更近一些,換句話說,斷續線和島嶼之間的距離通常遠大于與上述周圍沿海國家之間的距離。距島嶼最近的點,如斷續線距帕拉塞爾群島的島嶼最近的距離有84海里(第1條斷續線到中建島),距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島嶼最近距離有46海里(第5條斷續線到半月礁),距斯卡伯勒礁間的距離有75海里(第7條斷續線到斯卡伯勒礁)。一些斷續線距南中國海海域最近的島嶼太遠了,譬如,第3條斷續線距上述這些島嶼中的斯普拉特利群島有235海里,第4條斷續線距南通礁有133海里,第8條斷續線距斯卡伯勒礁的島礁最近也有179海里。
在2009年地圖和其他中國地圖如1947年地圖中,對中國斷續線的地理描述各不相同,因此很難弄清楚。上述地理描述適用于2009年地圖,而不適用于1947年地圖抑或當今的中國地圖,因為在這些地圖中,斷續線的位置和尺寸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本報告的第5號地圖中,2009年地圖和1947年地圖中所畫斷續線的變化有清楚的顯示,2009年地圖上的斷續線位置通常比1947年地圖上的斷續線位置更接近和靠近中國的這些南中國海鄰國。比如,2009年地圖中的第2條斷續線距越南海岸的距離,比1947年地圖中的第2條斷續線到越南海岸的距離少了45海里,而第1條斷續線則少了15海里。第4條斷續線距馬來西亞的海岸少了8海里,同樣地,第8條斷續線距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少了大約19海里。除此之外,1947年地圖中的第5條斷續線到印度尼西亞的色卡通島(Pulau Sekatung)有15海里,而在2009年地圖中卻只有3海里。相比1947年地圖,盡管2009年地圖中的第5條斷續線有個相似的彎曲,但相比之下,第7條斷續線卻比1947年地圖的更細長,更加靠近菲律賓的巴拉望島,也更靠近馬來西亞和文萊共有的婆羅洲。在每兩段相鄰的斷續線之間,1947年地圖比2009年地圖中的距離更近一些,譬如,在2009年地圖中,第8條和第9條斷續線相距竟多達290海里。另外,在1947年地圖中,第10條與第11條斷續線相距31海里,第4條與第5條斷續線則相距225海里。
2009年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交的斷續線地圖與其他時期出版的地圖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地圖出版社在2013年至2014年間出版的斷續線地圖,似乎也沒遵循作為其前身的2009年斷續線地圖,這種差異甚至可以追朔到1984年出版的中國地圖。在本報告的第6號地圖中,基于對第4條斷續線的考察可以揭示這些差異。
分析基礎
根據國際法,審查海洋主張的適用法律框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后文簡稱《公約》)所規定的國際海洋法。
海洋區域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體現的國際法包含了沿海國獲得海洋區域的規定。
《公約》第二部分闡述的海岸基線規則規定,海域界限要從基線進行測量。正常基線是指沿海岸的低潮線,在《公約》第 5條有敘述。《公約》還允許直線基線是用在“在海岸線極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緊接海岸有一系列島嶼,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的劃定可采用連接各適當點的直線基線法”(第7條)。在基線向陸地一側的水域稱為內水(第8條),向海的一側依次是領海、毗鄰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等管轄海域。《公約》第四部分包含關于封閉的群島國家的群島水域基線規則,例如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這兩個國家。
《公約》第二部分闡述了管理領海的規則,它可以伸展到基線之外 12海里,但是,沿海國所行使的主權要受到無害通過和其他國際法規定的限制。此外,公約第二部分還介紹了毗連區,毗連區從領海基線開始測量,最多不超過 24海里,其中沿海國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控制防范措施,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上侵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法律和法規的行為。
《公約》第五部分闡述了專屬經濟區的相關規定,可以伸展至基線之外最多200海里在專屬經濟區內,沿海國可享有列舉權利,值得注意的是,也包括像“有目的的勘探和開發,保護和管理自然資源等主權權利”,以及關于“建設和使用人工島嶼,基礎設施”,“海洋科學考察”,“海洋環境保護”等公約“所規定的管轄權”(第 56條)。與此同時,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還享有航行、飛越、海底電纜鋪設和維護,以及其他使用這些項目的自主權(第58條)。
《公約》第六部分闡述了有關大陸架——延伸到大陸邊緣的外側或者延伸至距離基線200海里處——的規定,一如第76條中所描述的那樣。沿海國對大陸架行使勘探和開發其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這些權利是“專屬的”,“沿海國對大陸架的權利并不取決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領或任何明文公告。”(第77條)。
《公約》第八部分將島嶼定義為“四面環水并在高潮時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第 121條(1))。它規定,一如其他陸地領土,島嶼對前述海域擁有同等的權利,只是“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巖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第121 條(3))。
在高潮時不露出水面的“島嶼”不是島嶼,不享有海域權利,它們構成了海床和底土的一部分,要按照其所在海事區制度加以管理。公約還明確規定,“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不具有島嶼地位。它們沒有自己的領海,其存在也不影響領海、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界限的劃定。”(第60條(8))。這種人工島嶼、設施和建筑物也要按照其所在海事區制度加以管理。
海洋邊界
當相鄰國家的海域出現重疊時,海洋劃界問題就出現了。《公約》第15、74和83條對有關相向或相鄰國家間的海洋劃界做了規定。有關領海劃界的第 15條規定,兩國中任何一國在彼此沒有相反協議的情形下,均無權“將其領海伸延至一條其每一點都同測算兩國中每一國領海寬度的基線上最近各點距離相等的中間線以外”。但是,如因歷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有必要按照與上述規定不同的方法劃定兩國領海的界限,則不適用上述規定。
關于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公約第74條和第83條規定,“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近年來,國際法院和法庭一般情況下會根據暫定等距線劃定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如果需要的話,會根據沿海構造和形狀的變化,包括巖石和其他小島的變化,再調整上述等距離線。
“歷史性”海灣和權利
《公約》的實質性條款是指“歷史性”海灣和所有權的兩個實例。首先,第10條(“海灣”)規定,有關法律的規定“并不適用于所謂的”歷史性“海灣”。其次,如上述第 15條規定,劃定兩國領海重疊區域的界限的一般性規定,則不適用“歷史性所有權或其他特殊情形”。這些規定與1958年日內瓦《領海和毗連區公約》第7條和第12條的規定基本一致。
聲索國必須聲明其關于歷史性海灣或歷史性所有權的存在。美國已經認同這種觀點,為了證明一個歷史性海灣或歷史所有權的存在,一國必須證明(1)在該爭議地區行使公開的、眾所周知和有效的管轄;(2)連續和不間斷地行使管轄權;而且,(3)其他國家默認其行使管轄權。這些限制與有影響力的國際法機構的觀點相互一致,這些權威觀點包括1962年國際法院有關“歷史性海域,包括歷史性海灣的司法管轄”的研究報告,并獲得正式通過1958年日內瓦海洋公約的大會的授權。國際法學界認為,歷史性主張被限定在:(1)有關海上邊界和陸地領土的主權糾紛,以及(2)涉及近岸水域的其他爭議,參照現行海洋法規則,這些近岸水域可以是用直線基線法劃定的海域。
第10條和第15條從地理上和實質上作了嚴格限制。他們只適用于針對海灣和類似的近海構造,而不適用專屬經濟區、大陸架或公海海域。在過去——當今海洋區域出現之前——的時期,公海制度適用于非常接近沿岸的低潮線,“歷史性水域”和其他保護沿海國家更寬廣利益的主張有悖于傳統的公海制度。《公約》及沿海國家的地理界限遷就這種愿望并闡述道:制定管理海洋所有區域的框架,不允許有任何保留(第309條)。
分 析
中國有關斷續線地圖的可能主張分為兩類:一是關于陸地的主張,二是對海域的主張。關于陸地的主張,中國立場是明確的,它聲稱對斷續線內所有島嶼擁有主權。中國 2009年外交照會指出,“中國對南中國海內的島嶼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種說法,與鄰國在這一海域的島嶼提出的主權要求相矛盾,但與中國官方以往的聲明一致,至少可以追溯到它的 1992年領海法。因此,顯而易見的是,中國打算在斷續線地圖內標明在南中國海內聲稱擁有主權的島嶼。
關于海洋主權的要求,中國立場是不清晰的。因此,下面,本報告將探討有關斷續線主張的3種可能的解釋,指出該主張與國際法的規定在什么程度上是一致的。這些可選擇的解釋來自于主要的參考資料,特別是官方聲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相一致。
(一)作為島嶼主張的斷續線
討論
根據這一可能的解釋,斷續線只代表中國對島嶼擁有主權。單是依靠畫在地圖上的海上線作為一種高效、實用的方法來識別一組群島,這種做法并不罕見。如果斷續線圖只描繪中國的陸地要求,那么根據這種解釋,中國的海洋權利主張是指那些僅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的內容。中國在其 2009年外交照會地圖上附帶的聲明可被理解為支持以下含義:
中國對南中國海島嶼及其附近水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并對相關海域以及海床及其底土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見附圖)。
對島嶼“附近”海域的“主權”范圍可能指的是 12海里的領海,這確實是根據國際法所規定“主權”的管轄區域。同樣,“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可以被理解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法律制度。該“相關海域”和“海床和底土”也可以被理解為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這種解釋的依據可以在中國的法律和聲明中找到。中國1992年領海法第2條主張對東沙(普拉塔斯)群島、西沙(帕拉塞爾)群島、南沙(斯普拉特利)群島及其他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周圍12海里海域擁有主權。中國1958年領海宣言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對于相關海域的海洋權利主張,中國 1998年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規定了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并介紹了中國的大陸架權利和管轄權。事實上,中國2011年外交照會闡明以下觀點,即“中國對南沙群島完全享有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并沒有提到其他海洋主張。
地圖證據和官方聲明也為中國的斷續線提供了解釋的根據,那就是中國的斷續線所描繪的是島嶼主權而非確切的海洋主張。如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最初的斷續線地圖——后來斷續線地圖的依據——的標題是“中國南海諸島圖”。這一地圖顯然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為中華民國在國內使用,而在這一段時期,國際法的海洋主張只限于對狹窄的領海的承認。實際上,中國自己的1958年領海宣言主張:
本規定(12海里的領海)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以及臺灣及其周圍島嶼,澎湖列島以及因公海而與大陸及沿海島嶼分開的屬于中國的其他島嶼。
將中國大陸和沿海島嶼與屬于中國的所有其他島嶼分開的“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管轄的海域——的使用表明,在1958年,中國沒有對斷續線以內的所有海域提出要求。
評估
拋開南中國海的陸地特征和未解決的海洋邊界的主權要求問題,如果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斷續線的上述解釋準確的話,則按照中國國內法律規定的海洋主權的一般性解釋與國際法并不相悖,列舉如下:
(1)中國大陸沿海和海南島有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還包括伸入南中國海的區域。
(2)中國主張的南中國海的其他島嶼——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條第 1款界定的——將同樣享有上述的海洋區域,根據第121條第3款,“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巖礁”不應具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3)那些在高潮時被完全淹沒的水下部分,不能受制于主權要求,也不產生自己的海洋區域。它們應服從于其所在的海域制度的安排。
(4)人工島嶼、設施以及建筑物同樣不產生任何領海或其他海洋區域。
該評估受制于幾個重要的附加說明:
第一,中國對南中國海島嶼的主權要求具有爭議。越南和臺灣也對帕拉塞爾群島提出了要求,菲律賓和越南聲稱對斯卡伯勒礁擁有主權,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中國臺灣也宣稱對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島擁有主權。因為中國的領土主張是存有爭議的,其基于這些陸地主張的上述海洋主張同樣存在爭議。
第二,中國尚未澄清與南中國海的某些地貌相關的海洋主張。譬如,根據《公約》第121條第3款,中國沒有澄清南中國海的哪些地貌被認為是“島嶼”(或者說,被認為是暗礁),或者如果有的話,哪些“島嶼”被認為是不享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權利的“巖礁”。斯卡伯勒礁和某些島礁等這些問題將是菲律賓和中國在《公約》附件7規定的仲裁的主要議題。
第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等國要求的海域從大陸沿岸延伸至南中國海。如果中國對所有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擁有主權,南中國海島嶼所產生的海洋區域將與對面的前述國家的海岸線所產生的海洋區域出現重疊。
(二)作為劃定國家邊界的斷續線
討論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中國地圖上出現的斷續線是為了表明中國與鄰國之間的國界。
正如該報告的第七張地圖所顯示的,現代中國地圖和地圖集使用一種邊界符號描繪南中國海的斷續線。事實上,中國地圖上陸地邊界與斷續線使用的符號是一樣的,這些地圖圖例的內容要么被解釋為“國界”,要么是“國際邊界”,這些地圖也使用另一種被理解為“未定”國家或國際邊界的邊界符號,但斷續線沒有使用這一符號,斷續線在開放海域空間的位置則表示海上邊界或界限。
評估
《公約》第74條和第83條規定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邊界劃界“應在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因為根據國際法,海上邊界是由相鄰國家之間的協議訂立的,一個國家不能單方面與另一個國家建立海上邊界。如果同中國有島嶼主權爭議,則需要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文萊對海上邊界劃定的重疊區進行協商。中國的斷續線也缺少海上邊界的其他重要標志,譬如說,一個將兩個國家的海洋空間分開的已公布的地理坐標列表和一條連續不間斷的線。
在某種程度上,該斷續線表明了中國單邊立場上劃定的與鄰國在合適位置上的海洋邊界,這一立場與國家實踐和劃定海洋邊界的國際法理背道而馳。在確定海洋邊界的位置時,國際法院和法庭通常賦予像南中國海上的那樣非常小的孤島相等或者更少的權重,更重要的是與那些小孤島相對的漫長而連續的海岸線。
如果該斷續線意在劃出一條單方面的海洋邊界,這個解釋也沒有表明中國自己主張的斷續線內的權利和管轄權的類別。如果要與國際法相一致,該斷續線就不能作為代表中國領海(及其主權)的一條線,因為該斷續線位于中國主張的陸地地貌的12海里領海之外。更有甚者,第2條、第3條、第8條斷續線不僅距離其他國家的本土海岸更近,全部或部分的斷續線也位于任何中國主張的地貌的200海里之外,因此,該斷續線不代表據《公約》第57條而產生的中國專屬經濟區朝向海洋的界線,而第57條規定,專屬經濟區的寬度將不能從沿海基線向外伸展超過200海里。
(三)作為歷史主張的斷續線
討論
根據這種可能的解釋,中國地圖上的斷續線傾向于代表所謂的“歷史性主張”。這一歷史主張或許是海洋領域的主權表現(“歷史性海域”或者“歷史性權利”),或者換句話說,或多或少代表著對這一海域的權利(歷史性權利)。
中國政府的一些聲明及行為可以被解讀為對這一歷史性主張的支持。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中國政府 1998年頒布的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及大陸架的法律,該法規定,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解釋,“該法律規定不能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性權利”。中國曾在 2011年的照會中指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立場及其所宣稱“主權及相關權利與管轄權”是有充分的歷史證據以及法律支撐的。即便不是中國政府的影響,很多中國研究機構以及評論員也都主張,斷續線地圖已經描述了對南中國海的歷史性權利。
此外,中國政府關于南中國海的一些聲明及行為也違背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然此類言行并不足以證明其歷史主張,但是卻表明中國考慮了他們對在南中國海的海洋主張的一個可選擇的依據,比如說歷史性權利。
例如,中國已經宣布中國在南中國海某些特定區域,甚至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甚至不顧第二托馬斯海礁(仁愛礁)的位置根本超出中國領海界限的事實而宣稱對它擁有主權。更有甚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甚至宣稱“我要重申一下,中國對南中國海及海域內的所有島嶼享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據報道,中國海軍也同樣定期在詹姆斯灘(曾母暗沙)舉辦宣誓儀式,以申明自己國家對這一海域的主權,盡管詹姆斯灘是遠離任何中國島嶼的水下暗礁。中國明顯把詹姆斯灘視為其“最南端的領土”。我們并不清楚是否應該從字面上理解這種中國“主權”,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的法律依據就不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無法成為其存在的法律基礎。因為《公約》規定沿海國家的主權不能超過領海范圍 12海里。因此,中國很可能是把他們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水域視為他們對南中國海宣布主權的法律依據。
2012年,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聲稱,他們在越南中部海岸對面的租用區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轄區范圍。然而,如第8張地圖所示,在該報告中,除了121條款問題以及海域劃界問題,這兩部分(BS16,DW04)的任一部分都距離中國宣示主權的島嶼(藍色部分)超過了200海里。因此,這一要求完全不符合《公約》的規定。
中國國內法律也認為中國的海洋主張有法律依據,例如,中國 1999年頒布的《海洋環境保護法》將其適用范圍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陸水域、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范圍內的其他海洋水域。”根據《公約》的規定,沿海國管轄權僅限于前述的海洋區域,因此“其他海洋水域”具體指代哪些范圍是不清楚的,或許這個詞語指的是那些中國認為自己擁有歷史主權的領域。
以下評估是為了審查中國宣布斷續線內區域為自己的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權利是否有國際法律的依據。
第一部分評估——中國是否擁有歷史依據?
一開始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此前討論表明的那樣,對于斷續線內的南中國海海域不論是“歷史性水域”還是“歷史性權利”,中國均未提出事實上非常清楚的主張。
任何一國提出歷史性所有權的時候,必須要國際社會了解這一主張。正如最近一項對歷史水域的綜合研究所指出的,“要使國際社會周知,正式宣示這一(歷史)主張通常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其他國家至少還有機會對其所宣示內容進行否認。”
至于南中國海問題,似乎沒有任何一項中國的法律、宣言、公告或其他官方文件能夠使國際社會意識到斷續線內的水域屬于中國的歷史性所有權。中國公布的 1998年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以及大陸架法案中所提到的“歷史性權利”作為法律條文屬于“保留條款”;聲明本身沒有提到任何主張,1998專屬經濟區法案也沒有對斷續線地圖提出只言片語。盡管中國某些法律提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區范圍內的其他水域”這一詞語,但對于此種管轄權的性質、依據或地理位置都沒有任何界定,同樣,這些法律也沒有對“歷史性”主權作出任何說明。中國曾在 2011年外交照會中指出中國的“國家主權及相關權利和管轄權”是由“歷史事實和法律證據”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像 1998年專屬經濟區以及大陸架法案本身都不屬于主權聲明法案。此外,“歷史……證據”指的是中國對島嶼而非對海域的主權要求。
僅僅由中國 1947年獨家出版的斷續線地圖并不能構成官方海洋主張的宣示。中國出版的“中國南海島嶼地圖”對宣示海洋主權毫無意義,而且該地圖僅在中國國內用中文出版這一事實,也不足以使國際社會所周知,因為不能正確提醒國際社會,使之了解這一主張,即使中國政府斷言已經做了這一工作。此外,中國歷年出版的各類地圖也在精確度、清晰度以及一致性方面有所欠缺,因此也無法表明其海洋主張的性質和范圍。國際法院對在處理布基納法索和馬里之間的邊界爭端時出臺的“原則聲明”對于地圖的法律效力有如下闡述:
無論是在邊境劃界還是海域爭端等國際領土沖突問題中,地圖的作用僅限于在不同的個案中提供精確度不斷變化的信息;而地圖本身,以及它們存在的事實無法成為領土所有權的證據,也就是說,在確立領土權利時,是國際法賦予了一個文件內在法律效力。當然,在某些情況下,地圖可能獲取此種法律效力,但是這種法律效力并不只源于其內在優點;因為這種地圖屬于一國或有關國家意志的有形表達的范疇。譬如說,當地圖附于正式文本并組成一個整體的時候,就是這種情形。除了這種明確界定的情況,地圖只是作為一種使用的可靠或不可靠的外部證據,和其他附帶的證據一起,成為建立或重構事實真相的證據。
中國 1958年領海宣言也與他們宣示的斷續線之內的“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所有權”不一致。該宣言指出“公海”把中國大陸及沿海島嶼與“其他所有屬于中國的島嶼分割開來”。早在中國 1958年宣言發布之前,“公海”不屬于任何國家水域、不受任何國家占有或專屬使用的概念就已經是國際法的既定規則,多說一句,在某種程度上,中國1958年宣言宣布了對位于中國東北海岸的一個海灣——渤海的歷史主權。如果中國在 1958年就認為其地圖斷續線內的海域為其歷史性水域,那么他們就應該像宣示對渤海主權一樣,申明他們對這一海域的主權。恰恰相反,在該宣言中,中國方面特別提及“公海”,從而表明中國并沒有認為斷續線內的海域具有歷史性特質。
國際社會大致認為中國繪制的斷續線與這種觀點有些契合。實際上,2008年發布的對歷史性水域的綜合研究沒有討論中國的斷續線,美國政府公開出版的歷史水域綱要也并沒有確認這些斷續線。一直到中國政府在本報告此前提及的 2009年外交照會上發布斷續線圖之后,國際社會的正式抗議才開始出現。
第二部分評估——歷史性主張是否有效?
中國沒有對斷續線內的海域(“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所有權”,historic title)或者對該海域的較低的權利(“歷史性權利”,historic rights)提出明確的歷史性主張。如果中國仍然堅持認為其地圖上的斷續線代表著一種歷史性主張,那么這種主張與國際法是相悖的。
支持中國歷史性主張的論據經常提及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承認這一主張。但是,中國在斷續線內的歷史性水域或歷史性權利的主張并不為《公約》所承認。無論是正式的《公約》文本,還是《公約》草案都清楚表明,除了近海岸的“歷史性海灣”(第10條)這一狹窄范疇以及領海劃界(第 15條)部分提到的“歷史性權利”問題之外,現代國際海洋法不把歷史特性作為任何判定海洋司法管轄權的依據。中國對南中國海的歷史性主張包括了遠離中國宣示的領土,因此牽涉到關于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可能的公海的《公約》規定。與第10條和第15條不同,《公約》內涉及到這些海洋區域的規定并不包含任何損害沿海國主權和司法權或所有國家自由權利的歷史主張的例外情形。
因為涉及到的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公海的《公約》條款并不包含有關歷史性主張的例外情形,《公約》在這一區域內的規定高于任何關于歷史性主張的聲明。1962年關于歷史性水域的研究報告——受通過 1958年《日內瓦公約》的大會委托——得出的結論,與1958年關于領海和毗鄰區公約的解釋一致。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沿用了有關歷史性海灣和權利的保留條款,與 1958年公約包含的條款在實質上相一致。如果《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起草者打算允許某國的歷史性主張可以壓倒其他國家明確規定的權利,該《公約》文本就應該表達這一意圖。然而,與1958年公約一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同樣限制了對海灣以及領海的劃界相關的歷史性主張。
因此,關于中國在南中國海可能的“歷史性權利”,任何此類的權利將因此需要遵守涉及相關活動的《公約》條款。《公約》規定了反映傳統的航海方法的航海條例。《公約》中同樣載有關于石油與天然氣的開采規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歷史性權利的例外情形。同樣,《公約》制定的漁業捕撈條例也包括了對不能作為主權、主權權利或管轄權依據的歷史性使用的限制條款。正如國際法院緬因灣會議1984判文所指出的,在其海岸200海里以內,沿海國家的漁業專屬管轄權可以優于該地區其他國家的使用權利。
也有觀點認為,“歷史性所有權(historic title)”以及“歷史性權利(historic rights)”是“不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控制的內容(因此)應該繼續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外的一般國際法的條款與原則加以調整”。這一立場不受國際法支持,也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綜合管轄范圍的誤讀。《公約》確立了所有海洋部分的法律體制。一如上述討論,凡是涉及到諸如海上航行、油氣開發以及漁業捕撈等事宜,實際上均受到《公約》的管理。因此,任何國家都無權在此類事項上通過“一般國際法”宣示歷史性水域或者歷史性權利而損害《公約》條款。盡管有些國家可能需要用“一般國際法”來界定《公約》中某些特定名詞的具體含義,比如第10條和第15條分別規定的歷史性海灣和歷史屬性,《公約》不允許任何國家把“一般國際法”作為判定海域管轄權的可選用依據,因為這與《公約》有關海域權利的條款是相悖的。
即便假設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性主張是由“一般國際法”而不是《公約》所決定的,中國的這一聲明也要在一般國際法的條款下接受審查。在這一前提下,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水域主張也同樣不能通過上文敘述的分析基礎背景下的 3部分法律測試中的任何一項:
(1)在南中國海沒有公開、眾所周知以及有效的行政管轄。在試圖建立對斷續線內海域的歷史性主張的時期,中國并沒有申明其主張的性質;事實上,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厘清斷續線之內海域主張的性質。同樣地,中國的主張也缺乏地理上的一致性與精確性。因此,這一聲明并不能滿足“公開”和“眾所周知”的標準,而這兩點正是歷史性水域的主張有效性的必要條件。
(2)在南中國海不存在持續的有效管轄。長期以來,其他聲索國在某種程度上對南中國海都進行了廣泛的利用,這與中國主權或專屬管轄權是不一致的。南中國海的許多島嶼和其他地貌并不僅僅為中國占有,還被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所占有,而且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的本土海洋主張也伸入到南中國海海域。這些國家在南中國海地區進行了各類活動,比如漁業捕撈和油氣勘探。在他們宣示的海域內,中國政府并沒有進行與其主權或專屬管轄權相一致的“有效的”或“持續的”管轄。
(3)中國在南中國海海域的權利行使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默許。沒有國家承認中國對斷續線內區域歷史性權利的有效性。由于中國的歷史主張缺乏上述討論的有意義的宣示,這些國家任何所謂的默認均是不成立的。某一聲索國因此不能依據非公開或實質上模棱兩可的主張作為他國默認的基礎,而與此相反,它必須將其主張建立在公開、眾所周知和足夠清楚的基礎上,這樣,其他國家才可能對其主張的性質和范圍有實際的了解。而對于斷續線地圖,在中國 2009年首次正式在國際社會提出斷續線地圖之時,幾個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就立刻正式、公開地提出了抗議。對于這一主張國際認同的缺乏,美國政府的做法也同樣值得注意。盡管美國政府在全世界積極抗議它認為過分的歷史性主張,它并未抗議這一斷續線,因為它不認為中國會提出這樣的一條斷續線,美國寧愿要求中國政府將其主張予以澄清。
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或國際法背景下,中國的主張早于《公約》的事實并不能作為其可以違背《公約》的依據。《公約》序言指出,其旨在“解決……有關海洋法案的所有問題”,并且建立一個提升穩定與和平利用海洋的法律秩序。其目標和宗旨是為了建立一個全面、可預測以及清晰的法律體制,以便于明確劃分各國在其海域內的權利和義務。因其主張早于《公約》通過的時間而允許某些國家違背《公約》的規定,是與《公約》的目標和宗旨相背離的,同時也會破壞《公約》的目標和宗旨。正如在20世紀50年代主張200海里領海主權的國家在今天不能合法地堅持上述主張一樣,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也都不能繼續對一個遠離其海岸的區域宣示歷史水域或歷史性權利。《公約》不允許此類主張,除非《公約》文本承認此類主張——諸如有關“海灣”的第 10條規定,否則《公約》的規定要高于任何此類的歷史性主張。作為條約法和國際習慣法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誕生后,各國在海洋主張方面需要與《公約》的規定保持一致。
結 語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并未按照國際法來闡明其與斷續線地圖有關的海洋主張。關于中國主張的性質和范圍,中國的法律、宣言、官方行為以及官方聲明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證據。現有的證據表明,中國可能有至少3種不同的解釋,包括:(1)斷續線是一些線,中國聲稱對線內島嶼以及那些島嶼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產生的海洋區域享有主權;(2)國界線;(3)界定各種所謂歷史性海洋主張的界線。
對于第一種解釋,如果中國地圖上的斷續線意在僅僅代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島嶼,那么與海洋法相符的話,中國在斷續線內的海洋主張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所規定的內容,即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些區域從中國大陸海岸和滿足《公約》第121條對“島嶼”的定義的地貌特征畫線。由于對南中國海島嶼的主權存在爭議,與這些島嶼相關的海洋區域也同樣存在爭議。此外,即使中國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根據第121條的規定,這些島嶼所產生的任何海洋區域也受制于與鄰國海洋邊界的劃定。
對于第二種解釋,如果中國地圖上的斷續線指的是國界線,那么,按照海洋法的規定,那些線則不具有適當的法律基礎。根據國際法,海洋界線由鄰國之間的協議加以確定;一國不可以單方面確立與另一國家的海洋邊界。此外,這種國界線不符合國家實踐和國際法理,在確定海洋邊界的位置時,這些國家實踐和國際法理不能賦予像南中國海上的那樣非常小的孤島以更多的權重,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與那些小孤島相對的漫長而連續的海岸線。而且,中國2009年地圖上出現的第2段、第3段和第8段斷續線不僅相對接近其他國家的大陸海岸,而且這些線的全部或一部分與中國所主張的任何地物的距離都超過了200海里。
最后,如果中國地圖上的斷續線意在代表中國所謂“歷史性海域”或對中國專屬海域的“歷史性權利”的主張,此類主張并不屬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0條和第15條所認可的歷史主張那一有限范疇。南中國海是一個遼闊的半封閉海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眾多沿海國家享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權利,國際海洋法不允許那些權利被另一國家基于“歷史的”海洋主張所取代。相反,公約的一個主要目的和成就則是將沿海國家所享有的海洋區域明確和一致起來。此外,即使歷史性海域的法理評估是可行的,斷續線主張也無法通過這一評估。
基于這些原因,除非中國明確闡明斷續線主張反映的僅僅是對線內島嶼、以及與國際海洋法相一致的那些地物所產生的任何海洋區域的主張,否則中國的斷續線主張不符合國際海洋法。
(原載美國國務院網站)
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鄭州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王 琛
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學專業2017級博士研究生 崔浩然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