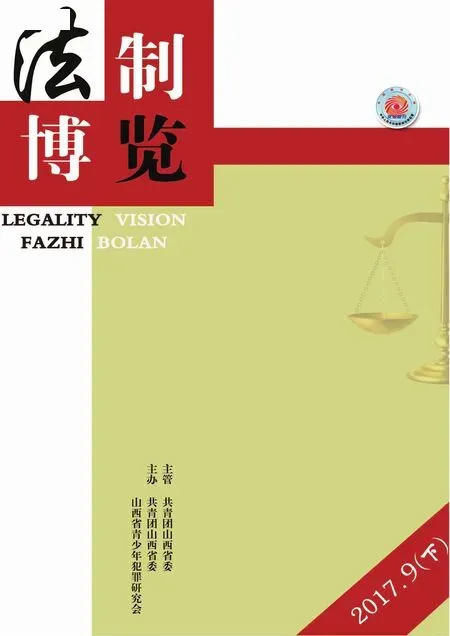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裁判路徑重構
——以法釋〔2017〕6號頒布為背景的思考
于 耀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裁判路徑重構
——以法釋〔2017〕6號頒布為背景的思考
于 耀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 401120
長期以來,我國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規則在司法適用中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規則存在著法律位階、認定標準以及價值取向方面的沖突。尤其是《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頒布以后,司法實踐的僵化和法官對法條的機械適用導致一些個案中的實質正義未能得到實現,質疑和反對聲音層出不窮。2017年2月28日,最高院又通過對原《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加“補丁”的方式①,再次強調了對夫妻中未具名舉債一方的利益保護。本文首先就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司法裁判標準進行梳理與反思,然后從司法中心主義的角度出發,嘗試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適用進行重新安排,構建合理的司法裁判路徑。
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困境
一、當前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困境
(一)法律解釋存在誤解
我國當前司法實踐中的通行做法是將夫妻共同債務的性質界定為夫妻連帶債務,由夫妻雙方對債務共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因此,債權人在向法院申請執行判決的時候,其執行標的不僅包括夫妻共同財產,還包括夫妻雙方的個人財產。②但《婚姻法》本身并沒有提到連帶責任的說法。《婚姻法》第41條③僅僅提到了“應當共同償還”,卻并未明確責任承擔的性質。從立法沿革上來看,我國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關于“共同償還”的對應表述分別為“以共同生活時所得財產”和“以共同財產償還”。④因而關于“共同償還”的正確理解應當是夫妻以共同的財產進行債務清償,承擔清償責任的范圍也以共同財產為上限。然而,在現實中該表述卻被望文生義地與共同債務、連帶債務、連帶責任等債法上的概念對應起來。最高院關于《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曾指出,“債權人與債務人設立債權債務關系之前,債權人對債務人的信賴建立在其夫妻關系存在和夫妻共同財產負擔能力的基礎之上”。⑤即便如此,也只能得夫妻共同債務的責任范圍是夫妻共同財產,而非雙方的全部財產的結論。最后,從保護債權人的角度出發,立法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夫妻一方利用夫妻關系的緊密性向另一方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但通過使夫妻對共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方式來達到此立法目的似乎有些矯枉過正。以常見的假離婚逃債行為為例,即便夫妻雙方約定將共同財產全部分給非舉債一方,后者也僅應以其所(多)接收的夫妻共同財產為限承擔連帶責任,而不應承擔無限的連帶責任。⑥
綜上所述,目前的司法實踐將《婚姻法》第41條中夫妻對共同債務的責任承擔方式錯誤地理解為“連帶責任”,不僅違反了法律解釋的方法,也造成了夫妻中未具名舉債一方的利益難以得到保護。
(二)法律規定存在沖突
當前我國針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法律規范非常豐富,存在著不同時期、不同位階、不同價值取向的法律規范,且這些規范相互存在著沖突,缺乏統一性,容易導致法官在法律適用上陷入難以抉擇的境地。具體而言,《婚姻法》第41條規定了夫妻共同債務的成立須以“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為限,這種理論被稱為“目的說”,即只有證明夫妻一方的舉債旨在為夫妻共同生活這一目的時,其所借債務才被認定為共同債務。⑦但由于夫妻關系具有緊密的人身性,債權人通常難以證明舉債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因此2001年新《婚姻法》出臺以來,大量出現了夫妻間利用假離婚的方式來轉移財產的行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出臺《婚姻法解釋(二)》,其中第24條本著保障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則對《婚姻法》第41條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是該條款在實踐中被法官“一刀切”地運用,即只要借債發生在婚姻存續期間,沒有法條規定的例外情況,就一律認定為共同債務,由夫妻承擔連帶責任。這種司法實踐雖然起到了節約裁判成本的作用,但卻凸顯出對債權人的過度保護,幾乎免除了債權人在訂立合同時的一切注意義務,對夫妻一方惡意串通他人虛構債務起不到任何防御作用。⑧正是由于這兩個價值取向截然不同的法律規定的存在,導致了法律適用中的沖突,甚至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現。
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裁判路徑重建
2017年2月28日,最高院在原《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基礎上增加兩款,即虛假債務和違法債務不予支持,再次重申了債務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向來是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前提。因此,各級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對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不能再僅憑《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就進行“一刀切”的認定,而是要綜合各認定規則并結合當事人的實際舉證情況,發揮出法院在證據認定中的的積極作用。筆者認為,在我國現行法的框架下,法院在對于夫妻債務的認定上要對債務的范圍進行細分,并在此基礎上適用不同的認定規則和舉證責任,以尋求對未具名舉債一方利益和債權人利益保護的平衡。具體而言,可以參考以下裁判進路:
(一)以債務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作為認定前提。即堅持《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新增的第二款和第三款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前提。同時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六條第二款以及第十九條的規定,綜合判斷查證借貸事實是否發生。
(二)以《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所確立的家事代理權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首要適用。就一方所負的真實合法債務而言,首先需要判斷該債務是否屬于因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或者該債務的那一部分屬于因日常生活所負。對于確實屬于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法院應當適用《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直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對于超出日常生活所負范圍的債務,法院推定為非共同債務,由債權人承擔表見代理的舉證責任。當然,由于《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并未明確家事代理權的具體范圍,法官應當結合通常生活經驗,并考慮到個體家庭的經濟情況予以判斷。
(三)超出日常生活負債范圍的債務,應當結合《婚姻法》第41條和《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共同判斷。具體而言,對于超出日常生活所負的債務,除依照《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進行認定之外,還需要結合夫妻雙方就該筆債務是否具有共同合意以及該筆債務是否用于共同生活等因素進行認定。裁判者不能片面地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一方舉債簡單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就舉證責任的分配而言,夫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以個人名義舉債,應當由舉債一方和債權人就否屬于共同債務承擔舉證責任,只有舉債一方和債權人能夠證明該筆債務的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另一方具有舉債合意的情況下其主張才能得到支持。倘若該部分債務的舉證責任分配給未具名舉債的一方配偶,由其證明其沒有舉債合意或者該筆債務沒有用于共同生活是難以做到的,也有違公平原則。
(四)堅守責任范圍的上限,明確未具名舉債一方配偶的責任限額。無論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情況如何,未具名一方的債務償還范圍應當以其離婚時所分到的共同財產為限。我國夫妻財產制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一方以個人名義的舉債應當以其個人財產進行償還為原則,以夫妻共同財產為上限,絕不能涉及另一方的個人財產,否則將會在突破合同相對性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同時,在債務的執行上,要樹立生存權高于債權的理念,債務的執行不能損害被執行人基本的生存能力,尤其要考慮到家庭撫養職能的實現,為被執行人的扶養家屬也應當保留必要生活費用。對被執行人名下的不動產進行執行時,要保障其生活所必需住房,防止出現被執行人無家可歸的局面。
三、結語
夫妻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具有緊密性,這就導致夫妻一方的舉債在某些時候必然要突破合同之債的相對性,這是市場經濟保障交易安全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在未具名舉債一方配偶和債權人之間尋求一個利益平衡,這是立法長期以來的追求。2000年修訂后的《婚姻法》第41條規定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需要以共同生活所負債為標準,這就導致了債權人舉證困難,故而出現大量的夫妻舉債后假離婚轉移財產以企圖逃避債務的情形發生。2004年《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企圖扭轉這一局面,以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作為共同債務的認定標準,雖然該舉措能夠簡化認定標準,節約司法資源,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間借貸不斷繁榮,該規則在司法適用中卻逐漸被僵化,甚至被法官機械適用而全然不考慮其他情況。隨之而來的,大量出現了夫妻一方偽造債務或者故意舉債損害另一方權利的現象,再次引發了社會上及學界對保護未具名舉債一方配偶權利的呼吁。最高法于近日又再次對24條進行了補充,同時又配套出臺了《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及夫妻債務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⑨,以加強對虛假訴訟的審查,防止夫妻一方或債權人濫用權利。雖然債務的合法性和真實性本來就是法院認定共同債務的前提,但是,最高法這一表態并非毫無意義,它至少預示著,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不再是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基本原則和唯一標準。
[注釋]
①法釋〔2017〕6號.
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婚姻法解釋(二)>)第25條、26條均提到了夫妻一方對共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③<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④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69.
⑤黃松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的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32.
⑥此類司法實踐,如(2010)粵高法審監民提字第47號(一審及二審判詞).此外,企業法上“債隨物走原則”也頗值參照:在原企業借新設公司之機而欲逃廢債務時,新設公司也僅僅是“在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補充責任或連帶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條、第7條;彭冰.債隨物走原則’的重構與發展[J].法律科學,2008(6).
⑦梁文書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解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223.
⑧劉雁兵.關于確認夫妻共同債務的審判思考[J].法律適用,2006(5):56.
⑨法〔2017〕48號.
D923.9
:A
:2095-4379-(2017)27-0048-02
于耀,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2016級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