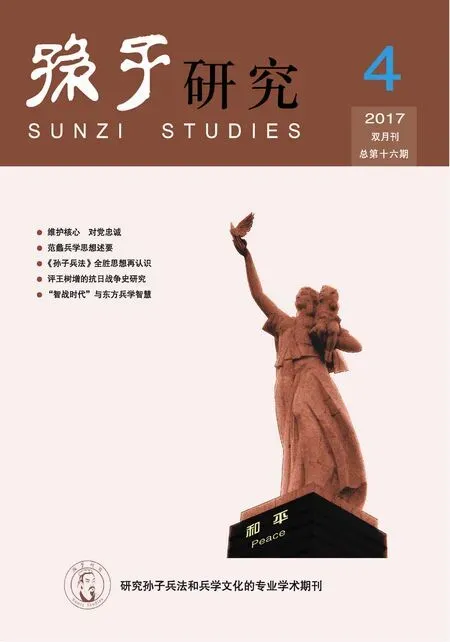范蠡兵學思想述要
黃樸民
范蠡兵學思想述要
黃樸民
范蠡是春秋后期著名的軍事家、謀略家。他在吳越戰爭中所以能扮演關鍵性人物的角色,發揮重大的作用,與春秋大國爭霸戰爭的背景密切相關;是楚國扶助越國,打擊吳國并制衡晉國戰略布局中的一步棋子。范蠡兵學思想體大思精、高明卓絕,突出體現了先秦時期南方兵學文化的基本特征與顯著成就,是中國古典兵學思想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范蠡 春秋歷史 爭霸戰爭 兵學思想
一、晉楚爭霸背景下范蠡之歷史使命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詳,春秋末期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扭轉吳越戰爭乾坤、改寫春秋后期歷史的關鍵性人物。
當時,列國紛爭,爭霸兼并無已,晉、楚、齊、秦等大國為了牽制和打擊各自的主要對手,紛紛“伐謀”“伐交”,爭取和聯合與國以為己援,力圖使爭霸對手陷于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面。
在整個春秋大國爭霸過程中,晉、楚角逐乃是一條主線,貫穿于春秋歷史的始終。其他像晉、秦之間的百年爭戰,齊、晉之間的偶爾戰事(鞌之戰),乃至后來的吳、楚戰爭,吳、越戰爭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不過是晉、楚爭霸戰爭的另類表現形式或回波余瀾而已。晉、楚爭霸的標志性事件,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戰、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戰、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戰以及稍后晉悼公在位期間的“三駕之役”。在這些戰事中,晉國取得了大多數戰爭的勝利,但它卻曾經輸掉了邲之戰。因此,在整個晉、楚爭霸態勢上,晉國稍占上風。“三駕之役”的勝利和蕭魚大會的舉行,標志著楚國已無力北上與晉國作全面的抗衡,即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晉爭”。但是,歸根到底,在整個春秋時期,晉國畢竟無法擁有對楚國的絕對優勢,而楚國雖然總體上處于被動的劣勢狀態,但也仍具有與晉國進行長期抗衡的基本實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晉、楚都將戰略重心投放到爭取盟國,努力置對手于多面受敵、兩線作戰的困境。
在這方面,晉國是率先著手進行部署和操作的。它曾積極扶植和支持吳國對付楚國,使其從側后騷擾、進攻楚國,嚴重抑制了楚國北上爭霸的勢頭。吳國建國歷史十分悠久,其政治中心在今江蘇南部一帶。其第十九代君主壽夢登位后,開始使用“王”的稱號:“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①《史記·吳太伯世家》。。他向中原先進國家學習“禮樂”,改良政治,發展經濟,繁榮文化,擴大對外交往,加強軍隊建設,使吳國迅速崛起而成為一個新興的強大國家。
吳國的崛起,與其西邊的強國楚國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與沖突。而晉國的有意介入,更使得吳、楚之間本已十分緊張的關系增添變數。當時,晉國出于自己同楚國爭霸中原的需要,采納楚亡臣申公巫臣聯吳制楚的建議,主動與吳國締結戰略同盟,讓吳國在側后打擊楚國,以牽制楚國勢力的北上。吳王壽夢二年(前584),晉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落實借吳制楚的戰略目標,與吳國國君壽夢締結實質性的對楚戰略同盟:“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①《左傳.成公七年》。日漸強大起來的吳國,正需要尋找大國做后盾,故欣然接受晉國的主張,擺脫對楚的盟屬關系,并積極動用武力,同楚國爭奪江淮流域。
自壽夢開始,歷經諸樊、余祭、夷末諸王,直至吳王僚,前后六十余年間,吳、楚兩國互相攻戰不已,先后爆發了多次較大規模的戰爭,包括州來之戰、鳩茲之戰、庸浦之戰、舒鳩之戰、夏汭之戰,乾溪之戰、長岸之戰、雞父之戰等等。這些戰事大都是吳的進攻和楚的反進攻,以爭奪淮河流域與長江北岸地區為重點,而吳國勝多負少。從總的趨勢看,是楚國日遭削弱,國勢頹落;吳國兵鋒咄咄逼人,漸占上風。到吳王闔閭時,雙方終于爆發了一場決定性的戰爭——柏舉之戰。
發生于公元前506年的柏舉之戰,是春秋晚期一次規模宏大、戰法靈活、影響深遠的大戰。是役,吳軍在闔閭、伍子胥、孫武、夫概等人的指揮下,先以“亟疑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的方式疲楚誤楚,同時翦楚羽翼,伐謀伐交,創造了十分有利的進攻態勢。待一切就緒后,吳軍即果斷出擊,靈活機動,因敵用兵,以迂回前進、后退疲敵、尋機決戰、長驅奔襲等戰法,直指楚都,五戰入郢,一舉戰勝了多年的宿敵楚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春秋晚期的整個戰略格局,為吳國的進一步崛起,進而爭霸中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楚國為了擺脫這種被動的戰略態勢,也利用越與吳爭奪江河湖澤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導致的矛盾,積極鼓動越國從側后威脅和打擊吳國,以減輕吳國對楚的壓力。而越國為了抗衡吳國,也正需要有楚國這樣的大國支持。于是,雙方一拍即合,迅速聯合起來,結成了相對穩定的戰略同盟。
越國在吳、越兼并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范蠡與文種,皆為楚國人士。其中,范蠡為楚國宛人(今河南南陽),文種系楚之郢(今湖北江陵一帶)人。他們都是肩負楚國的戰略重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越國,充當外臣,為越國滅吳殫精竭慮,不懈努力,并最終實現了楚國的戰略意圖。
范蠡入越后,由于政見卓犖、智謀超群,很快就獲得了越王勾踐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將軍,與文種一文一武,輔佐勾踐經國治軍,即所謂“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②《越絕書·外傳紀策考》。。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們終于使越國轉弱為強,在政治、軍事上徹底戰勝吳國,并幫助勾踐登上了“霸主”的地位:“當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③《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但是,事成之后,范蠡掛冠歸隱,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為一代巨商,世稱“陶朱公”。 當然,范蠡的這種選擇,也屬于迫不得已,應該與其出身于楚國不無瓜葛。在滅吳事業未竟之時,勾踐需要借重來自他國的能人干臣,替自己好好干活,但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定式,決定了勾踐不可能真正毫無保留地信任范蠡和文種。對勾踐而言,楚國的人才不過是利用的對象,一旦完成滅吳大業,這兩位大功臣的利用價值就不復存在了,即所謂“以勢利相交,利盡而恩義絕”,這時就應當棄之如敝屣。因此,范蠡的歸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功成身退”那么簡單。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勾踐內心深處對“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離與排斥的結果。
范蠡在軍事上有著很高的造詣與重大的建樹。對此,他本人也不無自負,曾云“兵甲之事,種不如蠡”①《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班固《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著錄有《范蠡》二篇,屬“兵權謀家”,顏師古注云“越王勾踐臣也”。這說明,范蠡曾有兵書流傳于世。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其書早在唐代以前就已失傳,《隋書·經籍志》即不曾著錄。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從《國語》《史記·貨殖列傳》《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史籍中尋找到某些有關內容,并據此初步考察范蠡兵學思想的大致情況以及特色。
《司馬法·嚴位》云:“人方有性,性州異。”范蠡的兵學思想同樣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區域——楚國,深受《老子》哲學思想以及陰陽五行觀念的熏陶和影響,這就決定了其軍事思想包含有豐富的樸素辯證法內涵。而他所從事建功立業的場所——越國,又是處于明顯被動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戰勝強大的吳國,必須韜光養晦,積蓄實力,逐漸完成戰略優劣態勢的轉換。這就決定了其兵學思想立足于后發制人的立場,即以積極防御為主要手段,最終實現反攻勝敵的戰略目的。
二、范蠡兵學思想擷要
具體地說,范蠡的兵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備戰為重的戰略觀念
“慎戰”與“備戰”并重的戰爭觀,“備者,國之重”,是中國古代兵學思想中的積極因素,歷史上絕大多數軍事思想家,都十分強調搞好戰備、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孫子兵法·九變篇》就明確強調:“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這一問題上,范蠡的認識沒有例外。他認為,從事戰爭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些條件既包括政治、經濟因素,也包含軍隊實力狀況。“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眾,則主安;谷多,則兵強。王而備此二者,然后可以圖之也。”②《越絕書·枕中》。他還進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陳隊伍軍鼓之事,吉兇決在其工。”③《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其基本原則就是:高度重視,充分準備,措施得力,以應萬變。用范蠡自己的話來說,即:“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④《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范蠡有備無患的思想還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它揭示了國防建設的一般規律。在階級社會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歷史上,總有少數戰爭狂人,出于滿足稱霸等私欲,乞靈于戰爭,窮兵黷武,將戰爭強加在人們的頭上。想乞求這些人發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現實的,正確的對策是,既反對戰爭,又不懼怕戰爭,以戰止戰,爭取和平。
要做到“審備慎守”“備設守固”,就必須修明政治,動員民眾,發展經濟,加強軍隊建設。這樣,廣大民眾才會積極投身于國防建設事業,國家才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持反侵略戰爭,軍隊才能具有強大的戰斗力并粉碎敵對勢力的進攻。這些,都是確保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也是范蠡有備無患思想應有的邏輯意義。
(二)“隨時以行”的攻守原則
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它的整體性與融合性。歷史上思想家在進行理性思辨活動時,其邏輯起點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構成模式,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與圓融,注重以普遍聯系,相互依存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全面認識和宏觀把握問題。反映在軍事斗爭領域,即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政事”推論“兵事”。
這一點在范蠡的兵學思想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在他的哲學觀念中,“天道”與“人道”是和諧一致的。他認為,“天道”的屬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①《國語·越語下》,以下引文凡不注出處者,均出此篇。。因此,人們在從事社會活動時,也應當因循自然,順應天時,“自若以處,以度天下”。這一思想引入軍事斗爭領域,就是所謂的“隨時以行”。這里所說的“時”,是指時機,也可引申為戰機。“隨時”,就是依據時機是否有利、戰機是否成熟來決定作戰行動展開與否,既不超前,也不滯后,這也叫作“守時”,即所謂“隨時以行,是謂守時”。
范蠡的“隨時”“守時”原理落實到具體的攻守行動中,實質上包含有兩層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意謂當有利的時機還沒有出現,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切不可主動發起進攻,而應采取積極防御,等待時機,以求克敵制勝:“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②《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他嚴肅指出在時機不成熟情況下盲目對敵進攻,那就會“逆于天而不和于人”,這就叫作“強孛”,而“強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慘重的失敗,“王若行之,將妨于國家,靡王躬身”。第二層意思是指“得時無怠,時不再來”。這是要求戰爭指導者善于捕捉戰機,一旦遇到有利的時機,就要適時地轉防御為進攻,而絕不能猶豫不決,貽誤戰機,縱敵遺患。他說:“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即應該以最快的速度去進攻敵人,實現自己后發制人的作戰目的。他指出,如果錯過了有利的時機,就會給自己帶來諸多不利,留下禍患,“得時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隨時而行”的攻守指導原則,在吳越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高明的運用。當越國尚處于被動弱小的劣勢地位之時,范蠡多次諫阻越王勾踐主動攻吳的計劃,反復用“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的道理說服勾踐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敵人力量的同時積聚自己的實力,為實現敵我優劣態勢的轉換,發起最后的反攻創造條件。而當吳國實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機出現時,則當機立斷地輔佐勾踐及時發動滅吳之戰,打得對手措手不及,全線崩潰。并且,他堅決地實施連續進攻,擴大戰果,直至攻占吳都姑蘇(今江蘇蘇州),贏得最后的勝利。
(三)“變易主客”的實力運用方針
所謂“主客”,是中國古代兵學的一對重要范疇。“主”,通常是指戰爭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實施防御的一方,起初處于相對被動的一方;“客”,則通常是指戰爭中進入他國境內實施進攻的一方,起初處于相對主動的一方。根據戰場形勢選擇適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為主,或變主為客,是從事作戰指導中的重要命題,也是軍事家奪取戰爭主動權、克敵制勝的基本保證。兵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廣泛的推崇,被視為古典兵學寶庫中的瑰寶,原因之一即是其作者在“變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闡述,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稱的那樣:“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變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時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關系的豐富內涵,那么我們對范蠡有關“變易主客”的實力運用方針的價值也就容易認識和把握了。應該說,這一方針在范蠡的兵學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積極意義。
概括地說,與《孫子兵法》中提倡進攻速勝的戰略指導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戰略指導上更側重于持久防御,強調為主而不輕率為客。這當然是與越國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戰略劣勢地位的特殊形勢有關。
范蠡注重為主之道,反復闡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的必要性。為此,他積極主張持久防御,避敵鋒芒,防止出現過早決戰的被動不利局面,指出“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做到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屈求伸,以主應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處,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極無為的舉措,而是積極能動的作為。換句話說,它僅僅是手段而絕非是目的。其最終的目標還是“變易主客”,即適時由戰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轉為戰略進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滅以為期。而實現“變易主客”的關鍵,就在于通過各種積極的手段,轉化雙方的優劣態勢,剝奪敵人有利的條件,暗中增強己方的實力,從而擺脫被動,立于主動的地位。用范蠡自己的話來講,就是“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這種以暫時的退守換取最后的攻取的戰略指導,乃是高超英明的實力運用方針,是范蠡軍事思想的優秀內核,它對于中國古代積極防御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四)“因情用兵”的致勝之道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敵而制勝”“致人而不致于人”①《孫子兵法·虛實篇》。,是作戰指導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來戰爭指導者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的用兵境界。作為春秋時期屈指可數的軍事家、謀略家,范蠡在這方面與兵圣孫子之間實有相通之處,他同樣以因情用兵為指導戰爭活動的最高原則。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運行規律在軍事斗爭領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義。范蠡認為,“天道”的運行是“贏縮轉化”的,即所謂“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世間萬事萬物同樣處于不斷變化、循環往復的過程之中。這就要求人們善于相因,“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而這一基本原則,同樣可應用于軍事斗爭。
為此,他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返,兵勝于外,福生于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這里所說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敵制勝,亦即根據戰爭的客觀實際情況的變化來決定作戰行動。在這一原則指導之下,后發制人和先發制人的內在關系乃是辯證的、相輔相成的。后發制人固然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排斥一定條件下的先發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戰指導上,后發制人和先發制人方針的不同應用,都必須隨時隨地靈活機動加以處置。在實行后發制人的原則時,要取法于陰象,即沉著應付,不動聲色,持重待機;而在先發制人時,則要取法于陽象,即雷厲風行,迅猛進攻,所向披靡!對此,范蠡本人曾作過深刻系統的論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后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從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認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淵源脫胎于《老子》,但又發展豐富了《老子》。《老子》一書在講進退、剛柔、強弱、先后時,總是無條件地強調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謂的“不敢進寸而退尺”①《老子·六十九章》。,一味地否定進、剛、強、先這一面。范蠡則不同,他避免了機械化、簡單化的傾向,主張量敵用兵,靈活機動,或進或退,或剛或柔,或先或后。他的這一認識,比較《老子》而言,無疑是辯證全面深刻得多了,這顯然是源于《老子》而又高于《老子》。
作為中國古代兵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范蠡的軍事活動實踐與兵學理論造詣,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和充分借鑒。
(責任編輯:李興斌)
Summary of Fan Li’s Thinking of Military Science
Huang Pumin
Fan Li is famous militarist and strategist of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 of Wu and the State of Yue,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of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of the powerful stat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State of Yue is a piece in the strategic layout that the State of Chu supported the State of Yue to attack the State of Wu and containing the State of Jin. Fan Li’s thinking of military science is extensive, profound and outstanding, which prominently show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southern military science culture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It also is a brilliant pearl in the treasure-house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lassical military science thinking.
Fan Li;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War of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Thinking of Military Science
B22
A
2095-9176(2017)04-0022-06
2017-06-21
黃樸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