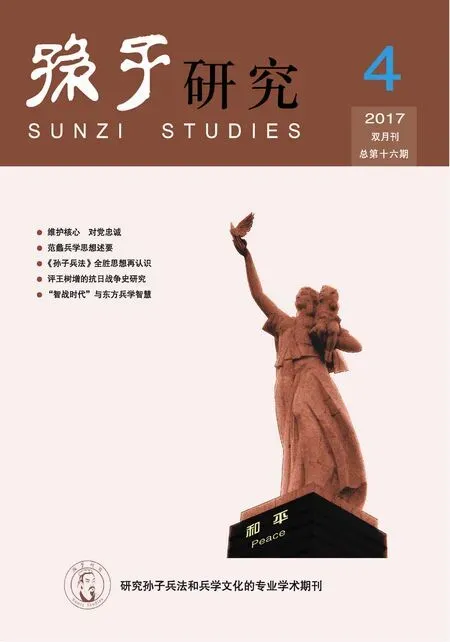《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再認識
姚振文
《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再認識
姚振文
本文在分析《孫子兵法》全勝思想內容及借鑒前人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對孫子全勝思想提出幾點新的看法和認識:孫子全勝思想更多的是對軍禮文化傳統的繼承而非個人創見;孫子全勝思想是出于我方之“利”的目的而非對敵方“仁”之關懷;孫子全勝思想不僅是一項思想內容,而且更是一種思維方法;孫子全勝思想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戰爭控制思想。
孫子兵法 全勝 再認識
全勝是《孫子兵法》的重要戰略思想之一,古今中外,人們對其贊譽有加,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如唐太宗李世民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乃是“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不殺”①《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的最高戰略境界。西方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在其《戰略論》中指出:“最完美的戰略,也就是那種不必經過嚴重戰斗而能達到的戰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②葛榮晉:《葛榮晉文集》(第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頁。吳如嵩也認為:“孫子的‘全’就如同孔子哲學的‘仁’,老子哲學的‘道’,是我們研究孫武軍事思想的一條重要線索”,“不經過直接交戰而使敵人屈服的‘全勝’戰略思想,是孫武對戰爭所希圖達到的最高理想境界。”③吳如嵩:《徜徉兵學長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頁。然而,在有關全勝思想評價的眾多的贊美聲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如郭化若將軍認為:“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孫子》中含有某些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成分。例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對戰爭問題的唯心論表現。”④孫武原著:《孫子兵法》(第1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頁。黃樸民先生則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并非《孫子兵法》精髓所在,不宜被過分“看重”和“夸大”。⑤黃樸民:《對“不戰而屈人之兵”評價要實事求是》,載《〈孫子〉新論集粹——第二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選》,北京:長征出版社1992年版。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任何一個學術問題,都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只有保持學術寬容的態度,彼此碰撞交流,才能使研究結論愈加接近于真理。有鑒于此,筆者結合自己對孫子全勝思想的體會和認識,也談幾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孫子全勝思想是對軍禮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而非個人創見
近年來,常有學者提出全勝思想是孫子獨創或創新的觀點。例如,“孫子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這個戰爭指導思想,并將其列為善戰的最高標準,應當說是軍事思想史上的一個獨創,至今仍有現實意義”①高銳:《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論新探》,載《孫子新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1—8頁。;“孫子繼承了這種講仁道、愛和平的思想,并將其運用于軍事領域,創造性地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編:《孫子兵法與和諧世界:第八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頁。;“《孫子兵法》‘謀攻’篇,主要論述了如何以謀略戰勝敵人”,“創造性地提出‘全勝’的思想。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③童光慶,鄢欣:《大學生軍事教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頁。。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其實有待商榷。
這是因為,春秋時代,在軍禮文化傳統的約束與規范下,“不戰屈敵”實在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此種現象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其一,戰爭中實力強大的國家,鑒于“興滅國,繼絕世”的戰爭目標與原則,對小國,或施以政治謀略,或加以軍事威懾,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條件而屈服。例如,公元前618年,楚穆王率軍伐鄭、陳,兩小國在楚軍兵臨國境后不戰而臣服;公元前571年,晉、宋、衛聯合攻鄭,亦曾逼迫鄭國求和。其二,大、中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矛盾和沖突,也是多以雙方妥協或一方屈服為結局,最后通過訂立盟約,結束戰爭狀態,以至于會盟成為當時軍事活動的一種重要手段。如公元前656年,齊桓公聯合諸侯國軍隊共同伐楚。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楚成王先派使者到齊軍中質問齊桓公為何要侵犯楚國,隨后又派屈完到齊軍中進行交涉,雙方先后展開了兩次針鋒相對的外交斗爭,最終達成妥協,訂立盟約。其三,當時有些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也可有理有據地通過闡釋道德或誠信原則,實現不戰而退敵的理想目標。如公元前634年,齊師伐魯,魯公使展喜以酒食犒勞齊師。齊孝公問展喜:“魯人為何不恐?”展喜答:“有先王之命。從前周公、太公夾輔成王,成王賜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及君即位,諸侯望之,豈其棄命廢職!如何對待先王?君必不然。因此而不恐。”一席話說得齊孝公羞愧難言,即刻引兵而還。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當時的大多數戰爭并非以消滅對方軍隊、兼并土地為目的,而是以使對方屈服為根本宗旨。而這一戰爭的時代特色,無疑為全勝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歷史依據。也正因如此,不只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其他一些先秦諸子也有同樣或類似的觀點和見解。比如,《軍志》《軍政》等古兵書中即早已有了“全勝”思想的萌芽。“有德不可敵”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⑤《左傳·昭公二十一年》。等,即是這一思想的濫觴。再如,孔子亦曾盛贊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⑥《論語·憲問》。荀子則有言:“……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者之道也。”⑦《荀子·王制》。老子主張:“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⑧《老子·六十八章》。管子也有“至善不戰”①《管子·幼官》。之論。《尉繚子》亦談道:“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逾垠之論,敗敵國可不戰而服。”②《尉繚子·戰權》。甚至《鬼谷子》也有全勝軍事思想:“主兵曰勝者,常戰于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③《鬼谷子·摩篇第八》。“戰于不爭”意思是不使用武力而戰勝之,“戰于不費”意思是不花費錢財就能戰勝之,其思想內涵的實質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可見,能夠認識到“不戰屈人”是一種有效的斗爭方式,并將這種實踐中客觀存在的斗爭方式由感性認識轉變為理性認識,使其上升到理論層次的,并非孫子一人。他們與孫子大致處于同一個時代(春秋戰國),均是立足于自己的學派主張和思想體系提出全勝之論的,各有自己的認知視角和側重點,我們并沒有任何證據和線索證明他們的觀點都是源自《孫子兵法》。
綜上所述,孫子的全勝思想,并非完全是其個人的創新之見,而更多的是對古代軍禮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以往戰爭經驗的抽象提煉和概括,是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內在邏輯演繹體現在戰爭問題上的自然結論。當然,我們也不否認孫子在這一思想理論方面的創新成分和獨特貢獻。首先,孫子提出全勝思想,主要是在戰爭范圍和戰爭領域內,是專門的軍事理論,這一點不同于儒家從政治視角和仁義層面提倡全勝。其次,孫子的“全勝論”是與他的“破勝論”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孫子作為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一方面認識到春秋末期戰爭的殘酷性和復雜性,故創新提出“兵者詭道”的思想和一系列的兵法謀略原則,以適應戰爭形勢的新變化;另一方面,孫子作為偉大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哲學家,又不滿足于對一般制勝法則的總結和概括,而能從國家利益的高度和歷史的深度來思考戰爭問題,孜孜以求戰爭的最高理想境界——全勝,從而實現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完美統一。
二、孫子全勝思想是出于我方之“利”的目的而非對敵方“仁”之關懷
孫子為何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大多數人認為其主要目的是出于我方戰爭利益的考慮,所謂的“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是為了避免雙方直接的武力沖突和攻城災難,進而使我方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但也有人試圖從更高的“仁義”層面理解孫子的全勝思想,“孫子兵法不僅重視對本國集體性的軍事人道主義關懷,而且更具有人道意義的是出于對他國、他城等集體性人權的尊重與保護,關注著敵國、他國的生存權利,以期將軍事人道主義關懷倡揚到最高理想境界”。如《孫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此‘五全’即是出于‘全’他人之國的具有集體意義的人道主義關懷”④王聯斌:《走向安國、人道與和平——孫子兵法道德資源對現代文明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第149—155頁。。對于后一種觀點,學術界是存在爭議的,我們需要從孫子全部戰爭價值觀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
孫子重“利”,毋庸置疑。《孫子兵法》全書講“利”的地方有52處之多,所謂“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軍爭為利,軍爭為危”,“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和為變者也”(《軍爭篇》);“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九變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這其中的“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一句話,竟然在《軍爭篇》和《火攻篇》兩次重復出現。可見,孫子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利本主義者,《孫子兵法》戰爭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就是“利益”。陳學凱曾指出:“正如儒家把‘忠孝’、‘仁義’作為自己的價值標準一樣,《孫子》一書則把戰爭對國家、人民、軍隊的‘有利’和‘無利’作為自己的價值標準……于國、于民、于主有利,是進行戰爭的最高原則。”①陳學凱:《論孫子兵法對古典軍事學的貢獻》,《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69—74頁。
孫子是否講“仁”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戰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安國全軍,因此《孫子兵法》開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為了實現安國全軍的目標,孫子十分強調將帥的責任與道德素養:“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謀攻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地形篇》)同時,將帥還要愛護士兵、以情帶兵,“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篇》)此外,《用間篇》還從十分重視情報的角度專門講到了“仁”這個字:“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孫子兵法》所講之“仁”主要是針對己方,而非敵方。這在《孫子兵法》全書中有大量的內容可以作為說明:“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作戰篇》);“侵掠如火”,“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軍爭篇》);“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于饒野,三軍足食”(《九地篇》)。這是公開提倡對敵方、敵國赤裸裸的掠奪,所傷害的不僅是敵方的統治者,也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再者,《火攻篇》專門介紹了一種威力巨大的“火攻”戰術,然而“火攻”既是戰爭中最有效的作戰方式,也是戰爭中對敵方士兵傷害最大的作戰方式,所以,當年“二戰”中讓人驚悚的火焰噴射器,現在也早已為國際所禁用。試想,如果不是出于一種對于戰爭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要兼顧敵方民眾,考慮人道主義關懷,《孫子兵法》怎么會大力主張火攻呢?
所以,孫子在《謀攻篇》提出的“五全”及全勝思想,力求保全的是己方的國家、軍隊,強調的是己方戰爭利益的最大化,而絕非敵國、敵城及民眾的利益,更不是什么人道主義關懷。否則,《九地篇》中的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又作何解釋呢?當然,我們不否認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過程中,客觀上具有減少雙方人員傷亡及物資消耗的進步作用,但這絕非孫子的主觀意愿。
《孫子兵法》全勝思想之主要出于“利”之目的而非“仁”之關懷,我們還可以從戰爭的本質及當時的時代背景予以論證分析。戰爭是不同政治集團圍繞根本利益進行的你死我活的暴力對抗。“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②吳自選:《對外傳播翻譯:思考與實踐》,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頁。孫子所處的春秋末期,時代思潮及戰爭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戰爭過程變得越來越復雜和殘酷,戰爭目的也變得越來越現實和理性。而《孫子兵法》作為兵學理論的杰出代表,必然強調功利的理性精神,必然“一切以現實利害為依據,反對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愛憎和任何觀念上的鬼神‘天意’來替代或影響理智的判斷和謀劃”①李澤厚:《孫、老、韓合說》,《哲學研究》1984第4期,第41—52頁。。可以說,“利”是孫子進行戰爭研究的根本出發點和立足點,原先軍禮中強調的“仁”的原則只能作為戰爭制勝的輔助條件來對待。所以,全勝思想絕對不可能是基于對敵方的人道主義關懷而出現在《孫子兵法》中。
再者,我們還可從孫子求仕于吳的個人目的來分析這一問題。當時,孫子千里迢迢從齊國來到吳國,恰逢吳國新興、與楚交惡之際,新任君主吳王闔閭極富遠見卓識,且野心勃勃,圖謀爭霸。此時,孫子以客卿身份向吳王進獻“十三篇”,目的就是要說動闔閭重用自己,以輔佐吳王成就霸業,同時也施展自己的經國治軍之才,實現自己宏偉遠大的理想抱負。試想,在這種背景之下,孫子怎么可能迂腐地對敵國講仁義,使自己的兵法理論像儒家思想那樣“迂遠而闊于事情” 呢?認清大勢,順應潮流,以利為本,以仁為輔,這既是《孫子兵法》整個理論體系的立足點,也是孫子全勝思想的根本宗旨。事實上,除《孫子兵法》流傳后世以外,孫子的人生經歷也正是因為“功利”而受到后人的高度評價:“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②《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三、孫子全勝思想不僅是一項思想內容,更是一種思維方法
孫子在《謀攻篇》進一步闡釋全勝思想時提到一句話:“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對這段話中的“必以全爭于天下”,古人有不同的理解。曹操的解釋是:“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于天下,而不頓兵血刃也。”③《十一家注孫子·謀攻篇》曹操注。這其中的“必完全得之”,顯然是指結果或目的。李筌的解釋是:“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兵收利也。”④《十一家注孫子·謀攻篇》李筌注。這其中的“以全勝之計”,顯然是指手段和方法。可見古人對于“全勝”,本來就有目的或手段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筆者看來,“全勝”之義本身已包括了目的和手段兩個方面。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一句,“屈人之兵”是目的,“不戰”是手段,只不過“不戰”相對于“戰”是更高明的手段,是“善之善者也”。臺灣學者鈕先鐘曾經指出,所謂“全”者在孫子的思想中也有廣狹二義。從狹義的觀點來解釋,“全”就是“破”的對應詞。簡言之,所謂求“全”,即力求保持現狀而不予破壞,至少也應把破壞或損毀減至最低限度。從廣義的觀點來解釋,“全”就變成了一種抽象的哲學概念,而在思想方法的領域中也代表一種特殊的思考途徑。⑤鈕先鐘:《孫子三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頁。
就此而言,孫子的“全”字無疑具有方法論的內涵,并且已經上升到戰略層次,涉及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問題,其本質是一種國家戰略或大戰略。對于后人而言,深入研究孫子的全勝思想,必須從下述三個方面對這種方法論的意義和價值予以審視和觀照:
首先,要立足于宏觀視角,綜合運用政治、外交、經濟、武力威懾等手段實現全勝。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在成就霸業期間,就非常注重綜合手段的利用,尤其是善于運用“會盟”這種“不戰”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在位43年,參與戰爭20余次。其中,除了長勺之戰、乾時之戰等個別戰例外,其他都是憑借軍事行動的威懾作用,促成各方會盟,來達到預期的戰略目的的,即所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春秋時期另一位霸主楚莊王,也具備這種大戰略的思維意識。他既注重武力的基礎作用,又特別重視運用政治、外交等手段配合軍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是“伐謀”“伐交”與“伐兵”“攻城”多措并舉,多管齊下。例如,他在以武力攻打國內若敖氏叛亂勢力的同時,注重以政治攻心的方法,瓦解叛軍的意志,分化敵人的營壘,最后取得勝利。又如在邲之戰前夕,他先用外交手段分化、拆散晉國的同盟,使晉國處于孤立無援的狀態,從而為楚軍一戰而勝創造了有利條件。
其次是通過高層次的戰略謀劃和戰略實施,著眼于整體和根本的利益,來運作自己的資源和實力,最終取得整個戰爭格局中的主導地位。戰爭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戰爭,孫子的“伐謀”“伐交”實際就是超越了單純的軍事領域,把雙方的對抗轉換到政治、外交層面進行較量,使雙方的斗爭在更高的層面展開,而越是在這樣的高層面展開斗爭,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小,獲得的收益卻越大。中國歷史上莊子說劍的故事,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種高層次運作戰略資源的思想境界:“天子之劍,以燕溪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劑,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天下服矣……”莊子強調的是什么?就是要在更大的空間、更高的層面去運作戰略資源,反對在狹窄、低下的層面,如同“庶人之劍”那樣單打獨斗。戰略關注點升得越高,手段和策略就會越多樣,所能運用起來的資源也就會越無限,這就叫戰略對抗點上移。在戰爭中,任何一位高明的統帥,都不會把軍事實力耗在局部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上,而是把有限的兵力和資源放在整體戰略布局的高端與關鍵部位,以求得最有利的戰略態勢。這體現的正是戰爭指揮者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的卓越智慧。
其三是立足長遠,規劃自己的戰略手段和戰略目標。“伐謀”與“伐交”兩種手段,相比于直接的暴力拼殺,運作的時間和周期更長,這就需要決策者和指揮者具有前瞻意識和長遠眼光。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①陳學凱:《論孫子兵法對古典軍事學的貢獻》,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第69—74頁。從事任何社會活動,都要求人們要深謀遠慮,未雨綢繆,這在生死較量的軍事斗爭方面尤其如此。作為軍事統帥或將領,如果不能參悟長遠的戰略利益與眼前的戰術得失之間的關系,只顧眼前的、暫時的蠅頭小利,那么他至多只能成為普通的戰將,而不可能成為高明的戰略家。從戰略層面講,中國歷史上所謂的“道勝”,實際就是一種立足長遠和根本的戰略思想和理論。荀子有言:“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②吳自選:《對外傳播翻譯:思考與實踐》,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頁。尉繚子也談道:“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③《尉繚子·戰威》。這里講的“王奪之人”及“兵以道勝”,實際就是通過施仁政、講仁義贏得人心,進而從根本上改變雙方力量對比格局。然而,這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最高領導者養成未來意識,進行遠程思考,立足長遠規劃自己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手段。博福爾在其名著《明日戰略》一書中說過:“戰略不是為今天(for today)而設計,而其一切都是為明天(for tomorrow)著想。”④轉引自鈕先鐘《戰略研究》,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頁。
四、孫子全勝思想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戰爭控制思想
全勝思想本質上是一種戰爭控制思想,體現了一種戰爭節制意識。這種節制主要表現為對戰爭暴力手段運用的限制及戰爭損害程度的控制。在孫子看來,既要承認戰爭乃“國之大事”,理性面對,認真謀劃,又必須“慎之”“警之”,保持一種敬畏的意識,將戰爭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這樣才是“安國全軍之道”。宮玉振在《和合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兵學的文化性格》一文中談道:“全勝實際是一種對戰爭進行節制的意識: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戰爭必然對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中國傳統兵家從一開始就對戰爭既可傷人、又可傷己的兩面性有深刻的體認。用兵者對于暴力的使用必須保持節制,堅持決策上‘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原則;同時,軍事行動也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否則用兵不已,為勝利而追求勝利,走上窮兵黷武之路,只能是禍不旋踵。”①宮玉振:《和合價值觀與中國傳統兵學的文化性格》,《濱州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對于這種戰爭控制思想,中國其他兵家也有深刻的見解。如《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②《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孫臏曾明確指出:“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③《孫臏兵法·見威王》。吳子也有類似的觀點:“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④《吳子·圖國第一》。這一思想理念,在楚莊王的具體軍事行動中有著更深刻的體現。例如,當鄭國表示屈服的時候,他主動撤圍,同意對方的請和要求;當宋國頑固抵抗失敗、愿意媾和時,他非常大度地寬恕宋國的所作所為,同意雙方結盟;當陳國滅亡后,他又根據“興滅國,繼絕世”的禮樂文明精神,同意其恢復國家。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楚國在邲之戰中大獲全勝之后,許多楚國將領主張將晉軍死亡士兵的尸體疊壘為“京觀”,以炫耀楚軍的神勇。然而,楚莊王堅決制止了這種舉動,并就此發表了深刻的見解:“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⑤《左傳·宣公十二年》。這也就是中國傳統兵學文化的最高境界——“止戈為武”,因為戰爭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為實現和平迫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他的這一卓越見解,正是孫子全勝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兵家戰爭控制思想的歷史見證。
孫子的戰爭控制思想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產物。農耕文明的特點不同于游牧文明,對于農業民族來說,戰爭往往更多地意味著生產力的破壞,乃至社會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的失衡。倪樂雄先生談道:“漢民族現實生活的幸福和希望都依賴于土地上的收獲,任何性質的戰爭都與這種農耕生活的秩序和狀態發生尖銳的沖突。這就是《詩經》中‘征夫怨’、‘思婦哀’等反戰意識和厭戰情緒的終極根源。”⑥倪樂雄:《東西方戰爭文化的原型蠡測——《荷馬史詩》與《詩經》的比較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冬之卷(總第6期),第116頁。在農耕文明社會中,一方面,戰爭被賦予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和掃除生產力發展障礙的最高使命;另一方面,任何性質的戰爭在客觀上又都直接影響農耕生產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人們在不得已動用戰爭暴力的同時,必然考慮如何把戰爭對社會的破壞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愿望。這正是孫子戰爭控制思想產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兵家對待戰爭的這種謹慎而又節制的心態,與西方戰爭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方,通過無限增大戰爭暴力以加強對敵方的打擊程度,幾乎成為軍事家必須遵循的基本法則。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明確指出:“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⑦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刪節本),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5頁。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中更坦言:“要對敵方整個民族實施打擊,軍人、平民、軍營、軍事經濟目標、交通等都是攻擊目標,因為既然一切都與戰爭有關,那么破壞敵方的任何部分都是合理的。”①轉引自沈偉光《生態戰:軍隊生態化生存與作戰Ⅱ》,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在這種思想理論指導之下,戰爭的發動者和決策者往往不遺余力地調動所有的國家資源和戰爭力量,不斷地推動戰爭“升級”,戰爭的慘烈程度日益加劇,特別是隨著飛機、坦克、大炮等現代化裝備投入到戰場,戰爭演變成了絞肉機,以至于使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人員傷害和物資消耗達到了人類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的程度。
直至20世紀70年代,人類開始進入信息時代,才導致戰爭的進行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控制戰爭、減小戰爭破壞性的思想和理論才開始萌芽。信息戰,不以消滅對方的人員多少為標準,而是以破壞敵人作戰能力為主要目標,其在戰略層面上的表現是要摧毀敵方發動戰爭進行戰爭的意志和信心,在戰役層面上的表現是打擊對方的決策程序、摧毀其指揮系統,在戰術層面上的表現則是使對方圍繞戰爭進程構建的整體力量體系癱瘓。這種戰爭指導思想與中國古人所講的“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斗智為上,斗力為下”②(宋)歐陽修:《準詔言書上書》。的用兵思路是一致的,其核心精神也正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的體現。
孫子的全勝思想及戰爭控制思想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在戰爭無法消除的今天,一旦戰爭爆發,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面對戰爭、打贏戰爭,同時努力控制戰爭的擴散與升級,是現代戰爭指導的必然要求。從理論上講,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破壞性是暴力在戰爭中運用的必然結果。所以,有戰爭就難免有破壞,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不斷制造出威力更大的武器,使得暴力運用的破壞性不斷增強。但是,人是有理性的,武器潛在的破壞性并不必然轉化為現實的戰爭破壞性,這就為我們研究并努力減小戰爭破壞性提供了基本依據。在戰爭指導中,人們可以采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有意識、有計劃地降低戰爭對物質財富和人類生命的直接破壞性,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積蓄的戰爭能量通過一定的渠道和場所釋放出來,最終以較小的破壞性達成理想的戰爭目的。
(責任編輯:李興斌)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of The Art of War
Yao Zhenwen
On the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ofThe Art of Warand drawing references from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the predecessor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new ideas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un Zi’s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including most of Sun Zi’s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is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of the military ceremony culture instead of his personal innovations; Sun Zi’s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is for one’s “victory” instead of “benevolent” care to the opponents; Sun Zi’s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not only is a thinking contents, but also is a kind of thinking method; essentially Sun Zi’s thinking of complete victory is a kind of warring control thinking.
The Art of War; Complete Victory; New Understanding
B22
A
2095-9176(2017)04-0028-08
2016-12-26
姚振文,濱州學院孫子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山東省兵學文化資源產業化開發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編號:11CGLJ06);濱州學院重大招標課題《孫子兵學與儒家思想的沖突與融合研究》(編號:2013zdw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