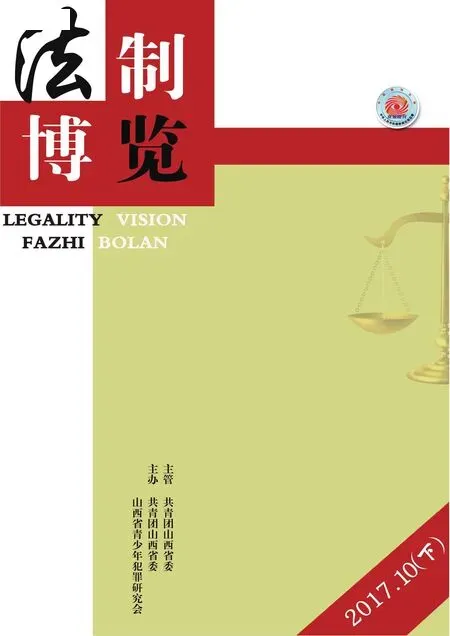淺談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賴成宇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淺談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賴成宇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保證了證據在訴訟中的合法性,起到保障公民個人權利、防止公共權力濫用的作用。雖然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經歷改革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是新的排除規則仍然存在諸多弊端。這表現在控辯雙方的舉證能力相差過于懸殊、非法證據認定標準不一、律師介入權受限等等。為了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國亟待繼續深化制度改革。
非法證據;排除;價值分析;現狀;構想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定義
非法證據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司法機關一方通過違反法定程序所收集到的言詞及實物證據。[1]“非法證據”這一定義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非法證據收集的主體是特定的人員,即負有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職責的公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具體而言包括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和審判人員。第二,違反法定程序,即收集證據的方式、程序、手段不合法。第三,非法證據產生于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分析、固定、收集與案件有關的各類證據材料的活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排除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通過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必須保證用以定罪的證據是客觀、真實、合法的。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不限于在一審的審判中發揮作用,而且在起訴中和各個審級的審理中都可以適用。我國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刑事訴訟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能促進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分析
(一)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7條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入侵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我國通過立憲對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進行保護,但在我國司法實務處理過程中,由于太過側重打擊違法犯罪活動而忽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太過注重辦案效率而忽視過程的合法性,最終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缺失切實有效的保護。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設置體現了人權至上的理念,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說,把其作為一個有權表達自己自由意志的訴訟主體來看待,不強迫其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權利的尊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還強調司法工作人員在合法搜查、扣押證據過程中,必須保障犯罪嫌疑人個人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基本人權。建立非法證據排除法則,可以有效遏制刑訊逼供和非法拘禁的現象。
(二)限制公權力的濫用
法治的一個重要目標在于制約國家公共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權利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設置有利于公民行使監督權,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有罪證據可以要求排除,通過對非法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達到遏止違法取證的動因,從而起到防止公共權力濫用、保障公民個人權利的作用,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的目的和要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執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他們在收集證據時更加注重分析、收集、運用證據的能力,促使他們不斷提高業務素質,更有利于加強司法隊伍自身隊伍建設,推動司法工作的正確進行。
總之,構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公民人權,限制國家公共權力的濫用,維護我國的司法公正與程序公正,加快促進我國的法治建設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施現狀
“證明責任的分配”和“證明標準”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得以真正實施的關鍵。我國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由哪方承擔并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當被告人在法庭上要求排除公訴人提交的非法證據時,法院通常要求被告人說明理由并提交相反證據,即“誰主張誰舉證”,但是基于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弱勢地位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境況,被告人很難提供相反證據,結果往往使公訴人一方提供的證據被作為適格證據來使用。
(一)“誰主張誰舉證”原則不適用于對非法證據證明責任的分配
目前,我國對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由哪方承擔沒有明確規定,而只能適用“誰主張誰舉證”原則。這一原則具體而言是指在訴訟過程中主張存在某一積極事實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否則需要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關于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早見于羅馬法中,是建立在事實的經驗基礎之上,存在的前提是訴訟的雙方都有相同的舉證能力。過去由于民刑不分,擁有審判職能的公權力機關只是作為一個中立的裁判者,不承擔任何證明責任。而在當今的刑事訴訟中,法律賦予了公安機關、檢察院強大的偵查權與監督權,使得有公權力的控方和辯方的力量對比懸殊。而實踐中法院屬于中立的裁判者,不易對辯方都沒有要求排除的證據主動提出排除意見。由此可見,由辯方對非法取證承擔舉證責任顯失公平,在分配證明責任時應考慮到雙方的力量對比。[2]因此,在我國刑事訴訟中適用“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對于辯方提出排除非法證據意見,讓辯方承擔證明存在非法取證行為的證明責任,往往容易造成辯方舉證不能而承擔不利的后果,最終使司法公正難以實現。
(二)立法對證據合法性的認定標準較低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控方提交的證據應該是真實合法有效的。實踐中,由控方證明收集的證據具有合法性可以說是輕而易舉。例如口供,控方只需要提供口供上有犯罪嫌疑人簽字確認,并保證訊問過程有2名以上偵查人員在場并由一名書記員記錄即可。司法實務中,對犯罪嫌疑人訊問通常采用封閉隔離式,訊問時律師不能在場,也沒有同步錄像或錄音,所以就算是在訊問過程中發生刑訊逼供,犯罪嫌疑人迫于壓力也不得不在偵查人員記錄的訊問筆錄下簽字確認,承認犯罪事實。即使犯罪嫌疑人拒絕簽字或者寫下非法取證的事實,偵查人員也有權決定不移交。對于移交到檢察院的證據,檢察院審查后向法院提起公訴,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要求排除非法證據時往往會迫于證據限制,意見很難得到支持。現行的偵查手段使得檢察機關難以認定非法取證行為,法院難以認定證據的合法性,立法對證據合法性的標準較低,使控方的證據收集的合法的證明標準缺乏實踐意義。
四、我國刑事訴訟法非法證據排除原則的完善構想
(一)由控方承擔主要證明責任
鑒于我國并未對非法證據的舉證分配規則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由辯方包括辯方律師提出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請求并提供相關依據。如此弊端是辯方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并未占據優勢地位,律師在偵查階段又被限制了介入權,使關鍵性證據滅失或無法取得。而控方所提出的證據,是由偵查機關移交或者檢察院調查取得,若控方否認證據的合法性,那么其應當在案件提起公訴之前予以排除,作出不起訴或者補充偵查的決定,相反既然控方提起公訴那么就不會反對自己提交的證據。如此一來,辯方很難提交反證推翻控方提交的證據,無疑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形同虛設。筆者認為,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應承擔較多的舉證責任,更能體現公平合理性。在堅持“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前提下,庭審中辯方只需提出合理懷疑的理由,法官認可該懷疑是合理的,此時須由控方對收集的證據承擔證明責任。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要確保舉證責任這個制度真正發揮它保障程序公平以及訴訟主體地位實質平等的作用。
(二)構建非法供述證據的認定標準
針對實踐中證據合法性認定標準較低的實施困境,當前我國的相關立法采用列舉方式,逐步擴大證據合法性認定標準的外延,進一步將非法證據的認定標準詳細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規定:“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應當排除。除緊急情況必須現場訊問以外,在規定的辦案場所外訊問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對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應當排除。”筆者認為,我國雖然通過列舉式擴大非法證據認定標準的外延,但司法實踐往往是復雜多變的,這種方式終究有其滯后及限制性,不能一一完全列舉。[3]因此,還應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統一的認定標準,同時將收集證據的現場同步錄音錄像作為輔助證據列入立法范圍,以此提高證據的有效性,達到一步明確非法證據認定標準的目的。
(三)放寬對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權的限制
我們所知,偵查階段辯護律師地位的確立及權利的完善,意味著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尊重與保障。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與1996刑事訴訟法相比,在偵查階段擴大了辯護律師的知情權及賦予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有不被監聽的權利,這無疑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又一長足進步。筆者認為,在偵查階段進一步擴大律師的介入權,包括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有在場權,如此能確保犯罪嫌疑人不被自證其罪,擁有完全意識和表達能力,也能提高供訴的有效性。同時,賦予辯護律師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享有向公權力機關申請調取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已形成但沒有移交法院的相關訊問證據,如同步錄音資料與視頻資料、體檢報告等相關證據材料。由此,辯護律師在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方面就享有一些特殊的介入權,以此更好幫助犯罪嫌疑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適用這些規則,將可能解決辯護律師閱卷難和調查取證難的問題,有利于遏制司法機關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更好實現司法公正。
[1]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2]劉計劃.中國控辯式審判方式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
[3]史立梅,胡長龍.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兩種立法模式[J].法學論壇,2001(3).
D925.2
A
2095-4379-(2017)30-008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