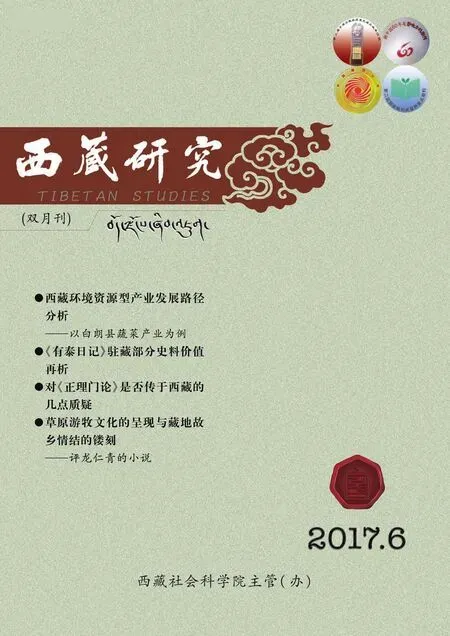國內藏族史學史研究述評
劉鳳強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陜西 咸陽 712082)
史學史是研究古今歷史著作,探索史學思想的源流與派別以及史學本身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藏族史學有悠久的歷史,從吐蕃以來一千多年中創造出無數優秀史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藏族史學體系。對藏族史學的研究早在20世紀上半葉已有零星的文章,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對藏族史學史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通過學術史回顧,總結這些研究成果,找到研究的薄弱與不足之處,有助于該學科進一步成長與發展。
一、通論性研究成果
最早系統全面論述藏族史學的當屬王堯的《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文章主要簡述歷史文獻的內容,其中對史籍體裁的劃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后來研究有較大影響。王堯、沈衛榮的《試論藏族的史學和藏文史籍》(《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對藏族史書體裁、結構及發展特點等作了精彩論述,對人們研究藏族史學史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不過,由于篇幅局限,兩篇文章內容都較為簡略。恰白·次旦平措(唐祥翔譯)的《略論古代藏文史料》(《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對古代藏文史籍作了全面辨證分析,認為既要重視古代史籍的史料價值,同時也不能盲目信從,對我們了解古代藏族史書特點以及利用藏文史籍有重要指導意義。王繼光、才讓連續撰寫《藏文史籍四種敘錄——青史、薩迦世系譜、娘地教法源流、拉卜楞寺志》(《西藏研究》1988年第3期)、《藏文史籍敘錄之二》(《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藏文史籍敘錄之三》(《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藏文史籍敘錄之四》(《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以及巴桑旺堆的《藏族十大歷史名著概述》(《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對一些藏文著名史籍的體例與內容作了簡要論述,不過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個案論述,缺少總體理論的闡發。馮智的《藏史學的傳統研究與時代特征》(《西藏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簡要論述了藏族史學的發展階段以及體裁分類,分析了藏族傳統學術文化與史學的關系,梁成秀的《試論藏族重要史學著作的編撰思想及特點》(《北京印刷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從編輯學角度論述了幾種藏族重要體裁形式的史籍,以上兩篇文章均涉及廣泛,但過于簡略。劉鳳強的《西藏通史編纂述論》(《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對古今西藏通史的編纂情況及特點作了梳理和總結,但相對于這樣一個大問題來說,文章顯得過于簡單。孫林的《從我國現當代藏族史學研究看少數民族史學史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簡要論述了藏族史學研究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研究的薄弱之處。
在藏族史學史研究中,孫林的《藏族史學發展史綱要》(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著作,該書共分五部分,按時間順序系統論述了藏族史學發展歷程,對藏族史學觀念、史學特點、史籍體裁、寫作體系等作了創見性分析,書中既有宏觀分析,探討藏族史學發展的一般性規律,也有微觀研究,對一些著名史籍作了深入細致的探討,是一部宏觀考察與微觀研究結合的著作。該書對藏族史學史每一個階段的特征都有詳細的述論,構建出藏族史學史的基本框架,奠定了藏族史學史學科的基礎,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將藏族史學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不過,該書主要側重于古代藏族史學研究,對于近代以來的藏族史學論述過于簡略。王璞的《藏族史學思想論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也是一部研究藏族史學史的重要著作,該書按時間順序分別論述不同時期藏族史學名著,對史籍的體裁、內容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但書中以個案研究為主,缺乏對藏族史學體系的總體論述,沒有對藏族史學理論作深入挖掘。葉拉太的《藏族古代史論及其史學文獻遺產研究》(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5年)共六章,較為全面地論述了藏族古代史學文獻的收藏狀況、體裁、歷史價值、特征等,對藏族史學發展歷程作了系統論述,探討了古代藏族史觀、史學體系、史學遺產研究方法等,并對藏族古代53部史學名著作了詳細論述,是藏族史學史研究的新成果,不過,書中對史學與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相對薄弱。其他一些不是研究史學史的專著,因研究內容涉及到史書體裁與內容,對史學史研究也有助益,如馬學良、恰白·次旦平措主編《藏族文學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對部分史籍的體例與內容作了詳細介紹,王堯等人的《中國藏學史(1949年以前)》(民族出版社和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對藏學歷史文獻(含藏文、漢文)的主要內容及特點作了簡略敘述,王啟龍、陰海燕的《中國藏學史(1950—200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藏學文獻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對新時期史籍作了簡明扼要的論述。
藏文史籍在命名上往往有很多修飾語,非常有特色,近幾十年來,對藏文史籍命名的研究出現了幾篇論文,這是藏族史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具有特色之處。萬果、德吉草的《試談藏文典籍命名中的色彩及修飾》(《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通過書名修飾的歸類,分析了書名背后的作者文化心態,以及藏民族重視傳統、追求真與美的審美情趣。綺羅、尕本加的《試探藏文史籍色彩命名中的意義》(《青藏高原論壇》2014年第1期)從佛教和史學兩個方面討論了史籍以色彩命名的涵義。尕本加的《試論藏文史學典籍之命名觀及其意文》(《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分析了藏文史籍中以作者、內容、修飾、色彩不同命名方式及特點,這些文章對我們理解藏文史籍命名非常有幫助。實際上,由于藏文史籍種類繁多,在命名上還有很多可以進一步考察的地方,很多史籍包含了作者對所撰寫書籍的期望,如以“明鏡”命名,反映了作者對書籍真實性以及社會功能的期望,這些問題有待學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從通論性論著來看,藏族史學史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績,對藏族史學觀念、史學發展階段及特點都作了初步探討,對史書的體裁類型、內容、史籍命名等作了相對深入研究。但相對漢族史學史來講,爭鳴不夠,討論較少,很多內容還是初步論述,總體研究還處于起始階段。
二、古代史學的斷代研究及史書個案研究
近幾十年來,隨著大量古代藏文史籍的整理研究,學術界對古代藏族史學的斷代研究以及藏文史籍個案研究有較為豐富的成果。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碑刻等是研究吐蕃史必備的珍貴資料,因此,研究成果相對較多。臺灣學者林冠群的《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書中有一部分專門對唐代吐蕃史學作了述評。林冠群的《從〈吐蕃大事紀年〉論唐代吐蕃的史學》(《中國藏學》2013年第1期)通過對敦煌文書《大事紀年》與漢文史料對比分析,認為這是一部帝王本紀,具有為統治者服務的國史性質,對我們重新認識敦煌吐蕃歷史文書性質,提供了新的視角。劉鳳強的《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的“春秋筆法”》(《中國藏學》2014年第1期),通過詞匯運用及史料選擇等分析了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具有模仿“春秋筆法”的寫作特點。其他介紹吐蕃文獻史料價值的論文較多,如王堯的《吐蕃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書“歷史文獻”部分;張月芬的《試論敦煌吐蕃歷史文獻的文獻學與歷史學價值》(《西藏研究》2000年第2期);尕藏加的《敦煌吐蕃藏文文獻在藏學研究中的史料價值初探》(《中國藏學》2002年第4期);林冠群的《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載《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趙天英、楊富學的《敦煌文獻與唐代吐蕃史的構建》(《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
對分裂時期及元明清時期藏族斷代史學史的研究成果較少,劉鳳強的《清代藏學歷史文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對清代漢藏兩種類型史籍,分別作了系統論述,探討了清代藏文典籍傳記、教法史、方志等的編纂理論與方法,梳理了清代漢文藏族史書編纂發展脈絡并分析了其特點,但書中內容局限于清代,缺乏宏觀視野及總體理論闡發。劉鳳強的《元明清時期藏族史書編纂與多民族共同體認識的形成》(《貴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1期),從三個方面論述元明清時期藏族史書編纂對中華民族形成的影響,是從史學與社會關系角度研究的成果。
對分裂時期及元明清時期藏族史書個案的研究較多,學者多針對某一名著或作介紹,或作述評,或作深入考證,推動著藏族史學史研究。近幾十年來學術界整理出版的古代藏文史籍,在前言或出版說明中一般都有對作者、成書年代的考證,對該書史料價值的介紹,這些內容有助于我們對史籍的了解,是藏族史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此我們不再一一提出,現在就史籍個案研究的論文作以簡要介紹。《柱間史》是藏族著名伏藏歷史文獻,對后來藏族史書寫產生了重大影響,群培、亞東·達瓦次仁的《藏族史學名著〈柱間史〉的初次發現與抄本傳承考證》(《西藏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對《柱間史》發現與流傳作了梳理;張云的《藏文史書〈柱間史〉有關西藏社會史的若干記載及辨正》(《中國藏學》2013年第S1期)從史學價值及史料考辨角度對《柱間史》作了詳細論述。對其他史籍的研究有,夏吾卡先的《一部吐蕃王陵的史冊——〈桑瓦央瓊〉的研究與翻譯》(《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分析了《桑瓦央瓊》與吐蕃其他史籍的關系,并探討了其歷史觀念等問題;東珠嘉措、才讓扎西的《藏文史籍敘錄一:吐蕃歷史文書、〈弟吳宗教源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對吐蕃歷史文書、《弟吳宗教源流》內容作了介紹;阿貴的《藏文史籍〈弟吳宗教源流〉史料價值探析》(《西藏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分析了《弟吳宗教源流》在研究藏族史方面的史料價值;常文濤的《藏族史籍〈弟吳宗教源流〉研究》(西藏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對《弟吳宗教源流》的編纂特點、史學價值等問題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萬瑪才讓的《藏文史籍〈娘氏教法源流〉之結構內容與史料價值探析》(《西藏研究》2016年第4期)對《娘氏教法源流》的內容與史料價值作了簡要論述;次旦扎西、頓拉的《芻論元代藏族史學名著〈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西藏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從境域觀、撰寫動機、史料來源、書寫方法等方面介紹了《奈巴教法史》的史學價值。張云的《藏文史書〈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學術價值》(《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既分析了《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價值及史料來源,又指出其不足之處,并據此分析了元明之際藏族史學發展的原因;伶錦華的《論〈巴協〉》(《藏學研究文選》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分析了《巴協》的主要版本情況,對該書的文學成就及史料價值作了詳細論述;劉鳳強的《從〈拔協〉看分裂時期藏族史學裂變》(《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對《拔協》與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的用詞作了對比研究,進而討論了分裂時期藏族史學發展特點;周清澎的《藏文古史——〈紅冊〉》(《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4期)、周潤年的《藏族古籍〈紅史〉》(《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兩文均介紹了《紅史》的史料價值;俄智多杰的《淺析蔡巴貢嘎多吉的名著〈紅史〉》(《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提出《紅史》為一部綜合體史書,較有新意;頓拉的《試析〈新紅史〉在藏族史學著作中的地位》(《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簡單敘述了《新紅史》的纂修特點及價值;崗措的《〈西藏王統記〉——一部富于濃厚文學情趣的歷史著作》(《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主要從文學角度分析了《西藏王統記》的編纂特點及價值;周潤年的《一部珍貴的藏文史籍——〈薩迦世系史〉》(《藏學研究》第6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分析了《薩迦世系史》的史學價值;楊公衛的《歷史神話與真實:藏族古典文獻的事實構建與想象表述——〈朗氏家族史〉的文獻創作、社會詩學與宗教哲學觀念》(《民族學刊》2017年第1期)通過分析《朗氏家族史》,對藏族史書中歷史真實與相像表述之間的關系作了探討,是一篇視角新穎的論文;《漢藏史集》是一部非常珍貴的藏文史籍,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長期未能重視,80年代王堯先生從國外帶回影印本,很快引起學界重視,沈衛榮的《一部珍貴的藏文史籍——〈漢藏史集〉》(《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陳慶英、沈衛榮的《簡論〈漢藏史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二文都對《漢藏史集》的史料價值作了詳細論述。陳慶英的《關于〈漢藏史集〉的作者》(《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對該書作者作了深入考證;張云的《藏文史書〈漢藏史集〉的文獻學特點及其史學價值》(《青海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在論述該書史料價值基礎上,還進一步分析了其編纂特點以及史學觀念。介紹《賢者喜宴》史料價值的論文有,才讓的《藏文歷史名著〈賢者喜宴〉史料價值探析》(《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1期);周潤年、黃顥的《〈賢者喜宴——吐蕃史〉的內容及其史料價值》(《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張屹、周潤年《藏文史籍〈賢者喜宴·噶瑪崗倉史〉的內容及其史學價值》(《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等。《青史》作為藏族史學名著,備受學者關注,王繼光的《〈青史〉成書年代考辨》(《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3期)對《青史》成書時間作了簡單考證;汪受寬、鄧根飛的《論〈青史〉的綜合體體例及其特點》(《西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5期)提出《青史》編纂是一種綜合體例,并分析了這種體例的特點;鄧根飛的《藏族史學名著〈青史〉研究》(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較為詳細地論述了《青史》的體例、內容、佛教史觀等;尕本加的《試探藏文史學名著〈青史〉之現代性意義》(《青藏高原論壇》2016年第2期)對《青史》的史料價值及史學思想作了簡單分析;還克加的《文獻學視野下的藏族史籍〈青史〉研究》(《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對《青史》版本、史料來源等作了簡單論述;張子凌的《論藏文史籍〈如意寶樹史〉的文獻價值》(《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不僅分析了《如意寶樹史》的版本、體裁及史料價值,還將之與《圣武記》內容作了對比,并進一步論述了藏族史學對蒙古史學的影響;趙梅春的《〈先祖言教〉的史學價值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從《先祖言教》史料價值分析了作者擺脫宗教史觀束縛,客觀求實的撰寫態度;米瑪次仁的《藏文歷史文獻〈協噶教法史〉史料價值探析》(《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從編撰緣起、成書年代、內容結構、敘事風格以及史料價值等方面對《協噶教法史》作了全面論述。
對古代藏文史籍人物傳記研究的論文也有不少成果,伶錦華的《十八世紀西藏政治風云錄——論〈頗羅鼐傳〉的主要思想內容》(《藏學研究文集》第3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對該書時代背景、作者以及史料價值作了論述;劉立千的《〈米熱日巴傳〉述評》(《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介紹了《米拉日巴傳》的內容,并分析了該書所載內容的宗教特點;何峰的《〈米拉日巴傳〉成功的緣由》(《青海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認為傳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但從本質上看該書仍具有為宗教服務的本質特點;張童童的《從敘事學角度解讀〈米拉日巴傳〉的文本和宗教思想》(《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從敘事學角度分析傳記的敘事結構、方法、特點等,其視角較一般史學史論文有別;伶錦華的《〈瑪爾巴傳〉評介》(《藏學研究文集》第4集,1986年內部出版)對該書的作者、生活時代、主要內容及人物形象作了簡要論述;洛珠加措的《一部不容忽視的古籍作品:〈蓮花生大師傳〉》(《民族文學研究》1992年第3期)簡略論述了《蓮花生大師傳》寫作特點及影響;還克加的《芻議蓮花生大師的傳記類型》(《青藏高原論壇》2016年第2期),對兩種類型傳記中關于蓮花生大師誕生的記載作了簡單對比;郭衛平的《〈倉央嘉措秘傳〉的真實性及其它》(《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通過漢藏史料對比,對書中內容真實性提出懷疑;賈拉森的《關于所謂〈倉央嘉措秘傳〉》(《內蒙古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根據不同版本對比,認為該書稱為秘傳是以訛傳訛的結果,結論較為新穎;謝后芳、周季文的《〈多仁班智達傳〉的若干特色》(《藏學研究文選》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論述了該書的作者生平、史學價值、文學價值及民俗學價值等;角巴太《〈多仁班智達傳〉研究》(青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從文學價值、史學價值兩個方面探討了《多仁班智達傳》的編纂成就。
《西藏王臣記》是五世達賴喇嘛撰寫的著名史書,除了一些專著中對這部史書有論述外,還出現了專門研究文章,阮銘樹的《五世達賴及其〈西藏王臣記〉》(《西藏研究》l987年第1期)對《西藏王臣記》史料問題、歷史與神話關系、歷史與文學關系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索代的《論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的歷史文化觀——評〈西藏王臣記〉》(《西藏藝術研究》1988年第3期)通過分析《西藏王臣記》的寫作特點討論了五世達賴的歷史觀;翟淑平的《歷史、神話與詩的三重奏——讀〈西藏王臣記〉》(《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結合書中內容分析了《西藏王臣記》中歷史、神話、文學三者交融關系。
方志是史書重要體裁之一,研究藏族方志的論文也較為豐富,吳均的《〈青海歷史〉評介》(《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全面分析了松巴堪布所著《青海歷史》的優點與不足;蔡志純的《松巴堪布益西班覺與〈青海史〉評價》(《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對《青海史》內容作了簡單述評;德格吉的《淺議〈青海歷史梵曲新音〉編排特點與內容》(《西藏藝術研究》2016年第2期)從編纂學角度高度評價了《青海歷史》的特色;德格吉的《〈青海歷史梵曲新音〉之成書背景》(《青藏高原論壇》2016年第4期)從松巴堪布與和碩特部后裔關系探討了松巴堪布之所以撰寫這部史書的原因;拉先加的《〈安多政教史〉的文獻學研究》(《中國藏學》2013年第4期)詳細論述了《安多政教史》的作者、史料來源、內容結構等;仁青的《〈安多政教史〉若干問題研究》(西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對《安多政教史》的體裁、史料、文獻價值以及漢譯等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劉鳳強的《論清代藏族的方志》(《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3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從方志命名、體裁、史料價值等方面論述了清代藏族方志編纂的特點及成就;彭祥琦的《〈后藏志〉體例研究》(《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探討了《后藏志》結構、筆法、詳略等問題。
對其他史籍的研究,丹曲的《藏族歷史上的〈佛歷表〉(bstan-rtsis)——兼談第一世嘉木樣〈佛歷表〉的內容與價值》(《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分析了一世嘉木樣所作年表的史學價值;阿貴的《新發現藏文史籍〈王統日月寶串〉評述》(《西藏研究》2016年第1期)介紹了新發現史籍的學術價值。
近幾十年來,對不同史籍進行比較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索洛的《〈米拉日巴傳〉與〈夏嘎巴傳〉之比較研究》(《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4期);陳立明的《〈米拉日巴傳〉與〈頗羅鼐傳〉對比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張未娜的《〈紅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較研究》(《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徐長菊的《〈青海史〉與〈安多政教史〉中的和碩特蒙古歷史記述之比較》(《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金烏達巴拉的《〈布頓佛教史〉與〈水晶鑒〉比較研究》(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等,這些論文多將兩部史書的作者、成書背景、主要內容、編纂思想、語言風格等加以比較,從不同史書異同看藏族史學發展,推動了藏族史學史的研究,尤其是金烏達巴拉的碩士論文,將蒙藏兩種歷史文獻作了對比研究,在選題上很有意義。
從上述研究成果來看,個案研究相對較多,對一些重要史籍的史料價值做了深入論述,但個案研究模式類同,缺乏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對藏族某一歷史階段的斷代史學研究很少,這也是藏族史學史研究還不夠深入的表現。
三、20世紀藏族史學史研究
20世紀出現了很多優秀的史著,但對20世紀藏族史學史研究相對較少,而且研究主要集中在個別重要史學家或史著方面。
根敦群培是民國時期出現的具有進步思想的藏族僧人,所著《白史》影響很大,對根敦群培的史學及《白史》研究成果相對較為豐富,杜永彬的《二十世紀西藏奇僧——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書中詳細論述了根敦群培的生平經歷、學術思想等,對我們了解根敦群培的史學思想非常有益;扎洛的《略論〈白史〉的史料價值》(《中國藏學》2004年第1期)總結了根敦群培撰寫《白史》所利用四個方面的重要史料;阿旺·澤仁扎西的《根敦群培》(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有一部分專門討論了根敦群培的史學觀念;端知加的《論更敦群培的歷史觀以及研究方法》(藏文,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根敦群培的歷史觀來源及其研究方法,論證了根敦群培對藏族史學界的重大影響;賈仁前吉的《史學名著〈白史〉簡述》(《藏學研究》第10輯,民族出版社2011年)簡要介紹了《白史》的史學成就。2011年西藏社科院召開的“根敦群培與恰白·次旦平措學術思想研討會”收到關于根敦群培史學思想的論文有,張云的《根敦群培與恰白·次旦平措的吐蕃史研究——新史觀、新方法、新資料、新發現》(又載《中國藏學》,2012年第S2期)對根敦群培與恰白·次旦平措治史所采用的史觀、方法、資料來源與發現四個方面進行了對比闡述;次旦扎西的《根敦群培史著〈白史〉評析》;才加的《根敦群培史著之〈白史〉評析》都簡要論述了《白史》的內容及學術價值;達瓊的《淺議根敦群培史著〈白史〉對西藏歷史研究的啟示》分析了《白史》對西藏史研究的啟發意義。亞東達瓦次仁的《新思維史學觀的倡導者:根敦群培與東噶·洛桑赤列——訪當代著名藏族學者仲布·次仁多杰》(《西藏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以訪談的形式談論了根敦群培與東嘎·洛桑赤列二人新的史學觀念。
對民國時期漢文藏族史著的評論文章有,楊仲華的《關于西康著述之檢討》(《新亞細亞》1卷1期,1930年10月)與《幾種捕風捉影的西康著作》(《蒙藏周報》第63期,1931年3月19日),兩篇文章全面評價了當時流行的幾部西康著作,批評了各書存在的問題;文萱的《評(梅心如著)〈西康〉一書》(《康藏前鋒》第2卷1期,1934年9月),批評了梅心如著《西康》記述失實不當之處,認為很多內容都是杜撰的;玄默的《〈現代西藏〉評介》(《蒙藏月報》第13卷10期,1941年10月)簡述了法尊法師《現代西藏》的內容,并對該書學術價值給予很高的評價;周霞的《妙舟〈蒙藏佛教史〉評介》(《西藏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論述了《蒙藏佛教史》的三個特點,并簡略分析了其不足之處;何燕航的《〈康藏史地大綱〉論評》(《康導月刊》第5卷第5期,1943年10月)對任乃強的《康藏史地大綱》中很多內容提出批評,并指出該書編纂的缺陷,任乃強則撰文《〈康藏史地大綱論評〉的批評》(《康導月刊》第5卷第5期,1943年10月)針對何燕航的指責逐條展開辯論,進一步闡明了《康藏史地大綱》編寫的依據和特點;王開隊的《任乃強的西南歷史地理研究》(《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3期)闡述了任乃強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成就,并總結了其治學特點,其他從治學成就等方面談論任乃強著作的還有王雨巧的《任乃強1894—1989學術及其治學特點之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徐振燕的《任乃強的西南圖景》(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楊鴻儒的《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強教授》(《西藏研究》2010年第10期)等,這些論文大都論述了《西康圖經》《康藏史地大綱》編纂思想及方法問題;鄧銳齡的《介紹李安宅著〈拉卜楞寺〉》(《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簡要介紹了李安宅著作的內容及特點;李紹明的《評李安宅遺著〈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中國藏學》1990年第1期)高度評價了李安宅著作的特點及學術成就和影響;郭廣輝的《“實地研究”與“歷史”的協奏——對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的再認識》(《民族學刊》2015年第2期)以較長的篇幅論述了李安宅實地研究過程中對人類學的超越,很好地實現了實地研究與歷史的結合。
對1949年以后藏族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綜述、書評和訪談上。張云的《1949年以來的西藏古代史研究》(《中國藏學年鑒》2009年創刊號,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對1949年以后很多史書作了恰當的簡評。其他個案研究有,肖干田的《西藏歷史的真實寫照(上下)——關于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書的評述》(《西藏大學學報》1999年第1、4期)全面論述了《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內容,對書中觀點作了實事求是的評論;仲布·次仁多吉的《試評東嘎·洛桑赤列教授〈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路徑》(《西藏研究》2014年第1期)認為東嘎·洛桑赤列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思潮相結合,充分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藏族歷史,取得了突出成就;洲塔的《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述評》(《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認為《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引用大量珍貴藏文文獻,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論的觀點詳細論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是藏族史研究方面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著作;王堯的《書卷縱橫崇明德、山河帶礪燦晚霞——評王森先生〈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藏學》1991年第2期)對《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巴桑羅布的《往事知多少 汗青映千秋——評介〈西藏簡明通史〉》(《中國藏學》1993年第2期)介紹了《西藏簡明通史》的主要內容,分析了該書編纂的四個特點;亞東·達瓦次仁的《西藏歷史巨著〈西藏簡明通史·松石寶串〉——訪著名藏族學者恰白·次旦平措》(《西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通過訪談的方式,介紹了《西藏通史》編纂緣起、特點,以及藏族史進一步研究的方法等;霍巍的《二重證據與西藏古史重構——論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對西藏新史學的影響》(《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認為《西藏通史》將西藏地下考古材料與文獻材料相互結合起來重構西藏古史,從而開拓出西藏史學理論與實踐的新理路;德吉草的《還史以真,寓情于文——解讀恰白·次旦平措學術思想中的文史雙重追求》(《西藏研究》2008年第6期)分析了《西藏通史》文史結合的雙重學術追求;王春煥的《一部厚重的中國地方通史——談恰白·次旦平措主持編著〈西藏簡明通史·松石寶串〉的治史精神》(《西藏研究》2011年第4期)認為《西藏通史》以西藏地方政權演變為基本線索,不僅闡明了西藏歷史發展過程,還揭示了西藏地方走向祖國完整的過程和規律,體現了恰白先生獨到的治史方法和高尚精神;徐志民的《著名藏學家恰白·次旦平措史學思想述論》(《西藏研究》2011年第5期),從指導思想、研究方法、治學精神等方面論述了恰白·次旦平措的史學思想;趙君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史學思想探析》(《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7期)從史學思想淵源、內容、影響等方面論述了恰白·次旦平措的史學成就;胡巖的《讀李鐵錚〈西藏歷史上的法律地位〉》(《中國藏學》1990年第2期)介紹了李鐵錚著作的內容,同時對其學術價值及不足之處也作了詳細論述;吳豐培的《班禪額爾德尼傳述評》(《中國藏學》1989年第2期)對書中內容作精要概述。邱立的《祖國統一的歷史鐵證——讀〈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中國藏學》1998年第3期)、常遠歧的《展示活佛歷史的畫卷——〈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評介》(《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兩文都簡要評價了該書的編纂特點及意義;邱其生的《一部頗有特色的民族關系史新著——〈蒙藏民族關系史略〉》(《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分析了該書編纂特點以及學術成就;李佩娟的《填補研究空白的一部佳作——〈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1期)、周偉洲的《西方與西藏地方關系史的研究碩果——〈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兩文均高度評價了《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一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周偉洲的《新視野、新思路、新觀點——評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中國藏學》1994年第4期)、李宗放的《藏學研究的新成果——讀〈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楊凌的《西藏與中原文明關系史研究的拓新之作——〈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評介》三文對石碩著作的編纂特點、學術價值作了論述;陰法唐的《一部還西藏歷史以本來面目的好書——評學術專著〈西藏歷史地位辨〉》(《中國藏學》1996年第1期)、姜思毅的《一部愛國主義的杰作——介紹〈西藏歷史地位辨〉》(《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第1期)都從反分裂斗爭角度評論了該書編纂特點及成就;松芳、綺羅的《關于藏族歷史研究的探討——訪藏族著名學者土登彭措教授》(《西藏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以訪談的形式討論了藏族史研究問題,其中涉及到《藏史綱要》的編纂問題。1949年至2000年間,藏族史書編纂取得了很高成就,各種類型的史書數量眾多,很多書籍都有書評,其寫作風格和模式大體相仿,基本上都是講史料翔實、結構合理、觀點新穎、意義重大等,對我們研究史學史有一定參考價值,但限于篇幅我們不能一一列舉。
1949年以后,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藏族史學史研究也走過彎路,有些認識并不合理,如柳陞祺的《評李有義著的〈今日的西藏〉》(《民族研究》1959年第3期)、汪欽的《評李有義先生研究西藏的論著中有關歷史部分》(《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兩文均對李有義《今日的西藏》展開批評,但批評方式與內容并不恰當,兩文作者均簡單機械地以唯物史觀作為衡量論著優劣的標準,以戴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批評,已不是純粹學術之爭。
四、對藏族史學史研究的思考
上面我們簡略回顧了藏族史學史研究概況,可以看出國內藏族史學史研究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史籍有較多的論述,闡明了這些書籍的史料價值,同時也涉及到一些史籍編纂特點、文學特色等,個別論著在藏族史學史的基本構架、史學觀念、史學理論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也要看到我們的研究還存在不少問題和薄弱之處。
(一)對藏文史籍挖掘還不夠
古代藏文史籍數量非常龐大,僅《安多政教史》卷首列舉的參考文獻就有432部之多[1],其中大部分都是史書類,目前學術界雖然有很多個案研究,但大都集中于幾部影響較大的史書,對其他史書缺少關注,深入研究就更談不上了,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藏族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很多學者作藏族文獻研究,古藏文的功底還不夠,有些熟悉藏文的學者卻不能流暢地看古藏文典籍,對古籍中所載歷史、地理、人名等非常陌生,影響了對文獻的挖掘,還有一些學者甚至完全依賴翻譯成漢文的版本作為研究藏文史書的依據,其研究質量可想而知。因此,加強藏族史學界古藏文閱讀能力,是提高藏族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個案研究多,總體論述少,缺乏理論闡述
我們上面所列舉的研究論著中,除了個別論述一些整體論述和理論構建外,多數都是個案研究,而且形成了一種慣性寫作模式,即圍繞著某一史書的作者生平、史料價值、史學意義撰寫文章。如果是新史料的發現,我們撰寫這樣的文章,可能有較大價值,如果是大多數人都可以閱讀的史書,我們再去做這樣的研究,而不是用新觀點、新方法去研究,肯定難出新意,甚至有不少人在做重復勞動。總體來看,國內對藏族史學史研究多是針對某一史書論述,這是史學史研究基礎,但我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這一階段,還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去概括總結探討,如對階段性史學成就及特點的研究還較少,對傳統藏文史書的體裁討論還不多,對傳統藏族史書編纂意義、編纂方法、撰寫史書應具備的素養、史書功用、求真與實證關系、史料的運用等問題很少有人深入系統的總結,對傳統藏族史學觀念的歷史變化缺乏研究,凡此等等都表明,藏族史學史的研究還有很多薄弱和空白之處,與漢族史學史相比,研究成果還較少,需要我們進一步投入時間和精力加強研究。
(三)對史書編纂與社會關系的互動關系研究不足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二者存在緊密聯系,史書編纂是時代的產物,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注意到了這一點,有不少論述,但另一方面史書形成后,對社會影響也是巨大的,依筆者淺見,有如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
1.古代藏文史書編纂的形式、內容與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互動關系。
2.古代藏文史書編纂與佛苯之爭之間的互動關系。
3.古代藏文史書編纂與藏傳佛教教派爭論之間的互動關系。
4.古代藏文史書編纂與藏民族的形成的互動關系。
5.古代藏文史書編纂與多民族共同體格局形成的互動關系。
諸如以上問題,我們的研究還很欠缺,需要更多的學者認真深入探討。
(四)對近現代藏族史學史研究還非常薄弱。民國時期藏族史學處于轉型階段,從藏族學者所編寫藏文史書來看,以根敦群培《白史》為代表的史著,開啟了新的歷史編纂模式,但我們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根敦群培一人身上,對其他學者的史書編纂缺乏關注。從漢文史書來看,對任乃強、李安宅等人有個案研究,但階段性史學成就的論述缺乏,更沒有理論性的總結,對進化論、民族、國家等新觀念與史學史發展關系都缺少闡述。1949年以后,藏族史學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系統研究這一時期成就的學者卻極少,唯物史觀與藏族史學史發展關系,這么重要的問題卻沒有人深入研究,目前所能見到的基本上是個案研究,而且多是以書評的形式出現,這些書評大都能反映所評之書的內容、特點和價值,對我們了解史書編纂有一定幫助,但也不可否認,很多書評都是同一面孔,只在末尾無關痛癢地說幾句不足之處,幾乎見不到諍友式的評論,更缺乏在某一領域內深入的見解,這種狀況顯然不利于學術發展,也不會促進藏族史學研究的進步。
[1]拉先加.《安多政教史》的文獻學研究[J].中國藏學,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