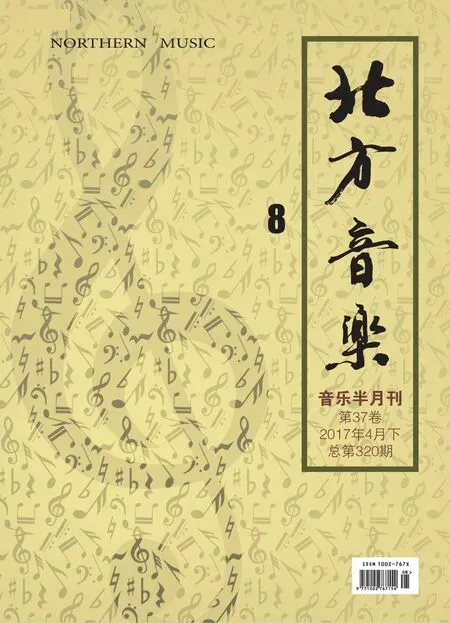淺談陜北民歌在中國民族聲樂發展中的地位
范志博
(山西大同大學音樂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淺談陜北民歌在中國民族聲樂發展中的地位
范志博
(山西大同大學音樂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陜北民歌作為高原文化的靈魂和高原人精神的結晶,是中國民族聲樂乃至民族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以陜北民歌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舉例等多種手法力求全面地論述陜北民歌在中國民族聲樂發展中的地位,充分展現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
民族聲樂;陜北民歌;發展;地位
陜北民歌是陜北人民生活最真實的反映,是一部鐫刻在西北黃土高原上的傳世巨著。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陜北民歌,大部分產生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現今流行的兩萬余首陜北民歌當中,有敘事的、言情的、說理的體裁等,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陜北的社會歷史發展及其變遷。這一首首精美的民歌,把陜北民歌帶出了山溝溝,并插上了音樂的翅膀飛向世界。陜北民歌種類很多,大致分為勞動號子、信天游、小調三大類。
一、陜北民歌的藝術特點及其分類
(一)勞動號子的產生及其藝術特點
勞動號子是伴隨勞動而產生的歌曲,它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早、最古老的藝術作品之一。勞動號子的曲調一般比較短小,節奏固定,鏗鏘有力,演唱形式多為一領眾和,也有齊唱、獨唱形式,例如《軍民大生產》。勞動號子題材極為廣泛,有打夯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場歌等。黃土高原是貧瘠的,陜北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陜北人民世世代代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辛勤的耕耘著、繁衍著,傳承著人類文明。
(二)信天游的流傳及其藝術特點
信天游又叫“順天游”、“爬山調”,是陜北地區最具有特色的民歌形式之一,屬于民歌中的山歌體,是農村流傳和發展的一種民歌體裁,以綏德、米脂一帶最具有代表性。傳統的信天游多是表現情感和對封建禮教束縛的反抗情緒,也有外出走西口的人們對家鄉及親人的思念之情,還有反映勞動人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
信天游的節奏非常自由,音域寬廣,旋律奔放,起伏大,用高腔、平腔演唱;信天游的曲調多為單樂段,由于是戶外的山野之歌,因此粗獷奔放、悠揚高亢,充分體現了陜北人的豪放性格,例如:歌手杭天琪演唱的《我熱戀的故鄉》,這首歌節奏自由明快,旋律奔放。“我的故鄉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一條時常干涸的小河,依戀在小村的周圍……”歌詞兩句前后呼應,描寫了黃土高坡的地理特點以及作者對家鄉的熱愛。
(三)小調的分類及其特點
小調是指流行在群眾生活休息、集慶等場合中的各種民間歌曲,被人們定義為“山野之歌”,多數小調是由城鎮傳往農村的。根據小調的演唱方式、思想內容和用途,分為通行小調、風俗歌曲、社火小調、絲弦小調、大型套曲五大類。小調的內容題材極為廣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有詠唱歷史故事傳說、描寫自然風光、表現男女愛情等等。它的曲調流暢,感情婉轉細膩,旋律常以起、承、轉、合的句式為明顯特征,結構勻稱規整;歌詞多為分節歌形式,一般詞曲較固定,不具有即興編唱的特點;演唱形式以獨唱為主,還有對唱、齊唱、一領眾合。
陜北民歌是陜北文化乃至黃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的雄奇、土的掉渣、美的撩人。無論你站在陜北的哪個角落,都能感受到陜北人的喜、怒、哀、樂。這種黃土高原上既通俗又明亮的特色,足以影響著中國的民族文化,影響著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的發展!
二、陜北民歌在中國民族聲樂發展中的地位
我國各民族的民歌是極其豐富多彩的,是民族音樂的瑰寶,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中國的民族聲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廣大的漢族地區流傳的民歌中,陜北民歌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它賦予了民歌充足的養分,使之健康的成長。
(一)從歌詞上看陜北民歌
陜北民歌的歌詞內容緊跟時代步伐,雖然陜北民歌的許多曲調相同,可以說得上是老調子了,但其歌詞內容與時俱進,常唱常新。以我們熟悉的《騎白馬》為例,最初是一首情歌“騎白馬,跑沙灘,我沒婆姨你沒漢。”抗戰時期,改為抗日愛國歌詞“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糧。”陜甘寧邊區時期,毛澤東主席領導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使人民群眾生活大為改善,又改為歌頌黨和領袖的《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從《東方紅》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陜北民歌的發展軌跡。因此,陜北民歌歌詞的時代性對民族聲樂歌詞創作具有很大的影響,推動了新時期民族聲樂藝術的發展。
(二)陜北民歌曲調的可塑性
陜北民歌曲調的抒情性很強,因為創作者是最普通的勞動者,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和最廣大的群眾氣息相通,生死與共。他們當過腳夫,趕過牲靈;走過西口,下過三邊;蘭花花或者類似蘭花花的故事就發生在他們身邊;三十里鋪、四十里鋪就是他們的家鄉;他們所唱的每—首歌都是真情實感的傾瀉和流露。他們的歌聲反映著舊時代人民的悲歡離合,也反映著新時代人民的激情和歡悅。例如《蘭花花》,它的歌詞有著強烈的敘事性特點,但它的曲調卻有著強烈的抒情性,多少年來一直被人們傳唱著,更是專業院校民族聲樂學生必唱的曲目。近年來,作曲家王志信在《蘭花花》原來的民歌主題基礎上進行編創,在作品頭和尾上保留了原主題音調,成為一首在藝術上、內容上另辟蹊徑,面貌為之一新的《蘭花花》。
(三)陜北民歌音樂形象的可塑性
優秀的民歌,是用音樂形象去感動人的。無論是寫景亦或抒情,一般都是通過具體生動的形象和鮮明的意境,來刻畫音樂形象的。在陜北走西口成風的時期,家里的妻子想念丈夫,經常嘴里吟唱,抒發他們對遠方親人的眷戀之情。“豌豆開花一點紅,拿針縫衣想哥哥,想哥哥想的見不著面,口含冰糖也像苦黃連。”這些民歌感情真摯、語言生動、比喻貼切、質樸無華。生動地刻畫出了相思之情。在我們新時期民族聲樂創造中音樂形象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作曲家經常下到地方,吸取民間音樂的養料,陜北民歌中對這種音樂形象淋漓盡致地刻畫,為我國民族聲樂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陜北民歌的聲音技巧
由民歌改編的作品和民歌風的創作在民族聲樂教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陜北是一個音樂的海洋,陜北民歌也在不斷的發展,不斷的完善。作為一名音樂學習者,在大學的學習期間,我接觸了很多的陜北民歌,喜歡陜北民歌那種奔放、粗獷但又婉轉細膩的感覺。在教學中,學生在不同的學年里對演唱的技巧、音域擴展、氣息、表現力等方面有著不同的要求。因此在選擇教學曲目時,要有明顯的變化,陜北民歌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有著難度不等的曲目適應教學要求,因而被廣泛的運用于聲樂教學當中,如《三十里鋪》、《我想親親在夢中》、《山丹丹開花紅艷艷》、《趕牲靈》、《蘭花花》等。
歌曲在演唱時,對氣息和聲音的控制要有很好的技巧和方法,呼吸控制要求比較深沉持久、平穩舒展;聲音要連貫柔和,圓潤結實。中間齊唱部分氣息要有流動感,呼吸要適當的變化,但要松弛,聲音色彩上也要因音域、音區、音高等的不同而有適當的變化,從而把人們的熱情激動之情抒發得淋漓盡致。結束段雖是再現,但在演唱處理上要有區別,要演唱得更加恬靜、徐緩,有種拉開放慢的感覺,控制音量做漸弱直到結束。
我們說陜北不止是人們在山溝溝里的野唱,它發展到如今,在聲音技巧上是有科學依據的,這些曲目被運用到中國民族聲樂教學中,對中國民族聲樂教育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黃土地”不是一塊平常之地,這一首首“黃土地上的歌”是陜北人真情的流露,是高原人精神的最深刻揭示,是“天地之間的自然之音”。作為高原文化的靈魂和高原人精神的結晶;作為20世紀民歌運動的引領者;作為中國民族聲樂發展的影響者,它已經將自己無法估量的藝術價值融入中華文化的寶庫中。在民族聲樂高度發展的當今,它用質樸優美的旋律、與時俱進的歌詞創作和科學的發聲方法影響著中國新民歌的創作;影響著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設;影響著中國民族聲樂事業的發展,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民族聲樂藝術的發展中起著先鋒作用,是民族聲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1]郭影.民歌 [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2]丁雅賢.民族聲樂教學去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1995.
[3]李曉貳.民族聲樂演唱藝術 [M].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1.
J616
A
范志博(1993—),男,現山西大同大學音樂學院2013級在讀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