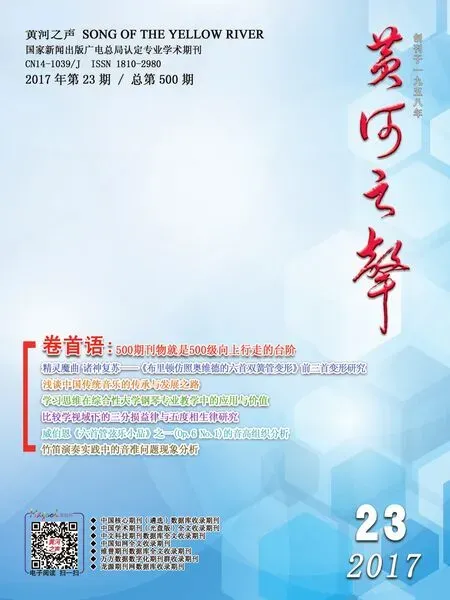比較學視域下的三分損益律與五度相生律研究
李平平
(忻州師范學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我們知道,目前在音樂活動中通常用到的律制主要有五度相生律(西方為畢達哥拉斯律即五度相生律,中國為三分損益律)、純律、十二平均律三種律制。本文對純律、十二平均律不做論述,主要對五度相生律和三分損益律做一些粗淺的辨析。
“五度相生律”(即沈知白先生所說的“畢達哥拉斯律”)發端于西方,在公元6世紀由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公元前550年,一說公元前497年)及其學派提出。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認為:“音樂同數學是不可分割的,數是理解整個精神宇宙和物理宇宙的鑰匙,所以按數字構成的音樂的音響、節奏體系也被看做是同宇宙相協調的例證”,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音樂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既是理論也是實踐”(秦序語),是科學與藝術的統一,也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畢達哥拉斯也因此成為了西方歷史上第一個用數理方式來解釋音樂現象的人。他認為宇宙是和諧的,其所以和諧是因為有一個完美的數的比例,又音樂是模仿宇宙的,那么音樂也是和諧的,它也有一個完美的數的比例,從而提出了“和諧論”。畢達哥拉斯通過實驗得出結論:“當弦長比為2:1時,兩音的音程關系為八度,當弦長比為3:2時,兩音的音程關系為五度,當弦長比為4:3時,兩音的音程關系為四度……”。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畢達哥拉斯也是以弦長為基礎,來計算各音的,因此它符合弦上發音的原理:弦愈長音愈低,反之亦然,即弦長與音高時成反比的。中國的三分損益法最早記載于《管子·地員篇》(完善于《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據管子卒于公元前645年可推斷中國的三分損益法比西方的五度相生律早了140多年。我們知道,在自然科學領域,通常有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之分,那么在人文科學領域也有應用科學和理論科學之分。如郭樹群就根據律學的研究范疇把律學分為了應用律學和理論律學;洛秦在《朱載堉十二平均律命運的思考》一文認為“新法密律創立的偉大意義應該是理論律學上而不是實踐律學上的”;秦序也認為:“……德國作曲家巴赫(1685~1750)先后創作了上下兩卷《平均律鋼琴曲集》,充分發揮了十二平均律在音樂實踐中的巨大作用以創作實踐顯示這一律制的合理性優越性。”據此可知朱載堉的十二平均律主要是“理論律學的產物”,而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則主要是“實踐律學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認為三分損益律也當是實踐律學的結晶,因為在《管子·地員篇》之前與其記載相同的五聲音階、三分損益法已經誕生,如春秋中葉的山西侯馬編鐘(公元前572年~前542年制成),其音階系列的五個音正好是《管子·地員篇》中所記述的五聲,由此可推斷“侯馬鐘是以《管子·地員》所記述的三分損益法調音的”,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可見,三分損益法在《管子·地員篇》記載之前就已經流行了幾百年的歷史,它最初是以實踐律學的形式長期存在,后來由管子及其門人將這種求律的方法上升到理論,如此,三分損益法也就完成了由實踐律學上升到理論律學的過程。理論和實踐往往是相輔相成的,是同一事物的兩極,缺一不可,實踐可以上升到理論,而理論也可以指導實踐。三分損益法正是經歷了由最初的實踐律學上升到《管子·地員篇》中所記載的理論律學的生發過程。由三分損益法所生的各律便形成了三分損益律,因此三分損益律是長期實踐的結晶,它是實踐律學的成果。
一、生律法方面的比較
五度相生律是利用泛音列中二倍音與三倍音的音高關系產生的一種律制,也即是用五度相生之法產生的一種律制。這是以純五度音連續向上或連續向下產生各律的一種律制,這種律制所求各律“既可從一音出發,向上疊加五度產生一律,也可從一音出發,向下每各五度產生一律”。而三分損益律則是以弦長為基礎,通過“三分損一”和“三分益一”來回交替,不斷相生的一種律制。若以c為基礎音,用五度相生律可以向上向下形成兩種音列,向上構成的音列依次為:c、g、d、a、e、b、升f、升c、升g、升d、升a、升e、升b,向下構成的音列依次為:c、f、降b、降e、降a、降d、降g、降c、降f、重降b、重降e、重降a、重降d,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用五度相生律向上生律12次,其中除c、g、d、a、e、b外,其他的音都帶有升號;而用五度相生律向下生律12次,其中除c、f外,其他的音要么帶有降號,要么帶有重降號。這樣看來,過去有些學者在論及五度相生律和三分損益律時所得結論為:“一個八度內三分損益法所求各律中的變化音都帶有升號,而五度相生律所求各律中的變化音都帶有降號”,這一說法值得商榷。準確地說,由五度相生律上行五度所生的十二律(不包括始發律)中的變化音是帶有升號的,而由其下行所生的十二律中的變化音才是帶有降號甚至是重降號的。造成這種認識上的偏差是有些學者在確定五度相生所產生的十二律時有選擇的把上行和下行中的部分音律組合在一起成為十二音列,從而巧妙的避開了其中的升號音和重降號音。實際上,由于五度相生律和三分損益律在生律法方面的不同而造成兩者之間的相同相異,這種區分正如華天礽在《對三分損益律和五度相生律異同的分析》一文說論:“在一個八度之內的十二律中……,三分損益律所生出的十二律,與五度相生律上行五度所產生的律,是完全一樣的;而五度相生律下行五度所產生的律,在三分損益律中是沒有的。”這是對五度相生律的生律法的全面把握,進而在與三分損益法所生各律進行比較中得出的音高結論。
關于三分損益法的記載最早見于《管子·地員篇》。其中所記:“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在野;凡聽宮,如牛鳴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凡將起五音之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這段話的大意即是說五聲的發音是借鑒了豬、馬、牛、羊、雞這五種家禽的聲音得來的,要想確定五個音,首先應該截取一定長度的弦作為標準音,也就是黃鐘,然后在宮音弦長的基礎上再延長其三分之一,就可算出比宮音低純四度的徵音;再在徵音弦長的基礎上減去其三分之一,就可得出比徵音高純五度的商音;再在商音弦長的基礎上增加其三分之一,就可算出比商音低純四度的羽音;最后再在羽音弦長的基礎上減去其弦長的三分之一,得出了比羽音高純五度的角音。這便是最早用數理的方式計算出的五個音,若把這五個音按其相對高度排列,即可得到一個以徵音為最低音的五聲徵調式音階。這五個音的弦長分別為:
宮:1×3×3×3×3=9×9=81
徵:81+81×1/3=108
商:108-108×1/3=72
羽:72+72×1/3=96
角:96-96×1/3=64
這是《管子·地員篇》中的計算方法,屬于先益后損的計算原則,而且只算到了第五個音。這種三分損益的方法在《呂氏春秋·慎大覽·音律》中得到了延續,其中記載:“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這是《呂氏春秋·音律篇》中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其原理與《管子·地員篇》所載基本相同,只是生律法有所區分,《管子·地員篇》中的生律法采用了先益后損的方法,而《呂氏春秋·音律》中的生律法則采用了先損后益的方法。而且它是最早對十二律生律法的記載,采用先損后益的原則繼續推算,得出了一個八度內的十二個半音。其生律次序依次為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這種方法所生的各律,若按各音的相對高度排列,則可得到一個以宮音為最低音的七聲宮調式音階。由最開始的五音到一個八度之內的十二音,也可以看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不定型到定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呂氏春秋·音律》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無疑是對《管子·地員篇》所載三分損益法的應用、深化和發展。只是生律到到第十二次時,第十三律清黃鐘比始發律黃鐘本律高了24音分,24音分即是“古代音差”。從中我們便可以看出“黃鐘不能還原”,因第十三律不能回歸黃鐘本律,因此也就無法進行“旋宮”(宮音位置的轉換)。自此開始,中國律學在其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涌現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學人,為了追求“黃鐘還原”、追求“旋宮轉調”,開始了漫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們或者通過加律的方法來縮小音差,如漢代京方的六十律、南北朝時期錢樂和沈重的三百六十律,盡管這些律制的出現帶有神秘迷信的意味,但在客觀上對律制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者通過在十二律內調整的辦法來縮小這種音差,如南北朝的何承天新律。直到公元1587年,明代朱載堉“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問世,才一舉解決了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黃鐘不能還原”、“不能旋宮轉調”的問題,“使得運用十二律進行旋宮轉調的理論終于在音樂實踐中成為一種現實”,而不再是一鐘美好的理想。據專家考證,朱載堉“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計算方法,是在1581年以前,而西方十二平均律在實踐中的使用最早在1702年以后,可見中國的十二平均律領先于世界,朱載堉也因此被稱為“明代的科學與藝術巨星”(戴念祖語)。實際上,不光十二平均律,即便在三分損益律,純律方面的成就,中國也遠遠領先于西方。
二、名稱、內涵方面的比較
三分損益律是否可以稱為五度相生律,在過去通常就把三分損益法稱之為五度相生律,其依據是三分損益法所生各律和五度相生律一樣,都是五度循環,這種認知缺少對三分損益律生律法的考量。不管是“先損后益”還是“先益后損”都脫離不了“三分益一”,當“三分損一”時,可以求得本律上方純五度,而當“三分益一”時,所求得的則是本律下方純四度,從這個意義上講,說三分損益律就是五度相生律欠妥,因為這兩種律制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人所推算得出,而且從審美層面來說,在這些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們的審美心理、審美習慣都是相異的。所以,不能簡單地說三分損益律就是五度相生律。而只能說“三分損益律是屬于五度相生律體系的一種律制,因為宮音下方純四度恰好是其上方純五度,但絕不能籠統地講三分損益律就是五度相生律”。再就是我們習慣的將三分損益律的方法稱為“隔八相生”法,這還是由于缺少“整體思維”而造成的疏漏。以黃鐘為本律,當“三分益一”時所求音律為宮音下方純四度音,按兩個音的相對高度排列,為中音5到高音1,那么其間的律高分別為中音部升5、6、升6、7,再加上首位中音5和高音1,共得六律,這樣說來,它是“隔六相生”并非全部“隔八相生”王光祈將這種生律法稱之為“進八退六制”,只有當其為“三分損一時”,也就是所求音律為本律上方純五度音時,才是“隔八相生”法。而西方的五度相生律實為真正的“隔八相生”法。
我們知道三分損益法既可以采用先損后益也可采用先益后損的計算方法。若按先益后損的樂律計算方法,假使宮音弦長為81,可求得徵音、商音、羽音、角音各音弦長分別為108、72、96、64:若按先損后益的樂律計算方法,假定宮音弦長海市81,則可求得徵音、商音、羽音、角音各音弦長分別為54、72、48、64。如果我們用先益后損求得的徵音與用先損后益所求得的徵音相比,其結果是二者的比值為2:1,兩音為八度關系;若我們用先益后損所得的徵音與商音相比,其比值為3:2,兩音為五度關系:余類推。我們從這樣的比值可以看到出按三分損益法所求得的各音之比是符合畢達哥拉斯“和諧論”的比值,所以說中國的三分損益法和西方的畢達哥拉斯律“在數理上是相通的”。
三、結語
總之,既然為比較,則既有相異也有相通。五度相生律和三分損益律在各自的“文化圈”中均屬于最早出現的律制,所謂各自國度的“樂律之祖”。二者均屬于不平均律,三分損益律有大伴音(114音分)與小半音(90音分)之分,直道朱載堉的新法密律誕生,始有了平均律。五度相生律則有大全音(204音分)與五度小半音(90音分)之別,直到巴赫兩卷賦格曲《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的生成;二者也都屬于“自然律”,它們揭示了音響世界中的自然規律,有別于“十二平均律”的人為性。
[1]繆天瑞.律學[M].人民音樂出版社,1996,1.
[2]秦序.略談朱載堉“音”、“數”思想的重大啟示[J].中國音樂學,2012,02.
[3]華天礽.對三分損益律和五度相生律異同的分析[J].音樂藝術,2015,04.
[4]戴念祖.“三分損益”法的起源[J].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04.
[5]羅天全.試論管子“三分損益法”[J].管子學刊,19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