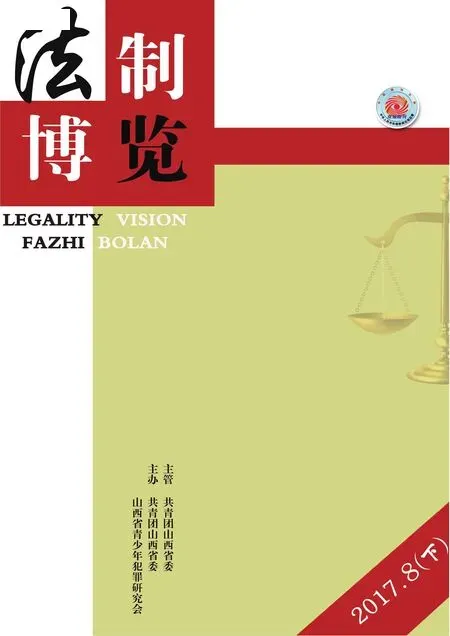機器人記者著作權問題探究
劉夢婷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機器人記者著作權問題探究
劉夢婷
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大數據時代下,機器人記者是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產物。傳統的著作權理論反對賦予機器人記者著作權,然而機器人記者創作品的獨特性及其為社會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容小覷。討論機器人記者是否享有著作權,初衷不是為了得出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為了在討論的過程中認清機器人記者的工作本質,厘清機器人記者侵權保護途徑,重新審視并界定《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以期獲得對社會利益的長遠保護。
機器人記者;機器人新聞;著作權
機器人記者自2014年投入新聞生產工作以來,備受各界學者的廣泛關注。現行機器人記者的主要業務分為兩種:一是具體的新聞寫作。Automated Insights公司自主研發的機器人Wordsmith便是典型代表,包括美聯社和雅虎等上百名用戶都在使用它所自助生成的財經數據內容。國內轟動一時的新華社研發的“快筆小新”以及騰訊公司自主研發的“Dreamwriter”也都是這一類寫稿機器人;二是篩選稿件等其他業務。這類機器人根據設定的程序,按照具體要求篩選出符合潛質的新聞稿件,如Blossomblot就是這類機器人的代表。
機器人記者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一系列發人深思的問題也隨之出現。機器人記者屬于真正的作者嗎?機器人記者撰寫的新聞是作品嗎?我國著作權法應該對機器人記者的創作品進行保護嗎?如果不保護,發生機器人記者侵犯他人著作權或者他人對機器人記者實施侵權的行為當如何救濟?
在傳統的著作權法理論中,作品是作者人格之體現,只有具備一定人格權的自然人才能成為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主體。①在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創作,代表法人或其他組織意志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中,法人或其他組織被擬制為該作品的作者。在此條件下,機器人的創作品即使具備作品的某些特征,也無法成為傳統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者。然而,大數據時代,高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向這個傳統觀念發起了強烈挑戰。著作權法應當做出修改相應邊界的回應,以順應大數據時代下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
一、有關機器人記者有無著作權的爭論
傳統著作權理論認為,將機器人新聞納入到著作權法保護范圍內是無據可循的。根據《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著作權是指作者及其他權利人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等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總稱。②從主體上看,現行《著作權法》對作者的規定僅限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在此范圍之外的機器人顯然不能成為作者。囿于法律自身所固有的滯后性的弊病,機器人記者難以在現行《著作權法》當中尋得一席之地。從客體上看,現行《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對象僅限于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傳統觀點認為,目前即便是讀者無法區分機器人新聞是否是真人創作,但人工智能創作物——機器人新聞也只能證明創作物符合作品文體范式和語法要求,并不意味著可以成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隨著機器人新聞的日益成熟,學界對此問題的看法出現了新的觀點。著作權法上的作品要求具有獨創性,即要求原創且能夠達到一般人認可的最低限度的智力創造的程度。從工作原理來看,機器人作者撰寫新聞主要是通過收集大量的高水準數據以及各種新穎別致的題材,利用算法編程程序建立龐大的數據庫,撰寫新聞報道的過程就是在數據庫中尋找模型、信息、數據,最后編輯其展現形式并自動生成新聞稿件的過程。機器人記者既符合新聞六要素搭建起來的對事實的簡單描述的要求,其所撰寫的新聞稿件也是基于大數據庫挑選、分析、比較、整合而來,并不能與常規時事新聞混為一談。更有甚者將機器人記者的創作過程與機器翻譯做對比。但機器人翻譯不僅依憑基本的詞典釋義和語法規則,而且要遵守基本的語言習慣進行語言輸出——Google翻譯已經可以向用戶提供符合基本語法語境規則的翻譯而不是單純的機械翻譯單詞組合而成的結果。《紐約時報》也認為,市場上一些軟件開發公司已經研制出了透露出一定的創造力的機器人寫手。“它不會像其他軟件那樣單純地復述事實,而是會給文章加入一些不同的元素。”③表明機器人記者已經步入了能夠通過對數據優勝略汰的篩選,自主的選擇視角來撰寫新聞稿件的新階段。大數據時代下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無法預估的事實,機器人記者通過不斷的編程更新,不斷地模仿人類的智慧,并經過完美的系統篩選,選擇最佳寫作方法與內容,最終創作出與人類記者旗鼓相當甚至更加優秀的新聞稿件。自DeepMind公司研發的機器人棋手AlphaGo打敗了圍棋高手李世石之后,機器人在不斷的更新發展中獲得了更高級的判斷力和理解力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機器人記者在撰寫新聞過程中體現的人工智能既為人類的知識和智慧貢獻點滴,也為具有著作權法上的創造性提供了支撐依據。
基于以上觀點,機器人記者撰寫的新聞稿件在事實上屬于一種可以被復制的思想、情感的表現形式而非思想、情感本身。機器人新聞不屬于單純思想與情感、與思想混合的表達、實用功能、單純事實、官方文件等著作權法無法給予保護的范圍,不致形成對思想、事實等的壟斷權。判斷機器人記者是否享有著作權不應該一味的遵照現行的著作權法相關來盲目評判,而應參照自然人記者所寫新聞作品的劃定的客觀標準,并在合適情況下考慮著作權法保護對象的界限和范圍。
二、機器人新聞侵權問題探究
雖然機器人記者著作權問題在當下仍然存在眾多爭議,但是機器人記者的高產高效與對社會的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機器人新聞侵權與被侵權問題是繼機器人記者有無著作權之后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如果機器記者撰寫的機器人新聞構成作品,毫無疑問,將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權的可能性。在現有技術條件下,機器人記者大多是按照一定的編程和程序在大數據庫中選取有利信息,并對信息進行刪選和加工,完成機器人記者自己的新聞創作品。若在此過程中,信息若是未經允許而被使用,根據《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剽竊他人作品或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構成侵犯著作權”。然而機器人作為沒有人格的無生命體,不享有民事上的權利和義務,如何承擔民事上的侵權責任?倘若將機器人新聞視為職務作品,試圖探索新的法律依據。但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職務作品的主體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機器人記者并不在其列。因此,機器人記者侵權并不能視為職務作品侵權,無法依照現有法律規定對其定性處罰。現行著作權法尚不能解決機器人記者侵犯他人作品的侵權問題,應當適當修改和補充相關規定。既然機器人記者本身沒有人格,不能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可以考慮將部分責任讓渡給機器人所有者,即安置并使用該機器人作者的企業。企業有義務管理自己使用的機器人,使其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機器人的不當行為造成他人權益受到損害的,由機器人的所有者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是合乎法理,更合乎情理的。
其次,機器人記者雖然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者,其撰寫的新聞也很難被認定為作品,但是機器人記者撰寫的部分新聞具有獨創性的新聞價值與社會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信息更新傳播速度對一個企業來說可以說是命運攸關的。④機器人記者以其速度快、效率高等特點著稱,可以給企業帶來最新動態以及時事新聞,提升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作用。而在現實社會中,一些沒有在第一時間獲得更加有價值的新聞信息的媒體可能會直接對此類機器人新聞進行冒用和盜用。這無疑是對機器人使用企業的權益的傷害。若僅以機器人新聞在著作權法中無對應保護機制而放棄對此類創作品的保護,勢必會引發道德上風險以其社會秩序的動亂。也違反了著作權法的宗旨,即:“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即有關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顯然,對機器人創作品權益的保護是法律的一個空白。機器人記者所撰寫的新聞權益被侵害,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即是機器人所有者因不能利用機器人記者創作品的價值而受到損害的權益。機器人本身不是利益主體,不能獲得任何利益賠償。侵害機器人作者創作品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不應當逍遙法外,而是應該以自己的名義對機器人所屬的企業承擔侵害相關權益的責任。
人工智能快速發展下,機器人記者由新生事物萌芽,慢慢轉變成市場經濟發展條件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機器人記者的快速發展與不可或缺給《著作權法》提出了一個新命題。是否予以機器人記者創作品以法律保護,應當以鼓勵創新、增進社會福利為出發點,以當前的科技水平和社會倫理觀念為依據,并在法律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尋找一個合適的解決途徑。⑤
三、著作權邊界的重新劃定
討論機器人記者是否享有著作權,初衷不是為了得出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為了在討論的過程中認清機器人記者的工作本質,重新審視《著作權法》的相關規定,厘清《著作權法》保護對象及其邊界,以期獲得合理的解決方式。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優勢就體現在它的“智能”方面。在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背景下,要求擁有前瞻視角分析相關問題,調整相關理論和規定以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我們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機器人記者在對豐富語料的大數據庫進行學習吸收后,撰寫出很深層次的評論,跳出模板的限制,從而形成自己的作品風格;翻譯機器通過對翻譯手段的學習以及特定語境的模仿,翻譯出入情入理的結果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大數據時代下,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這一切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我們不能只是一味的規避相關問題,而應該運用前瞻的眼光審視現行著作權的規定,完善并修改其相關邊界。
根據前文所述,機器人記者的創作品至少在某些時候是一種獨創性的的表達,即可以稱之為作品。是否給予機器人記者以作者身份予以法律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是個政策考量的問題,關系到個人與社會、競爭與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⑥著作權本質上是一種對作者對作品在有限時間和有限地點內的絕對性壟斷權,目的是為了激勵創新,增進社會福利,以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這個衡量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到人工智能的放任裸露的使用會導致創作的價值缺失與內容趨同。這些都給基于機器人作者權益以保護提供了正當性理由。法律與社會永遠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雙向命題。大數據時代下,知識產權的實踐方式隨之改變,使得法律和政策也需要隨之調整,與相應領域形成樣態交織,形成協調自洽的瑰麗圖景,以期完成又一次的深刻變革。
[ 注 釋 ]
①白帆.機器人“記者”享有著作權嗎[N].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02-11.
②吳漢東.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③魯燁.“機器人記者”在發酵[J].中國傳媒科技,2015(3).
④[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英]肯尼迪·庫克耶著,盛楊燕,周濤譯.大數據時代[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⑤Robert freitas:the legel rights of robots,student lawyer,1985,13:54-56.
⑥郭娟,宋頌.“機器寫手”的著作權問題研究[J].寧德師范學院學報,2015(2).
D
A
2095-4379-(2017)24-0087-02
劉夢婷(1994-),女,湖北黃岡人,華中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