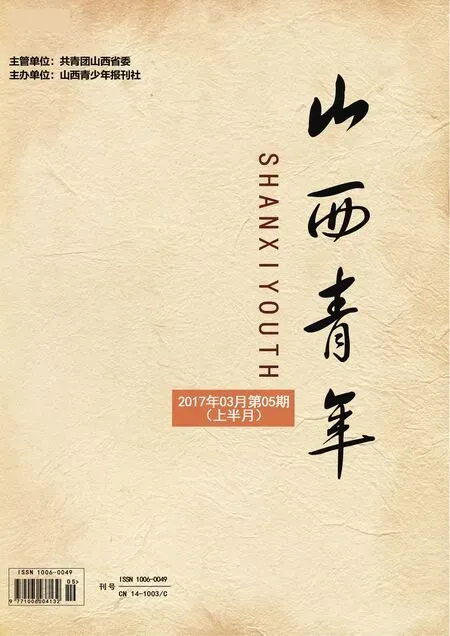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與文化認同芻議*
楊玲玲
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陜西 咸陽 712000
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與文化認同芻議*
楊玲玲**
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陜西 咸陽 712000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個體自我構建與文化認同呈現出與傳統媒體時代完全不同的圖景。本文從傳播學和文化社會學角度出發,分析了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主動性與被動性悖論并存、自我迷失的現狀,以及文化認同過程中激烈沖撞的時代現實,并對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和文化認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
新媒體;自我構建;文化認同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人類逐步進入信息社會,八九十年代后隨著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人類信息社會進程的廣度和深度出現了質的飛越,邁入了新的媒體時代。“新媒體”(Newmedia)一詞最早于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其后,該詞在美國逐漸流行并被廣泛使用,不久后成為全球性熱門話題。而所謂新興媒體,就是依托全新的傳播技術,以改變傳播形態為主要訴求點,強調體驗和互動,內容生產日趨分散化和個性化,以網絡媒體、手機媒體和(互動性)電視媒體為代表[1]。其具體內容載體表現形式上以博客、推特、臉書、微信、QQ等最為流行。新媒體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傳播圖式,消解了意識壟斷,使個體開始掌握媒體話語主動權。個體通過新媒體在主動交流展示和互動的過程中對自我的構建和文化認同都產生了與傳統媒體時代不同的特質。新媒體用它全新的傳播模式解構舊的生活圖景重建出新的個體自我認知與文化認同方式。
一、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的圖式
(一)自我構建的自由主動性
沃爾特·李普曼認為傳統媒體時代人們通過對世界本真環境即“直接環境”的親身參與和感觸獲取“直接經驗”,通過媒介傳播所締造的“虛擬情境”獲取“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受制于人本身,“間接經驗”受制于媒介掌控者。“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相互融合完成了個體對世界的認知與自我的構建。因此,傳統媒體時代下媒介傳播“他者”對個體的自我構建具有強約束性。
而進入新媒體時代后,隨著微信、微博、QQ為代表的眾多新媒體的出現,媒體對個體自我構建的強約束性受到了沖擊。新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個體只能作為單一向度接受者的被動局面,令個體開始擁有媒體話語主動權。個體能通過新媒體提供的更為私密和自由的空間上傳圖片、文字、視頻和音頻,更加主動和自由的表達思想、展示生活、分享感受,與他人進行互動,并藉由此過程達成自我展示,完成一種主動自由而不是被“他者”過分規制的自我構建,完成如福柯所說的“自我技術允許個體按自己的方式或在他人的幫助下,對自己的身體、思想、行為和存在方式實施某些影響,以實現自我達到某種幸福、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2]。
(二)悖論并存的自我構建被動性
阿爾弗雷德·舒茨說:“我日常生活的世界決不是我私人的世界,而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主體間的世界,是我與周圍的人共有、由他人經歷和解釋的這樣一個世界:簡而言之它是我們所有人的共有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在我生存的任一時刻,我發現我自己的那個獨特的生平情形只不過是在很小的程度上算是我自己制造的[3]”自我的最終成形受主體主觀意識形態的控制,同時也無法脫離客觀環境的制約。新媒體使個體自我構建在主觀意識形態上擁有了更加自由和主動的通道,但新媒體自身形成的客觀環境依然規約著自我的構建。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究其本質依然是群體的圈子,這個圈子充滿了圍觀者、互動者而非一個人自言自語的世界,且這個圈子本身就是一個不能背離的媒體客觀環境,只是與傳統媒體時代相比多了幾分主觀能動性的選擇權罷了。然而這個作為自我主動選擇的媒體環境仍舊會默默規約自我的構建。以微信為例。微信熟人圈中,個體發表言論的自由依然如故但人們發表言論的同時卻都會恪守現實社會與熟人相交的規則,避免思想行為上過大的異動破壞掉熟人慣知的自我形象,而通過微信搖一搖與非熟人之間的相交則極有可能異化成與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同的自我。而這種恪守與突變之間的巨大差異完全取決于新媒體環境的客觀差異。
(三)自我構建中的自我迷失
無論是在新媒體下獲取自我構建的積極主動權亦或是遵守新媒體客觀環境下自我構建潛在的規約,深層生命意義的自我在新媒體時代卻變得格外容易迷失。個體在新媒體進行的錯綜復雜的互動中,既可以隨時參與某個交流發表某些只言片語后就又隨心所欲的撤出并迅速跳轉另一個場景,也可以在某種情緒觸動下發表某種言論或者圖片之后又很快將其忘記。這些隨性的言論和交流與紙媒時代相比缺乏持續性和連貫性,缺乏前后嚴謹的承接性和陷入式的思考,本質上不過是些碎片化的文字羅列和堆積。這種碎片化的表達方式很容易導致個體思維邏輯性和嚴謹性的渙散,也容易使自我認知在大量碎片化內容的沖擊下變得碎裂不完整。另一方面,迅速的時空場域輾轉也會引發個體自我認知在多場景轉換下的混亂。與印刷媒體時代自我持續、穩定的表達相比新媒體時代的自我構建雖然多元而且自由,卻缺乏穩定而持續的存在,缺乏嚴謹而深刻的思考。自我常在膚淺的大眾文化消費中被消遣,在生命深層意義的解讀中缺失。缺乏靈魂和信仰的自我在無數個積極主動的自我展示中迷失。
二、新媒體時代激烈沖撞的個體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指對某一文化的身份認同感,或者是指個人受其所屬的群體或文化影響,而對該群體或文化產生的認同感[4]。在全球化的進程下,世界各國都面臨經濟互通與文化沖撞的問題。新媒體強大的圈際互動性加劇了不同文化之間擴散的廣度,放大了不同文化之間撞擊的力度。
(一)文化帝國主義滲透的加劇
亨廷頓曾說過,在后冷戰的世界里,人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文化的區別,最普遍、重要和危險的沖突是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
在封閉的單一環境中個體的文化習得對象是單一的,只存在唯一認同對象,個體只需按照單一文化規范生活,很難產生思想認知的混亂。而文化全球化的到來卻使得單一國度的一元環境格局被打破,單一的文化規范受到了嚴重沖擊,思想認知導向出現了多種可能。個體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此時變得格外重要。而在文化全球化個體必須進行文化身份確定時,文化帝國主義悄悄滲透進來,竭力誘導個體文化身份認同的方向。文化帝國主義究其本質而言就是通過文化傳播和文化入侵的手段,以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對他者進行思想意識的控制繼而達到對其行為的控制。
新媒體依托互聯網技術進行的互動超越了時空地域和種族的限制,以圈層的結構模式容納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全球化文化可以在此自由出入。而新媒體圈層結構具備的人際交往特性增大了文化交流的往來性和擴散性。也正因為新媒體交流的自由和強大影響力使得不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利用它進行文化帝國主義行動。他們不斷散布西方世界文化理念滲透腐蝕他國人民的文化認同感,甚至為了更進一步消解他國人民的文化認同操控某些已然西化的面孔蠱惑其國人。國內曾經熱議的微信圈大V事件,正是這些全然已被西方文化洗腦的人,利用自己在微信圈意見領袖的優勢不斷替發達資本主義文化來正名,散布各種西方言論,蠱惑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向往和認同,進行全盤西化。而這種來自新媒體領軍人物的觀念和言論對圈際之內個體的影響性和破壞性比普通個體要強烈的多。
(二)民族文化認同的被沖擊
民族文化認同主要指民族成員對所屬民族主體文化的贊同和歸屬感。民族文化認同隸屬文化主體的價值系統,通過態度心理結構得以展現。它是指人們基于不同文化的接觸和實踐,以自己選擇的標準對各種文化事項作出的認知判斷、情感依附、行為選擇和調整傾向[5]。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推動文化全球化迅速發展,文化帝國主義侵入日益加劇,民族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文化帝國主義沖擊。而民族文化是民族凝聚的根基,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根基,民族文化的被沖擊若導致民族文化認同弱化也將致使民族弱化國家弱化。在民族國家存在的歷史時期內,民族文化的認同是民族國家存在與繼續的保證。民族文化認同在新媒體時代受到沖擊已經確之鑿鑿,如何積極應對不得不慎思。
三、新媒體時代個體自我構建與文化認同之反思
(一)引導正確的自我構建
社會學家羅姆·哈里認識到自我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自我是在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文化作為自我獲得精神安定的源泉,影響著個體自我構建的方式,而自我構建的方式反過來影響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新媒體時代,自我構建圖式最大的進步就是突破了單向傳播的被動性,雖然自我的構建依然受到自我主動選擇之后環境的制約,但相比傳統媒體時代的基本被動接受而言,自我可以借助新媒體積極主動的構建想象中的那個自我,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然,這個巨大的進步仍然是存在缺陷的,自由的自我構建中常常隱埋了生命深層意義的自我。
然而我們對新媒體時代帶給個體積極主動的自我構建之現實不能否認、推翻和抹殺,否則就是阻擋歷史潮流和時代的發展,但積極主動的自我構建必須建立在正確的認知之上。自我構建應當是對自我生命深層意義的追求和探究,是持續和穩定的慣性過程,而不是碎片化的生命消遣和娛樂。新媒體賦予了個體自我構建的積極主動性應該被珍惜,并被應用到深層的自我構建當中去。
(二)反對文化帝國主義,增強民族文化認同
縱觀人類歷史,每一次新媒介技術的出現和發展,都會讓人類文明隨之一變。當前新媒體的出現和發展,使文化帝國主義借其之便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大肆侵入,使民族文化認同受到了劇烈的沖擊。習總書記曾指出:“經過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我國56個民族、13億多人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非凡奮斗,是我們共同創造的美好家園,是我們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貫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然而文化帝國主義借新媒體無孔不入,以各式各樣的面孔不斷削弱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認同。
民族文化認同是民族國家存在的根基,新媒體加速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使民族文化認同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然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社會關系的發展,既有可能削弱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強更為地方化的民族主義情緒。[6]”新媒體既能為文化帝國主義所用,也自然能成為增強民族文化認同之利器。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也應充分利用新媒體平臺被廣泛傳播,在新媒體中不斷植入民族文化正向話題,引導國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和贊美,引導民族文化自豪感,增強國民判斷力,與不斷蔓延的文化帝國主義相抗衡。
[1]宮承波.新媒體概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3-4.
[2]朱波濤.福柯自我構建理論對高校體育教學改革的啟示[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13(10):126.
[3]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19.
[4]李娜.文化認同視域下的個體生成[J].教學與研究,2015(1):84.
[5]王沛,胡發穩.民族文化認同:內涵與結構[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1(1):102.
[6]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57.
*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課題“新媒體視域下高校教師黨員組織生活方式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DJZ15—03)。
G
A
1006-0049-(2017)05-0016-02
**作者簡介:楊玲玲,女,陜西咸陽人,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文化傳播、教育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