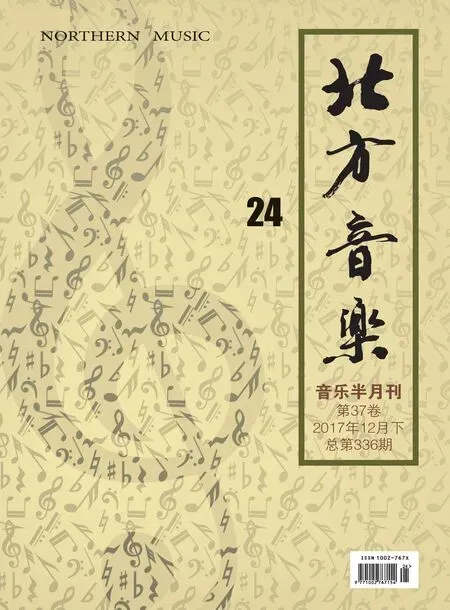觀呂劇《墻頭記》《姐妹易嫁》有感
黃超群
(山東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
如實地說,在沒有觀看這場演出之前,我除了對“呂劇”這兩個字熟悉之外,其他的一概不知,但讓自己感到吃驚的是,這場演出激發了我對戲曲藝術的興趣,也引發了我對戲曲的思考。當時的感受很清晰,由于之前的一周跟著導師去參加西安音樂學院的學術交流會,和朋友好幾天沒見,相見竟是這次相約去看戲,那么些天沒見的日子有很多話要說,但我們進去的時侯演出即將開始,邊聊邊看,但不出幾句話,我們就都定睛注視著舞臺上的表演,我們被眼前的這一幕吸引了眼球,有舞臺表演、有唱腔意蘊,它還有一定的故事情節在里面,我們都愛看故事、聽故事。最直觀的感受是對于戲曲,我們愿意去看,能看、能聽得進去了。我相信這種感受不只我一個人會有,呂劇演出結束以后,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為什么現在我們能靜下心來聽戲了?這說明我們老了……”在大家的意識里是老人才喜歡聽戲,所以都說自己老了,如今我們能坐在一起安靜看戲,是我們真的老了嗎?那到底多大年齡算是老?看戲是用年齡來衡量的嗎?這顯然是不成立的,現在小年輕就愛把自己老了之類的話語掛在嘴邊以示自己的成熟老套,我們用“老了”這個詞為如今能正兒八經坐在那里看戲的自己來開脫,那天晚上朋友圈里被呂劇的小視頻占滿,很多才思如泉涌般冒了出來,用長篇大論來描述呂劇的感受,我相信這都是發自肺腑的感想,被呂劇這種戲曲藝術所感染,被它優美的唱腔所吸引,總之,這些表達方式與內容都是我們對于戲曲的認可與肯定。
那么問題來了,那么多同學用“老了”的理由來為自己認真看戲開脫,這個現象就說明了問題,我們為什么對這場演出有如此的反應?是因為我們看得少,聽得少,這種視覺經歷是比較匱乏的,所以我們對于此形式比較驚奇,我們其實不用找任何的理由解釋自己會去看戲的原因,也從來沒有一本書上用年齡作為戲曲欣賞的標準,我們本就能夠去看戲,也能看懂、聽懂。但這種儀式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太少了,有這么一次我們就會顯得這么新奇。在我們的學習與生活中,涉及這方面知識的學科寥寥無幾,我們只是偶爾聽到過某戲曲的劇種,很少有機會去感受與體驗戲曲的風采,更不會懂其中的文化,而對于當今文化藝術的發展而言,藝術的學科交叉固然重要,尤其是高等教育師范類型的教育模式下,更需要培養全面發展的藝術人才,戲曲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去傳承這種藝術文化,我們連自己的文化都不懂,又何來學習外國的文化?我的家鄉菏澤是著名的戲曲之鄉,戲曲種類繁多,但我真正了解的并不多,但在今天看來,作為一個地道的菏澤人而當之有愧。在我的記憶中,每逢村里有喜事時總會在空曠的地方扎起臺子,三五成群地組成一個團體,我們俗稱“響器班”,在這里面節目形式最多的就是戲曲,村里的人晚飯后就愛圍在臺子下面,烤著柴火聽戲,尤其老人很多。但在近年來這種形式越來越少,曲目也逐漸流失,會唱的人也越來越少。近年來,對戲曲的消聲匿跡之類的詞頻繁出現,其實這些消逝是缺少傳承與發揚的人,而所謂的傳承就在于如何對待戲曲的發展方式。
因此,通過這場戲曲藝術的啟發,我在這有一個大膽的想法:若是能把戲曲藝術引進校園,引進課堂,搬上舞臺,這將對戲曲的傳承與現階段學科的交叉互動有著積極的意義。在當今的音樂藝術教學領域,在實施聲樂教學的過程中完全可以與戲曲文化相結合,戲曲藝術的唱腔與聲樂教學相結合,互相促進,互相借鑒,戲曲中一招一式的舞臺表演對于聲樂的表演與演唱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廣泛地收集各地方戲曲,通過整合,把戲曲文化引入課堂,學生在通過鑒賞對戲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與掌握。同時可以邀請民間的老藝人或某戲曲的傳承人來為我們授課學藝,逐漸在課堂的教育中轉向舞臺實踐,把一些經典的劇目搬上舞臺,在舞臺上進行實踐,從以課堂傳授知識為主的學校常規教育與直接獲取實際經驗、實踐能力為主的舞臺演出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戲曲的舞臺實踐,不僅使學生得到了鍛煉,積累了一定的藝術實踐素材,也促進了戲曲藝術的傳唱與發揚。在這這門課的限制之下,我們就會在逐漸地學習過程中,享受戲曲文化,傳承戲曲文化,在大眾的生活中傳唱的人會逐漸增多,在此情境下高等藝術教育院校中可以開掘這種戲曲類型的專業,并納入藝考項目的行列,為民間游走的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從而也避免了人才的流失。這門專業的開設所提供的教育與培養模式,將與各研究院以及戲曲的專科學院形成對接,對日后所想考的碩士專業學科形成一種鋪墊,避免了學科過程的斷層,為人才的培養提供很好的平臺與機會。一個淺顯的例子,若一個本科生想考戲曲類的碩士研究生,若他本科的課程從未涉及這門課,那么在考研的過程中會比較艱難......但我相信在課程創新之后將會對此有很大的幫助,改善創新課程的設置,逐漸地形成學科教育的連續性,這對于戲曲文化的發展將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從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提供可考的印記,通過這樣的改進與創新,我相信人人都能把身邊的戲曲唱下去,傳承下去,更好地為傳統文化發展的盡一己之力。